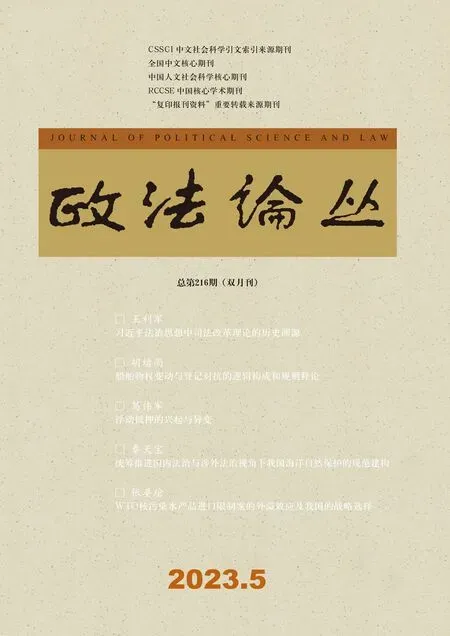对人工智能非法律主体地位的解析*
2024-01-02黎四奇
黎四奇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人工智能法律主体①说所引发的忧虑
“人工+机器+智能”的组合使得人类的生活日益缤彩纷呈。因机器智能化,我们也得以不断地从生存必须的艰辛劳作中解脱出来,但是在另一方面,与日俱增的机器依赖与“技术膜拜”也日渐使得人类踏入了一个风险社会,同时人②与物主从关系的摇摆也日渐加重了人类文明演进方向性主客不清的危机。“电脑和互联网之后,世界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人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葬送自己通过500年努力获得的主体资格,走向爆裂之路,这就是主体的碎片化之路。”[1]P131随着人类在机器智能化发展上的一路狂奔突进,这种生存或毁灭并非杞人忧天。在孜孜以求的探索中,有人基于“乌托邦”的理想情怀提出“人——物”的统一说。“生物学意义上的AI出现,继续融合‘人’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主体——客体’分离,走向互动、生成的人与自然关系,人类逐渐学会放下高高在上的神圣面孔,从自然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作为造物主的重要的产物,以及应该对自然产生何种反思以及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工智能的胜利也是人本身的胜利。”[2]P117虽然这种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博爱观体现了虚怀若谷的胸襟,但是人与物边界的混淆也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法学与法律是服务于人的事业,而这也决定了法律主体是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元素。基于人机象棋或围棋比赛中自然人不敌机器人等现象,在法律研讨中,有人主张主体资格不应以生物结构为依据,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主体资质,并为此提出了诸多标注性的见解,如法律人格扩展说、有限人格说与电子人格说等。流行与潮流从来不代表真知与真理。很久以前,英国人罗吉尔·培根即认为人们在获取真知上存在以下四种障碍:“一是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二是习惯的影响;三是流行的偏见;四是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妄虚夸的潜在无知。”[3]P285古语云:智慧出,有大伪。人工智能如火如荼之下,虽然别具心裁的见解能吸收大众眼球,收割流量,但是为了不偏轨,有必要对时下流行的人工智能主体说保持深度的质疑与审视。
人工智能以算法为基础。为此,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有人得出以下结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就是法律。”[4]P6“代码是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基石,因此它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个人行为。”[5]P9除此之外,更有甚者,建议承认或确立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而且这种看法呈现出喧嚣尘上的态势。算法确实给人类的快速统计与精准预测带来了光明,但是也给人类带来了主客晦暗不清的风险。数字社会下,人工智能正全方位地向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渗透,而且随着机器智能程度的不断升级,人工智能不仅会在智商上超过其缔造者,而且还能从事一些人类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高度危险与高度精细的事务。无处不在的存在及无法挣脱的依赖使得自然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奴役与被奴役的界限日渐影影绰绰。客观上,人工智能正使得主体及主体观念破碎化,“人是谁”日益变得虚无飘渺。“创制机器的人对于作品毕竟没有付出直接的脑力劳动,并且与职务和雇佣行为也相去甚远,由创制机器的人享有和行使权利有违事实与本质,而由智能机器人作为实际权利享有人,并通过权利代理人去代为行使权利也并无不可。”[6]P61“与普通机器人相比,智能机器人可能产生自主的意识和意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智能机器人可能超越程序的设计和编制范围,按照自主的意识和意志实施犯罪行为,因而完全可能成为行为主体而承担刑事责任。”[7]P40-42
机器智能化、工业智能化确实解放了人类,但是其也如同普罗米修斯盗得火种一样,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温暖,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但是也给人类带来了痛苦与灾难。人类进化的过程是一个如何认知自我的过程,或许作为物的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是问题,其核心可能是在人类愈加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人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及究竟是谁来主宰机器、技术、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法律追求稳定性与确定性,但是这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富有生命力且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为了维护其正义性,就必须“在运行和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通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寻求某种和谐”[8]P3。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法律应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正义就只能是一个泡影。人工智能已开始搅动人们的感知与法律知识体系。人工智能具有或应当具有法律主体资质吗?这不是一个激情的问题,需要批判性的哲学分析。
莎翁曾自豪地认为:人是宇宙的灵长,万物的精华。虽然迄今为止,人类已业绩斐然,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处于一种多元、杂乱的朦昧状态。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中,为了生存,人的地位似乎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什么是人”及“人该是什么”并非一下大同的概念。科技越是发展,人与物,特别是人造的智能物之间的关系越是显得扑索迷离,另类的人工智能主体论就是这一混沌的现实影射。无可厚非,相对于守正的人工智能客体论,标新立异的主体说无疑更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与关注。然而,必须正视的是,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冲击并非简单的人应有的位置与人的事务被机器取代,而更是人本身被机器边缘化、虚无化与去意义化。
在学术舆论的渲染之下,当这一切正悄然发生,并呈扩大之势时,面对这充斥工业机器的世界,无论是智者,还是愚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恍惚与迷惘、裹挟与盲从之中。主次不明之下,“我是谁”“我该是谁”与“谁是我”是一个颇令人神经错乱的问题。费尔巴哈曾言:人就是他吃的东西。人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更是一种精神性的栖居。人与人类的生活不仅要追求物质富有,而更应追求灵魂高贵。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如果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客紊乱,则其结果就必然是人与人格的自我精神迷离。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对“何处去”的探索与回答。虽然为了增加说服力与思想兜售,不拘一格的人工智能主体肯定论者能够罗列相关逻辑进行解构,但是反对者亦可以针锋相对地展开强有力的反击。在解析人工智能是不是人之前,我们必须先扪心自问下:我们为什么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应基于什么样的立场与方向来展现“诧异”?如果方向错了,无论陈述的语言如何华美动人,亦无论语词如何雄辩,那么除了玄虚与遮掩之外,语言也只是强词夺理的工具。而且,在资源稀缺的社会中,若研究严重脱离于人与人类的主题,那么研究者也有必要进行良心性的拷问:什么是我的贡献?虽然肯定说有些眼花缭乱,概括而言,其结论不外乎电子人格说、法律人格拟制说、人格代理说等。在成因上,也不外乎以下三种:“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不以生理结构为基础……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意识……具有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现实必要性。”[9]P125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应以人为中心,如果研究的立意是将物化为人,那么无论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措辞多么煽情,多么旁征博引,其都和研究服务于人的本位南辕北辙。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智商过人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无论机器智能到何种境地,在人为自然立法的世界中,人是目的,而不可能是手段。人工智能只是物,而不可能是人。在学术观点混杂的当下,有必要从多元的角度深入地对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进行正本清源。
二、对人工智能非主体性的词义解读
人们所看到的并不必然是真的,而只是现象。正所谓,我们的感觉超不过经验。面对杂音与新说,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在认识批判的开始,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的、最后还有人自身的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10]P28为了看到真相,就必须进行心灵转换。根据培根的“四假象说”,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状况,不单纯是因为人受到错误观念的影响,而更源于认知者被相关幻觉所支配。由于观念中掺入了认知主体个人的情感、期待与欲望等,所以其难以看到事物本来的形态。主体肯定论者之所以通过推演认为,人工智能“是”人,或者认为可以被法律③拟制为人,除了高傲地认为法律万能之外,还在于没有对词话进行“考古”,即没有从概念的角度来理解物与定位物,进而确立与巩固人与物的关系。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繁琐杂乱的世界。为了使这个世界井然有序,人类具有语言的天赋。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思想离开了语言这个媒介,那么其只能是缺乏定型、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语言凝固的是一个世界,其目的是使人类能找到回家的路,而不是让我们离自己的家园越来越远。概念是一种语言性的表达,人类是通过概念来对事物进行识别、定限与归类。在人类的知识谱系中,概念标志的是抽象的本质、原则、秩序、逻辑与常识,是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物之间关联的基本桥梁。客观上,概念是知识构成的基本单元,是人类认知与构建世界的窗口。缺乏概念,知识、文明与世界就处于一种晦暗不明状态。怀疑论者休谟即认为:“概念永远先于理解,而当概念模糊时,理解也就不确定了;在没有概念的时候,必然也就没有理解。”[11]P189为了阐明人工智能是什么,人工智能与人、人工智能与其他物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从概念着手,考察人在造出这种物件时是如何赋予其意义的。人工智能是一种简单的表述,其完整的词汇应该是人工智能机器人。若对这一概念的构词进行拆分,则其由“人工+智能+机器人”三个词组合而成。词与词之间的联合对于语义的溯源与逻辑考证具有重大关联。“人工智能概念的历史规范主义维度,主要是考察人工的(artificial),智能(intelligence)与机器(machine)三个概念。”[12]P18在这种联合中,作为中心的“机器人”并非孤立的存在物,其边界、内涵、语境、关系等受“智能”与“人工”的限制,并最终受“人工”的约束,其表达的逻辑是“人工→机器人→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递进式的创新与发展。在词源上,人工(artificial)源于技艺(art),而在英语中,art指的是人与神制作工具的能力。这也表明,虽然机器人被智能化,但是人才是缔造者,人才是整个过程的主宰,其表达的语义是智能化的机器人是具有生命的自然人基于自己的智慧与目标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种相对于“自然物”的财产型“人造物”。虽然基于人的意向或设定目的,人造物被赋予或分享一定程度的“人性”,但是“人造物又不是人,不具备他者的品性,因为它身上的意向并非它自身固有的,而是人类通过感性实践活动附加在它身上的。”[13]P84
所谓智能指的是人的知识与智力能力的总和。虽然机器被人类赋予智能,但这也只是人类智能的技术性或工具性延伸,而并不能改变机器“物性”的本质。“智能是一种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人类生物的和心理的本能。尽管老鼠、鸟类和计算机也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人类具有智能是一种解决问题或创造产品的能力。”[14]P7实际上,人工智能只是人类技术的推陈出新,源于对人类思维模式的模仿,是自然人大脑“山寨版”的技术性客体,是一种服务于人类诉求的工具性存在。无可非议,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是人类的得力助手,比人更具有优势,但是其模仿性恰恰说明与强化了其创立者的主体地位。在逻辑上,人类绝不可能去打造一个新生事物,而让其否定、威胁,甚至是毁灭自己。
语言是通往法律正义的桥梁,所以法律人讲究法言法语。若不能明确语言的含义,就没有资格讨论法律与正义问题。词语不单纯是沟通与交流的工具,而更是历史传承、传统、知识、价值与文明的基因。为了系统地了解某个字或某个词的真实意图,我们就不能仅仅盯着其当下,而且更应着眼于其过去、现在与未来,因为由字词句构成的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在只是对过去的映射。正所谓,“法包含着一个民族经历多少世纪发展的故事,因而不能将它仅仅当作好像一本数学教科书里的定理、公式来研究。为了知道法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过去以及未来趋势。”[15]P5“机器人”是一个外来英译词汇,在英文中,对应的有三个词语,即robot、automaton与android。为了“信”“达”“雅”,就有必要对其在英文中的表现有个整体性的理解。在英语中,对robot原味的解释是:a machine that resembles a living creature in being capable of moving independently (as by walking or rolling on wheels) and performs complex actions (such as grasping and moving objects)或者a device that automatically performs complicated, often repetitive tasks (as in an industrial assembly line)。其对应的中译是,一种类似人、能够独立移动的机器,如行走或借助轮子来滚动,且能完成复杂的动作,如抓取或搬移物体,或一种能自动完成复杂、重复性工作(如在企业的流水线上)的装置。对automaton的英文定义是:a mechanism that is relatively self-operating;或a machine or control mechanism designed to follow automatically a predetermined sequence of operations or respond to encoded instructions;或an individual who acts in a mechanical fashion。对应的中译是,一种能相对自己操控的机器,或一种被设计出来能根据既定操作程序或密码执行指令的机器或控制机制,或以机器模式运行的个体。Android的英文释义是:a mobile robot usually with a human form,derivers from Greek andr plus oeides。其中译是,一般具有人形的能够行走的机器人,是古希腊词根“人”(andr)与“形状”(oeides)的组合。
法律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法律人不可能脱离语言建构起理想与现实的法律王国。本质上,法律学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虽然一个词或概念的语义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注入新的内容,但是在这一注入中,注入者并非可以肆意妄为,其必须围绕词或概念的核心义进行扩展,同时其必须遵循应有的社会伦理。从词义考究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与未来,在创制相关词汇时,造词者并不认为机器人具有人格。自始至终,机器人只是“机器”“机械”或“设备”,是人设计、能执行人所发出的指令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形的器械。随着人类超算能力、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人不仅能高效地代替人工作,而且在造型、质感、语言、行动上越来越逼真于人。尽管如此,如果游离于语言的真义来讨论其与自然人的关系,并意想天开地认为其也可以和自然人一样平起平坐地具有人性,那么这不仅是无视法律语言性的本质,而且也更是对法律精神的疏离与亵渎。虽然端坐书斋的学者琢磨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资格,但是在实证的法律层面,立法者对此并不太领情,如被热议的欧盟2021年4月推出的《人工智能法案》就将人工智能宽泛地定义为利用一种或多种技术或方法研发出来的计算机软件,该类软件能基于一组特定人群预设的目标能够进行内容、建议、预测或决定之类的输出。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无论在学术上如何鼓吹人工智能主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立法者现实的眼眸中,人工智能是“物”,而不可能是“人”。
三、对人工智能非主体性的法学视角证成
(一)法律主体应有的思想元素
在法律体系中,法律主体是核心命题,权利、义务、责任、作为或不作为、法律关系等都是紧紧地围绕法律关系主体展开的。离开了法律主体,整个分工细密的法律关系只是一个空壳而使得其存在的本位价值荡然无存。然而,问题是如何界定与类分法律主体?在构词上,法律主体是一个“法律+主体”的联合。在词条上,主体指:“有认识与实践能力的人。”[16]P1712实质上,主体的意义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应有的主从关系;二是作自己的主人;三是突出本位性。简而言之,所谓法律主体即法律所承认拥有自己的财产、能评估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负有义务,并能承担责任的人。为了归纳总结,有人认为:“法律主体的特征包括人之唯一性、人之普遍性、人之时间性、人之社会性、人之主体性和人之法上权义性。”[17]P46-54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自己的关系中,主体是一个演化式的概念。法律主体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法律主体乃是人从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必然产物,是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且必须由法律来调整的结果。法律主体是一种人格人,其特征有三:具有意志;属于目的性存在;能够自律。”[18]P73
虽然在已有的著述中,有关法律主体特性的释义较多,但是其核心要素不外乎以下几点:生命性、意志性与财产性,而独立、平等、尊严、自由、权利、义务与责任则是前三种主特征的延伸与扩展。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门类的体系性划分,但是在总体上,法律主体同质性地表现为自然人、法人与其他非法人性的组织。在这一大框架之下,刑法的行为主体为自然人与单位,而单位则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19]P126-131民事主体则包括自然人、法人、合伙与国家。[20]P39-85在我国的《民法典》中,民事主体表现为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由与福利,人类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但是哲学、艺术、化学、文学等门类繁多的求知都体现的是对自然人地位的肯定与尊重,法律更是将这些利益进行固化与强力保护,而这也是现实法律并没有对人工智能肯定说给予“理睬”的原因。“法律主体的范围虽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扩张,但始终强调人格对法律主体构成的重要性。”[21]P86在当下学界的主体肯定说中,有人试图凭借法人拟制来打通人工智能主体与拟制之间的障碍。然而,持此论者,恰恰忘记了法人拟制的原因与其被自然人驾驭的事实。“自然人→合伙→法人”的演进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主体的演进程式与法律人的胜利,其背后更是风险防范与经济利益的权衡,是法学与经济学价值理念的“共和”。法人的产生,特别是公司,是政府与市场协作的结果,是国家信用与自然人信用的叠加,其目的在于在投资者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筑起一道风险有限的法律隔离墙,从而激励投资、创新与扩大就业。正是因为这样,拟制性的法人复制了自然人的法律表象,如生命、住所、名称、名誉、财产与责任等。在此,仍以我国《民法典》为例,该法典明确规定法人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其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自法人成立时产生,至法人终止时消灭。正义代表正确的理性,在于凸显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坚定与永恒的意图。同时,正义是一个附着有浓厚理性的伦理学概念,服务于自然人是正义的本质体现。尽管法人分享了自然人的属性,但是其背后自然人掌控的事实说明,法人只不过是被当事自然人摆布的木偶,自然人仍然是法人组织的现实存在。
两组均无眶内损伤、鼻腔大出血、脑脊液鼻漏及鼻中隔搧动、鼻中隔穿孔、外鼻下塌畸形等并发症,术后随访第二周发现对照组2例和观察组1例中鼻甲与鼻腔外侧壁粘连,经粘连分解、明胶海绵隔离创面后恢复正常。
(二)人工智能主体论的非“法性”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为了实现和平、共和与正义,人们选择了相信法律,但是在人定法的演进中,人并非可以为所欲为。创制法律的目的也并不是使人类俯首听命于法律,将人变成手段或牲畜,而是应时刻彰显人的价值本位,突出对自然人生命、健康、自由等的保护。在时下人工智能主体说的论证中,有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在现行法上并不具备法律主体地位。但是,按照跟法人制度同样的法理,未来的人工智能法理学可以考虑通过位格加等,而把人造的智能机器提升到类比自然人的法律位格。”[22]P60为了逻辑自洽,人们又试图通过人工智能具有独立的“意志”与“思想”来自圆其说,如“在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及权利归属方面,应当从保守路径转变为激进路径,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权利主体,并由其享有创作物著作权。”[23]P73法律之所以能被称之为法律就在于其“法性”,而所谓的法性即人性。如果法律思想或承载思想的法律规范悖于人性,那么就自然因丧失了法性而不具有任何意义。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的理念应由安定性、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组成。“从正义的角度看,若实在法违反正义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那么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为法的‘法性’,甚至可以被看作是非法的法律。”[24]P172法律研究旨在通过学理创新去扩大与保障自然人的地位、自由与尊严,在于通过客体来厘清人与外在物的关系,而不是去限制与弱化自然人的地位、自由与尊严。法律正义是人与人性化的事业,在数字治理中,如果对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探讨是使人的中心地位黯然失色,那么这种思想就不具有正义性,自然也因此失去其法性基础。
人工智能主体说中的“我思→我在”是一种黑格尔的推理。虽然由“我思”能推导出“我在”,但是并不必然能推演出“我主体性”的存在。而且,这也恰好是对笛卡尔思想的曲解,因为我思故我在突显的是人的意志与存在,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的体现与强调。“人文主义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来回答由神的全能引出的问题:设想一种新人,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唯名论所设定的混乱世界中保护自己。”[25]P44“这里的‘我’自然不是笛卡尔本人,而是任何一个思维着的主体,因而是大写的人。从‘我’出发构造一切哲学、一切知识,让‘我’成为出发点,这当然是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26]P156然而,问题是对于已客观存在的人,我不思,就不存在吗?在法律中,如果一个人不具有正常的思考能力,依然具有人格,如无民事行为能力就享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反言之,会思考也并不必定使得某物获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非人的动物亦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如被作为人类“祖先”的猿猴就具有思考的能力,但是我们并没有从骨子里认为它就是我们的同类。猪狗牛羊亦会一定的思考,但却是作为人类的劳力或盘中餐而存在。
为了构建行为模式,法律具有指引、评价、教育与预测等功能。人工智能究竟是法律关系中的客体,还是法律主体并非学术论证的产物,而是法律现实的产物?虽然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与此亦步亦趋的法律并没有与主体肯定论遥相呼应,相反,而是将人工智能作为风险规制的对象,如为了因时制宜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欧盟就将人工智能视为“产品”对待。欧盟《产品责任法》通过于1985年。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其已时过境迁。在法律修补中,欧盟一改传统的立场,在归责原则上,允许基于产品缺陷,而不是过错来严格追究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该法第9条规定,只要存在供应商未披露系统信息、或受害人证明系统存在明显缺陷、或供应商违背了安全保障义务,则会引发损害和缺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推定。在美国2022年10月发布的《人工智能权利法案》中,人工智能也不是被当作主体进行确认与保护,而是基于问责将人工智能作为风险防范的对象加以控制,并倡导公民权益与技术服务于社会的宗旨。若非要将法人拟制的逻辑强加于人工智能主体的正当性与可行性论证,则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嫌。而且,即便法律将人工智能拟制为“人”,但是其也不可能如同法人一样分享“人性”,其原因在于:
其一是人工智能不可能拥有财产。财产是自由的基础,也是自由的保障。现实中,每个法人都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自己独立的账户,有自己名下受法律严格保护的财产。对此,各国公司法无不规定,作为企业法人,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必须敲黑板的是,法人财产最终的控制者是自然人。生活应先是一种物质的形式,尔后才是精神的方式。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知礼节。大逻辑上,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技术的物化旨在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而不是让人所炮制出来的物分享人的财富。是故,无论人工机器如何强智能,其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权,而这也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其二是人工智能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在诸种论述中,人工智能思维的独立性与意志性一直被津津乐道。事实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是遵照其操控者的命令来行事的,体现的是自然人的意志。根据肯定说的“无意志,则无存在”的逻辑,其也不可能是“人”。同时,也必须明确的是,法人之所以能被拟制就在于法人是一种抽象、无形性的存在,其基础是具体、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此外,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且自然人也予以认可,那么这对于我们的世界而言,是福音还是万劫不复的“人祸”呢?早在1982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片《银翼杀手》已给人类提供了警示。其三是人工智能也不可能具有权利与行为能力。在时下的法律体系中,无论不同类别的法律部门对自然人的权利如何进行划分与保护,其无非都表现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即便某个自然人先天或后天地丧失了行为能力,但是权利能力的自然存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否定其人格。在本质上,无论思维、辨识能力如何,自然人生而为人。因此,在法律中,侵犯或危害他人生命或健康是头等之恶,轻则监禁,重则以命相抵。然而,损毁某个智能机器人,多是一个民事法律问题,不会血仇性的抵命。其四是人工智能不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承担表现为财产性与非财产性,前者如损害赔偿、罚款、罚金或没收财产,后者如对自由的限制、对生命的剥夺、排除妨碍、消除影响等。即使采取拟制论,人工智能也无法承担可能的法律责任。然而,法人则不存在障碍,因为法人可以其财产独立承担责任,且自然人控制因素也决定了直接责任与法人的双罚逻辑。我国《民法典》第62条即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又如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虽然法律体系日益庞杂、森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以人为本,实现人对自由、平等、安全、秩序、效益等价值目标的渴望。“人”在法律中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基础性概念。在开放语义下,在既有的法律主体体系中,尽管我们可以对“人”这一术语进行解读,但是在这种释疑中,解释者并不能信马由缰。自然人是法律主体架构的基石,这是法律的根本所在。在法律解释中,这也是必须恪守的遵循。然而,在这种解释中,为了实现人工智能主体说的“逻辑自恰”,有人认为:“主体范围处于不断的扩张状态中,主体的外延不再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物种差异不再视为获取主体地位的法律障碍。”[27]P86虽然物种平等显示博爱,但是却与人类的自身需求格格不入。④学术研究并不必然同步于现实,相反,有时会严重成为社会前进的阻碍。在现实法律对客体的规范中,将自然人及其器官组织、细胞排除在“物”之外张扬的就是法律的人本性。给付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等其他客体也是对法律人本主义的伸展。如果在法律的演进中,脱离这一主线,那么与其相关的研讨与规范也就自然而然地丧失了其法性与正当性。
四、对人工智能非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考察
高速运转的社会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焦虑、彷徨、失落等不适应,这是人类自发性的应急综合症的表现。“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的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出于困境,有说不出的焦虑;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又不能把它表述为明确的论题。”[28]P12虽然人工智能极大地减缓了人类的劳作之苦,但是也从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对人类提出了全面的考验与挑战。法律不可能无中生有,都是特定时代下传承性的应景之作。“任何一种法律思考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得以型塑的‘历史气候’的印记;同样,处在‘意义之网’中的著者们也从一开始就被不知不觉地限制在历史可能性和规定性的界限之内。”[29]P1虽然学术研究宗旨在于揭示真相,但是也必须承认,有些研究却是反弹琵琶,致力于掩盖真相与误导。面对人工智能所生的困局,在学术研讨中,研究者的心态显得错综复杂,比如惊喜、急切、投机、焦躁、沽名钓誉等。斑驳陆离的人工智能主体肯定论就是这种复杂情感的浮光掠影。
为了划清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之间的界限,从而保证其独立性,法律人意图像自然科学一样打造一个结构严谨、逻辑自洽的法律体系,所以法律人注重法的内生性。不可否认,法内言法益于法律的自主与神秘,但是却容易滋长法教条主义,从而背离法律正义的初衷。人工智能促进法律研讨的“繁荣”,但是为什么会剑走偏锋地认为应紧跟时代赋予其法律人格,其因也在于死守法教义学的刻板。法并非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除了法内言法外,为与时俱进,还必须法外言法,或者说在社会关系日益连带中,还应更多地法外言法。对于这一点,霍姆斯曾提醒:“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31]P469美国大法官布兰代兹更是认为:“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公敌。”[32]P195基于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动静对立,在研究方法上,法律人不能坐井观天,必须走综合化的路线。“研究法律的任何方法,不论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社会的法律,必须是折中和综合的。”[33]P26
在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中,人工智能究竟是主,或共同为主,或是主客关系,这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并非一个纯法学的概念问题。“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具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界的关系。”[34]P146自我意识不仅塑造了主体,而且也导致了在主体话语中,于主体之外的其他存在是作为客体与对象而存在。主客关系的确立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在研讨中,虽然强人工智能者认为,人工智能是如同人一样拥有心灵的机器,但是会思考并不必然会改变人工智能的客体本质。在认知中,我们并不能否认其他动物也具一定的心智能力,但是在其与人类的关系中,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动物会思考而改变猪狗牛羊等被作为人类手段的法律地位。同样,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我们也不会让任何其他物种及人自身的缔造物来共享人性。尽管有时为了体现文明与仁慈,我们会通过法律禁止虐待与杀戮动物,但是这种赋权并没有改变其客体属性,也并没有使受保护的动物摆脱可能成为人类玩物或食物的命运,因为它们的存在是服务于人类的需要。人是万物的尺度。虽然机器可以模仿人,但是“人类心智是理性、情感、欲望的复合体,它的运作有复杂的机制,这个机制是人工智能不具备、也无法模拟的。”[35]P30在人的世界中,为了生存及生活得更加美好,人工智能只是物,人不应该自我否定而反客为主地将其升格为人。“人工智能目前只能作为一种技术而存在,对人类而言,是对人脑工作方式的模拟,是对人脑逻辑思维能力的强化,是人脑的延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获得主体性,奇点不会出现。”[36]P22多年前,马克思就精辟地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7]P89
在人类文明的持续推进中,随着理性自由向意志自由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前期的认知关系变成征服与操控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化。“在所谓价值和价值观念领域中,正是人(实际上也唯有人)普遍居于最高的、主导的地位,人是根据,是尺度,是标准,是目的。”[38]P7科学研究的目标是造福、服务于人,而不是通过研究性的说教来限制人、矮化人与否定人。本质上,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自由史,而自由史则是一部工具创新史,智能化机器人只是这部工具史的一个“小插曲”。旬子言:君子生无异也,善假于物。去伪存真地看,人是通过工具来影响、改造自己与世界的。“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与人类相伴而成的,因而技术的生成和发展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存在的。”[39]P558然而,为什么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还有人力捧人工智能的人格化,致力于使其在法律关系中实现客体主体化的转型呢?在多姿多彩的研讨中,仅仅列明事实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更重要的是针对这种另类进行穷根究底——为什么会这样?在回应人工智能挑战的制度性探讨中,之所以出现强化“工具”的主体性,而弱化人真正的主体性,其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是主流价值的迷失。在人与外物的关系中,“谁主”“谁客”本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公理问题,但是由于在当下的世界,物质文明已是千姿百态,人们已多不再衣不蔽体与食不裹腹,在思考者价值错位而穿凿附会之下,精神文明并不总能与物质文明齐头并进,相反,极有可能是对物质文明的异化与直接否定。在这之中,技术理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技术理性假定了一个外在本质和规律的存在,把人同化到外在的本质之中,就会使人失去自我,成为本质的附属品。”[40]P59法律旨在于保障与扩大自由,而不是限制与消灭自由。在法律主体类别的演进中,人类之所以在合伙的基础上拟制出“法人”,其目的亦是服务于自由、效益与富足等向善的目标。人工智能主体化不仅会削弱对自然人的权益保护,而且也会混淆“真人”与“假人”之间的界限。对人类的发展而言,人工智能主体论无异于作茧自缚与“武功自废”。事实是:无论人类自诩的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除了人本身之外,文明的本质决定了必须放弃法律关系主体物化重构的痴心幻想。
其二是对自然人的人性认识不足。“人是什么”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为之贴上不同的标签,如社会人、文化人、政治人、经济人等,但是人和人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才是“人是什么”问题的核心所在。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与主宰者。“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P60人类之所以能够理所当然地将外在的事物作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其根源就在于人绝对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地位是在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通过实践活动体现并确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AI根本无法复制、模拟和超越人类主体性。”[42]P53人工智能主体论之所以能够死灰复燃地掀起论战原因就在于,时至文明“发达”的今天,在学者们的脑海中,人们并没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无可争辩的共识性定论。
其三是知识伦理性的缺失。人工智能是知识沉淀的结晶。在逻辑上,对于人类而言,知识越多意味着越文明与越自由,但是知识似乎越来越不受我们所控制,其反因其权威性而开始控制我们,并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权力与主宰。作为知识载体的技术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其“善”能给人类带来预见、财富与自由,但是其“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困扰与不安,并“玷污”人的心灵。自由与技术并不绝对相容,一种可能的后果是,技术越进步,自由越退步。随着知识的与日俱增,科学技术不仅会日渐改变人类的言说方式,当精确的技术语言“篡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人类的生活将不再是充满诗意的栖居。在技术统摄之下,人会日益精神迷茫,并最终可能找不到自己。虽然物质、知识、技术、财富等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技术并不必然会扩大自由,而只会使得社会中的一少部分人更自由、更富有,而大部分人自由空间的被挤压、财富被缩水,并使得资源、权力与利益等进一步被集中,甚至垄断。历史经验证明,技术发展衍生问题的效率远大于人类解决问题的效率,其将人类带入了一个难以轻易走出的死胡同。人性恶决定了技术并不中立,人类知识化的文明必须接受伦理的检验与评价,或者说知识向善应以伦理性为依托,因为“没有伦理的技术,就象一个没有灵魂和没有良心的活物一样。”[43]P300人是什么及人与自然物和人造物应是什么关系,这本应是常识,但是为什么人工智能会使一些人对这些常识产生质疑,并试图挑战而立新呢?其因即在于技术“膜拜”下的技术控制及知识伦理性的缺位。
其四是视野的狭窄与研究目标的错误。法律是什么并非一个恒定的命题。也正因为这一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从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法学派系,如自然法学、实证法学、历史法学、利益法学等。法律是一种连带性的社会现象,为了知道法律是什么及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就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与理解法律,而不能基于所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将法律视为可以在一个严格密闭的容器里茁壮成长的事物。有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人工智能应具有主体资质,其因就在于在他们看来,法律是可以特立独行的,至于其社会连带效应则不属于思考的范畴。对于人工智能的主客体之争,法社会学的观点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无论是现在或者是其他任何时候,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44]因此,为了知道与了解人工智能是不是人,法学研究者就不能埋头于一大堆的法律文献,而必须走出书斋,脚踏实地地观察与体会世俗的烟火气,从而找到人工智能在社会关系中应有的位置。
根据分工,学术研究的宗旨在于认知、探索与创新,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服务于人类的福祉才是目的。虽然读书人的闲暇和“诧异”能为社会贡献有效的智慧,推动社会健康前行,但是对于作为读书人的“诧异”,笛卡尔的以下批评是深刻的:“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多得多。普通人是对切身的事情进行推理,如果判断错了,他的结果马上就会来惩罚他;读书人是关在书房里对思辨的道理进行推理,思辨是不产生任何实效的,仅仅在他身上造成一种后果,就是思辨离常识越远,他由此产生的虚荣心也就越大,因为一定要花费比较多的心思,想出比较多的门道,才能设法把那些道理弄得像是真理。”[45]P9
结语——法律应以人性为依归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突破,人类日益如同“温水煮青蛙”般被智能化的机器所影响与控制,随处可见的智能化产品就是对这一现象最真实的写照。传统的世俗社会悄然间已被网络虚拟化再造,人已在事实上深陷于自己开发出来的网络、平台、数据、软件与通点人性的机器中而难以自拔。“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46]P416方兴未艾的网络化、程序化与数据化浪潮中,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人已不可能做到时刻保持绝对骄傲的“主人翁”姿态而对作为“它者”存在的智能机器颐指气使或不以为然,相反,在应然的主客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已并非那么牢不可破,作为主体的人已在事实上成为一个个“附庸”。在客体的萦挠之下,智能机器可以不需要人,而人却离不开已会自我“思考”的机器。需求关系失衡使得主客关系被模糊与被颠倒,人的主体资格被人为破裂。真相是,时下形形色色的人工智能主体说就是人们精神已开始出现物我关系错乱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这样,强化人的主体性与明确人工智能的客体性才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人工智能主体之争看似一个法律何处去的革新问题。其实,其更是一个科技伦理问题。“现代科技伦理应然逻辑是现代科技实然逻辑——‘是什么’和‘能做什么’基础上,关注其‘应是什么’和‘应做什么’”。[47]P16无论科技的发展如何触动法律的变革,所有法律的研讨、法律的运作都是服务于人,以人为本位,而不是要让任何第三者来分享人神圣性的主体地位,更不是要将人变成附庸或他物的奴隶,而这是法律理论者与实务者必须坚守的底线。在法律发展的路径中,一直存在以下两种比较针锋相对的思维:一种是法律理性建构主义,其以卢梭、笛卡尔为代表。该论认为,凡物皆可法,法律人可以通过理性打造法律帝国;另一类是法律进化主义,其以托克维尔、休谟、哈耶克等为代表。前者自豪地认为:人可以凭借自己无所不能的理性来塑造人类的文明,而后者则谦卑地认为:“制度的源始并不在于构设与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48]P64虽然人贵为万物的灵长,但是在人改造世界中,人并非全知全能,其都必须遵守应有的刻度与底线。那就是,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与任何问题的解构,除了人自身之外,都必须体现人性、以人为本位、以人为归宿。归根结底,无论强弱,人工智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人创新与运用工具探索世界的过程。
法律主体事关人的地位、人与物的关系、人的发展与担当,其并不是一个法律人可以随意游戏与致命自负的问题。在人工智能的法律应对中,必须消除法律人是绝对理性、万能、可以随性拟制某物为人的幻想。法律设想中,“我们应当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的秩序的方式(置其于权威当局的指导下)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我们能够通过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49]P5法律研究者与立法者不是自然科学家,法律也并不是“1+1=2”的数学游戏,但是在法律之路中,“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50]P183人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其更是一种文化、精神与社会性的存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回应中,必须自始至终恪守人本来就是什么这一永恒的主题。
注释:
① 本文中的“主体”均指在法律的语境下,具有独立的意志、能够引起法律关系设立、变更或终止、能享有权利并能履行义务、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责任的当事者。
② 由于本文的命题在于宣扬与强化人类中心主义,彰显人的本位价值,所以在论证性的陈述中,除了“法人”外,“人”都指“自然人”。
③ 有学者认为,人格源于法律的赋予,即使在生物特征上为人,但是如果法律不赋予其人的法律地位,那么其仍不是人,如在古罗马,奴隶是“人”,但是在法律上被视为“动产”。实质上,这种观点有些过于抬高法律的评价功能。人是否是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其并不需要法律的标签。而且,如果法律将客观上的人识别为非人,而归入“物”的范畴,除了说明这种思想与规定反文明、反法律、反人性外,而别无其他。乌尔比安即认为:就国家法而言,奴隶被认为不是人,但是依照自然法,这一规定就是错误的,因为在自然法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④ 与人工智能相比,猪狗牛羊等动物则更是血肉性的生命存在。从“格”的认可来说,赋予被人类作为盘中餐的动物以人的“格”不仅显得急切,而且更能体现人性与大爱无疆。尽管我们反对虐待动物,甚至为之立法,但是人类并没有赐予动物以“人格”,其因在于牛羊等动物是作为人类的手段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