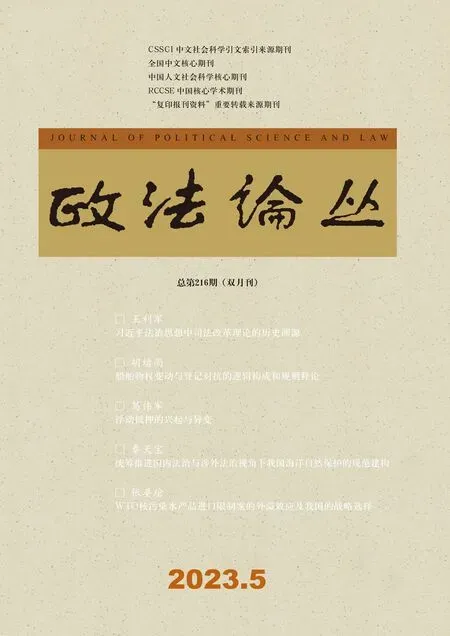“毗连区第一案”的司法解析及中国应对*
2024-01-02朱利江
朱利江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生效以来,国际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已在九个案件中适用了《公约》。法院对《公约》的适用呈现两种情形:一是因为案件当事国是《公约》缔约国而适用《公约》,①二是虽然案件当事国并非《公约》缔约国、但《公约》中的有关条款属于习惯国际法而适用《公约》。②尽管第二种情形并非《公约》第293条意义上的适用《公约》,③但实际上也是在适用《公约》。而且,此种情形与第一种情形相比较而言,更具争议,更受各方关注。
2022年4月21日,法院对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以下简称“本案”)作出判决,认定哥伦比亚虽不是《公约》缔约国,但其“整体毗连区”不符合《公约》第33条和第303条体现的习惯国际法,要求哥伦比亚采取措施,使“整体毗连区”与《公约》体现的习惯国际法保持一致。④这是法院对《公约》缔约国与非缔约国间的海洋权益争端中最新适用《公约》的案件。而且,在《公约》确立的八大海域制度中,毗连区制度是受关注最少的制度,《公约》中关于毗连区制度的条款只有2个(第33、303条)。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由于沿海国可以对毗连区内的外国船舶进行管制,随着科技的发展,沿海国在毗连区内的管制能力已大幅提升,所以毗连区制度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虽然司法判例本身不是国际法,但它里面含有国际法的内容,有助于查明、澄清、确定国际法的内容。⑤
本文尝试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进行解析,首先论证该案在国际海洋法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即该案是国际裁判中真正的“毗连区第一案”,其次证明法院在本案判决中对毗连区制度的三个方面作出的司法创新,并揭示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所存在的推理缺陷。最后就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建议。本文认为,法院在本案判决推理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依然作出了司法创新,这一点与法院长期以来在适用《公约》中存在的政策取向是分不开的,即通过判例推进《公约》的普遍性、有效性与完整性。
一、“毗连区第一案”的证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律方法的兴起,国际仲裁和司法开始介入国家之间关于毗连区的争端。1917年,中美洲法院(CACJ)审理的“萨尔瓦多诉尼加拉瓜案”是这一问题上的国际司法尝试。在该案中,中美洲法院指出,国际法承认沿海国有两个海域,一是宽度为1里格的领海,二是宽度为3里格的出于防卫和财政目的而管制的“管辖海域”。⑥虽然该判决没有明确指出宽度为3里格的“管辖海域”就是毗连区,但从内容来看非常接近毗连区。即便如此,该案判决对毗连区制度的内涵并没有阐释。而且,正如英国学者罗威所言,即便它是一个涉及毗连区的国际判例,这一判决认定的也只是拉丁美洲的“区域国际法”。⑦因此,在当时英国等少数国家与美国等多数国家之间存在关于毗连区制度巨大分歧的情况下很难说具有普遍意义,该案也就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毗连区国际判例第一案。
1919年,随着美国公布“禁酒法”,美国与英国之间关于毗连区的争端加剧。1921年,两国决定通过协定设立国际仲裁庭,解决由此引发的争端。在“漫游者号案”的裁决中,国际仲裁庭指出,“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是,除非在战时或者存在特别协定,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对公海中从事合法活动的外国船舶登临和搜查。”⑧该裁决为和平时期沿海国对公海中活动的外国船舶行使登临和搜查权指明了法律依据,即缔结特别协定。在这一裁决的影响下,美国与许多国家缔结了特别协定。1924年,经过谈判,美国与英国缔结了“酒精条约”(Liquor Treaty),美国承认3海里领海宽度,英国承诺不再反对美国登临和搜查距离美国海岸一小时帆航内的英国船只。⑨发生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著名的“孤独号”仲裁案就是在该条约的背景下发生的。⑩随后,美国与欧洲国家及巴拿马、智利和日本等15国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一方面承认沿海国的领海宽度为3海里,另一方面又承认沿海国在3海里外的公海中可以对对方国家的船舶采取一定措施。
“漫游者号”国际仲裁案需要裁决的美国在公海中的执法权也非常接近毗连区权力,但该裁决认定有关国家在和平时期只能通过缔结特别协定的方式彼此扩大在公海中对对方国家船舶的执法权,这实际上否定了沿海国有权在当时的公海中单方面设立毗连区,而且该案本身是一个临时的国际仲裁案,其权威性和普遍性均有限,因此该案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毗连区国际判例第一案。
此后,有关毗连区的国际判例销声匿迹,直到《公约》在1994年生效。1999年,在“塞加号案”(第二)中,第一次出现了通过新成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对沿海国毗连区制度进行国际司法审查的机会。然而,由于几内亚后来主张自己的执法权不是基于毗连区制度,而是专属经济区制度,因此国际海洋法法庭并没有在判决中对沿海国的毗连区制度进行司法审查,从而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不过,一些法官在该案判决的个别意见中对毗连区制度发表了意见,特别是来自伯利兹的莱恩法官,其在个别意见中对《公约》第33条规定的毗连区制度中的三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即:沿海国在毗连区中的权力是否仅限于“管制”,而不是立法和执法管辖权?几内亚对在毗连区和领海外发生的违反海关和相关法律的行为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第33条?第33条是否授权几内亚对在毗连区和领海外实施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然而,莱恩法官的意见也只是他自己的个别意见,不能代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观点。
2020年,在印度和意大利之间的“莱谢号”案仲裁裁决中,依据《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一个国际仲裁庭认为,由于印度在本案中并未在毗连区中对“莱谢号”及船上的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士兵采取执法行动,因此,即使可能产生印度1976年《海域法》和1981年“通知”将印度的刑事管辖权扩大到毗连区是否符合《公约》第33条第1款的问题,也没有必要在本案中处理。这样,该国际仲裁庭也就失去了对毗连区制度进行仲裁审查的一次宝贵机会。
至此,《公约》在生效后,无论是国际海洋法法庭还是《公约》附件七的国际仲裁庭都曾有过审查沿海国毗连区制度的宝贵机会,但均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实现。因此,202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是真正意义上的毗连区国际判例“第一案”。
二、“毗连区第一案”中的司法创新
(一)毗连区国际法制度性质认定方面的创新
毗连区国际法制度的性质涉及《公约》中的毗连区制度是条约制度抑或习惯国际法制度。《公约》中的毗连区制度主要规定在第33条,此外,第303条第2款也涉及沿海国在毗连区的权限,而且这一权限不受第33条第1款中的“在其领土或领海内”的限制,并扩大到了海床中的行为。[1]P81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第33条和第303条第2款是否是习惯国际法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2]P110在本案中,由于哥伦比亚并非《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就出现了无法适用《公约》、只能适用习惯国际法的局面。
在第33条问题上,法院完全支持尼加拉瓜的主张,认为第33条构成习惯国际法,不仅沿海国设置毗连区的宽度,而且管制的事项,均应遵守第33条。此外,在第303条第2款的问题上,尼加拉瓜主张哥伦比亚不可援引第303条第2款,因为哥伦比亚不是《公约》缔约国,但哥伦比亚主张第303条第2款是习惯国际法。法院经过审查后认为,《公约》第303条第2款也是习惯国际法的体现。这是法院在判例中首次宣示《公约》第33条、第303条第2款为习惯国际法,这一点无疑具有开创性。
(二)毗连区的设置及划界方面的创新
在本案中法院指出,毗连区与专属经济区受到两套不同制度的调整。一般说来,一国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建立毗连区与另一国在同一个地区存在的专属经济区不会发生冲突。法院还对沿海国在毗连区中的权力与在专属经济区中的权利进行了区分,认为根据国际海洋法,一国对毗连区行使的权力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中的权利不同。这两个区域有可能重叠,但可以在里面行使的权力和地理范围并不相同。毗连区是基于沿海国管制权的扩张,其目的是预防和惩罚那些违反沿海国国内法和规章的行为,而专属经济区则是沿海国对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及对保护海洋环境建立管辖权。这两套制度之间的区别在《公约》的谈判过程中就已得到承认。在行使这两套制度中的权利和义务时,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合理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法院认为,在哥伦比亚的“整体毗连区”与尼加拉瓜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部分,哥伦比亚可以依据《公约》第33条第1款体现的习惯国际法行使管制权,但是,在与尼加拉瓜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整体毗连区”部分行使权力时,哥伦比亚有义务顾及尼加拉瓜依据《公约》第56条和第73条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法院还确认,由于在两国2012年的判决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毗连区,因此该判决书划定的两国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单一界线并不意味着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包含毗连区的划界。可见,在法院看来,毗连区划界是一个不同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独立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注重对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的区别,但对于毗连区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区分关注较少。本案判决首次对沿海国的毗连区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制度进行了区分,澄清了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建立本国毗连区和行使管制权的限制问题,同时还肯定了沿海国进行毗连区划界的可能。这些都具有创新。
(三)毗连区的管制目的方面的创新
关于《公约》第33条第1款列出的“海关”、“财政”、“卫生”、“移民”四个毗连区管制目的,由于哥伦比亚将其中的“卫生”一词解释成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院因此对该词进行了解释。法院否定了哥伦比亚对该词的扩大解释,因为海洋环境是一个受到关于环境的习惯国际法另行调整的事项。这是国际司法判例第一次解释毗连区管制目的中的“卫生”一词。更加重要的是,本案判决还首次澄清了沿海国对《公约》第33条第1款规定的四个管制目的和第303条第2款规定的考古和历史文物的管制权范围。法院认为,习惯国际法只承认对毗连区进行上述四个目的的管制,其他诸如安全、打击海盗、贩毒及破坏海上安全,均非各国同意沿海国可以在毗连区进行管制的目的。而且,习惯国际法在这个方面从1982年《公约》通过以来也没有任何发展。法院还指出,在一国的毗连区与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发生重叠的情况下,一国不得在重叠的部分对“国家海洋利益”、“环境保全”目的进行管制,否则将会侵犯另一国依据《公约》第56条第1款享有的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关于《公约》第303条第2款,法院承认其为习惯国际法,因此沿海国有权对在毗连区内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进行管制,在这个问题上,哥伦比亚的“整体毗连区”并不违反习惯国际法。
三、“毗连区第一案”的司法缺陷
(一)毗连区国际法制度性质认定存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缺陷
1. 偏离国际法委员会《习惯国际法查明结论草案》
2018年,国际法委员会经过6年审议,二读通过了《习惯国际法查明结论草案》(下称“《草案》”)。虽然该文件只是一份“草案”,但鉴于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法编纂领域的崇高地位,它应该是这个问题上较具权威的一个文件。《草案》第二项结论指出,“要断定存在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及内容,必须判断是否存在经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亦即:“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是习惯国际法规则存在必须同时满足的两个要件。然而,在本案中,法院在认定《公约》第33条第1款规定的毗连区宽度规则是习惯国际法时,并没有严格遵循两要件的分析路径。
关于毗连区的宽度制度是否是习惯国际法,法院只是说,“建立了毗连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将宽度设定在24海里,这与《公约》第33条第2款一致。有些国家甚至缩减了原先设定的毗连区宽度,以便使其与《公约》的规定保持一致。”在这里,法院显然只注意到了毗连区宽度的“一般惯例”,并没有阐述这些国家如此实践的“法律确信”。国际法委员会在对《草案》第11条的评注中特别提醒,在经由条约证明习惯国际法时,仍应得到“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因为履行条约义务的结果。同样,《草案》第9(1)项结论在解释“法律确信”时认为,作为习惯国际法构成要件的“法律确信”,是指必须在法律权利或义务的意识下开展有关实践。在对该项的评注中,国际法委员会写道,并不要求所有国家都承认该规则是习惯国际法规则,但该规则必须得到“广泛的、有代表性的接受”。
然而,在本案中,在证明毗连区已成为习惯国际法上的概念时,在法律确信方面,法院只是说,各国的一般实践“经两当事国接受”。法院并没有证明,这样的法律确信是否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公约》的其他缔约国来说也是一般存在。这显然与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要求不一致。
2. 偏离法院的判例
首先,在证明毗连区概念是习惯国际法时,法院只是提到,“现在大约有100个国家建立了毗连区,包括《公约》的非缔约国”,但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国家实践。在证明《公约》第303条第2款也是习惯国际法时,法院提到,《公约》通过后,有越来越多国家将文物立法扩大适用到毗连区,但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国家实践。这与法院之前在一些案件中认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时同样依赖各国立法的做法不同。例如,在2012年德国诉意大利的“国家豁免案”判决中,法院在证明一国武装部队在他国境内的行为是否构成豁免例外时,在提到各国立法实践时,具体列出了美国、英国、南非、加拿大、新加坡、阿根廷、以色列、日本、巴基斯坦等国的国家豁免法。但是,在本案中,法院在同样的问题上并没有这样做,显然存在做法上的不一致。
其次,本案在证明《公约》中的毗连区宽度制度也已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时,在法律确信方面,法院只是说,各国的一般实践“经两当事国接受”。然而,法院在1986年尼加拉瓜诉美国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的判决中特别指出,“当两国同意将某项规则规定在条约中时,这种同意就足以导致该规则成为对两国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但是,在习惯国际法问题上,当事国关于其认为是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合意是不够的。法院必须证明,这种规则已经得到了各国法律确信的支持。”显然,本案判决在这一点上与尼加拉瓜诉美国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判决不一致。
最后,在证明《公约》中的毗连区管制目的也是习惯国际法时,法院认为,哥伦比亚提供的不少国家的毗连区立法纳入“安全”事项的证据不足以构成习惯国际法,因为这种实践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法院在本案中对这种各国立法不一致的实践的“解读”与法院之前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案件中的“解读”也不一致。在1951年英国诉挪威的“渔业案”中,法院面对各国领海基线划法不同的局面,指出:“虽然一些国家采取了10海里规则,但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规则。因此,10海里规则并没有构成一般国际法规则。”在1996年的“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中,法院面对各国对“核威慑政策”的分歧时,也认为不存在不得使用核武器的法律确信。在2010年的“科索沃案”咨询意见中,法院面对各国对“救济性分离”的分歧时,甚至不对其是否是习惯国际法进行表态。可见,在法院判例中,当遇到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分歧时,通常认定不存在习惯国际法或不对其是否是习惯国际法进行表态,但在本案中,法院同样在面对“安全”是否是毗连区管制目的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分歧时,却认为存在一项否定“安全”是毗连区管制目的的习惯国际法,与之前判例中的做法不一致。
(二)阐释《公约》毗连区制度内容中的司法缺陷
1. 毗连区的设置及划界方面
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在《公约》中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海域。它们的范围、沿海国的权利都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在空间上有重叠,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可能产生“重叠”。沿海国在毗连区中可为防止外国船舶在沿海国领土或领海违反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或为惩治外国船舶在沿海国领土或领海内违反上述法律和规章而对外国船舶进行必要的“管制”。预防性质的“管制”措施可包括警告、搜查、登临、责令改变航线、禁止驶入领海、责令船上人员下船或限制、禁止人员上下船、责令卸货或限制、禁止卸货、拦截、跟踪、监视,甚至逮捕或扣押;惩罚性的“管制”措施可包括登临、检查、拦截、紧追、扣押、逮捕、罚款、查封、没收、拍卖、甚至拘留等。[3]P330
同样,在专属经济区中,按照《公约》第73条第1款规定,沿海国在行使其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时,也可以采取为确保其依照《公约》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因此,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外国船舶未经沿海国同意非法开发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后企图直接进入沿海国领海进行走私,此时该行为可能同时违反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和领海的法律,由于《公约》第73条第1款并没有指出沿海国可登临、检查、逮捕的海域,因此这种措施有可能发生在毗连区内。如果在毗连区内进行登临、检查或逮捕就有可能既是在依据《公约》第33条第1款对毗连区进行管制,也有可能是在采取《公约》第73条第1款规定的措施。因此,沿海国在行使权利的措施方面也会产生“重叠”。
此外,《公约》第66条第2款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应有专属管辖权,包括有关“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规章方面的管辖权”。当为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的目的而建设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位于毗连区内时,沿海国若依据《公约》第66条第2款对其基于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进行专属管辖,则也有可能与沿海国依据《公约》第33条第1款对毗连区的管制发生“重叠”。当同一个沿海国在自己的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海域行使上述可能发生“重叠”的权利时,还不至于引发国际争端,然而当某一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与另一个沿海国的毗连区发生海域“重叠”时,它们行使上述“重叠”的权利时则有可能引发国际争端。对此,高健军教授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这一问题,认为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一国可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设置毗连区有可能为两国埋下将来产生新的冲突的种子,这不利于化解两国的海洋权益争端。[4]P11
此外,法院认为专属经济区划界不包括毗连区划界,暗示毗连区划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问题,但这一点并没有《公约》上的依据。《公约》在毗连区部分并未规定毗连区划界的条款。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33条第3款规定的毗连区划界条款在《公约》中已经被删除。《公约》删除毗连区划界条款的原因是,由于大多数沿海国都将会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因此毗连区就将作为沿海国之间 “多种海域”单一划界的一个部分。[5]P42换言之,对于宣布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而言,它们之间的毗连区划界等于是专属经济区的划界。[6]P307因此,《公约》第33条的起草历史表明,《公约》似乎不再承认沿海国之间有进行毗连区划界的必要。然而,本案的判决却暗示毗连区划界是一个独立的海洋划界问题,这就不符合《公约》第33条的起草历史了。不过,自1982年《公约》通过以来,也的确出现过毗连区划界方面的实践,包括国际仲裁实践。1992年,在加拿大和法国之间的海域划界案仲裁裁决中,国际仲裁庭就认为,两国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之间的毗连区划界需要依据“合理与公平”原则解决。
2. 毗连区的管制目的方面
在毗连区制度问题上,长期以来,对于沿海国是否可以突破《公约》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对毗连区规定海关、财政、卫生、移民四个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不论在学术还是在实务中,均存在分歧。[7]P208认为沿海国对毗连区的管制目的只能限于上述四个目的的理由主要是,沿海国的法律必须与《公约》保持一致,而且习惯国际法也不允许突破四个目的,例如德国学者卡恩、[8]P271中国学者张新军[9]P117。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也持这种立场和理由。与之对应的观点则认为,虽然《公约》规定了四个管制目的,但《公约》也没有明确禁止沿海国扩大管制目的,并认为习惯国际法允许扩大管制目的。美国缅因州联邦地区法院在1975年的“地洋丸号”(Taiyo Maru)案中就认为,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24条并不禁止缔约国为该条款所列的海关、财政、移民、卫生以外的其他目的建立毗连区。中国学者童伟华也认为,由于《公约》第33条第1款没有明确禁止,因此增加规定“安全”目的具有合理性。[10]P147
可见,两者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公约》是否明确禁止扩大管制目的,二是习惯国际法是否允许扩大管制目的。关于第一个焦点,法院的日本籍法官岩泽雄司对本案的判决撰写的声明中指出,哥伦比亚将毗连区管制目的扩大到“安全”目的,侵犯了尼加拉瓜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享有的航行自由权,因此是《公约》禁止的。美国学者罗奇(J. A. Roach)和史密斯(R. W. Smith)也认为,增加规定“安全”目的侵犯外国的航行自由权。[11]P17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公约》之前,毗连区是建立在原来是公海的海域,因此扩大管制目的将是对公海自由的威胁,有可能被公海自由原则禁止,但在《公约》通过后,毗连区是建立在专属经济区之内(如沿海国宣布专属经济区)的海域,而《公约》第59条规定,“在本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任何其他一国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因此沿海国将毗连区管制目的扩大,可能得到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中的权利的许可,不一定违反公海自由原则。[12]P314遗憾的是,法院并未回应《公约》第59条的关联性。
关于第二个焦点,毗连区管制目的是否属于《公约》序言第八段所指的“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这是一个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德国学者拉戈尼(Rainer Lagoni)就指出,哪些事项属于“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13]P16只有当答案是肯定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去考察习惯国际法。然而遗憾的是,法院也没有处理这一问题。而且,即便是认为毗连区管制目的是一个习惯国际法问题,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法院在本案中对这一习惯国际法的论证也是存在问题的。
四、“毗连区第一案”中的政策取向
上文表明,本案判决无论在毗连区国际法制度性质认定方面还是内容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司法推理缺陷。既然如此,法院为何仍在毗连区制度的适用和解释上作出司法创新呢?本文认为,这与法院长期以来在适用《公约》方面追求的政策取向是分不开的。法院适用《公约》的所有判例整体显示,法院一直在追求《公约》的普遍性、有效性与完整性。本案判决只是法院这一司法进程中的最新“作品”。
(一)追求《公约》的普遍性
法院追求《公约》普遍性这一政策取向体现在对《公约》中的毗连区制度的习惯国际法认定方面。《公约》作为一个条约,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的规定,原则上只对缔约国有拘束力,而且《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还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然而,《公约》序言第5段提到《公约》的目的之一是,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这似乎在表明《公约》旨在对“所有国家”产生影响,不论是否为缔约国。尽管如此,《公约》面临的一个现实是,40年过去了,《公约》并未实现普遍性。虽然目前已得到了168个国家等主体(含欧盟)缔结,但仍有不少国家没有缔结《公约》,包括美国及本案中的哥伦比亚。因此,就很容易产生《公约》能否拘束非缔约国的问题,这是国际司法和国际仲裁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法院。
在此问题上,法院在实践中不断利用审理案件的机会发表自己对《公约》中的条款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意见。总的说来,法院的判决体现的政策取向十分明显:法院但凡有机会需要对《公约》中的条款是否是习惯国际法发表看法,几乎都是倾向于作出肯定的表态。因此,可以说,法院存在一项推动《公约》习惯国际法化的政策取向。
例如,在1984年的“缅因湾划界案”判决中,法院的一个分庭认定《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在1992年的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领陆、岛屿、海洋边界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公约》第10条规定的海湾制度是习惯国际法。在2001年卡塔尔诉巴林的“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领海制度、第7条第4款规定的直线基线制度、第13条第1款规定的低潮高地制度、第15条规定的领海划界规则、第17条规定的无害通过制度、第74条第1款和第83条第1款规定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制度、第121条第2款规定的岛屿制度均是习惯国际法。在201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的领海制度、第5条规定的正常基线制度、第74条第1款和第83条第1款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制度、第76条第1款规定的大陆架定义、第121条规定的岛屿制度均是习惯国际法。在2014年秘鲁与智利之间的“海洋争端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公约》第74条第1款和第83条第1款规定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制度是习惯国际法。
本案是法院遇到的需对《公约》中的毗连区条款是否是习惯国际法进行表态的首个案件。之前,法院在实践中从未遇到需要对此问题进行表态的机会。法院在本案中认定《公约》中的毗连区制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是在加速《公约》的习惯国际法化的演进。由于习惯国际法原则上约束所有国际法主体,具有普遍效力,因此这等于是追求《公约》的普遍性。
(二)追求《公约》的有效性
法院追求《公约》有效性这一政策取向体现在认定一国可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设置毗连区的方面。《公约》规定了八种不同的海域制度。这些海域制度都具有自己的法律地位和制度规范,彼此不同。同时,《公约》序言第三段也指出,各个“海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可见,《公约》中的海域制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有效解释原则是条约解释中的重要原则。它的首要含义便是,条约的用语、条款的存在应具有自身的意义,发挥自身的效果,即所谓“与其毁物不如使之有用”(ut res magis valeat quampereat)。[14]P103虽然有效解释原则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中没有明确提及,但该原则在这两个条款中也可以找到潜在的依据,包括条约解释应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行“善意解释”。
法院在之前的一些案件中实际上运用了有效解释原则。在1949年的“科孚海峡案”判决中,法院指出,“(这种解释使得)此类特别协定中的规定变得毫无目的或效果,不会为普遍接受的解释规则所承认”,这实际上肯定了有效解释原则。在1950年的“和平条约解释案”(第二阶段)咨询意见中,法院指出,“法庭的职责是解释条约,而不是修改条约”,并强调“如果解释者给和平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赋予了一种与条约文字、精神相背离的意义,那么这种行为是不能援引“与其毁物不如使之有用”的格言来进行抗辩”。这是法院第一个在判决中明确肯定有效解释上述含义的判决。在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之间的“领土争端案”判决中,法院说,其他任何解释都将使得对该案附件一中文件的援引变得“无效”,因此不可采。这实际上也肯定了有效解释原则。在2001年格鲁吉亚诉俄罗斯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适用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必须赋予该公约第22条中的“争端不能……解决者”实际含义。在2020年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1899年领土争端仲裁裁决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在决定将争端提交法院前还需要征得两国同意,那么两国签订的协定就将无效。这实际上也是在肯定条约文本的有效解释原则。
在本案中,法院在处理在别国专属经济区能否设置毗连区问题时,对《公约》中的条款进行了细分,确认不同海域制度的独立价值,否认一国的毗连区在与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情况下毗连区将被专属经济区“吸收”的观点,这一作法实际上是在维护《公约》中毗连区制度的独立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通过对《公约》毗连区条款的有效解释是在追求《公约》的有效性。
(三)追求《公约》的完整性
法院追求《公约》完整性这一司法价值体现在维护《公约》中的毗连区管制目的方面。《公约》序言第一段指出,《公约》的愿望是本着以互相谅解和合作的精神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第八段同时又指出:“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就《公约》本身而言,维护《公约》条款完整性是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公约》第309条提示,除《公约》其他条款明示许可外,对《公约》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联合国大会也在涉及海洋法的许多决议中重申, “《公约》的统一性和维护《公约》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学者们对《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进行考察后也认为,维护《公约》的完整性是争端解决机构的目标之一。例如,英国学者博伊尔(Alan Boyle)指出,《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被要求促进《公约》的完整性。[15]P38日本学者玉田大也认为,《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约》的完整性。[16]P134
法院过去的判例显示,在《公约》已作出规定的事项上,法院总是维护《公约》制度的完整性,倾向于否定发生冲突的习惯国际法的存在。法院从来没有在任何判例中宣布存在一项与《公约》规定不一致的习惯国际海洋法。在习惯国际法问题上,法院过去的判例承认存在习惯国际法。被法院判例承认的习惯国际法有两类,一类是体现在《公约》条款中的习惯国际法;另一类是《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第一类判例在本文前面已有列举。第二类判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82年突尼斯与利比亚之间的“大陆架案”判决。在该判决中,法院认为,历史性权利或水域制度一个受到习惯国际法调整的事项。由于《公约》没有对历史性权利和水域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公约》外独立受到习惯国际法调整的事项。在上述两类判例中,《公约》本身的条款都没有被习惯国际法“侵蚀”,因此法院的判例明显体现了追求《公约》完整性的司法价值。
五、中国的应对
法院维护《公约》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的政策取向符合中国关于《公约》的立场。2022年9月1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纪念《公约》开放签署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坚定维护《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12月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在第77届联大“海洋和海洋法”议题下发言时指出,“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应完整、准确、善意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本文论及的“毗连区第一案”而言,可发现中国的毗连区制度存在“积极内容”和“消极内容”,对于其中的“消极内容”,需要加以应对。
(一)从本案判决看中国毗连区制度的“积极内容”
经过30年的建设,中国形成了以1992年的《领海及毗连区法》为基础、以2021年的《海警法》、相关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司法解释为辅助的毗连区制度。结合本案判决,中国的毗连区制度中的“积极内容”有两个:第一,毗连区的宽度。中国的《领海及毗连区法》第4条规定,中国的“毗连区为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海域。毗连区的宽度为12海里”,即中国毗连区的“外部界限为一条其每一点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等于24海里的线。”从内容来看,中国的毗连区宽度符合《公约》第33条第2款的规定,也符合本案判决认定的习惯国际法。
第二,毗连区的多数管制目的。《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3条规定,中国有权在毗连区内,为防止和惩处在其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行为行使管制权。2021年《海警法》第28条进一步明确,为预防、制止和惩治在中国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海警机构有权在毗连区行使管制权,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可见,中国对毗连区管制的目的有五个。这五个目的中,除了“安全”外,其他四个都与《公约》第33条第1款的规定一致,也符合本案判决认定的习惯国际法。虽然《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3条和《海警法》第21条用了“入境出境管理”这一措辞,而不是《公约》第33条第1款中的“移民”一词,但一般认为,“移民”的含义要比“入境出境管理”更加丰富,[17]P45因此,使用“入境出境管理”不会与《公约》第33条第1款发生冲突。
(二)从本案判决看中国毗连区制度的“消极内容”
从本案判决看,中国毗连区管制目的中有一个目的与《公约》及本案认定的习惯国际法不一致。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3条和《海警法》第28条均将“安全”列为毗连区管制目的。这是中国海洋法制度遇到的挑战之一,[18]P42是中美关于航行自由的争议焦点之一。[19]P136在美国国务院2022年发布的“海洋界限”第150号报告中,这个问题继续被提出来。因此,至少从《公约》第33条第1款的文本及本案判决认定的习惯国际法来看,存在不一致。
(三)关于“消极内容”的应对
关于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13条和《海警法》第28条中的“安全”目的,中国可暂且不必因为本案判决而立即删除。这是因为:
首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虽然本案判决认定习惯国际法不允许沿海国出于“安全”目的对毗连区进行管制,但正如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的,法院作出这一习惯国际法认定在司法说理方面存在缺陷,其结论是无法令人完全信服的。
其次,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承认,一国的立法是否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院援引了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国际法委员会在对《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12条的评注中说:“有些国际法义务可能仅仅因为一国颁布不符合该国际法义务的法律而遭到违反。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颁布法律就会产生该国的国际责任,因为一国立法机关是该国的机关。在其他情况下,颁布法律行为本身不一定就是违反国际法义务,尤其是如果该国可以通过一种不违反有关国际法义务的方式执行该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违反国际法义务的情形取决于该法律是否、以及如何得到执行。”在本案中,哥伦比亚第1946号总统令之所以被判不符合《公约》第33条第1款体现的习惯国际法,除了第1946号总统令规定的内容与《公约》第33条第1款体现的习惯国际法不一致外,还与哥伦比亚关于法院2012年判决发表的声明、后续发生在海上的事件一起促成两国之间的争端导致尼加拉瓜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了尼加拉瓜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等诸多因素有关。可见,一国扩大毗连区管制目的的立法不一定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还取决于如何解释该事项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适用该事项。
最后,从政策角度说,将“安全”事项纳入毗连区管制目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毗连区问题上的立场之一。早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中国就持这一立场。[20]P4而且,将“安全”纳入毗连区管制目的,也并不只有中国一个。在世界上建立毗连区的90个左右沿海国中,有15个国家将“安全”纳入管制目的,占到六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不小。因此,中国是否仅仅因为本案判决而取消毗连区立法中的“安全”管制目的,需要认真思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毗连区制度中设置“安全”目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上世纪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海上形势,随着中国国防综合实力的提升与海军逐步走向远洋,实际上中美在该问题上的看法会逐步走向一致,中国未来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取消该事项的管制权。[21]P4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在最终取消“安全”管制目的之前,由于中国是《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就潜在地面临《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可能利用《公约》中的强制仲裁机制,对中国毗连区制度中的“安全”管制目的发难的国际法风险。
结 论
国际判例是推动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案在毗连区制度的习惯国际法地位、毗连区的设置与划界、毗连区的管制目的三个方面对毗连区制度首次作出了司法解释,必将成为研究毗连区制度的经典案例,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毗连区第一案”。国际法院在上述三个问题中分别采用了将《公约》中的毗连区条款习惯国际法化、严格落实《公约》中的毗连区条款、以及拒绝承认存在毗连区管制目的与《公约》规定不一致的习惯国际法的手段,显现了法院试图追求《公约》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的司法价值,彰显了法院在毗连区制度问题上积极的司法能动姿态。然而,在司法说理部分,本案判决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完全令人信服。就中国而言,本案判决在给中国的毗连区制度带来“底气”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应警惕外国利用中国毗连区制度中的安全管制目的向中国提起强制仲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受到本案案情的限制,本案判决并未就毗连区制度的其他争议问题作出回应,例如沿海国对毗连区管制的权力性质、[22]P51预防和惩罚措施的对象、[23]P65沿海国对毗连区的刑事管辖权。[24]P105这需要等待将来更多的国际判例检验,而通过国际判例不断澄清规范的内涵,正是国际判例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 这种情形的案件有五个,分别是: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 Nigeria: 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 Judgment of 10 October 2022, para. 285;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Honduras), Judgment of 8 October 2007, para. 261;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3 February 2009, para. 31;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Caribbean Sea and the Pacific Ocean (Costa Rica v. Nicaragua), Judgment of 2 February 2018, para. 90;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Somalia v. Kenya), Judgment of 21 October 2021, para. 33.
② 这种情形的案件有四个,分别是: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Qatar v. Bahrain), Judgment of 16 March 2001, para. 167;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19 November 2012, para. 118; Maritime Dispute (Peru v. Chile), Judgment of 27 January 2014, para. 178; Alleged Violations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Maritime Space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21 April 2022, para. 167.
③ 《公约》第293条规定,如两当事国选择了国际法院作为解决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国际法院“应适用《公约》和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
④ ICJ, Alleged Violations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Maritime Space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of 21 April 2022.
⑤ ITLOS, Case No. 28,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Mauritius and Maldives in the Indian Ocean (Mauritius/Maldive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28 January 2021, para. 203.
⑥ Central American Court of Justice, El Salvador v. Nicaragua, Judgment of 9 March 191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1917, p. 674 at p. 706.
⑦ A. V. Low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ntiguous Zon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2, Issue 1, 1981, p. 138.
⑧ Owners,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Wanderer (Great Britain v. United States), Award of 9 December 1921, RIAA VI, 68, 71.
⑨ 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 for the Prevention of Smuggling of Intoxicating Liquors, 23 January 1924, LNTS 27, 182.
⑩ I’m Alone (Canada v. United States), Award of June 30, 1933 and January 5, 1935, RIAA III, p. 1609-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