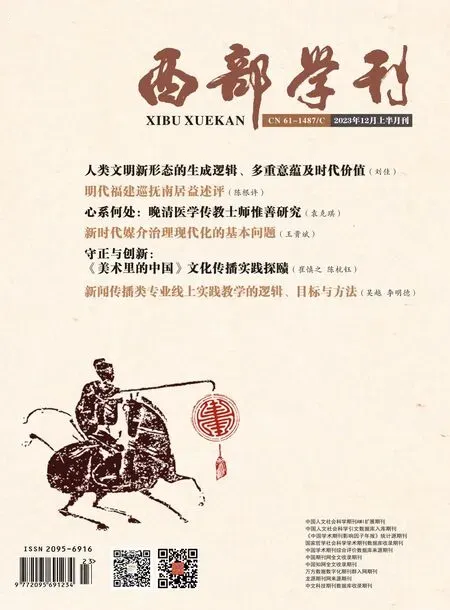论大川周明的思想核心及其实质
——从宗教观到政治思想
2024-01-01张志昂
张志昂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苏州 215009)
大川周明(1886—1957年,以下简称大川),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在法庭上大闹装疯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1957年12月24日死于日本东京。
1925年,为宣传国家改造的主张,大川创立行地社,游说陆军幕僚层。1929年(昭和四年),他担任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参与1931年发生的三月事变、“九一八”事变、十月事变。1932年,因卷入“五·一五事件”被逮捕。大川周明的思想一般被认为是超国家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被解释为在思想上补充超国家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思想的问题一般很少被论及。就大川的思想来看,事态不那么单纯。例如,松本健一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大川归类为右翼。右翼通常把反共产主义作为最大的特征,但大川不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当然,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俄国革命爆发之际,满川龟太郎为拥护列宁等布尔什维克而写的《为何与激进派为敌》一文,大川对此表示赞同。这种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为是在冷静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此为例,松本健一指出,一般被认为是顽固的皇室中心主义者的大川在思想上具有灵活性。
一、大川周明的思想起点
(一)宗教认识
大川进入大学哲学系“绝对不是为了成为学者,而是为了寻求真实的宗教”[1]78,由此可以推测,对大川来说宗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毕业后,他没有固定工作,专门到大学图书馆搞宗教研究,可见这个问题对他是多么迫切。大川在战后有自传《安乐之门》,以及战前发表的《宗教原理讲话》(大正九年)衍生的《宗教论》(生前未发表,收录于全集)等宗教著作。虽然不标榜国家主义,但他在这些方面的立场是和战前是一以贯之的,这说明他的思想不是单纯的时局意识形态,在原理思考的意义上是本质性的。大川的道义国家色彩很强,将道义置于国家中心的根据应该就是他的宗教观。对大川来说,宗教和道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大川在大学以西欧文献为中心研究“真实的”宗教。他认为,西欧哲学家的宗教论,以认为宗教是唯意志的康德、认为宗教是主知识的海莱、认为宗教是主情感的施莱耶马赫这三种立场为代表[1]79。但是,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都不能使他信服。“哲学是学者通过个性的认识,其宗教哲学可以说是哲学家自己的宗教的理性翻译。因此,对于那些有着与哲学家不同宗教经验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宗教论是无法接受的。”[1]80
真正抓住他的心的是印度哲学。这意味着印度对大川来说属于精神共同性的范围之内。大川大学毕业后在图书馆埋头研究印度哲学,对印度宗教“梵我如一”这一视角的重视,使得后来他提出了个人与整体相结合的观点,这种取向在他对印度哲学的着眼方式中已经有所体现。另外,在多样性背后有着共同性乃至普遍性这样的思考方式在他心中继续保持着。
提到大川与宗教的关系,就要提到他加入了松村介石主办的道会。道会是独立于基督教之外的宗教团体,以信神、修德、爱邻、永生为纲领进行传教。最重要的是,以松村介石为契机,大川开始研究日本,并被委托为修改、评论后出版的历代天皇传记的草稿。
这一工作激发了大川对日本历史、日本精神的浓厚兴趣。“我读《古事记》《日本纪》等六国史,其实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然而,在阅读了许多史书之后,我意外地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我花费了比预期多出几倍的时间,总算完成了《列圣传》,作为日本人的自觉变得极其强烈,对一切日本事物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薄伽梵歌中写道:‘设虽劣机,尽自己的本然,做他的本然好;死于自己的本然是善,他的本然是畏。’这条铁律,不仅对个人,对民族也是不可磨灭的真理。于是,我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按照日本的方式思考,按照日本的方式行动。”[1]128被认为标榜皇道主义的《日本精神研究》(昭和二年)和《日本二千六百年史》(昭和十四年)都是这项工作的副产品。
(二)对亚洲的现实认识
大正二年,大川读了亨利·科顿爵士的《新印度》,这是让立志探究宗教的大川打开对现实认识的第一个契机。大川在后来的自传《安乐之门》中提到,因为偶然拿到的这本书,“向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迈进了一生的步伐”,“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现在的印度几乎一无所知。(中略)然而,这本书以朴实无华的笔锋,以不容伪造的事实,鲜明而深刻地把印度的现实呈现在我眼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悲惨,我看到了现实中的印度,它与我脑海中所描绘的印度有着天壤之别,我感到惊讶、悲伤、愤怒。(中略)不仅是印度,在茫茫的亚细亚大陆上,西欧的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也不在少数。”[1]114
从此,大川开始积极研究亚洲统治和殖民地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大川思想参与现实的第一个契机在于对亚洲的认识,而不是对日本的认识。当然,日本日益紧张的状况也是大川思想形成的一大原因。但是,对亚洲现实的认识并不是在与日本的关联上,而是在其本身上,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大川并不是为了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三)对日本的现实认识
大川的超国家主义理念的出现,需要一个现实的契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内外交困,大川认识到需要社会改革,也就是说,大正七年(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正八年(1918年)的“米骚动”,以及这一时期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激化,佃农斗争的爆发,西伯利亚出兵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凌驾于大正民主的风潮之上。特别是“米骚动”带来的冲击更大,可以说是群众发出的悲鸣,如何回应成了考验大川思想的试金石。松本健一指出:“他(大川)将国民生活中‘必要’的革新,转化为自己的国家改造思想。换言之,就是把因米骚动而爆发出的群众生活上的混乱,作为改造思想成立的契机。”[2]大川参加了老壮会(大正七年)、犹存社(大正八年)、行地社(大正十三年)等政治结社的活动。
大川目睹了疲敝的农村现状和国家伦理上的堕落,认识到这种危机状况是由对西欧近代的盲从引起的。要超越这一危机,只能找到超越西欧近代原理的原理。从大川的历史主义的思考方式来看,他将宗教和道德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立场,对由东方或日本的宗教所孕育出来的东方或日本的精神,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当大川进入政治领域,主张根据固有传统进行改革时,即使改革本身是政治性的,他也会解释为是与道德、宗教有密切联系的东西。他的国家论被称为道义的国家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大川周明的宗教理论
大川的宗教理论是他政治理论的基础,说到宗教,大川关心的不是既成的一定的宗教或宗派,而是宗教的本质。“为什么我们要寻求宗教”是大川的起点。“宗教的要求即是我们的生命本身的要求。虽然我们有肉体和精神的要求,但这些要求的总和不过是所设自我的一个方面的要求。只有宗教才是全我的统一要求,是自我本身的解决。(中略)我们要过宗教的生活。”[3]大川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宗教上的教条,而是从信仰根源迸发出的情感。
在大川看来,这种宗教生活所指向的,无非是人的人格生活。不是宗教标定人格生活,而是从人格生活的观点来标定宗教。大川的《宗教论》一开始就以“人格生活的原则”为题目,提出宗教本质论,并非没有道理。
大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理想,而不是自然属性。“人的本质是超越自然的、机械的法则所束缚的自然生活,而经营精神生活即有价值的生活。”[4]243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精神领域得到承认,进而在这个精神领域确立理想,由这个理想来衡量现实生活,精神理想的本质则是“道德精神”。
大川强调伦理道德是源于内心的,他的伦理学说从感情论展开,道德由羞耻、怜悯、敬畏三个感情基础构成,“分别代表我们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和自己地位同等的、比自己地位高的对象,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人性本来具有的感情。”
在中国,这三条原则被称为“天地人”(这个天、地、人对应着敬畏、羞耻、怜悯),大川借用儒家的概念将外界三种对象称之为天地人,而个人精神生活三原则就是个人和天地人的关系,他给这三原则起了新名称:克己、爱人和敬天。克己的原则是克制物欲;爱人的感情基础是怜爱;敬天的感情基础是敬畏,敬畏首先是孩子对父母的敬畏,而由于父母死亡,人们对父母和祖先产生了神的观念。这就产生了宗教的萌芽,“人类最明显地抱有神的观念的,其实是被死亡的神秘所包裹的父母。”[4]213因此,大川说:“宗教最根本的,也是最原始的,毫无疑问是对祖先的崇拜。”[4]213宗教礼仪的存在是为了了解父母的意志,可以说是神人交往的手段,这种祖灵崇拜是日本及亚洲的特征,而“孝”也是敬天最基本的要求。
大川认为东方的宗教观与西方很不一样,他以儒学为例,引用儒家的天命观说明东洋人仅仅是敬畏天,并不会将其变成专门的宗教,古东方的精神生活并不会专门区分宗教和道德。“人的实践生活是宗教、道德、政治的三个方面。在西欧,这三者逐渐分化,每一个都实现了自己的发展,要求规范各自的领域,在东方,没有将这三者分化,而是将人生视为浑然一体,寻求包容这三者的精神生活的整体规范。因此,在东方有表示人生整体规范的语言,而在西方则没有适当对应的语言。”[1]183在西方,它们因其分别的、特殊化的精神和历史原因而很早就分化了,而在东方宗教中三者的特征是停留在浑然一体的状态。
通过考察大川的宗教理论,可以看出,大川使用东方传统思想建立了自己的伦理学说,并将东洋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进行对比,有意强调东方传统思想的特性,并和西方的价值观对立。
三、大川周明的道义国家论
大川认为个人道德促进社会进步,之前提到的“人格生活三原则”外化为家族关系,进而向着更高层次演变。大川在宗教论中以“人格生活原则”为根本,这与国家论中的“国家生活原则”相衔接。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是对天皇制这一宗教进行理论上补充完善的过程。
通过对“人格生活的主体是什么”大川阐明了个人和整体的关系。简单来说,“人格的内面发展到某种程度,相应的社会必然会实现。即家、部族、国家这样层次的社会组织,与内面深化的程度相适应,逐渐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4]45另外,人们思想的基础是祖先世代相传的经验,一种社会遗产,在这个意义上实质方面也要共同生活。
大川总结日本就是由家族、部落、部族而演变成国家,即“许多家族结合而形成部族时,作为各家族共同祖先而意识到的部族神,作为比各家族诸神更高级的神而被崇拜。(中略)接着,当众多部族统一为一个国家时,整个部族的祖先作为国祖成为国民崇拜的对象。但是,在现实的许多国家中,对国祖的宗教关系已经消失,这些国家“不承认作为国家生命本源的国祖,而直接仰视作为全宇宙本源的神为天父”[5],但大川说日本是例外,“只有日本,从建国之初至今,国家的历史进化始终继承而没有中断,而且由于作为国祖(天皇)的直系延续而君临国家,国民对君主即天皇的关系,今天仍然鲜明地体现在宗教上。因此,在祖先的本质上,对天皇的忠与对父母的孝是一样的。(中略)作为子女孝父母,作为国民忠天皇,作为一个人拜天父,这三者都是‘敬天’的具体表现,因此是我们真实的宗教。”日本在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上,与外国有着最大的不同点。在日本,将每一个国民称为“分灵”,这无异于“日本国民是同一生命的特殊表现的意识”[6]46-47。天皇是国民的宗教对象,“国民通过天皇与自己生命的本源相连。”[6]50每一个国民与天皇之间的彻底的连续性被阐明,天皇是从家族的父亲、部落的族长演变为国家的君主,天皇崇拜是日本国民道义精神的根本,于是,大川的宗教论成为天皇中心论强有力的补充。
大川认为这种道义立场也适用于国家论和经济领域。国家是精神上的存在,即国家的本质在于道义主体,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社会。就是说,大川承认人的本质是道义的主体,把这个命题作为绝对正确的东西放在出发点,一切都从这里演绎,所以演绎的东西也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
四、大川周明道义国家论的实质
大川政治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于其道义性。“道义国家”思想属于日本思潮,虽然大川是以儒家思想阐述自己的理念学说,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天皇中心主义,而从思想所展现出的现实来看,道义国家实质就是“天皇中心论”“日本优越论”“东西方对抗论”以及“日本支配亚洲论”。
关于“天皇中心论”,上文已经提到大川认为天皇崇拜是日本国民道义精神的根本,要强调的是,大川以道义国家思想阐明日本文明的原理在于天皇中心主义的“道义”精神,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来源于与日本天皇崇拜的“道义”精神不相容的西方化,因此他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与大正民主运动潮流相对立。
大川认为日本继承了亚洲传统精神,其他亚洲各国则违背了道义国家的原则,导致传统精神逐步丧失,西方的侵略加速了这一过程,而日本不同,在吸收了中华及印度的文明之后,保存了自身大和文明的根基。也正是由于这种根基的存在,日本才有可能打破西方对“文明”的垄断,这是大川“日本优越论”的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大川认为能够带领亚洲走出现状的是日本。“因为日本有着世界独一无二的皇统的延续,从未被异邦所征服的崇高自尊,能延续祖先思想与情感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正是日本能作为‘亚细亚思想’及其文明的真正守护者的保证。甚至说到我等今日之意识实为‘亚细亚意识’之综合。我等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之表现,而日本文明之真意亦存于此。”[7]以日本为核心,站在日本看亚洲,再从亚洲看西方,是大川的视界,亦是他的学术自信。
只是,与其说大川对日本精神的自豪源于其对日本传统的自信,倒不如说他是对西方“强势”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始终支配着大川的研究,在对外关系上,大川认为,世界史就是东西方对抗战争的历史[8]47。西方文明原理不仅有害于日本天皇中心论,也会破坏亚洲传统精神,是不道义的。他极力宣扬世界史上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对立,意在更加强调世界史是由东西方对立、抗争构成的;宣扬战争在形成世界史上的作用和东西方战争历史的必然性,就是为对美英开战打舆论基础。
在以大川为中心,概括了大川思想的政治结社“行地社”的纲领中有一项是“世界道义的统一”。日本被视为这个道义世界的盟主,不能寄希望于西洋的东西。大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经营人格生活,世界应该道义化,从他的立场来看,西方已经脱离了这个本义。与此相对,东方特别是亚洲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一体,亚洲连绵不断地保持着万代不易的东西。这里承认了亚洲保守主义的特点和优点,但这种保守主义同时也带来了停滞的缺点。正因为这种停滞,亚洲在面对西欧时不得不处于劣势。但是,日本是亚洲各国中唯一一个拥有可以与西欧列强相媲美的国力,并且在精神上与亚洲保持同一性的国家,所以日本应该领导亚洲对抗西方,去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但大川所谓的“道义”其实充满虚伪,尤其在与满蒙利益相关的领域几乎完全是以日本视角进行的,目的是为军部的满蒙、大陆侵略政策辩护。他很早就提倡将满洲从中国分离,1928年9月与张学良会谈时,他提出了使日满废除精神国界的主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他批判中日在满洲问题上的争议是因为日本统治者忘却了明治维新以来庄严的东洋政策精神,未能在道德与政策上积极促进日本民族在满蒙的地位造成的,所以双方在满蒙的斗争只能采取最原始的自然法则,“如果日本不能以自然法则的手段取胜,在满的日本人早晚会被赶回日本。”[8]152显然他认为在与日本利益切实相关的国权问题上不适用精神与道德,遵循武力与“丛林法则”,可见“道义”不过是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遮羞布。
五、结语
作为法西斯主义时期大力宣传日本精神的先驱性研究鼓吹者之一的大川,其思想核心是他的宗教观,对于亚洲文明的解释是他对印度宗教理解的基础上的延伸。大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道德精神,国家的核心在于民族精神,而日本的核心就是天皇制的道义精神,而这只是为了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和西方争霸,他的思想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天皇制的强有力补充。他固执地相信现实中的日本正在通过战争实现他在思想上所视同的亚洲解放和日本解放。这种相信,还表现为对日本侵略亚洲的支持。大川明知日军在亚洲的残暴,却顽固地认为是为了亚洲人民。但是很可惜,大东亚战争即使被装上了道义,也不是道义的问题,结果就是他的思想补充了日本侵略主义。他坚持的所谓正义到最后,却成了对历史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