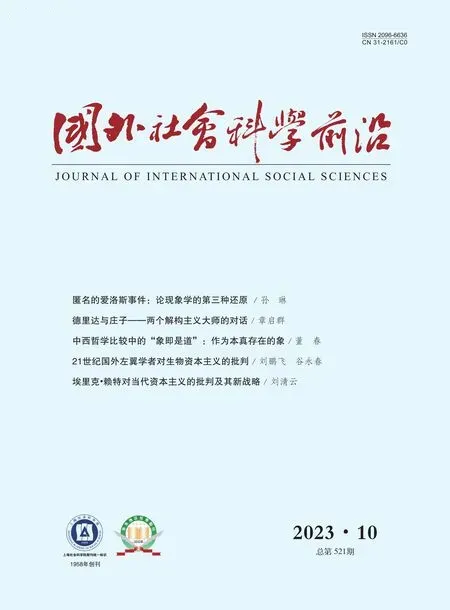中西哲学比较中的“象即是道”:作为本真存在的象*
2024-01-01董春
董 春
在易学哲学的理论体系当中,象乃是其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正如《系辞传》所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以阴阳符号为基础,《周易》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流动与转化建构了一套精密的哲学体系,而这套哲学体系之核心就在于“象”。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性与自主性不断增强,开始在传统易学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而“象思维”正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象思维”乃是王树人在深入考察中西哲学之别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观念。他认为:“‘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乃是区别于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1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7 页。在这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下,王树人对《周易》之象思维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阐述。2如王树人:《〈周易〉的“象思维”及其现代意义》,《周易研究》1998 年第1 期;王树人:《“易之象”论纲》,《开放时代》1998 年第2 期;王树人、喻柏林:《论“象”与“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4 期;王树人:《“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周易研究》2004 年第6 期;王树人、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常青的智慧与艺魂》,作家出版社,1996 年;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等。学界对此问题亦展开了系列的研究和讨论,如何丽野、张祥龙、黄玉顺、康中乾等诸位学者均围绕《周易》象思维的特点、建构方式、思维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3何丽野:《〈周易〉象思维在现代哲学范式中的解读及意义》,《社会科学》2006 年第12 期;康中乾:《论〈易〉的“象”思维认识》,《中国哲学史》2007 年第4 期;张祥龙:《概念化思维与象思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5 期;黄玉顺:《中国哲学的“现象”观念——<周易>“见象”与“观”之考察》,《河北学刊》2017 年第5 期;董春:《易道的显现与感通:以“象”为枢机的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等文皆从不同角度对易学之“象”进行了解读。但与此同时,在“象思维”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王树人提出了象思维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特征,4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学术月刊》2006 年第1 期。但是并未在易学语境中展开详细论述,而对易象的这些特性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完整地展现“象思维”的内涵,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周易》为切入点,通过阐明易象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三个特征,以期能推进“象思维”的研究。
一、唯变所适:易象的非实体性
中西哲学的开端,无不试图为此纷繁复杂的世界寻求一个根源,而对此根源问题的不同回答,则形成了中西哲学发展进路的差异。古希腊之际的哲学诸多流派,聚焦于从变化之中寻求一个永恒的存在物。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对超越现实世界、脱离人类生活的那个纯粹存在(being)的探索和追寻,成为西方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哲学的发端之际,虽亦有“道”“无”“太极”等最高观念,但细而观之,无论是《周易》的阴阳之道还是孔孟的“仁义”之道,均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是息息相关的。故,在中国哲学当中,并不执着于寻求一个超越于万物的、永恒存在的不动之实体。也因此,西方古典哲学逐渐将“存在”视为一个认知对象,并使得存在沦为了存在者,让人走向了存在的对面,从而造成了主客二元之对立。而中国哲学中的道不离器、天人相继之特点,意味着道不是外在于人的一个认知对象,而是一涵摄天人、生生不息的过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哲学的道从来不是游离于人的生活世界之外的纯粹原理。这样,中国哲学之当代发展,不在于如何去解决主客二元之对立,而是在于在天人合一的语境当中,阐述这个道、这个世界如何向人呈现的问题。在易学理论体系当中,这种呈现方式被称为“象”。
《周易》中的“象”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了外在世界的物象,也包括了人头脑中的意象,特别是还包括着《周易》以阴阳符号为基础的卦象。无论是哪一种,象所指称的都是处于我们生活世界当中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在《周易》所有的象当中,以阴阳符号为基础的六十四卦卦象是最能展现其理论特色的内容,故曰:“易者,象也。”(《系辞传》)《周易》的这套卦象体系,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僵化的、静态的模仿,而是有人融入其中的动态的整体,其所展现的是《周易》“唯变所适”的哲学特征。正如《系辞传》所言:“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故这套易象体系的核心,就在于“变”。以“变”为核心的易象体系,其所展现的不再是一个个固定的对象,甚至可以说这种阴阳符号为我们展现的乃是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生存世界,也就是“道”的世界,正如王树人所言:
“象思维”之“象”亦可称为“精神之象”。这种“原象”或“精神”之象,在《周易》中就是卦爻之象,在道家那里就是“无物之象”的道象,在禅宗那里就是回归“心性”的开悟之象。借用海德格尔的“缘在”(Dasein)之义以及“自身缘构发生”(Ereignis)之义来说明这种“象思维”之“象”,那么,这种“象”都不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1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9 页。
“易道”无论多么广大深邃,都有得以生成的始源。这个始源,就是“象”。或者说,“易道”始于象,源于“象”。没有“象”,就没有“易道”。2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8 页。
在这里,“象”成为“道”得以生成的根本,或者说象就是道的“始源”,易道依象而显,因象而成。道与象不再是简单的形上与形下的关系,或者说生与被生的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言:“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则相与为两,即甚亲,而亦如父之于子也;无外,则相与为一,虽有异名,而亦若耳目之于聪明也。父生子而各自有形,父死而子继;不曰道生象,而各自为体,道逝而象留。然则象外无道,欲详道而略象,奚可哉?”3[明]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1 册),岳麓书社,2011 年,1038 页。也就是说,当我们以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来裁剪易道之时,无疑是割裂了象与道的这一本源性关系,象与道则“相与为两”,这实际上是通过人的认知去寻求一个指导规范万物存在根源也就是寻求一个“什么”。这种观点认为,一旦我们对这个“什么”有一清晰的认知,那么一切存在对于我们就没有秘密可言了。故,在近代以来,人们试图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围绕“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有太极”(《系辞传》)等论题展开易学哲学之建构,也从易学中提炼出了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本体”。但是,随着中国哲学主体性的觉醒,人们逐渐发现,中国哲学的体用论与西方哲学的ontology 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中国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不在于存在之整体为何这个问题,而是将其精力放到了如何去处理现实世界(人的世界)与超越世界(天的世界)的关系之中。也因此,中国哲学中的“体”不是一个永恒存在,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流动转化。故,在易学思想当中,无论是“形上之道”还是“太极”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也就是说,在易学思想当中,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终极对象可供我们去思考,一切都处于生成变化当中。就《周易》的六十四卦卦序排列而言,以未济结尾。“未济”有事情尚未完成之意,之所以如此,乃因“物穷而不变,则无不已之理,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之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22 页。故在易学中,道即生生不息,变化不已,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者。以此观之,《周易》所寻求的这个道,“固非由存在问题所引导,但确乎同样以不息不殆之永恒运动为经验上的基本问题线索,且将存有(是)之意摄入运动原理之下。”2丁耘:《道体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44 页。
在《周易》看来,没有比人的生活本身更为本源的东西,故其通过阴阳符号的重叠与变化建构起的这套卦象体系,展现的便是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唯变所适”之过程。也因此,“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近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传》)以此观之,在《周易》中的“象”,不再是简单的对外在事物的模拟,而是“道”得以展开的根源。在易学当中,“道”与“象”的关系,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与现象不同,道并不是在易象背后的一个他者,易象所展现的就是道之全体,我们不需要去追问在易象背后的那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易象就是道。这样,易象就不是空洞的、无意义的抽象符号,也不是那个冷冰冰的最高实体;易象所承载的乃是我们生存世界的最原初之意义,通过易象,这个世界才能真正地为我们所展现。这样,作为依象而显的道,或者说作为道的易象,不再是一个实体化的对象,亦不是一个现成的、静止的死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通过“象”,我们才能进入到易学所建构的生生不息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之中,“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66 页。
故,《周易》六十四卦经由卦象、卦爻辞为我们所建构的象世界,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存在者。“实际上,‘象’和象的思维就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内容一样,‘象’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4何丽野:《中国哲学“象之思”的研究及其意义》,《社会科学》2012 年第12 期。例如,坤卦初六爻曰:“履霜,坚冰至。”这一句话,为我们描述了一幅脚踩着霜,冬天即将到来的情景。但是,《周易》所要告诉我们的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试图让人置身于此情景当中体悟到这种自然现象所要告知我们如何生存的智慧,正如《文言传》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这个“霜”和“坚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感性经验直观,亦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履霜坚冰与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必须要将履霜坚冰之象与个人之生存体悟相结合,方能得出“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 年,第708 页。的经验智慧。故在易学当中,只有当我们身处在具体的情景之中,方能体悟《周易》中“履霜”而“顺致其道”的经验,这不再是一种感性的经验直观,更多的是生命的体悟。这样,《周易》对象的这种阐述就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人们需要将自身的生存经验与此自然现象相结合,去领取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智慧。
以此观之,“象”就不再仅仅是可被观察体悟的对象,而是具有了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又与那种经由概念推演而得来的普遍本质不同,它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而是经由阴阳的交感与变化而展现出的全部的可能性的态势;它也不是悬挂于人之上的形上之物,而是有人参与并融入其中的天然境域,这一境域乃是人与万物在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中不断构成的本源性状态。“象”只有与人在这种共在中,方能将其全部的可能性充分显示出来。
二、见乃谓之象:易象的非对象性
在西方哲学的论域中,实体性与对象性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一个实体是什么,只有从它的对象中去认识,一个实体必须牵涉到的对象,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它自己的明显的本质。”2[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126 页。而易象,或者说作为易道之源的易象,它的非实体性意味着,对于我们而言,象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抽象对象。易象的这种非对象性的特点,是与《周易》的理论特色是息息相关的。作为圣人以卜筮觉世牖民的《周易》,并没有脱离人事而空谈天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论架构决定了在易学理论体系当中,人不再是处于天命流行之外的观察者,而是融入其中的参与者,也因此《系辞传》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观点。这个道,既不是受人崇拜的人格神,也不是那个孤立高悬于生活世界之上的实体,而是与人的生活存在息息相关的生化流行之过程。故方能“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系辞传》),也因此,这个阴阳之道便具有了人生存于其间的当下构成之意。而易道之所以有“仁”“知”不同的展现,其中之关键就在于这个“见”。在易学当中,“见”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这个“见”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看”,当“西方哲学去‘看’世界的时候,人就不知不觉地站到了世界的对面,即人与世界处于分离的状态”。3俞宣孟:《本体论研究•前言》(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1 页。易学中的“见”,是一种可以提升生命境界、展现人生体悟的方式;它是一种对存在的体悟,而非单纯的观看。《系辞传》所讲的“见乃谓之象”之“见”,有着两重含义:既可以读作见(xiàn)乃谓之象,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描述了一个世界向人展现,由隐而显的过程;还可以读作见(jiàn)乃谓之象,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人参与到世界当中,让自身明亮起来的过程。虽然可以从见(xiàn)与见(jiàn)两个角度讲,但是这二者是一个同时发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不是如同外在于人的物体一般去显现,人也不是将世界视为对象去看见,而是人与世界在这个“见”的过程中互相成就——人与世界构成了易道生生不息的一体两面。在易学当中,不存在人的生存经验之外的易道。也因此,虽然“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但是其却“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系辞传》)道并不远离百姓之人伦日用,故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单纯的远离于人的形而上者,其潜藏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故这个“盛德”不是一个现成的单纯依靠遵守某一规定就可以达到的境地,而是在“鼓万物”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德性之智慧。
以此观之,《周易》所强调的象,不再是独立于人的、可被观察的对象,而是一种当下构成的境遇。也因此,它才能成为道之源头。正如《系辞传》所言: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周易》中的象,从其产生之时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对象,而对它的观察和剖析并不会让人对“象”有一个更为透彻的了解。只有当你将象真正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之时,其本性才会逐渐显现,而且你越不将其作为一个对象去思考,才能够越明白如何在“几微”之时运用对象的体悟,也才能真正地体会“失得”“忧虞”“进退”之象的内涵。如果人为地从天地万物中抽象、抽绎出其“几”“神”的话,这是生吞活剥,就将天地万物的“几”“神”弄死了,所抽象出的“几”“神”也就成了僵死的概念而非事物活的本质了。1康中乾:《中国古代的本体论》,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776 页。也因此,通过“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活动去让象真正地处于上手状态(Zuhandenheit)中,这个状态就是王弼所讲的“得意忘象”。故,一方面王弼强调“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另一方面王弼又说“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2[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2009 年,第609 页。这里,王弼在强调象能够展现全部意的同时又主张要忘象,但这个忘象,并不是说舍弃象,而是忘却了“象”的用具向度。海德格尔就认为:“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80 页。真正的“忘象”,是对“象”的用具性的瓦解,而非对“象”本身存在的瓦解。“对‘象’之存在的瓦解会导致人们误以为可以经由人心而直契道体,这种瓦解不是通过让心直契道体而否定‘象’的存在,这样就会使得易学对道的体认陷入对心的重视,成为有心无物的理论。”1董春:《易道的显现与感通:以“象”为枢机的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这会使得易学中最具特色的表意方式被遮蔽。易学所强调的忘象,乃是强调人的存在与这个世界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与天地万物有着一种原本就冥然契合的关系,而忘象则是要回到这种处于前反思状态的、和谐融洽的关系当中。故,处于忘象状态当中,就如同“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庄子》)的庖丁一般,获得了最自然、最本真的存在状态。这样《系辞传》所讲的“观其象”,就意味着不是将象作为一个对象去观察;理解这种“观象”之关键,在于“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一般而言,如果将天地作为一个纯粹客观的对象去观察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有天地变化的过程,而如何将这种天地变化与人事吉凶相联系,才是易之“观象”的关键,这就体现出“易象”的非对象性。
这样,《周易》为我们所展现的“象”,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对象,而是有人存在于其中的生命的体验。易象为我们呈现道体的方式,不能通过认识论去解决,因为认识论的主体——客体的理论框架会遮蔽易象的言说方式。这样看来,卦象为我们展示的也不再是一个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人处于不同的境遇当中所引出的如何生存的智慧。在易学当中,“象”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种种“境遇”。因此,无论是易象还是蕴含在其中的易道,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可被我们观察的“存在者”,对这种象的“观”必须突破概念思维的束缚,回归到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象思维当中,体悟易象的本真。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在易学理论体系当中,人不再是一个观察的主体,而是处于一种与世界的牵挂当中,人在宇宙中不是一个现成的、已经完成的存在者,而是在天人、物我、人己关系的处理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存在。因此,“对于这些人,不应说他们是各自独立的现成的人,而最好用进行时态的‘人之生成’的语言来描述。”2安乐哲、秦凯丽、关欣:《生生论(Zoetology):一种传统思维方式的新名称》,《周易研究》2023 年第1 期。《周易》通过象为我们所展现的,就是这种天人、物我、人己之互相牵引、密不可分的境遇。在易象的世界当中,并没有人与世界的二元对立,人之本真乃是在世间所生存的活生生的人,而世界本质上就是有人生存的世界。二者不存在一方主导另外一方以及一方迁就一方的情况,而是在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共同构成了一个有人参与的世界。在这种相互构成的理论当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一个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共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人与世界最为本源的构成方式。
《大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展现了易学中的象,不是单纯的对这个世界对象的认知,而是展现着人的存在之境域。易象不是要去完整、真实地反映客体的存在,而是指向一种更为本源的主客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境遇。“《易经》中的‘象’作为符号系统便既包含认知—理解之维的意义,也渗入了目的—价值之维的意义。”3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45 页。因此,单纯的认识论或者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是无法理解这套易象体系的,这是因为,易象思维从其产生之初就不再将天地、道器视为一个纯粹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场域。只有身处其中,不再将天地视为外在的对象去观察时,才能更好地融入其中体会到这种天人一体的关系,也才能真正地明白为何君子能将天之运行不息的状态与人之自相不息的精神相关联。在易学的领域当中,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不再是简单的知觉性的了解,而是融入其中,在生命的历程中突破自己与世界的界限,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是其所是的本性当下地显现出来。
以此观之,“象所启示的存在意图是最平凡之道,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存在之道,无论天道人道,并非主观感悟,不是私密境界,而是事关万物终生之生存通理。”1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93 页。故,这套易象体系,不是从认识某个“什么”出发,通过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来解决人生的意义、价值以及信仰等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真正地落实在人的生存境遇当中,通过人的生存来展现这个天人合一之境。因此,我们不能将象作为一个知识性的对象去研究认知,而是要将自身投入到生生不息的阴阳变化流转当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周易》之象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
三、生生不息:易象的非现成性
在《周易》当中,以阴阳符号为基础建构的这套卦象体系,不是一个现成的道理在这里,它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例如,在《周易》的卦爻辞当中,乾卦以“龙”之“潜”“见”“或跃”“飞”“亢”之象告知人们在不同阶段应该如何行为应对的道理。《周易》与其他经典之不同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卦象、卦辞、爻辞描绘的很多并非现实中发生的事,如《春秋》之“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以及《尚书》之“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均依实理、实事来指导人们如何去行为应对。而在《周易》古经当中,虽亦有部分历史故事,但是大部分用以表意的是种种的象。正如来知德所言:“若易则无此事,无此理,惟有此象而已。有象,则大小、远近、精粗,千蹊万径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弥纶天地;无象,则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弥纶?”2[明]来知德:《周易集注•序》,中华书局,2019 年,第9 页。亦如朱熹所言:“《易》如一个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 年,第1647 页。亦如冯友兰所言:“照《易传》的解释,《易经》可以说是一部事物规律的‘代数学’。它认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其卦辞、爻辞可以带入事物的一切规律。”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652 页。“ 代数学讲的是一些公式,公式中没有任何数目字,而任何数目字都可代入其中。”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432 页。而《易》之所以能如同镜子一般,或者说能够作为代数学,就在于易象的非现成性。
易象的非现成性,意味着它不会表现为一种现成的、固化的概念。就人类理性而言,似乎总要落实到一个终极的头上。以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为代表,自柏拉图之后,哲学家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寻求这个“什么”,但经由休谟的普遍怀疑之后,这引发了人们对这种追寻那个终极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活动的反思,也由此产生了康德对认识如何可能的思考,以及强调“直观自明构成”的胡塞尔现象学的诞生。在易学哲学当中,虽然《系辞传》也有关于形上之道、形下之器的区分,但是其对于道——也就是这个终极的理解——与西方哲学不同,它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对象,也不是那个远离于人的高高在上的存在者,而是有人参与其中的、终极不离人的世间境域。故,对易象的理解,就不能再将其拆分为一个个概念进行分析,因而概念式的分析无法揭示出象思维的关键特性——天人合一的终极境域,因为“凭借任何被现成化了的观念绝不足以达到思想与人生的至极”。1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347 页。故,《周易》虽只有六十四卦,但不是六十四个现成的对象,其所描述的不是一个个现成的状态,也不是最终要指向一个终极的存在,这些象最终点示的乃是在不同的境遇当中如何生存的道理。
易象的非现成性展现为一生生不息的过程。《系辞传》曰:“易者,象也。”又曰:“生生之谓易。”这样,易象之核心就在于生生,体现为生生的象所展示的正是人生存于其间的全部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易象所展现的世界乃是人与世界都处于不断生化流行的世界。这一理论的核心,包含着两个方面:首先这个世界是一生生不息的过程,没有一个至高的存在者去生化万物,一切皆从生生而出。这就是说,生生为一切的本源,任何实体化的现成的终极的追寻都会遮蔽此生生的意蕴。其次,这个世界的最终目标也是生生,一切皆为了生。这样,生生既是原因又是目的,是万物之所以生、之所以成之根本。这样,由易象所展现的便是万物之生生不息的过程,这个过程更类似于赫拉克利特的becoming,如同朱熹所言:“易是变易,阴阳无一日不变,无一时不变。”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 年,第1895 页。
易象的非现成性,最终指向的是人的生存。“我们感知的生生世界是人的生生世界,没有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人的生生世界之道也是不存在的。”3林忠军:《〈易传〉“生生”哲学之我见》,《周易研究》2023 年第3 期。《周易》六十四卦为我们所勾勒出的,便是有人生存于其间的生而又生的世界。这种生生的世界所显现出的状态,便是那个主客尚未二分、某种前反思中的一种状态。在这个世界中,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处于圆融无碍的最恰当的状态,它与人的生命体悟是密切相关的,也蕴含了对人生命的最终极的了解。故,《周易》所展现的是我们最本源的生活状态,卦象所描述的便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其所彰显的乃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如何打交道的智慧,故在卦爻辞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利见大人”“利涉大川”等围绕我们生活展开的情景。在易象的理论架构中,当我们与世界相处之时并不会刻意地关注它,但是当我们处于一种不恰当的境遇当中,如否卦所勾勒的天地否塞不通、小人之风盛而君子之德息之时,我们才会注意到君子小人之别,与这个世界的对象性就会凸显出来。人作为主体,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打量和思考,这样我与世界之二分,主客二元的对立才会显现。而一旦“否极泰来”,这种对立就会消解,人又重新与这个世界融而为一。
在这种非现成性的易象境遇中,阴阳之道向人充分地开放,“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实用的溶于一象。”1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611 页。经由易象,人真正融入这个世界当中,以最恰当的姿态而生存,从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整个世界。这意味着,在易学哲学当中,虽然没有西方哲学的本体、逻格斯、理念等哲学观念,但是却达到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未曾达到的那种非现成的构成状态。但是,要真正地做到融入易象当中并非易事,因为在此生生不息的世界当中,人们所要做的,既不是对这个世界进行一个清醒的反思,亦不是进行道德的省察,而是要融入此生活之流当中进行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人总是对他生存的世界充满了关切,注意观察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等自然现象。但与此同时,其更关注的是,这些象对于不同生存境遇中的人的意义,即在不同的时态中如何保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果行育德等道德品质。这样,人生命展开的过程便是此“阴阳之道”的显现过程,这决定了人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他的存在作为最本己的存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既存在着又不能被规定为什么,这就是《周易》为我们描述的“此在”(Dasein)。“此在”不是什么,而只是生存着,故而,我们在对人的考察过程当中,不能追问这个“此在”是什么,而应该追问他如何?《象传》中的“君子以经纶”“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饮食宴乐”等语,意味着此易象所勾勒的便是我们所生存的活生生的世界。这样,易象中的君子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视野下的“主体”,人在这种种的观象过程中成就自身,是一种真正朝向自身的最切己的生存状态,让人自发地选择真正的生存状态。它是以人的生命体验为出发点,将那个超世间而又不离世间的终极融入不断生成的、发生流动的生命过程当中。这样,“观象”的活动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的衍生过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存活动。阴阳之道由此生存活动而向人展现,经“观象玩占”而挺立的“此在”,作为人最原本的存在状态,其存在的意义不需要外界的赋予,其自身便有着积极的意义,一切的意义都由此而发,我们不需要在此之外另寻一个标准,我们在生存着这个经验本身就是自足的。
故,易象体系不是一个现成的、僵化的、静态的系统,而是以人之存在为根本的动态整体。“静态之象只能展示对象的一个角度、一个侧面的僵滞状态,不可能具有无限包容性。相反,只有活生生的动态之象,才能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展示对象的变化与发展,从而具有无限包容性。”2王树人、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作家出版社,1996 年,第79~80 页。易象的这种非现成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和领悟必须在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中,其核心在于展示人如何更好地生活的智慧,一旦将其固化,一切事物的本真就会被遮蔽。故,我们要理解易象就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对象去看,而是要真正地融入到这一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当中。这就意味着,《周易》真正地将易象的“观”或者体悟纳入到了存在论的维度。将易象作为一个非现成的、动态的、生生不息的过程,体现的是人之生命的本真。
四、结 语
在易学哲学的理论框架当中,象即是道,因而我们不能粗暴地以西方哲学的本体与现象去解读《周易》中有关象与道的关系。在易学当中,不存在象外之道,其所具有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决定了它能够直接呈现存在。它克服和超越了西方哲学中一与多、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这种表达方式甚至可以成为海德格尔毕生所向往的那个未经污染的、能将事物存在直接呈现的最高明的语言。故,对这个象,单纯地依靠感觉以及概念思维是无法感受到它,经由易象而获得的那种生命的直观感受既不是一个理智的观念也不违反理性,而是一种清晰明白的终极的境遇。人只有借助易象真正地融入世界当中,才能更好地去观照这个世界,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