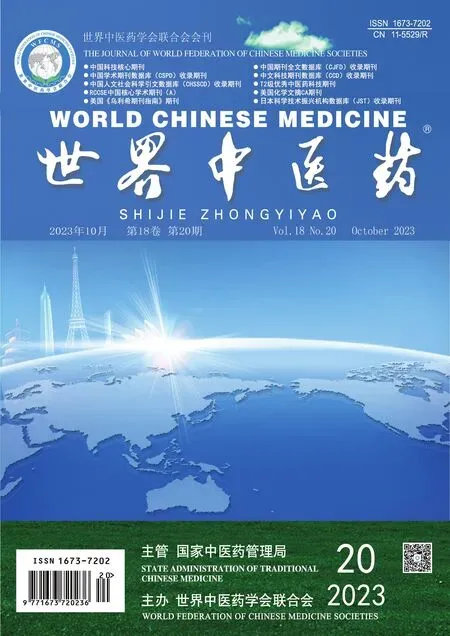基于文献与清代医案的半夏泻心汤证因机辨析
2023-12-30周冉冉罗亚敏李伊然李芊芊陶晓华
周冉冉 罗亚敏 李伊然 李 冉 杨 凤 李芊芊 陶晓华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100053)
半夏泻心汤出自《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1]又见于《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2]原著记述半夏泻心汤证的病因是柴胡汤证误下,主症为心下满而不痛、呕而肠鸣,然病机则未论及。《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3]古往疾病变迁无迹,而每个方证皆有其恒应病机,变中有定,因而病机乃是疏通中医古今临床异病同治的枢纽之一。半夏泻心汤被视作寒热并用的代表方剂,历来医家精研其义,法古博新,辨病求因,析证述机,从理论到临床拓展了其方证研究。
1 半夏泻心汤理论文献辨因机
1.1 半夏泻心证文献辨病因 半夏泻心汤证本自“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六经病解》论述此方是“少阳妄下”变证[4],从六经辨证角度阐释其证由少阳柴胡汤误下所致。《伤寒明理论》认为邪气在表,未应下而强下之,可见心下满而不痛之虚痞证,脱出半夏泻心汤证与少阳病的直接联系[5]。其中,“邪气”可指太阳表邪,《伤寒缵论》云:“泻心汤诸方,皆治中风汗下后,表解里未和之证。”[6]亦或其他外邪,《六因条辨》曰:“伤暑曾经吐泻……宜用半夏泻心汤。”是为外受暑邪[7]。现代有学者持“汗、吐、下”后皆可见半夏泻心汤证[8]。由上可知,经过中医临床不断实践,古今医家对半夏泻心汤证病因体悟日臻完善。见图1。

图1 半夏泻心汤证理论文献之病因
1.2 半夏泻心证文献辨病机
对古今理论文献记载的半夏泻心汤证病机进行梳理,研究解析其内容及关联,将之概括为寒热相兼、升降失常、湿热饮痰、少阴热化与太阴阳明开阖失司5类。见图2。

图2 半夏泻心汤证理论文献之病机
1.2.1 寒热相兼 半夏泻心汤作为寒热并用的经典方剂,历代众多医家对其病机持“寒热相兼”观点,但就寒热具体见解各异。《伤寒海底眼》首倡“寒多热少”[9],《伤寒来苏集》提出“痞因寒热之气互结而成”[10],现代《方剂学》教材以及部分学者与之一致[11]。柯氏旨在强调不足之心阳与外感寒邪交争的动态,交争则寒热必有交锋触碰,而非强调“互结”二字。《订正金匮要略注》将半夏泻心汤证“呕而肠鸣”的病机解释为“下(虚)寒上(实)热,肠虚胃实”,而在《订正伤寒论注》:“虚热益甚之痞。”其中“实热”与“虚热”有互为矛盾之疑[12]。此外,现代学者有将半夏泻心汤证病机认作胃寒肠热、胃热脾寒、胃寒心热等[13]。
1.2.2 升降失常 半夏泻心汤的配伍特点为辛开苦降,成无己言其“中气得和,上下得通,阴阳得位,水升火降”[4]1,恢复阴阳升降,李静等[14]认为半夏、黄连是发挥其效的核心药物。《金匮要略注》指出呕而肠鸣是因“心气逆”“脏腑之经气亦逆”,《南阳药证汇解》与之观点相近,其曰:“以其中虚,胃寒胃土上逆……致心火亦不降而上炎”,表明半夏泻心汤证与气火上逆相关[15-16]。中焦脾胃是全身气机升降的枢纽,尤怡认为“中气为上下之枢,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气结得散,中焦气机升降复常,诸证随之得解[17]。
1.2.3 湿热饮痰 元朝戴原礼最早提出半夏泻心汤证的病机为湿热,其言:“泻心诸方,取治湿热最当”,后世部分医家循此拓研,取效于临床[18]。湿热既定,相兼有别,《伤寒论辨证广注》:“泻湿热不调、虚实相半之痞。”[19]指出半夏泻心汤证以湿热为实,中焦为虚。《伤寒大白》将半夏泻心汤证之痞满呕吐症认作“皆是痰涎作祸”,提出“重治痰涎”之法[20]。《伤寒论后条辨》言其病机是“气即挟饮,未成实秽,故清热涤饮……故复补胃家之虚”[21],即阳郁成热,胃虚挟饮。民国医家朱壸山与程氏观点相似,其著《伤寒论通注》认为半夏泻心汤证“只是水火无形之气结,非血与水凝聚成痰之实结”,两家之论与秦之桢观点相背[22]。
1.2.4 少阴热化 《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少阴太阳从本从标,……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3]。张锡驹与陈修园将“心下满而不痛”之痞证病机归结为“病发于阴,误下之后,感少阴之热化。”少阴以热气为本,热气以少阴为标,故半夏泻心汤证是少阴从本而化所致[23-24]。
1.2.5 开阖枢论 阳主外,三阳经开则泻,阖则纳;阴主里,三阴经开则纳,阖则泻。李明珠和方剑锋[25]认为半夏泻心汤证是因少阳误下,中气则伤,外邪内陷,阳明失阖,太阴失开。足阳明胃腑主受纳水谷,手阳明大肠主传导糟粕,阳明失阖,阳气不得下行内达,胃失和降,故上逆而呕;足太阴脾脏主运化,手太阴肺主宣发,太阴失开,阳虚不运,寒湿困脾,则肠鸣下利。
2 清代医案探半夏泻心汤证病因
医案是现代医者向古代医家取经的重要门径之一,正如周学海所言“宋以后医书,唯医案最好看,不似注释古书之多穿凿也”[26]。清代是中医学发展的繁盛之期,诸家学术思想灵活通变且论著颇丰,其中医案类论著多达三百余部,高于清以前医案书目之和。下文即通过研究清代140余例半夏泻心汤证医案,析证述机,探究此方文献理论与临证医案的内在关联。
其中,医案纳入原则:1)清代医家应用半夏泻心汤的医案与医话;2)医案拟用药物应包含“半夏、黄芩、黄连、干姜、人参”中三味药物,且必须包括“半夏”和“黄连”或“黄芩”两味药物;3)处方中增加的药味数不得多于原方药物味总数,即相似度sim≥0.5;4)排除记载处方为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小柴胡汤与黄连汤等类方的医案。
2.1 致病为因 本文将半夏泻心汤证病因大致分为3种:第一,因于外,致病为因;第二,本于内,素体为质;第三,内外合之,相兼为病。上述在清代医家应用半夏泻心汤的医案皆有呈现。见图3。

图3 清代半夏泻心汤医案之病因
半夏泻心汤医案记载的病因,其中暑邪8次居首,如《眉寿堂方案选存》记载某患外受暑邪而致热邪内结,症见耳聋、自利稀水[27]。《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嗌燥耳聋。[3]手太阴肺经会络于耳,暑热之邪侵犯肺卫,经气不通,故见耳聋;暑多夹湿,暑湿热结,困着脾胃,中焦升降失常,大肠传导失司,则见自利稀水,叶桂以半夏泻心汤去参、草、枣加枳实、芍药治之。此外,原著记载的下法误治4次,汗法误治、受惊各2次,醉酒、劳伤、饮冷、食复、动怒各1次。临床病情复杂多变,通过研究可发现半夏泻心汤证病因除少阳误下之外,暑邪、误汗、受惊等皆可致病,无须拘泥于原著之误下。
2.2 素体之质 体质,是指在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28]。本文清代半夏泻心汤证医案记述的体质皆是后天所得,可分列如下:内虚劳肾、七情多郁、体丰膏粱、阳气不足、疟后为病、阴虚火盛等。七情多郁,是半夏泻心汤证常见的致病体质,《赵文魁医案选》载有“孙氏呕吐月余未止”案,患者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有余化火,肝气横逆脾胃,左升右降失司,胃气上逆,历经月余则又见中阳虚[29]。先生选用半夏降逆止呕,干姜、肉桂、砂仁壳、茯苓补中温阳,黄芩、黄连清肝胃之郁热,乌梅敛阴缓急,苦辛并用,分调升降,呕吐遂愈。图3可见部分患者多种体质合兼,如《龙砂八家医案》“此七情饥饱房室”[30],此内虚劳肾与七情多郁相兼,而《医案集存》“人肥,中阳最薄”[30],则是七情多郁与体丰膏粱并见。笔者发现七情多郁者,医家处方多加枳实,陈俢园认为此药“性宣发而气散”[31],可理气解郁,泄热破结。
3 清代医案探半夏泻心汤证病机
通过研究清代医家应用半夏泻心汤的一百四十余则医案,其内论述的病机体现八纲辨证71例,气血津液辨证48例,脏腑辨证43例,六淫五邪27例,六经辨证16例。见图4。
3.1 八纲辨证 八纲以阴阳为总纲,又分表里、寒热与虚实六纲,《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虽未明八纲辨证,但其内容无出乎此。本文清代半夏泻心汤医案的病机蕴含八纲辨证者占一半,居五类病机之首。
辨病当析阴阳,医案记载的病机常见阳气不足,兼有肝阳上逆、心阳上亢证,或浊阴凝聚与阴液衰于下证。医案内记载半夏泻心汤证的病位在里,唯有《王应霞要诀》“疟痞成臌”案,先生辨其病机“表邪溜入于少阳半表半里经络之间,以致气阻血滞,阴阳混淆于中焦”[32],此案病机表里、虚实与阴阳六纲皆有体现。古今医家对半夏泻心汤病机多持寒热错杂观点,但医案记载的病机则以热为主,寒热错杂次之,兼见少许寒证。《临证指南医案》记载陆某患痢病,症见自利不爽,神识昏乱,叶桂辨病识机为湿热内蕴,中焦痞结,阳气素虚之体[33]。医案记载的病机常为虚实并见,次以为实,少数是虚。《临证指南医案》记载何某患呕吐,症见寒热,胸中格拒,喜暖饮怕凉,叶氏辨其为热邪内结,但患者素体胃阳不足,病机乃是体虚邪实,虚实并见,故以枳实破气祛邪,半夏、人参、姜汁降逆温中,黄芩、川连清热燥湿止呕[33]。由上可见,八纲辨证需得多纲兼合,方可明析为半夏泻心汤之病机。

图4 清代半夏泻心汤医案之病机
3.2 气血津液 气血津液的生成与运行有赖于脏腑的功能活动,又是脏腑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清代半夏泻心汤医案病机蕴含气血津液辨证者占1/3。气病多与气机郁结、气机升降失常及气虚相关,如《疫证治例》记述袁君可染得瘟疫,先后服用表剂、温剂,愈治愈甚,刻下症见“按摩导引不可释手,四肢厥逆冷过肘膝”[34]。朱增籍加文献细思此为痞证,四肢厥逆乃由渗邪盘踞上中,郁遏阳气不达四布所致,上中二焦痞塞不通,以半夏泻心汤二三服而愈。此案,患者染疫屡经误治,病及上、中二焦及四肢,先生但治其中,正如《金匮要略心典》所言:“中气为上下之枢,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津液运行失常、输布与排泄障碍,则化饮酿痰,半夏泻心汤医案与之相关的病机包括饮邪阻气、水饮内结、气逆痰凝、里蕴湿浊等。
3.3 脏腑辨证 脏腑辨证作为中医临床辨证体系之一,多见于杂病的辨治过程中。清代半夏泻心汤医案记载的病机之于脏腑辨证,其病位以肝、脾、胃为主,兼见肺、肾两脏,根据其内容可概括为脏腑述机、生克制化、经络指代脏腑3种,又可互兼合见。《也是山人医案》记载吴氏病吐蛔一症,先生辨病识机为厥阴犯胃[35]。此案“厥阴”实指肝脏,其病机为肝木犯胃,木旺火郁,上热下寒,蛔虫上扰。蛔虫得乌梅之酸则静,得半夏、干姜、川椒之辛则伏,得黄芩、黄连之苦则下,再加芍药敛阴柔肝,全方共奏平肝降逆、清上温下、安蛔止呕之效。再如治胃反病,叶桂辨其病机为“肝阳上逆,肺胃不降”,以旋覆花、代赭降逆平肝,半夏、干姜、人参温中补虚,药简而精[36]。
3.4 六经辨证 六经辨证体系是张机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论基础之上,结合脏腑经络辨证所创。半夏泻心汤出自《伤寒论》,但清代医家进行六经辨证以审度病机的情况并非习见,医案言及少阳、阳明、太阴、厥阴四经,未拘泥于病在少阳半表半里之观点。《静香楼医案·诸郁门》记述某患“寒热往来,色青,颠顶及少腹痛”,尤怡辨其病机为“病从少阳,郁入厥阴,复从厥阴,逆攻阳明”,生动地呈现出由阳入阴转阳的动态传变进程,治以“泄厥阴之实,顾阳明之虚”[37]。此案记录较为简练,病从少阳,往来寒热,郁入厥阴,足厥阴肝色为青,循行所过之颠顶及少腹痛,故泄厥阴之实,防其表里互传,是以顾阳明之虚,处方半夏泻心汤去干姜、大枣加柴胡、陈皮、吴萸、茯苓治之。再如《倚云轩医案医话医论》记载蒲氏外感寒热,频进苦泄之剂,致湿热阻遏阳明,医者选用半夏泻心汤,去参、草,加苏叶、豆豉、赤苓、泽泻,辛开苦降治之[38]。
3.5 六淫“五邪” 六淫之邪与内生“五邪”,皆含括风、寒、湿、燥、火,前者多出暑邪。半夏泻心汤医案论述内容既有六淫之邪,暑邪为主,又见内生“五邪”,湿、火为多。《顾西畴方案》载有伏暑一案,患者张某外感暑邪,次诊症见“蒸热不扬,胸痞呕恶,谷少,面垢舌浊,脉濡细数”[30]。外受六淫之暑邪,暑多夹湿,顾先生认为暑湿内伏至秋,内蕴化热,故蒸热不扬、面垢舌浊等,湿热中阻,气机升降失常,则见胸痞呕恶,故选用半夏泻心汤去甘温之干姜、大枣,加陈皮、茯苓、生姜治之。经过分析,清代医家应用2种、3种和4种辨证方法交互述析半夏泻心汤证病机的医案分别为37、22和6例,单种辨证方法述析其证病机的医案为27例,其中,应用六经辨证法的医案为16例。见图5。综上可见,半夏泻心汤证清代医案病机内容常由多种辨证方法交合而得,同归殊途,圆机活法,皆可取效于临床。

图5 清代半夏泻心汤医案之病机辨证方法
4 总结
通过梳理半夏泻心汤证的病因病机理论文献,研究清代医家对此方的临证应用,认为其病因病机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互有异同。文献记载其病位多在半表半里,而医案则以内、里为主;理论文献记载此方病机主要为寒热相兼、升降失常、湿热饮痰、少阴热化与开阖枢论,清代医案仅论及前三者,但内容更为翔实。具体而言,如理论研究半夏泻心汤病机以寒热相兼多见,而医案记载则以热证为主。古代医案内容从简,并未完全呈现医家思辨的动态诊疗过程,医案内常将2种及以上辨证方法交合并以示病机,每种辨证方法的内部子类亦互兼合见。由上可知,中医临证需将理论与临床结合,多纲辨证以辨析半夏泻心汤证的病机,发挥中医“异病同治”的优势,为中医现代临床的辨证论治提供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