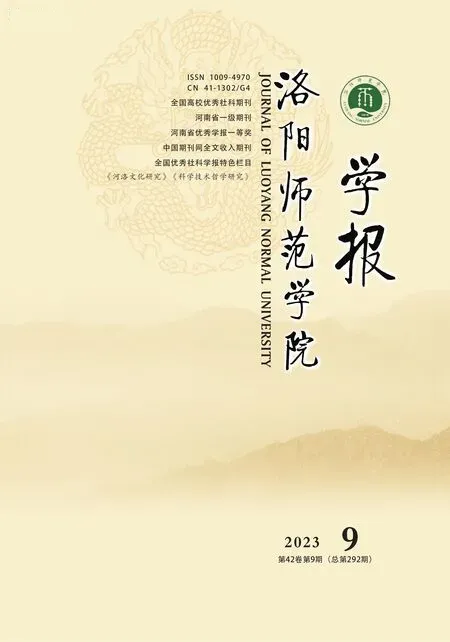《度训》《命训》《常训》的“中”思想
2023-12-29马书琴李春利
马书琴,李春利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中”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字习见于甲骨文,字形多样,学者们对其不同字形所代表的含义多有探讨。唐兰在《殷墟文字记》一书中认为“中字之范围甚广,有上下之中,有左右或四方之中,有大小之中,其义殆难缕举”[1]77。在“中”本义研究上,有“圭表”“旗帜”“建鼓”等主要观点,且与王权政治紧密联系,“中”字的重要性无疑。“中”思想源远流长,经历由具体实物象征到具有抽象性理念的发展过程,经过不断发展和演变,“中”思想被应用到国家政治中,成为古代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中”观念自尧舜以来就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并作为政治理念传授[2]。西周时期重德治,基本指导思想即为“中德”,是“中和”观念与德治融合的体现[3]。“中”在西周初年也运用在司法实践中,穆王时期《吕刑》的出现标志着“中刑”观的形成[4]。战国时期,子思作《中庸》形成“中和”思想,儒道理论的互补,则使中和统一形成中庸之道[5]。同时,战国时期儒家在礼崩乐坏、诸国争霸的时代背景下,以“训”文体为载体,论述治政之策。因此,主要论述为政治民原则和方法的《度训》《命训》《常训》(以下简称三《训》),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儒家关于“中”的思想。笔者拟以《逸周书》一书中《度训》《命训》《常训》三篇为例,探讨“中”思想。
一、“训”体探源
从“训”字本义看,释为教导、教诲。“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6]91《尚书·伊训》记载:“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7]302《尚书·五子之歌》中有“皇祖有训”[7]264“训有之”[7]265。《尚书·洪范》曰:“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7]464所见文献中“训”是君主或臣子的训诫之言。随后史官将训诫言论记录成为“书”的一种,作为教化之用。正如《尚书·说命》篇中傅说让高宗“学于古训,乃有获”[7]374。《尚书·顾命》篇中记载成王丧礼中,“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7]730。《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孙,训的假借。训,指武王遗戒后王的训典[8]604。《诗·大雅·亟民》有“古训是式”[8]675。《左传·文公六年》有“告之训典”[9]599。这些文献中所记的“训”,是指具有训诫意味的“书”,是世传之训典,用以教化统治者。据《尚书》《左传》等文献所载,“训”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动词,表训教、教导之义;二是作为名词,作为训典存在。此种训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以“训”为文体篇章。郭英德曾说:“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这一点从早期文体名称的确定多为动词性词语便不难看出。”[10]29在《尚书》《左传》等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训”既有动词用法,也存在名词用法。现在虽不能完全确定“训”作为名词是何时出现的, 但可从《尚书》是史官记载君主政治言行而成,或可认为“训”在史官记录成书时,已见端倪。先秦文献中确切记有引用《尚书》以“训”为名的篇章,有《左传·鲁襄公四年》记载的以“训”为名的《夏训》一篇,《国语·郑语》中所引以“训”为名的有《训语》一篇[11],共两篇。从所引称谓类属性看,“训”这一文体已经出现萌芽[12]。“训”开始虽未形成一种体裁,但已经作为古时先王遗典,成为教化后世的文献。
对于《尚书》一书而言,“训”已经成为六种文体之一。但以“训”为篇名的只有《伊训》一篇,但观《尚书》全书,《五子之歌》《洪范》《说命》《旅獒》《酒诰》《无逸》等篇,虽未以“训”为名,却是关于政治训诫之辞,具有训诫之意。训诫之辞多见于传世文献,并作为历代宝训,笔者认为应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是周公殷鉴思想的影响。自周代商后,周公鉴于殷亡教训,总结夏殷两代兴亡经验,《尚书·召诰》中记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7]586,以此作为周人治国的典范。史官也时常将殷鉴思想用于记言著书,以垂训后世。二是西周礼制发展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周人对丧礼中临终遗言的重视。《周书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传》。”[13]1124《顾命》篇记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12]721《顾命》即临终之命。周人慎终追远,通过遗训、遗言的方式,对身后之事做出安排和预判[14]。正是由于对训辞的重视,文献中关于“训”的篇章繁多。孔子时“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7]11,将“训”定为《尚书》六体之一。
《尚书》内容是史官所记关于统治者政治言行的记录,因此《尚书》中记载的训文体篇章,侧重于因事而训的政事之“训”。三《训》成书时代,经过现代学者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基本形成春秋说与战国说。从三《训》语言风格、使用的思想概念看应属于战国时期儒家作品[15]。三《训》篇名虽以“训”为名,但其篇章内容与《尚书》“训”的文章多有不同。三《训》文本的生成是当时已有的成熟思想的一个总结,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背景。时人借助“训”文体,作三《训》以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三《训》的训诫者、训诫方法皆有所变化。从三《训》内容观之,其更侧重于说教,是对统治者传授的关于“度”“命”“常”治国之策三方面的劝说之辞。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6]675因此,三《训》则是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变化形成的文本。为何以“训”为名,应是鉴于自西周以来形成的鉴戒传统,时人以“古政”论“今政”以劝政,“行古治今,政之至也”[13]47。因此,三《训》虽均以“训”为篇名,但与《尚书》中所记载的“训”文体的初形不同,可以认为其是带有时人政治思想,用以表达时人论说、为统治者提供治政经验所作。
二、“中”思想在三《训》中的运用
《度训》《命训》《常训》三篇皆开篇就描述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中”,也是三篇的核心思想。《度训》篇言“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13]2,《命训》篇言“广以敬命,则度至以极”[13]23,《常训》篇言“明王于是生政以正之”[13]43。“中”是三《训》所要最终达到的一种政治伦理道德理想主义,通过三《训》内容及“中”在三篇中的含义主要是适中、中正、适度,主要体现的是“中”的辩证法思想。
(一)“中”的思想内涵
“中”在三《训》中虽不多见,但“正”“极”与“中”,以及三《训》中统治者的治政理念均体现“中”观念。“中”既体现在政治法度上的适度,又表现在对民众外在行为的规范。
三《训》皆提及的“慎微”,即慎重对待和处理细小的事情,是明王掌握的一个用中之道。《度训》“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13]6,《命训》有“权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终”[13]40,《常训》篇中提到“慎微以始而敬终,乃不因”[13]49,“权数以多,多难以允,允德以慎”[13]49,要注重小的细节,防微杜渐。“慎微”思想的出现,均是在训教统治者为政之时,认为统治者遇到政事矛盾,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即把握“中”的辩证法思想,要慎始而敬终,达到合宜的状态。这种表示适度、合宜的“中”的精神贯穿在《度训》《命训》《常训》三篇的字里行间。
《度训》之“度”,为“法度”意,即等级与准则。开篇言“序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14]3-4,点明确定等级次序是为政治民的首要准则。《论语·颜渊》篇中记载,齐景公问政孔子时,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7]499维护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使民各居其位,国家才能治理好。明确等级对于民众而言,则和睦,知乐哀,促使人际和谐,最终知仁爱。《度训》中有言“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哀乐以知慧,内外而知人”[13]6。《吕氏春秋·论人篇》曰“哀之以验其人(人,即仁之假字)”[18]77,与《度训》篇中知哀、知慧同义,因此,人也同“仁”[13]8。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是“礼”,同时“礼”也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礼的核心思想为“中”,《度训》中提出“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礼非乐不履”。潘振云:“中者,和之本也。礼教中,乐教和,此制度之大成也。”[13]14孔子于《礼记·仲尼燕居》中有言:“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19]1926礼,是天地之序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19]1478。礼,根据人情特点,有仁义、有理智、有节限和权变,故礼能制中[20]。因此《度训》曰:“力争则力政,力政则无让,无让则无礼。”[13]10“无礼,虽得所好,民乐乎?”[13]10相争则无礼,无礼则不敬,臣民对君主则无敬意,就会违法犯纪。同时,老幼之养、痛疾死丧皆无人可用,均是不明等级所能引起的后果。明王如何做到礼仪法度不被破坏,即如何维护礼制。《度训》中提到“人众,赏多罚少,政之美也;罚多赏少,政之恶也。罚多则困,赏多则乏”[13]15,赏罚得当,依中道,则礼行。同时,三《训》从统治者和民众角度,提出二者自身均要明德丑,礼法才能达到中正。孔子于《论语·子路》中有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7]524只要统治者能自身修德,礼、义、信皆备,民自然敬君、事上、和顺,这样社会和谐,君主就会达到“中”道治国目的。《常训》中也记载“明王自血气之习以明之丑”[13]45,强调君主首先要自身修德,才可对民众施行教化。因此,《常训》篇言:“常则生丑,丑命生德。”[13]42“以习为常,以常为慎,民若生于中。”[13]43《命训》篇中也提到六条“度至于极”,即“广以敬命”[13]22“惩而悔过(居德)”[13]22“惩而悔过[13]23”“有丑而竞行不丑”[13]24“劝之以忠”[13]24“恐而承教”[14]25,关键在依中而行。《命训》《常训》两篇均认为民自身要知丑(耻)、居德,从外在行为上遵守礼法。
(二)“中”的方法论要求
三《训》篇作者在教导统治者为政治民之法时,以论述“过”或“不及”两种极端导致的后果,训教君主行政、施教化时要有“度”。儒家认为“中”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尺度,在面对矛盾时,要执其两端,不偏不倚,正如《度训》篇记载:“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确立标准,掌握度才能保证损益平衡。但并不是说完全的均衡,而是有所偏向的动态的平衡。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的作用在于使小大、轻重、本末处于适中位置。但人皆有好恶,好恶,既可是人的生理本性,“生,好物也;死,恶物也”[9]1622;也可为情,“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9]1622。又有“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13]8。乐大于喜,哀大于忧,六情因好恶所发。但好恶之情过度,就会相争、相离,致民不安,礼不行。因此民要克制好恶,《中庸》记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9]1989情感未发为中,释放情感要符合度,遵循适度原则。
《命训》篇也提到“六极”,即六种过度,“极命”“极福”“极祸”“极丑”“极赏”“极罚”。这六种情况的出现,使民不信人道、不畏天道,最终致政事不行,也是政事危殆的表现。故统治者昭明号令:“大命世罚,小命罚身。”[13]32同时《命训》也教导统治者理政时谨防过犹不及,“哀至则匮,乐满则荒,礼无时则不贵,艺淫则害于才,政成则不长,事震则寡功”[13]38。且《命训》篇也提及“均一则不和”,意思是过于均衡没有分次,也会不和。《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7]545,《国语·郑语》也有相似记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1]470,即要有“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中”不是完全的均等,而是要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正如《常训》所言:“顽贪以凝,疑意以两。平两以参,参伍以权。”(两,表矛盾之意。)[13]48唐大沛言:“中无定体,参之伍之,必权而得中,非执一定之中也。”[13]48也就是说处理矛盾时,要全面考虑,选择最佳效果,“中”并非片面性,而是适度、协调。《度训》篇记载,“赏多罚少,政之美也”[13]15,是为善政。《命训》篇也有“赏莫大于信义”[13]33,“罚莫大于贪诈”[13]33。所以赏罚标准要以“中”为准则,正如《礼记·中庸》所载“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3]1992,无过也无不及,但不是完全平均,而是实现多元性“统一”。
三、结语
三《训》体现的“训”文体,呈现出三《训》作者对统治者治国之策的劝说之辞的特征,明显不同于《尚书》《左传》中所载的因事而训内容,及臣子或君主借先祖之言训诫在任君主或后继君主体例。三《训》作者提出自己的治世之策,并借用“训”文体证明是古代先王之言。“训”文体也正是在不断地以古政释新政的过程中,其内涵产生变化。同时,在对三《训》内容的分析过程中,发现深刻体现儒家中庸思想。先秦儒家思想存在一种否定过多也否定过少的倾向,即否定极端现象。政治需要统治者政令实现,也需要礼与法作为辅助,但也需要配合伦理教化的实行而实现。儒家借用“训”文体,为统治者提供以“中”为政治原则的为政之法。三《训》在法度、天命、常性中的“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使统治者、礼法与教化之间达到一种合宜状态,深刻体现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通过对三《训》“中”思想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训”原为臣对君或君对下任统治者的具有训教性质的言辞,自《尚书》成书时起,“训”正式成为政治性文体之一。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训”文体由原本的政事之“训”变为说教之“训”。
第二,三《训》成书时代虽还有争论,但从三《训》文本内容看,其是儒家学者关于统治者政治之策的劝说之辞。
第三,三《训》的“中”主要表示为“适度”“适中”之意,不仅是指政治措施上的适度,也指民众外在行为上的适度。
第四,三《训》对统治者的劝政之辞,深刻体现儒家的中庸之道。无论是政治准则还是道德修养,都要坚持“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