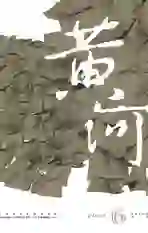吃了酸枣攒下核
2023-12-28王海英
王海英
有一天在街上溜达,碰见路旁有一老妇人叫卖“酸枣!酸枣!”哈,酸枣,我心中一喜,赶紧过去问怎么卖,妇人便从身边拿出叠好的锥形纸袋子,说大袋5块钱,小袋3块钱。那酸枣长得真俊啊,大而圆红而亮,玛瑙珠子一样在我眼前晃动,这么好的酸枣,我毫不犹豫买了两大袋。兴冲冲地把酸枣拿回家,吃了几颗,品质确实不错,酸酸甜甜的,家里人尝了尝也都觉得不错。但先生说怕倒牙,不能多吃,孩子们说酸枣肉太少,吐核麻烦,偶尔吃一点。其实我也容易牙酸,每次只能吃几颗,那些酸枣便在家里存在了好久。
我看着又大又圆的酸枣,不禁有点悻悻然,要是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好的酸枣那得有多开心啊,娃们怎么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又不会倒牙,为啥不喜欢吃?转念一想,现在的娃各种零食数不胜数,美味食品比比皆是,酸枣算什么?充其量就是尝个稀罕,再说了他们又不知道酸枣的前世今生,跟酸枣没有过缘来缘聚的亲密关系,甚至连酸枣怎么长出来的都不知道,凭啥要喜欢这种毫不起眼的小玩意儿?
而酸枣于我们的童年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那时候可没有卖酸枣的,即便有,也没钱买,我们的酸枣都是自己一颗一颗从树上摘下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享用酸枣时必须要吃了酸枣攒下核,那核在之后会派上大用场。
酸枣是野生灌木,那时候我们把春夏秋长叶子时的酸枣树叫作“酸枣树”,到冬天树上叶子落尽了就叫它圪针,可想而知,要摘取树上的果子,需要冒被扎手的危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只要能结出可以吃的果实,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会有不少人惦记,酸枣就是这样。
摘酸枣,我们也叫打酸枣,不过,在我们平川,打酸枣是不可能真正“打”的,其实就是摘。秋天里,每到星期天,女同学们就会约好了结伴儿去挖猪草或者割羊草,顺带着打酸枣。挖野菜、割野草是主业,打酸枣是副业,只能捎带。
作为家庭成员,即便只是十来岁的娃娃,我们当时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家庭任务的,那就是给猪、羊弄吃的。养猪、养羊是家里最大的副业,这些家畜长成了或增加收入或补贴肚子,反正都是普通老百姓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猪、羊肉虽然好吃,可它们都是长嘴的生命,每天一睁眼就需要吃食儿,粮食那么金贵,连人都得节省着吃,牲畜自然不能和人抢食了,所以到了土地上能生长植物的時节,娃娃们就会被派出去觅草,从春到夏再到秋,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会挎了箩筐去田野上薅草。
那时候生产队也养羊,和社员们的羊一起组成一群,指派一个羊倌放羊。每年开春以后庄稼长起来时羊倌会赶着羊群上山,找一个有草坡的小山村住下来,每天把羊们赶上山坡吃草,山坡上不种庄稼,羊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咀嚼时光。上山的羊群到秋收以后天冷了才返回村里,回来以后先给生产队踩粪,就是白天在收割过的田地里觅食,晚上屯在村边让它们拉屎,拉一层屎垫一层土,沤肥。踩完粪羊们才能上圈,也就是晚上可以回主人家自己的圈。因此,羊不怎么费吃食。猪就不一样了,每天就在猪圈里,吃了睡睡了吃,哪顿喂食迟了便会用嘴拱猪圈门还不停地嚎叫。即便是不怎么能上膘的野草野菜,总还是能让它安静地生活,所以,我们便要日复一日地帮猪们觅食。
秋天的草比较多,不用太费劲就能装满箩筐,做完了正事儿,就可以打酸枣了。初秋时候,酸枣熟得并不多,零零星星有红了的、半红了的,后来随着季节的深度熟得慢慢多起来。每次我们必须先观察好下手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绕开圪针,扯开缠在酸枣树上的野草藤蔓,有时候还得躲开树上的柴蜂窝,果子又稠又大又红的枝子上经常会隐蔽着一个硕大的蜂窝。柴蜂不比蜜蜂和马蜂,蛰了人很疼,且疼的时间会持续很久,所以看见了就必须躲开,要是蛰到胳膊上和手上,可以自己赶快吸吮出毒液,然后抹上醋泥,或者用童子尿和了泥抹上,消肿止痛。万一被蛰到脸上、眼睛上了,那就很麻烦,要肿好几天。要是没有意外,我们便一颗一颗把红了的酸枣摘下来揣进衣袋里,能把两个口袋放满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听山区的人说他们是用棍子打酸枣,像打枣一样,然后到山崖下去捡,我们听了羡慕得直咂嘴,看人家多奢侈,我们所谓的打酸枣可是一颗一颗论的。
我们村没有山坡、丘陵地,所以能让酸枣树生长的地方并不多。虽然不多,但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地上,还是有一些酸枣的身影的,它们毫不起眼地兀自生长着,如一些久远的符号,烙印在泥土上,承接着年复一年春夏秋冬的轮回,也为童年的我们营造了不少野趣和美好的记忆。村里土地金贵,地埂都很细小,偶尔有高低落差大的两块田地之间会有一条大地埂,也能长一些酸枣树,但多数酸枣树长在老坟场里,仿佛在守护那些或新或旧大大小小的坟头,大人们也说不清这些酸枣树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似乎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许多个春秋,不管是风调雨顺还是旱涝不均,每年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休整,既年复一年地满足着村里孩子的小小心愿,也给这单调的原野增添了一些风景。
我们王家的坟叫槐树坟,原来长着一棵大槐树,后来槐树被锯掉盖了学校,坟场里除了坟头就只剩下这些酸枣树,它们长在坟场西面。每年端午节时跟着母亲去上坟,正赶上酸枣树开花,那些细小的淡绿色花儿,也能吸引来飞舞嬉戏的蜂蝶。王家坟的酸枣是那种圆溜溜的小颗粒,口感甜但肉薄。离王家坟不远的胡家坟酸枣树最多,长长一排,酸枣是椭圆形的,也不大,有点酸。品种最好的是圈墙坟的酸枣,粒儿大,肉厚且甜。圈墙坟离村里有点远,应该是许多年前村里富人家的坟,很大一片,还圈了围墙,但后来可能是人家衰落了,后人不在了,村里人一代一代下来,慢慢也就说不出坟的主家了,因为圈了墙,就叫圈墙坟。我们去打酸枣的时候,坟场周围的墙已残破不堪、所剩无几,坟头上都长满了草,有的坟头已被风雨侵蚀得几近平坦,但酸枣树却因为无人干扰,无忧无虑地欢乐滋生着,酸枣又大又圆很是喜人。小时候无知,对坟墓无所敬畏,经常一群小女生叽叽喳喳穿梭在坟墓间,评价着酸枣的好赖,甚至还嘻嘻哈哈嬉笑打闹,有时有的墓穴被雨水冲塌了,我们还要探头探脑地过去查看一番,从来没有想过会不会惊扰先人,也许睡在那里的前辈们不会计较小娃娃的无礼,亦或有时他们也会感到沉闷,正好有童言童语可以添些童趣。
酸枣打回家以后,晾在小笸箩里面,晾到半干的时候收在大肚子瓦罐里,瓦罐雖不算大,但要装满也很费劲。整个秋天,我们就那样一点一点一把一把攒着,慢慢让瓦罐的肚子充实起来。等到西北风把酸枣树上的叶子和果实都扫净以后,母亲便从父亲的酒瓶里倒一小盅烧酒,把酒盅放在瓦罐里的酸枣上面,再把瓦罐封严实。
终于到了能吃酸枣的时候,那时候瓦罐里的酒盅早已没有了一滴烧酒,烧酒被完全挥发吸收掉了,而酸枣红亮亮的,飘着丝丝缕缕的酒香。每天我们上学时抓两把酸枣揣在衣服口袋里,有时候还要揣一把咸菜丝。时值隆冬,天寒日短,村里改了作息时间,一日两餐了,这些酸枣和咸菜就是我们下午三点放学之前的课间零食。
前面说过,我们吃酸枣是不能丢掉核的,必须是吃了酸枣攒下核,所以吃酸枣也要格外仔细。其实酸枣上那一层薄薄的果肉也就是能给口腔和舌头添一些味道,但吃的过程却十分美妙,一颗酸枣在嘴里停留好长一段时间,有时是好几颗同时进到嘴里,然后慢慢啃食、慢慢吮吸,让那些酸酸甜甜的味道慢慢钻进喉咙,咽进肚子。而那些要攒下的酸枣核,从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光滑、干净,小巧玲珑,被我们认真地装进另一个空口袋里,放学以后统一收进家里的容器晾晒。
酸枣核也不是我们最终要的东西,我们要的是核里面的仁儿,那仁儿我们村里保健站收购,1两3块钱。从核里面取仁儿,既不像打酸枣那样快乐、充满期待,也不像吃酸枣那样满足、尽情享受,那是一种充满挑战的活儿,挑战人的耐心,挑战手上的巧劲儿。砸酸枣核时左手捏着核儿右手拿一个小小的铁锤子,关键是要砸开壳儿,还不能损坏了里面的仁儿,要把仁儿完完整整地取出来。酸枣仁儿千呼万唤终于和我们见面了,那些棕色的小精灵安静地躺在那里,犹如初生的小宝宝,懵懂而不知所措。整个冬天,瓦罐里的酸枣在一天天减少,这些小宝宝们在一天天增加。等到所有的酸枣仁儿都收集起来了,我们便可以兴高采烈地拿去保健站卖。有时候还同时拿着晒干了的枸杞,那也是我们一粒一粒摘下来的,当时枸杞收购价好像是1斤6块钱。村外有几丛野生枸杞,一丛长在干渠的渠堰外侧,一丛长在古堡墙上,还有几丛生长在地埂上。除了这两样,保健站还收购甜根苗(甘草),甜根苗是从地里刨出来的,一般是男娃们弄了去卖。
我们每年重复着这样的操作,总能去保健站换一些小钱,买一块头巾,或者买一双鞋,有时也能扯一块花布,来年过六一时做一件花衫子穿。有一年,我的酸枣仁和枸杞总共卖下6块多钱,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让我妥妥地做了一身新衣裳。当时一件花罩衫需要6尺5寸布,1尺花市布4毛2分钱,1尺花线呢布4毛6分钱,做一条裤子需要6尺布,我选了花线呢做上衣,蓝线呢做裤子。一身崭新的衣服,而且是用自己劳动所得买的,过大年穿在身上别提有多自豪多高兴了。那个正月,走在村子的街巷里,总感觉有人在欣赏自己的衣服,于是满满的快乐便在小小的胸膛间激荡。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回望当时的自己,我仍能感觉到那种喜悦和满足。
每当看见那些买来的酸枣,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想起家乡的时候,一些美好便毫不吝啬地覆盖着我童年的记忆,那里的阳光刚刚好,不厚不薄地照在身上,那里的炊烟刚刚好,不多不少地飘在脑海,那里的乡音刚刚好,不软不硬地钻进心里。那个普通的晋北村庄,是我生命最初的落脚地,我经常想着,自己需要用一辈子的时光来偿还那里给我的第一缕曙光。
只是,当我想起那些酸枣树的时候,它们早已随着老坟场消失在了家乡的原野上。土地承包以后,人们为了能多种庄稼多打粮食,平了不少老坟,酸枣树自然不会留下。回了村偶尔在田野上走走,满地的玉米映衬着浩荡长空,也寂静也灿烂,也冷清也温暖,四周飘荡着深沉的简洁和卑微的自足。一些熟悉又陌生的场景从眼前闪过,我认出了那是我们的酸枣树曾经生长的地方,恍惚间它们还在各自的位置上优雅着、端庄着,静静地等候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女生来和它们一起收获快乐。
责任编辑: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