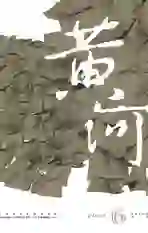在水之上
2023-12-28景平
景平
夜光里的城市
这个城市,终于拥有了晴云朗月的夜空。
云熙熙攘攘铺在湛蓝里,月藏在云上,不时从云缝里跳出来,尖叫一声,又倏然隐去。月隐藏的时候,掩不住光华,光从云边上溢出来,云被月照得朦朦胧胧,云与月,变成了天上的灯笼。似乎天上什么人,在打着荧光的灯笼行走。
突然,我看见一串光斑打在许多云上,然后迅忽离去;迅忽打来,又迅忽离去。我惊异,哪来这么强烈的白光,把白云都打得忽忽闪闪?月亮吗?星星吗?然星与月都没有跳动的光芒。
稍瞬,循着光斑,我看到一道穿透夜空的光柱,打在云端,把云打得光斑点点光影闪闪。循着光斑、光影、光柱,我终于发现,这打上云天的光柱,扫射着,回旋着,交织着,它竟是从汾河直射而起的。
我急急走向汾河公园的夜光水岸。
走近夜光里的汾河,就被一种天籁淹没。明明暗暗的灌丛和树林间,鸟扑棱棱飞动,激起它们唧唧喳喳熙熙闹闹的鼓噪;幽幽亮亮的芦苇和水草深处,蛙拉开嗓子叫嚣,爆出远远近近咕咕呱呱的蛙鸣。城市的喧闹远了,自然的聲音袭来。天光里,褐黄的胖乎乎的大鸟飞过,砸下嘎嘎嘎的声音,砸在半空,砸在那些细密琐碎的鸟鸣和蛙声上,成为穿透在夜空里的具有磁性质地的声音。我奇怪了,蛙声是属于夜的,但这夜何以密集了如此蓬勃的鸟声呢?
也许,鸟被夜光照得找不到了黑夜?或者,鸟们也在夜光里寻找未有过的欢悦。人们创造夜光世界的时候,有谁知道,自然的精灵们也融入这夜光的世界?
这时候,我就在汾河的水岸上看到了那些射向天空的长长的光柱。汾河的水岸已经是华彩的水岸。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紫的灯带,分布在东西两岸,由北向南窜过去,又由南向北窜过来;那些缀在灯带间的月亮一样的射灯,旋转着,照射着,光柱在天空中交织着,扫射着。亮亮的光斑,就打在高高的云上,似乎和月亮比光辉,又似乎和月亮追云翳。天上一个月亮,地上多个月亮。欣慰的大概只有夜光里的云了,竟然被天上的月亮和地下的月亮纵情簇拥。
我没有想到,人们创造的水岸射灯,居然打到了荧亮的白云之上,而且,于无霾的晴丽里,把城市的夜空打扮得光怪迷离,演绎着一个现代光影的神话。
于是在长长的汾河水岸,我看到一个水上水下的世界。那里,夜光在汾河水岸升起,在城市地面铺开,在楼群空间矗立,空中有带灯的风筝飘移,天上有闪烁的飞机划过,云和月与射灯在天幕上演着游戏,霓虹与彩灯肆意炫耀着,直直延伸到近近的深邃和远远的幽冥里去。这时,水里就有了一个光影世界。水岸游走的灯带,地面铺开的灯河,岸边矗立的霓虹,空中带灯的风筝,天上闪烁的飞机,都在水里构筑了一个辉煌宫殿。水上水下,似是神秘的N维空间。
也许是太像世外造物了,也许是太像仙境幻境了,似乎,是天上掉下来了一角,又似乎,是整个天宫搬到了人间,不经意间,就给人玄奥的感觉,也给了孩童玄妙的想象。
之前,我曾在我10楼的凉台,看汾河夜光里的城市。我对俩外孙说,看看,黑夜的城市像什么?可可说,城市的夜空就像黑色的画,画上洒满点点的光,城市点着数不清的灯笼。乐乐说,城市的楼房就像黑夜的星星,我们就住在星星里,我们住在星星里面数星星。我总是惊异于孩子的想象。孩子人之初的画笔,在纯白的纸或纯黑的纸上,画出自己的发现。那是想象的自然空间和城市空间,也是现实的自然空间和城市空间。
这光怪的现代自然空间和神秘的现代城市空间,使我想起30年前的城市夜空,和我写作的一篇散文《城市的夜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夜空呢?我曾说,是像坟墓一样的夜空。
那时,我这样说,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的夜空早已着魔:它一边把城市点燃把城市照亮,一边却又酝酿光幔把星空遮没;它一边燃烧着黑色的太阳石把城市烘得热热烈烈,一边却又蒸腾着黑色烟尘把城市熏得浑浑沌沌。现代工业的魔力,成就了城市的夜世界,也污染了城市的星空。现代文明之光把城市点得亮亮堂堂却无法把城市之顶的烟雾澄得清清净净,现代人创造了光世界烟世界却无法把世界从光与烟的雾中解脱出来,我们,还能唤回纯净的美丽么?
应该说,30年过去,这纯净这美丽,回来了。
就像汾河水岸构筑的夜光世界:水上岸上是一个世界,一个透明的、霓虹的、现代城市的天空世界;水下岸下又是一个世界,一个幽亮的、幻影的、现代城市的水域世界。两个世界融为一个世界,成为这个城市重新归来的真实世界。
晴空,朗月,白云,星斗,是真实的,汾河的射灯打在云端上,是灯光伸长了向天的射程,也是云天辽阔了清洁的空间;看得见八千里路云和月,看得见月亮与云捉迷藏,看得见星斗重新挂在天空上,一切,具有了天大的真实。
碧波,芦苇,鸟鸣,蛙鼓,是真实的,城市的霓虹倒影在汾河,是汾河幻化的城市形象,也是城市虚构的现代生动;然汾河千里清水复流是真实的,汾河碧波流向黄河是真实的,汾河重回大河风光是真实的,一切,具有了水样的真实。
如此,不就还给了你一个彩云追月的夜空么?
玉门河叙事
玉门河是从太原西山的玉门沟里流出来的,也是从城市楼群的沟壑流里出来的。河里流着沉云落月的水,天空流着滚雪卷浪的云,一条玉门河,就这样晴云碧水地流进汾河。
我居住的地方,就是玉门河与汾河交汇的夹角。
这地方,看得见汾河之水天上来,一川清波走长云,也看得见玉门远上白云间,碧水一线下蓝天。如此,即使玉门河不从玉门沟流出,也称得上这冰清玉洁的名字了。
玉门河,流淌的就应该是这琼浆玉液般的流水。
不过,曾经的玉门河可不是这样。
曾经的玉门河,河里流的是黑的脏的污染的水,而且,是不羞不臊地流进汾河。
那时,春天,青绿的河滩流着的是黑色的水;夏天,绿的草遮掩着黑的水,空气里荡起熏人的臭;秋天,河岸的树冠金亮起来了,黑色的水和熏人的臭,却给河岸金色的树涂上一种蒙羞的色气;冬天的时候,雪覆盖了黄草的河滩,却覆盖不了流泻的污水。
城市走过四季,玉门河却只流着一种颜色———黑色。
这不应是一条河的颜色,也不应是这个地方的颜色。
这个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所在,理当是绿色的。楼虽不是绿的,但楼里蕴酿的决策却是绿的。
这里的绿,要说,也不负这个颜色。树是绿的,草是绿的,这绿的决策,与头顶的蓝天白云有关,与地上的河流湖泊有关,当然与楼外的这条玉门河,也应该有关。但那时,眼皮底下这条河,却与绿和绿的决策相悖。于是成为许多人的痛:心痛,隐痛,久痛。
多少年前,这座楼立在这里的时候,这里还是城中村。那时,河里就流着黑水了。不仅北面的玉门河流着黑水,西面的城村渠也流着黑水,东面的汾河公园暗涵也流着污水。那时候,盖起这座银灰色楼的局长,静静地指挥着城乡关停取缔土小企业,静静地把楼内楼外检点得干干净净。这个人,总是检视着厕所,说,一个地方,厕所干净了,就没有不干净的地方了。
几年后,这楼换了主角,局长的交椅换成厅长的交椅,这时候,城市空气质量成为全国倒数第一。这个人,声言要人知道环保的大門朝哪开,发誓让城市摘掉黑帽子戴上绿帽子。后来也真的摘掉黑帽子了,而且西边城村渠的黑水,也渐渐消灭了。不过黑水的消灭是城市城中村改造的结果:一座城中村变成了一群楼房。厅长铁青的脸,欣欣然露出了骄色。
又几年,楼的主角再次易人,这个人,首开城乡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先河,抗霾之战打得异常激烈,“山西蓝”刷满天空,给“北方蓝”送上了清风。但中国南方北方都在追云,北方的蓝毕竟比不过南方的蓝。费了多大劲,拿了多少方案,空气质量还是被甩回全国倒数第一的位置,水也破例第一次排了个全国污染第一。空气和水,都成了老末。
如此,眼皮底下这条黑河脏河,又岂能够改善?
一晃这楼又换了俩主角,上来就扛了两顶污染黑帽。他们都发誓要摘掉全国污染最重的黑帽。但一位身手方开,铁拳方出,即被委以重任,到那个抱回空气污染全国第一的城市当了市长。一位继任,受命于危难,更敢于铁腕动“刀”,说约谈市长就约谈市长,说拿下干部就拿下干部,90天竖起71个监测水站,人说,这回眼皮底下的黑水,该流到头了。
然而眼皮底下的河,黑水该流还流,脏水该臭还臭。
黑水并没给自动吓跑,而且白天黑水不流,空气是臭的,黑夜黑水流出,空气更臭。夹在这个角落里的人们,看惯了河里的黑闻惯了空气的臭,没有人吭气,或窃窃私语,或干脆就是麻木。也难怪,能和谁说呢?
当然,不论和谁说,毕竟还是会有人说破的。
事情是在后院吵响的。后院是大楼背后的住宅。
起因是我在微信群发了一组玉门灯影里流淌黑水的照片。当时,山西消除黑臭水体正铺开“百日清零”行动。我说,黑臭的玉门河,白天不流黑夜流,是否有人在偷排?我问,我们远查汾河入黄口,近查吕梁磁窑河,怎么不查查眼前的这条黑水河?我从手机地图上查看,玉门河从西山流出来,流过城市,流过环保大楼,流进汾河公园,流进公园暗涵,最后流进汾河河道,看不到汇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人们说,这玉门河挖掘多年,开合多年,开开合合,不是在治污么?开始,河道被划开,划开的地方砌出渠道,渠道里边排过黑水,渠道两边杂草横生。之后,河道又被挖开,河道地下埋了管道,管道不知流过什么,合拢之后却黑水照流。再后,突然之间全线翻开,河岸筑成沿河大道,河坝铸成水泥长城,人们以为这下黑水治了,可流来流去黑臭依旧。
当然,这样的黑水臭水,不仅玉门河是,别的河道也是。汾河岸畔的太原,是多条黑水往汾河里排;而汾河沿岸的山西,也是多少条黑水往汾河里排。太原的黑水,原先号称13条黑龙;也许觉得说法刺耳,后来就改称为边山支流;再往后,就说成了9条黑河……当然,13到9,是越治越少了,但城市长高了,道路长长了,这玉门河怎么就越发地黑臭了?
于是就有人猜测,这黑水,是这城市给生态环境部门点的“眼药水”。你不是管生态环境保护吗?你不是统一监管生态环境吗?连眼皮底下的生态环境都管不好,你管的哪门子的生态环境?你又能管好哪门子的生态环境?
要是这样,这黑水,不光是黑,不光是臭,是太刺鼻了。
看着我发在微信群里的“月夜黑水图”,有人说“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臭水沟,但就是没人落实啊!有人就说,当下不是消除黑臭水体吗,何不借新厅长的铁腕拿下这个又黑又臭的顽症?“百日清零”如果连眼前这个黑臭水体都消除不了,就不好相信太原会全部消灭黑臭水体了,也不好相信山西会全部消灭黑臭水体了。
应该说,道理就放在那里,看你做不做。不是说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特警”吗?不是说有一支铁律为后盾、铁心为意志、铁腕为武器的环境保护“铁军”吗?“环保铁军”的司令部就在这里,“生态特警”的指挥部就在这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本营就在这里,竟治理不好玉门河的这个“眼底病”?
于是,后院的人们在微信群里就又议论了,生态环境大楼这“灯下黑”或者“眼底黑”治了,人们不会认为山西的水就都治好了,因为按照常理,各人打扫门前雪,你不应该治好眼皮底下的事吗?但这“眼底黑”或者“灯下黑”要是治不好,人们绝对会认为山西的水没治好,因为,你连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都办不了,又何谈别的?
同事把我发的图片转发了给新厅长,说我们楼前的玉门河臭气熏天,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却视而不见。建议趁消除黑臭水体行动,逼住太原市限期年内彻底解决,不然会影响“百日清零”的结果。不然,人们会说,生态环保部门眼皮底下的问题都没解决,消除黑臭水体的实际效果能有多大?新厅长当即在自己建立的“百日清零”微信群里转发了图片和建议,批示:“请太原组督办,省督查办跟进。对市县相关部门约谈督办!”
很快,真的有机器在行动了,真的有人在清理了,真的有人在巡检了,也真的有人在取水化验了。也很快,玉门河里黑水臭水不流了,淤积的黑臭水体也排掉了。然后,在大楼后院的微信群里,就有人发上来了太原市生态环境局的报告。
报告说,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太原市就实施了玉门河综合治理工程。工程从河流起点到终点11.06公里,雨污分流,铺设污水管24公里,雨水管25公里,沿线101个排污口污水全部收集至汾东污水处理厂处理。之所以形成黑臭,原因在于,玉门河流入汾河暗涵的500米河道里,因雨水阻塞无法排泄和污水外溢入河而导致积水黑臭。鉴于此,紧急整改措施是:立即清挖淤阻,全程清理垃圾,巡查排水管网,监督截污设施,杜绝污水溢流,彻底消除黑臭。
这个时候,人们才明白之前河道开挖的真相。原来,雨水管道是真的早就埋在河道里了,污水管道也真的早就埋在河道里了。就是说,城市的治理已经落到了地上,地下的管网已经布在了深处,那可是长长的地下巨龙呀,但就因雨水阻塞和污水溢流,这么久,竟任黑水流成了臭水,臭水流成了水患,水患殃及汾河。人们于是感慨,要彻底消灭玉门河和所有河里的黑水脏水臭水,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铁军铁拳背后,就得有铁腕,否则黑水禁不绝。
之后,不知不觉间,玉门河变清了;不仅玉门河变清了,北涧河、北沙河、南沙河、风峪河、冶峪河、虎峪河、九院沙河、小东流河,也都变清了;不仅河里的水变清了,而且河岸上都建起了快车通道,快车通道外建起了人行步道,人行步道左右种植了生态花树,所有的河流,和所有河流上的道路,成为了伸进汾河和飘进汾河的缕缕彩带。
一条汾河,就成为了舞动长缨和彩带的一条巨龙。
这条玉门河,从山的沟壑里流出,流进了城的沟壑,变流成了一条彩带。
我沿着玉门河溯流而上,踏着崭新的绿树绿篱绿草簇拥的河边步道,追溯到玉门河流来的远处,河道在清流之外,植物鲜亮,黄沙洁净,建筑清新,河畔或是绿廊,或是花园,或者说,整个河畔就是一个绿荫荫的公园。
一条玉门河,由此成为这个城市所有河流由浊到清由黑到美的一个缩影!
是啊,西山是它出发的地方,也是它出身的背景,西山都绿了,它能不绿么?汾河是它流向的地方,也是它奔逐的前景,汾河都清了,它能不清么?天空是它顶着的盖头,也是它扬着的披风,天空都净了,它能不净么?
晋阳湖时间
晋阳湖是住在太原时空里的一汪清波,住满了过往,住满了向往,住满了沉在碧波里沧海桑田的时光。
城市突然生出这么个绝尘而来的湖泊,把天和地融在一起,连城市自己似乎也不曾想到,它像天外飞来的一个演绎,我觉得,城市见到它的时候,肯定也和我一样惊奇。
其实,它是城市变迁的一面奇幻的水镜。
似乎,天看不见自己什么颜色,就把自己放到湖里去看,于是湖成了天的颜色;湖看不见自己什么颜色,也把自己投到了天上去看,于是天成了湖的颜色。水天一色的时候,云似乎不知道自己什么颜色,地也不知道自己什么颜色,就都把自己托给天或者托给了湖,于是天和湖就都看到了云的白和树的绿。白的云,绿的树,都成为湖上的风景。
当然,天地也不只是看看而已,天地也变幻莫测地给予。天把夕光里的云霞给它,它于是荡漾着云霞;地把晨露里的绿意给它,它于是波叠着绿意;天把寒日里的晶莹给它,它于是覆盖着晶莹;地把秋风里的亮黄给它,它于是辉映着亮黄。天地间茫茫一派的时候,又是天给它注入什么或它给天回赠什么。天和地云和霞,浑然成为湖里的日月。
是的,天给了它月光星光,它就用月光星光勾勒出水里的宫殿;地给了它城市夜光,它就用城市夜光浸染出湖里的梦幻;天给了它万鸟和鸣,它就用万鸟和鸣点缀平湖的寂静;地给了它群楼霓虹,它就用群楼霓虹点亮满湖的辉煌。湖每天都在天地间画山画水,然后又全然消弭,重新在天地之间画山画水。湖的每一次画都是新的,湖的每一天画都是新的。
一个生态的晋阳湖,就飘落在现代城市的世界。
湖背后的吕梁山早已远去,湖畔的楼群成了近的山。吕梁山见过湖过去的样子,楼的山只见过湖现在的样子。于是吕梁山和楼的山讲起湖的往事,讲起远古晋阳湖的迷离身世。
知道“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故事吗?
彼晋阳湖不是此晋阳湖,晋阳湖曾是一个海样的存在,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系舟山和韩信岭之间,一个激流恶浪竞逐、凶波狂澜共舞的水的世界。那时,水世界里没人,却有一女子驾一叶扁舟,悠然垂钓。大禹遇之,敬一钵米酒,女子竟轻轻一弹,弹破钵口,酒液流尽。大禹遂悟,钵之缺口,犹灵石口也。遂打开灵石口,任晋阳湖洪水流泻。
人类伟大的秉性就是创造,创造一个神和它的神话,然后靠神创造人间奇迹。中国流传的治水时代的大禹,不知是有或者无的人物,但许多治水故事都来自大禹的神话。打开龙门口,黄河入海流;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当我们穷究打开龙门口或者打开灵石口的故事的时候,以人类最原始的生产力而言,大禹及大禹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打开了山口?
大禹打开龙门口或灵石口的故事,实际是地壳变动山河变迁的人文寄寓。太行山呂梁山,曾经在地壳隆起中双臂一抱,抱成山岩堰塞的太原盆地;太原盆地于是成了晋阳湖;而在又一次地质断陷里,太行山吕梁山双臂一松,太原盆地水流泻了,就空出突破堰塞的晋阳湖。故事由地质世纪演绎到人类世纪,远古的晋阳湖,演绎成大禹治水的另一种传奇。
这样,历史给远古的晋阳湖,注入浓重的人文精神。
吕梁山太行山都知道这个传奇,也都铭刻着晋阳湖的记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大禹空出的晋阳湖,崛起噬水如龙的现代工业,然而远古的晋阳湖,已水湖无存。
于是,现代工业的钢构铁臂,挖掘出一个工业的晋阳湖。
于是,太原盆地拥有了包围在工业王国的这个工业湖泊。一个冷却工业热水的湖泊,一个沉淀工业用水的湖泊,一个排放工业废水的湖泊,而后,变成一个遍布渔业养殖的湖泊,一个走向农业灌溉的湖泊,一个将被城市废弃的湖泊。而这个过程,曾发生一场罕见的“晋阳湖鱼殇”,我就曾走向那片工业的晋阳湖,在泛着鱼肚白的湖水里打捞鱼殇的故事。
一片无边的死寂,一片无边的惨白,整个晋阳湖变成白的湖。湖边看过去,是翻着鱼肚白的湖,湖心看过来,还是翻着鱼肚白的湖。鱼们睁着死不瞑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天空发问,鱼缝里冒起腥臭的气沫,像鱼们吐着不甘寂寞的泡泡。渔户的狗朝着湖面狂吠,工业烟囱却不在意地吐着黑龙。满湖的惨白告诉人们,绝不要再用鱼肚白形容天边的曙色。
如此悲惨的鱼殇,人们竟然没有弄清楚什么原因。养鱼的人们说,是工业的管道排过来工业废水,工业废水把鱼给毒死了。企业的人们说,是养鱼户投放了太多养鱼饲料,水体富营养化把鱼给憋死了。事情终究没有给出一个结果,结果于是成了“富营养化+工业废水”。鱼们死了个不明不白,最后,冤屈的鱼们只能守着一个天生的执念:死不瞑目。
这样,污染的晋阳湖,就成为工业时代不灭的记忆。
当然,工业的晋阳湖最深刻的记忆,应该是工业的远去和工业成为了遗址,而晋阳湖自己,则由工业的湖泊废弃的湖泊,变成了生态的湖泊现代的湖泊,又一次经历乾坤轮转。
生态的晋阳湖是一次诞生,现代的晋阳湖是一次再造。
河流是有灵性的,湖泊也是有灵性的,河流的靈性和湖泊的灵性,源于水的根性和水的神性。晋阳湖始终嘹亮在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晋阳湖始终跳动在汾河盆地太原盆地的心脏。远古的晋阳湖远去了,灵魂和基因留给了现代的晋阳湖,现代的晋阳湖就做着了远古的晋阳湖的梦。向往着澎湃,向往着汹涌,向往着流淌,这难道只是晋阳湖做着的梦么?
黄河在晋阳湖里回旋,汾河在晋阳湖里回旋。晋阳湖,又流进了汾河,汾河又流进了黄河……
河的心,走向海洋,湖的心,也走向海洋。湖河连通,河湖贯通,湖河海遥通……
于是,天就看到,晋阳湖已经不是一面孤零零的水镜,它与古老的魂脉融通了,它与现代的水脉融通了,它与生态的命脉融通了。一个古老泽国的现代传奇,一个现代城市的生态构想,从梦的天空落下来,落在了城市的擘画里,落在了城市的创造里。我想,这注定是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刻,而这个时刻就是晋阳湖时间。
我看到的梦,就在晋阳湖时间之后的一日,圆了。
我觉得,晋阳湖已经急不可耐,晋阳湖的鱼和鸟已经急不可耐。要不,鱼们何以嗖嗖嗖跳出湖急着看看外面的世界?要不,鸟儿何以喳喳喳呼唤湖快快做着走向河流的演习?
花们树们也怒放着自己的花叶,等待着,等待着,等待河流到来,它们就哗哗哗投进去,追着河流,奔向海洋……
责任编辑: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