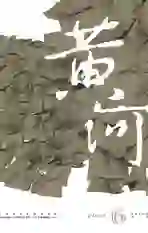只有诗成为可能
2023-12-28悦芳
悦芳
与时间有关的一切,总是在被书写,并作为诗歌永恒的主题。
最近,读了诗人赵建雄的诗集《时间的暗伤》,这是赵建雄继《零度左右》《时间之上》之后出版的又一部诗集。此时的他已不在“零度左右”踯躅徘徊,也不在“时间之上”自由抒情,而是把笔触伸向时间深处,伸向了世间万物的存在之境,把一种深切的关注与忧伤注入到时间的内核,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探寻生命个体的一个个痛点,以其精微的观察与深刻的体验舔舐伤口,直逼现实、直击人心。他一方面从里尔克的“诗歌是经验”的经典表述出发,另一方面又开始关注内心的审视,通过内省的精神品质构筑了主体和客体深深介入的完整经验,从而给精神以自由翱翔的空间。观照与慈悲、伤痛与追问构成了其诗歌的深度和力度。无论写人、叙事、状物,都是透过语言进行“自我”指涉,同时混合着诗人激情、策略、幻觉和现实感的书写。他拥抱生命的底色,同时也感叹命运的遭际,他在成长中固守着时光的信任,又在无休止的抗争中抚摸着伤口,并试图从日常语调的冷叙述中突围出来,走向理性的判断和哲学的提醒。
是对视,也是反思
一个诗人总是处于孤独状态。但当一个人孤独久了,总要寻找表达的途径;一个人历经世事,就会把沉淀的情感酿成一壶芳香醇厚的浓酒。这两点都恰到好处地体现在了诗人赵建雄身上,他把时间的暗伤融化成了一首首疼痛的诗。
在第一辑“凛冽的对视”中,诗人带着怀疑的眼光探询个体的内心世界,关注“人”的生存空间,思考“人”与“天地”和“自然”之间隐秘的内在联系。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岁月无声,尘世如此苍凉/万物柔情,却喊不出一声疼痛”(《尘世如此苍凉》),“绝望和夙愿隐忍着/灵魂,寄托在身体别处/爱与恨,索与取,生与灭/时间开出一张苍白的凭证”(《一枚落叶的命运》)。“骨节与骨节碰撞的疼痛与欢愉/灵魂与灵魂搏击的喝彩与尖叫/与观者,与过客,充满对立与统一/而水与火中,舞动的影子/如月如刀,皆是孤独”(《舞者》)。人是生命的主体,但也是生命里最渺小的存在,个体在承受由生命带来的疼痛体验之时也试图揭示这隐藏于生命之上的事物,这是一种共时性的社会认同或集体情绪。诗歌写作需要关照世界、时代、人群、苦难,这也就意味着诗歌是一个承载者,是一个心灵容器。当一个个现实的镜头闯入诗人眼中:“一头老牛/五花大绑,被几个大汉/死死地摁着,却始终没有叫喊一声/只是眼角的两行泪”(《宰牛现场》),“一只鸡被扔进虎笼里”(《在虎园》),“一条冰冷的铁链锁住八个孩子的母亲”(《这个春天》),诗人“久久地坐在窗前”,无奈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界荆棘密布。我们被尘世拘押/尘埃覆盖着大地的凄凉/人间的盐,撒向河流的伤口/所有的命运都是永恒的谜”(《凛冽的对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情境性述说,而是带着现代人的焦虑对生命的理性洞悉和由此及彼的关切与审视。诗人冷静地处理着眼中所见,为我们呈现出生存的艰难、生命的无奈与悲壮以及等待他们的残酷命运。
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在诗作中写道:“我想到这个世界如此多难/必须不时为某种歌唱/且想到顺序有所助益/一如秩序/先是自我/而后磨难/而后歌唱。”诗歌创作是一个从“自我”到“万物”,从个体经验出发到多维度探索的过程。如果诗歌忽略这一切,而只关注自我,那么诗歌就会沦为狭隘的自我表达。一首有力度、有厚重力量的诗作后面承载的是以真实为原料,有着蓬勃生命力的情感体验。
诗是存在忧患意识的,正如杨匡汉先生所说,“一旦诗人意识到历史的必然法门和人自身生命运动及其现实实践活动之间无法规避的冲突的时候,生命的困惑和体验的痛苦便开始折磨着他”(《中国新诗学》)。诗人在这里感受到的正是来自现实与想象差距的煎熬。“黑夜是一间黑屋子/没有门,也没有窗子/我和你在屋子里/面對面坐着。我们/彼此陌生又熟悉/黑夜永远是背景/上演着一出出话剧”(《我们在黑暗中相互活着》),人活着本身就是悲剧,反过来说,人活着本身也是戏剧。当“呓语者的躯壳慢慢复活”,当“流浪者的足音开始响起”,“幻像就在黎明时成熟,说出黑白之间的逻辑/和那些生命的奥义”(《黑夜在诗歌里绽放花朵》)。诗人紧紧跟随内心的脚步,锲而不舍的自我追问,不断地进行自我剖析,以期实现宇宙意义上的自我关怀的可能。虽然带有某种悲剧的意味,但与此同时,在灰暗之中也是带有希望的。他的希望,就是那种在痛苦中绝不放弃的坚持,就像那些存活黑暗中的微光,即使微小却足以成为希望。
是言说,也是沉默
这是个不安的时代,因为不安,更需要写作。
当沉默无法承载情感与思绪,写作成为言不可言之自由与可能。“沉默本身就是回答,或回答本身也归于令人不寒而栗的沉默”(诗评家金汝平语)。
在第二辑“时间的暗伤”中,诗人用真挚的情感向我们揭示了其真实的内心世界,而这份真实又来源于他最本真的生命体验和日常经验。“一切都在沉睡,星星陷落/失眠的人置身何处/隔壁的酣声沉着而冷静/呼喊是一个人的解脱/所有的声音只给一个人听”(《时间的暗伤》),“我的天空,一半是火,一半是冷/这些雪,会不会覆盖我贫穷的余生”(《等待一场大雪来临》),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真实地感知到个体在生命长河中对自我,对宇宙的思考。他的思考不是空洞、浅显的,他将自我与万物并置,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内核,依赖生活的真实,融合个人的思考于诗歌的语言,以此实现省思世界,探索生命的过程。
诗人对生命和宇宙的思考是宽广的,他并不局限于自我。而是将关注、思考的对象转向世间万相,无论“穿衣镜前的女人”还是“天桥上的农民工”,无论“向日葵老人”还是“斑马线上的狗”,他都以平等的心灵观照并与他们对话,带着诗人的悲悯并以独特的视角专注且深情地审视着这个世界。但是,诗人也是具有各种情感与感悟的普通人,诗人并不能抽离现实生活而存在,所以诗人赵建雄不免悲伤地书写道:“时间的暗伤,无休无止/在虚无里沉浮。仿佛/陈述命运的悖论”(《时间的暗伤》),“日子深处,只有孤独的影子/拆借尘世间最后一点温暖”(《向日葵老人》)。诗人面对生活的苦难,生命的痛点也常常感到无力和不堪,于是将这种真实的情感体验放置于诗歌当中,建构起生活的真实和生命的温度。“此时,文字是唯一的醒者/牙齿坚硬,翅膀轻盈/思想放射出光芒/我们互不打扰,互相体谅”(《我不喜欢虚度光阴之人》),虽然个体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通过现实世界的生活获得生命体验,但个体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完全参透生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工业文明突飞猛进、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环境之下,个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个体在获得物质补偿的同时精神领域却愈加贫瘠,以至于人们常常陷入孤独、迷惘、抑郁、荒诞的生活迷宫之中。“我和我的影子如同虚设/春天,像一个悬念挂在枝头”(《悬念》),个体无法完全揭露生活的真相,而在浩瀚的宇宙时空、无形的宿命以及巨大的死亡阴影下个体承受着生命带来的无形的疼痛,这样的疼痛是未知的却又无处不在。于是,在仅有的沉默中不得不借助时间的更迭自我言说。
所有的旧日子,已消耗殆尽
时间的指针开出苍白的花朵
钢铁的齿轮咬紧牙关,磨碎
无数透明的词语
内心的呼吸与呐喊
被卑微的尘埃掩埋
这个世界,终将归于秩序
过去,无非是一朵花的凋谢
苍穹之下,已经响彻击打的钟声
看见了吗,飞鸟的羽翅
扑射着金色火焰,黑色的石头
喊出一生的疼痛
雪花在大地上写下了信仰
总有一道闪电唤醒春风
———《元旦献词———兼致自己》
诗人通过诗歌不断抒写着个人化的命运,这既是面向时间和个人的,又是面对更多的读者和大多数人的。他從“自我”出发,以“生活”作为其诗歌写作的立足点,将日常经验融入创作中,继而升华诗歌主题。对生命、时间、死亡、天地、世界、永恒、宇宙作出诗意的阐释,也借由此重构个体信仰,恢复个体内心秩序。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同时面对光明和黑暗,面对幸福和苦难,面对你愿意接受的和不愿意接受的一切。对此,赵建雄在诗中也做出了非常艰难而理性的回应,类似于波兰伟大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的态度。让诗歌作为承载者,承载起个体的命运,承载起真实的苦难,承载起时间的重力。“诗意让敞亮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诗·语言·思》)。
正如蒋勋先生所说:“有诗,我们就有了美的钥匙……生活有时候沉重心酸,也许给自己一首诗,可以让生命飞翔起来。”
是暗伤,也是解药
当时间作为一个表述元素出现诗中时,诗作为一个载体,洋溢在诗之空间中的时间往简单一点说就是人的生命意识。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所关切的人,都是用自身的生命来感知时间的存在和流失。如果说诗中有时间或时间感,就表明其中充满了人性。诗中的时间是人带来的而非与生俱来的。
而诗人仿佛是一个走入历史深处的孤独者。
在《万物皆化相》这组长诗中,其涉及的社会现象和世态人心可谓缤纷杂呈,无论是白天还是暮晚,无论是此岸还是彼岸,无论是向阳还是逆光,无论是曲折还是浑浊,无论是丰盈还是枯竭,无论是泡沫还是沉渣,它们都如此具体可见而又虚幻不可见,它们几乎对应了这个庞杂而深邃的世界本身,对应了每一个人的精神渊薮和复杂体验。这些诗篇,既有情感潜流的描述,亦有情绪的瞬间聚集,还有温暖的亲情和人间烟火、寻常人的磨难。无论写作的客观对应物是否发生变化,诗人都始终保持一种警惕———自我模仿和复制。在处理诗人主体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时,他十分注意主观体验和客观审视的沟通与融洽,涵纳了互为补充又互为矛盾的辩证思维。“影子被困在玻璃中”“一朵被深藏已久的花蕊”“风尘中有轻微的呼吸”“蛰居黑暗的心萌生触角”“穿越时空的陌生人”“洞穴中沉睡的智者”“公园长椅上的老夫妻”等等等等,诗人使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聚拢在一起,使那些看似毫无联系的事件显示出它们内在深刻的联系,让我们辨识出文字里逐渐显形的世界的另一个层级,并在诗句中拼起它们原有的完整。诗若不是这样的事物,那还能是什么?它在最真实的时刻,既不是技术,也不是修辞,它是我们思想与情感的倾诉和相互的听到,是世界在语言中的复活时刻,是穿越死亡再次新生的时刻。
我写作,是要救出我内心的疼痛,让这疼痛纯粹,干净,不变质,不腐败,不自私,不作秀。这疼痛,是一切人的疼痛。诗是自由的国度,因此只有写诗才可以来解救被束缚的自己,带领人走向广阔无边的“自我解放”:每个人活着必带着一定的束缚,当人被束缚的时候其实与活在地狱无异。而只有在写诗的时候,它为我带来“活着”的快感,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于是,一个诗人所能做的———写吧,记录吧,在诗中,使你的感受进入并融合于他事他物之中,并与它们一起处于现时性、共时性和宇宙的整体性之中:所有的时间都在时间之中。时间是暗伤,也是解药,难道不正是这样吗?诗人在诗句中打破了时间的线性物理属性,重新创造了空间的现时性,这就是诗的秘密。在诗人那里,时间失去了长度,变为了无限敞开的空间,变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正像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的那样:“是的,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有毒的。但是,在每一分钟我们都可以找到解药。”对于诗人来说,诗就是最好的生活解药,在苦难与创伤面前,只有与命运处于抗拒状态的写作,才是可能的。所以,带着诗在时间的伤口中前行,便是写诗的意义了。
责任编辑:宁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