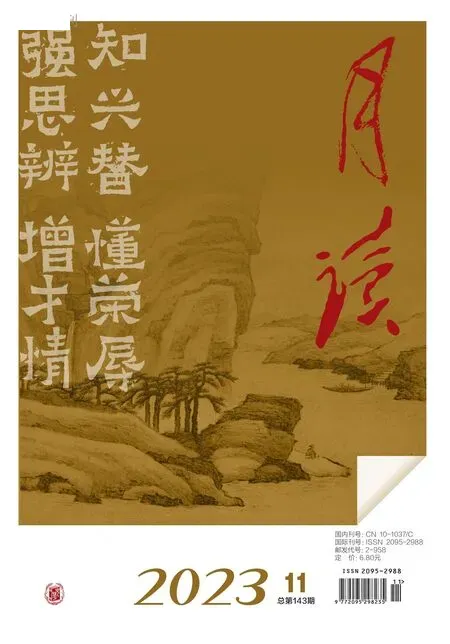陶渊明的螺旋形怪圈儿
2023-12-26◎顾农
◎ 顾 农
中国古代士人中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高人总是相信自己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也能独善其身:适时走出茅庐,就可以济苍生,安社稷;建功立业之后迅即急流勇退,重入山林,又自能享受幸福和自由。唐人李商隐有两句诗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正是讲这种理想境界的:先出山做一番慷慨激昂、改天换地的大事业,立功于庙堂之上;然后归于江湖之远,乘一叶扁舟淡出世局。
达到了这种境界的著名典型是春秋时期的范蠡。他先是帮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成就了一番霸业;然后迅即淡出政局,改名换姓,以陶朱公的化名大做生意,四海为家,获得巨额利润,成了超级富豪。(详见《史记》之《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当官也行,发财也行,两手皆硬,一切圆满,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人生圆圈啊。
陶渊明也有他心目中理想的圆圈,那就是先行出仕,游行四方,获取官俸改善生活;然后归隐,回老家过潇洒惬意的田园生活。他出仕的目的主要在于具体的经济利益而不包含多少高远的政治宏图;其归隐则是回老家的农村,绝不到处奔走去搞什么商业活动。陶渊明赞叹歌咏过的先贤甚多,却没有提到过范蠡。先进入体制获得物质利益,后退出体制享受自由,为了实现这样的人生规划,陶渊明把这样一个美妙的圆圈反反复复地画了五六次,结果形成一套色彩越来越浓的螺旋形怪圈。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是到江州刺史桓伊手下效劳,作为他的使者到外地执行种种公务。那时东晋正利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的有利时机出兵北伐,人心振奋,形势大好。但是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没有唱任何高调,只说此番出山完全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所以干了一段时间就回老家去了,这就是《饮酒》其十诗里所说的“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回故乡闲居,人很舒服,但官俸就没有了,所以后来他又曾多次出仕,以求“一饱”。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是充当本地江州的祭酒,时间甚短就弃职而去。《宋书·隐逸传》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出为州祭酒的原因是“亲老家贫”,可见此番出马仍然着眼于经济,与他的初仕并无二致;而匆匆自解而归,则是因为此乃“吏职”,同他的平生志趣、生活方式不能兼容。祭酒、主簿之类都是州里的僚佐,即所谓“吏职”。魏晋以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的格局,州一级衙门里的主簿大体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主管稽核文书、执掌印鉴等事。郡、县和若干中枢机关里也都设有主簿,从事类似的公务。
至于祭酒一职,《晋书·职官志》虽有记载,但只说此乃是列卿之一的太常衙门的一种职务的头衔(“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而没有提到地方行政单位的州里也有什么祭酒(“州置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又有主簿,门亭长、录事、记室书佐、诸曹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成书于前的《宋书》在《百官志》里说到了州一级衙门里有祭酒:“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而别驾从事史如故,今则无也……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这里的记载比《晋书》更详细,也更重要。陶渊明所任的祭酒究竟是一般的祭酒从事史,还是地位相当高的别驾祭酒,史料有缺,现在已难确指;按一般的情理来推测,应当不是高居于吏职之首的别驾祭酒,而是分管某一领域的祭酒从事史。
如果陶渊明连“居僚职之上”的别驾祭酒都不肯干,州官再来召他为主簿,那就不合官场运作的逻辑了。他先前那个祭酒的地位应在主簿之下。何况《宋书·百官志》明明说江州设有“别驾祭酒”乃是“晋成帝咸康中”(即335—342 年间)的事情,到陶渊明任江州祭酒的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之时,“别驾祭酒”一职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东晋王朝政局混乱,官职的编制时有变易,咸康中王羲之曾一度担任江州刺史,别驾祭酒一职也许出于他的设计,其人地位高名气大,不免多有创意,有所更张,大约也没有人来干涉他。
你嫌祭酒从事史的官小,现在请你当主簿,总该可以了吧。此时江州州官王凝之大概是这样想问题的。看上去不无道理,其实是看扁了陶渊明,所以当然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实际上陶渊明的苦衷是“不堪吏职”,而不是计较不同诸“吏”之间地位高下的差异。祭酒从事史是“吏”,主簿也是“吏”,而凡是“吏”,就总是得在衙门里看长官的脸色做事,时时要向比自己地位更高的各级长官“折腰”,遵守种种规则和潜规则—这是陶渊明完全不能适应的。先前当陶渊明在桓伊手下任职时,他人不在州府的衙门里,而是在外面到处跑,执行种种秘密的使命—他只对最高地方官刺史负责,而一向不同种种级别的官僚打交道,那就自由得多,也潇洒得多了。
从太元十八年(393)抛弃了江州祭酒,又拒绝担任主簿之时起,到隆安三年(399)再度出山到桓玄手下任职以前,陶渊明有五六年时间是在故乡闲居的,相对于他第一、二两次出仕之间的初隐,这一段时间或可称为他的再隐时期。
从陶渊明的初仕、初隐、再仕、再隐这两个圆圈看去,陶渊明看重的,一是经济收入,二是自由和尊严。最好能同时具备,如果不能,宁可抛弃收入,务必确保个人的自由。当然这也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经济收入也很重要啊。如果自己家底丰厚,完全不需要依靠官俸也能过非常体面的生活,那么本来也可以不必考虑出山的。
陶渊明当官相当于后人为解决生计而谋职。
但是除了要吃饭,他还需要自由,精神生活的意义决不下于物质生活。县令本来也还是可以当的,这同在州里担任“吏职”要时时看上司的脸色、听领导的吩咐不同;可是一个郡里下来的纪检官员督邮忽然对他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宋书·隐逸·陶潜传》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公田之利”固然重要,个人自由价值更高,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熊掌,于是即日解印绶去职,回故乡隐居。
陶渊明又画了一个始于出仕搞创收,终于退场要自由的圆圈。
陶渊明归隐以后,也曾有人劝他东山再起,他不同意,说是“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隐逸·陶潜传》)言行一致,态度坚决。
为了生活,创收是必须的,但自由高于创收,而生命又高于自由。最好是既有较多收入而又相当自由,可惜这两者不容易兼顾。
陶渊明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端中摆来摆去,多次往返于体制内外,先后画出了一个又一个圆圈而始终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折腾中,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