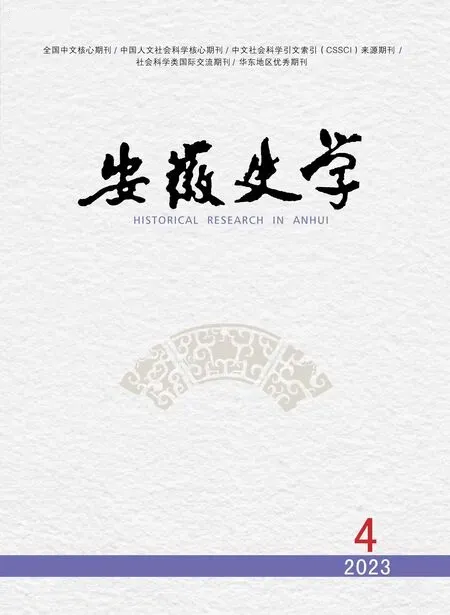庆酬与传宣:闻喜宴所见宋代国家治理方式探微
2023-12-25纪昌兰
纪昌兰
(信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宋代闻喜宴,又名琼林宴,是为庆贺新科进士及第而举行的宴饮活动。受国家“右文”政策的影响,闻喜宴的开设显得颇为引人瞩目。已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宴席设置内容、礼仪程序、具体事项等方面(1)祖慧:《宋代科举唱名赐第与期集仪制》,张其凡、李裕民主编:《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周兴禄:《宋代科举诗词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版;张希清:《宋朝科举赐闻喜宴述论》,戴建国、陈国灿编:《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中国商务出版社2017年版;杨倩丽:《北宋闻喜宴探析》,《湖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但是对于宋代设置闻喜宴的政治意义及相关宣传手段、所取得的社会效应等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就以上几点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以闻喜宴为观察视角探讨宋代国家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一、宋代闻喜宴及其设置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自创立以来就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宋代倡导以文治国,大力鼓励世人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借此吸纳知识精英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科举及第就成为广大士子通往仕途的重要途径。为了庆贺士子及第,各方通常会举行一系列隆重的庆祝仪式,闻喜宴就是其中的典型,也是备受世人瞩目的一大盛事。
闻喜宴肇始于唐朝的曲江会聚,最初是为下第举人而开设的宴聚活动,后逐渐演变成为及第士人的欢宴。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中所谓“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已来,然盛于开元之末。今琼林赐宴,亦唐曲江、杏园之事尔”(2)高承:《事物纪原》卷3《赐宴》,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172页。,即是如此。这一时期,士子及第仅于礼部南院之东墙贴榜公布,尚无官府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闻喜宴相当于及第者之间的私人宴聚。
由唐入宋,科举诸事受到国家的特别重视,及第士子也因此而获得优待(3)后唐已出现国家出资支持期集活动,参见《册府元龟》卷641、642,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691、7699页。,以国家为支撑举行包括闻喜宴在内的大规模聚会活动,即当时所谓的期集。(4)方健指出,唐代的“闻喜宴”,宋称“琼林宴”,又称“鹿鸣宴”,南宋时期的费用由及第进士自掏腰包。参见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此处将琼林宴与鹿鸣宴混同,且未注意到南宋时期公费宴集的状况,大概与作者研究视角为北宋士人有关。期集一般在唱名之后举行,活动大体上包括正谢、谢先师、叙同年、拜黄甲、赐闻喜宴、刻石题名等。北宋,士子及第之后,按例期集两个月。南宋时期,时间缩减为一个月。据《咸淳七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咸淳七年与宝祐四年的期集活动流程基本上按照惯例执行,内容包括朝谢、谒先师先圣、赐闻喜宴、拜黄甲、叙同年、刻石题名等,程序大体一致,间或稍有调整。(5)刘埙:《隐居通议》卷31《咸淳七年同年小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6—338页;佚名:《宝祐四年登科录》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页。
期集期间最著名的活动当属闻喜宴,闻喜宴也完成了由私人宴会到官方举办的实质性转变。宋代的闻喜宴无论从举办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与前朝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宋时期,闻喜宴分为两日,一日宴进士,“请丞郎、大两省”;一日宴诸科,“请省郎、小两省”。(6)《宋史》卷155《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8页。北宋末年及南宋,朝廷罢去诸科,闻喜宴也由两日缩减为一日。闻喜宴上除美酒佳肴、歌唱奏乐之类传统内容之外,尚有各种必备仪程逐一展开,大体上包括簪戴宫花、赐诗与文章等环节。朝廷特派掌管、主持宴会的官员即押宴官,一般为近上臣僚。此外,席间照例有赐宴口宣,大多属于例行公事之类的礼仪说辞。当然,闻喜宴也存在着罢举状况。例如,治平二年三月,知贡举冯京等引新赐及第进士彭汝砺等已下诣垂拱殿谢恩,因西夏战事未平,边境不宁,朝廷下令罢赐闻喜宴。(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69—5270页。嘉定元年五月殿试之后,宋理宗成肃皇后凡筵未除,闻喜宴未能举行。(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31,第5283页。淳祐七年七月,因“天久不雨”,亦未能举行。(9)从绍兴十八年至咸淳十年,将近130年间,共开贡举43榜,除嘉定元年五月“成肃皇后凡筵未除”、淳祐七年七月“天久不雨”,两榜免赐闻喜宴外,其余41榜,均赐及第进士闻喜宴于礼部贡院(张希清:《宋朝科举赐闻喜宴述论》,戴建国、陈国灿编:《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第265页);周兴禄认为,从光宗直至南宋最后一科之前共28科中有23科有赐诗,其余5科皆因未进行殿试及闻喜宴,故未有赐诗,其中3科是宁宗、理宗、度宗登基后的首次贡举,在“谅暗”中,不举行殿试及闻喜宴,其余2科,宁宗嘉泰二年、嘉定元年未举行闻喜宴(《宋代科举诗词研究》,第312页)。
宋代闻喜宴开设地点相对固定。唐时,礼部放榜之后“醵饮曲江,号曰闻喜宴”,五代则举于佛舍名园。(10)王应麟:《玉海》卷73《礼仪》,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5页。北宋初年,沿袭前朝旧例,通常于园林寺庙举行。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大开科考,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11)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全宋笔记》第7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命中使典领,整个宴席“供帐甚盛”。到太平兴国八年,赐新及第进士宴于琼林苑,“自是遂为定制”。(1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2,第5265页。至此,闻喜宴一般于琼林苑举行,因而又称琼林宴。宋徽宗前期,国家施行太学舍选,一度改赐闻喜宴于太学辟雍,后又复置琼林苑。(1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3,第5272页。宋室南渡,建炎二年,因诸事草创罢赐闻喜宴,“自后五举皆免宴”。(1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4,第5272页。绍兴十七年十一月,朝廷采纳礼部侍郎周执羔重启旧制的建议,赐闻喜宴于礼部贡院,闻喜宴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对此,李心传不禁感慨:“自军兴,废此礼,至是乃复”。(1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十月丁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8页。之后,礼部贡院成为南宋闻喜宴的常规举办场所,所谓“在京则赐及第进士宴于琼林苑,中兴以后,就于贡院”(16)赵升:《朝野类要》卷1《闻喜宴》,《全宋笔记》第8编第3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432页。,大致如此。
从整体上来看,设宴地点由寺庙园林到贡院的转换,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转移,某种程度上是时代文化特色和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深刻反映。北宋时期,闻喜宴的常设地点琼林苑属于皇家园林,宋太祖乾德中期建造,与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并称皇家四园。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于苑北凿金明池,导金水河水注之,用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且作为水嬉之地。之后宜春苑、玉津园日渐衰败,“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琼林苑,惟独琼林、金明二园最盛。(17)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全宋笔记》第2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琼林苑位于新郑门外,俗呼为西青城,苑中松柏森列,百花芬郁,亭台楼榭林立,流水潺潺,美不胜收。(18)周城:《宋东京考》卷1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3页。国家庆贺进士登科,赐宴择地于此,欣赏美景之余,愈加彰显及第之后士人的欢喜惬意与志得意满,流溢出尽享皇家天恩的美意与盛世荣耀。加之,皇家园林的开放特色(19)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7《驾幸琼林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6页。,普通百姓耳闻目睹之余,又不免具有极强的社会宣传效果与激励作用。当然,也不能忽视设宴地点的选择与更替,具有传承唐朝曲江盛宴旧例的延续性。另外,这一时期及第人数较多,需要足够宽敞且开阔的空间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客观因素。(20)两宋320年,开科118次,登科人数约10万,平均每榜取士847人。笔者据龚延明、祖慧撰《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统计。南宋时期,闻喜宴多在贡院举办,更增添了一层来自于国家的庄严与肃穆底色。深而究之,南北两宋宴设地点由开放到封闭的空间转换,某种意义上又深刻折射出南宋时期国家逐渐丧失了北宋的些许自信与张扬,总体姿态上显得不够从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与风尚的内敛趋势。(21)参见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闻喜宴举办之际尚有皇帝所赐教化之类文墨篇章,大多是由皇帝书写的先贤圣文。淳化三年三月,闻喜宴日,宋太宗赐新进士孙何等御制箴一首,后又赐《儒行》篇各一轴,“令至治所著于壁,以代座右之诫”。(22)王应麟:《玉海》卷30《圣文·太平兴国赐进士诗》,第572页。《儒行》是《礼记》中的一篇,从挂于墙壁代座右铭之要求来看,宋太宗希望新科进士们以儒家的标准来规范自身言行,做到修身正己。此后,闻喜宴日,赐新科进士先贤圣文成为宋代历朝的惯例,所涉不外乎四书五经范畴,注重其中所展示的修身规范和为臣之道,具有极其深刻的警戒意味。领受以帝王为引导的谆谆教诲,对于即将踏入统治阶层之列的士子们而言,可谓是首次,也是较为深刻的训诫,寄托着国家对人才选拔的良苦用心与期冀。
二、宋代闻喜宴的官方宣传
宋代闻喜宴的设置规格与仪礼细节相当引人注目,不仅意在营造宴会场面之盛大且隆重异常的热烈气氛,更在凸显士子及第之后的无上尊崇与荣耀。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宣传效应更是不容忽视,与宋代国家以文治国的基本策略高度契合,蕴含着十分浓郁的政治色彩。
第一,闻喜宴注重细节设置,行簪花之礼是典型。簪花即戴花,所谓“幞头簪花,谓之簪戴”。(23)《宋史》卷153《舆服志》,第3569、3569—3570页。进士行簪花之礼始于唐朝,唐懿宗时“宴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盒,遣中官驰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饮酒,’”此举“世以为荣”。(24)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4《科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5册,第512页。以上记载并未明确指出是赐花于每位进士抑或仅为某种象征性举措,但赐花之举却影响深远。宋代沿袭了簪花之礼,程式愈显复杂,也更趋于完备。关于簪花之礼,宋代规定:“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其中,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锡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25)《宋史》卷153《舆服志》,第3569、3569—3570页。不难看出,闻喜宴上行簪花之礼属于国家规范的礼制范畴。与此同时,闻喜宴赐花的仪礼程序也有着十分具体的要求:“人赐宫花四朵,簪于幞头上(花以罗帛为之),从人下吏皆得赐花”,“又到班亭下,再拜谢花,簪而谢之。兼坐带花”,退场之时“皆簪花乘马而归”。(26)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0《置状元局》,《全宋笔记》第8编第6册,第273—274页。从赴宴赐花到拜谢花礼、簪花乘马而归,无一不充满了喜悦与荣耀,可谓是载誉而归,荣宠至极。
对于宴饮簪花所具有的政治宣传意涵,朝臣们也是了然于心。庆历年间,侍御史知杂李柬之指出:“本朝故事,赐宴推恩,赴座臣僚所赐花并戴归私第,在于行路,实竦荣观,耀于私门,足为庆事”(2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45之12,第1725页。,可谓一针见血,意图相当明确。无论如何,闻喜宴簪花之举具有十分鲜明的视觉效果,世人因之受到强烈的刺激与激励,也是宋代国家创制此举的题中之义。传宣之下,赴闻喜宴、簪花作为一种荣耀性标志,无形中也就成为了普通士人的一大追求。当时社会就流传有所谓的赴省登科五荣须知,其中“三荣”便是御宴赐花、都人叹美(28)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0《赴省登科五荣须知》,第266页。,从侧面反映出世人对于新科进士赴宴簪花而归的艳羡与认可,某种意义上更显示出国家宣传手段的高妙与智慧。
闻喜宴还有所谓的探花郎之说。唐朝时期,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二人少俊者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使皆被罚”。(29)叶廷珪:《海录碎事》卷19《文学部下·科第门·探花使》,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宋人赵升认为“此唐制,久废”。(30)赵升:《朝野类要》卷2《探花》,第450页。事实上,探花郎的风俗到宋朝尚有余迹,且发生了些许变化。闻喜宴当天“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与唐人杏园寻花折花有所区别。宋神宗熙宁中,余中为状元,请求朝廷罢期集、废宴席探花,以厚风俗,执政从之(31)魏泰:《东轩笔录》卷6,《全宋笔记》第2编第8册,第46页。,此后少见探花郎的记载。闻喜宴上偶有探花郎折花吟诗之事也未可知。
闻喜宴簪花之举具有广泛而鲜明的宣传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从宴会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诗文中所见诸如:“名标金榜,喜仙桂之搴枝。宴洽琼林,分宫花而剪彩。共歌《既醉》,均被湛恩”(32)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9《赐进士闻喜宴御筵花酒果口宣》,《宋代诏令全集》第4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4页。、“柳染青袍,叨预天官之燕。花裁绛彩,更分禁籞之春,敢望微生,遽承华宠”(33)楼钥:《攻媿集》卷19《代新进士谢赐花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7页。、“香风遍袭于衣冠,淑景顿移于尊俎。事维循旧,宠实更新”(34)卫泾:《后乐集》卷6《谢赐花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533页。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流溢出浓郁的荣宠意味,又充满着对天子的感恩戴德之情。
第二,闻喜宴场面壮观且隆重,营造“科举盛宴”的规格与印象。早在唐代闻喜宴便成为一大盛事而备受瞩目,直到唐末黄巢之乱,曲江盛事才日渐零落“不复旧态矣”。(35)王定保:《唐摭言》卷3《散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宋代,受国家右文政策的影响,闻喜宴作为科考及第系列庆贺活动——期集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礼仪程序设置,还是场面气势之营造都达到了某种极致。天圣八年,身为昔日新科状元的宋庠参加了闻喜盛宴,兴奋之余,作《庚午春观新进士锡宴琼林苑因书所见》诗。诗文详细描写了所见闻喜宴的热烈恢宏场景,热情洋溢地赞颂道:“丛楹开玉宇,华组会琼筵”,“银珰尊右席(中贵人主宴),绿帻佐双笾(太官先置)。饰喜优坊伎,均恩醵礼钱(诸君子合钱以劳供帐优伶之费)。沼浮渑酒渌,坻聚舜庖羶。场迥歌声合,风回舞节妍”,“绨囊赍睿什(中席,使者以御诗驰赐),钿轴照儒篇(复镂印《大学》、《儒行》以赐)。宝思垂霓烂,欢声抃岳传”。(36)宋庠:《元宪集》卷8《庚午春观新进士锡宴琼林苑因书所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页。可见宴会上美酒佳肴俱备、音乐歌舞杂陈,众人举杯欢庆,场面热闹非凡。宋人杨侃曾经作《皇畿赋》一篇,不仅提及琼林苑,更是将“列席广庭”的闻喜宴作为一大盛事而着浓墨进行铺陈,并强调此举“盖我朝之盛事,为士流之殊荣”,一语道出闻喜宴所具有的独特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37)吕祖谦:《宋文鉴》卷2《皇畿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进士及第参加闻喜宴无疑是士人身份地位转换的重要标志,宋人王谠就曾记载,唐代宰相薛元超曾感叹平生三恨之一即有“始不以进士擢第”(38)王谠:《唐语林》卷4《企羡》,《全宋笔记》第3编第2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其中的无奈和惋惜之情在科举制度兴起伊始就已经相当浓烈了,更不论宋代科举取士繁盛之世。有学者就认为,这种强大的社会示范作用,影响了社会风气,使举国为之倾倒。科举激励了读书人的进取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普遍的观念。(39)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张希清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不容忽视的是,闻喜宴之日,例有御赐诗文,也是宋代为彰显郑重其事的重要举措。闻喜宴举办当天,皇帝通常会遣人赐御制诗文以示庆贺。南宋延续前朝旧制,依常例“皆赐御写经书一轴,或赐御制诗一首(临安府镌碑表装,赐宴时以分赐士人)”。(40)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0《置状元局》,第274页。所赐诗文多为应景之作,意在宣传国家文教之盛、勉励士子忠心报国、表达皇帝获得贤才的喜悦。《咸淳临安志》中就收录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帝闻喜宴赐进士诗20余篇。嘉祐四年,宋仁宗赐状元刘辉等人及第诗,对即将步入仕途的士子们寄予“思民善政”“惠体君情”之厚望。(41)诗文曰:“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并蹑云梯峻,联登桂籍荣。庇民思善政,慈惠体予情”。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35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册,第4400页。
三、闻喜宴蕴含的宋代国家治理策略
借闻喜宴而推行国家右文政策,不仅符合宋朝的祖宗家法,更有利于创造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呈太平盛世之景象。深谙国家治理之道的君臣更是不遗余力予以支持,闻喜宴场面之盛大热烈、仪礼程序之正式隆重恰是在此种基调下形成的,由此产生的社会宣传效应也是空前且深入人心的。
闻喜宴等科举系列庆酬活动对寒门子弟有巨大的激励效应。闻喜宴作为宋代国家的科举盛宴,很好地见证了寒士的崛起与世族门阀的没落。在官方的不断宣传和引导之下,以参加闻喜宴为典型代表的科举盛事就成为了激励寒门子弟的重要手段和突出方式,也是刺激寒贫士子跻身显贵阶层的不二法门,由此而产生了极其显著的社会效应。郑樵在《通志·氏族略》总序中直言不讳地说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而“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42)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宋代的科举策略,对于寒门子弟的刺激和鼓励作用不容小觑。宋人赵彦卫就有所谓“本朝尚科举,显人魁士,皆出寒畯”(43)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5页。之感慨,言语间流溢出些许叹赏之意,虽不免具有夸张之嫌,总体上却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宋代科举制度施行的实际状况。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对于科举考试的整体期待相对较高,“通过科举考试晋升统治阶层之列是无可辩驳的正途”作为潜行于社会的一种重要规则,日渐成为上至皇家贵胄、下到平民百姓的普遍认识,并且趋于根深蒂固。南宋时期,番阳士人黄安道“累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遂往来于京洛关陕之间经商为生,“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即便如此,适逢国家颁布开科取士诏令,京城诸位故旧依然责问道:“君养亲,忍不自克而为贾客乎?”(44)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6《黄安道》,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0页。很好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民众对于“科举及第为正途”的认识不仅一致,而且深刻,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明国家施行科举取士策略的社会成效显著。
巨大的科考效应,催生出了“榜下捉婿”风潮。宋代“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45)朱彧:《萍洲可谈》卷1,《全宋笔记》第2编第6册,第147页。,另有所谓“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46)彭乘:《墨客挥犀》卷1,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之说。从这个角度说,宋代科举不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还是一种笼络士人的怀仁制度,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治理方略。关于此,唐代欧阳詹就曾做过极其深刻的分析:“进士者,岂不言其可以仕进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终自上而利下者也?”(47)李昉:《文苑英华》卷693,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册,第3573页。无怪乎宋太祖曾经充满自豪地宣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4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二月戊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6页。,传递出统治阶层的治理筹谋与策略。
科举及第某种程度上还能避免产生潜在的社会动乱。宋代推行以闻喜宴为代表的科举盛事,不仅能够广泛吸纳人才,为国所用,更在于科举为底层民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众人汲汲求取功名,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贫苦寒门走投无路而引发的一系列潜在社会隐患。关于此,宋人王栐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49)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第239—240页。
王栐以汉唐时期社会所见叛乱之事为例进行对比,盛赞宋代广开科举取士之道,具有“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的奇效,是汉唐所不能企及的“御天下之要术”。广大应举参考的平民百姓,既是此种策略的执行者,也是受益者。正如有学者所说,科举成功者不仅改变了自身地位,也改变了门庭,促进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为统治阶层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此外,流风所及,科举在民间形成一种文化。将相无种,通过努力就可以得到成功,就是科举制影响下形成的广泛的社会理念。这种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普遍奋发进取的心理,激发了社会创造性,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成为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50)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张希清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第39—40页。
宣传之下,民间社会对于科考成功之后的反应更为强烈。进士及第后加官进爵指日可待,状元更是无比荣耀。洛阳人尹洙甚至宣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疆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备受瞩目,“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欢动都邑”。(51)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新科进士之间也会举行同乡会等宴聚活动。如嘉定元年,应中书舍人邹应龙之请,宋宁宗特许新科进士在御苑聚景园举办同年聚会。预宴者正奏名12人,特奏名17人,宗室取应1人,真德秀等人也参与其中。由邹应龙主盟,“调官较艺中都者三十人同席”。众人遍游御苑内翠光亭、会芳堂诸地,会素食五杯,流连之余分茶、劝酒七盏荤食(52)金盈之:《醉翁谈录》卷2《戊辰亲恩游御园录》,《全宋笔记》第10编第11册,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觥筹交错中共叙同年之谊,具有极强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宣传效应。
及第者衣锦还乡,荣耀异常。及第者荣归乡里地方,州县长官同样会举行盛宴予以款待,尤以状元最荣耀,所谓“文武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州县亦皆迎迓,设宴庆贺”。(53)吴自牧:《梦粱录》卷3《士人赴殿试唱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苏德祥为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宴席上伶人致语:“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5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6《贡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赞美之意不言而喻。其余及第者在乡里地方也是相当荣耀。如淳祐年间,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皆为三衢(浙江衢县)人,一时士林歆羡,以为希阔之事。杨彦瞻以工部侍郎守衢县,意欲大势宣扬,讲述前辈所传故事:“吾乡昔有及第奉常而归,旗者、鼓者、馈者、迓者、往来而观者,阗路骈陌如堵墙。既而闺门贺焉,宗族贺焉,姻者、友者、客者交驾焉。至于仇者,亦茹耻羞愧而贺且谢焉。”(55)周密:《齐东野语》卷16《省状元同郡》,《全宋笔记》第7编第10册,第270页。虽不免有夸张之嫌,但及第后所带来的荣誉与社会反响则不可否认,也是科举取士制度在当时社会拥有广泛认可度的绝佳证明。
结 语
宋朝对文治事业之重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尤为显著。蔡襄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56)蔡襄:《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反映出宋朝重视文治事业和重用文人的事实。宋朝官员选拔方式有五,分别为科举取士、恩荫补官、纳粟摄官、流外出职、从军补授(57)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其中“计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5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6,元祐元年八月辛亥,第9402页。通过科举考试确实为宋朝政府输送了大批德行出众的人才。宋代高级官员大多数为科场出身,《宋史·宰辅表》所列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比例达到92%。(59)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科举之盛为前代所未有。在此背景之下,围绕着科举取士而开展的系列宣传活动就显得不可避免,闻喜宴就是其中的典型。
宋代的闻喜宴无论是组织规模、礼仪程序、宣传程度还是社会影响力在历代科举庆酬活动中都是引人注目的,由此形成了独具宋代特色的科举系列活动仪程。在国家认可的名义下赋予闻喜宴以象征化符号意义,成为激励世人晋升统治阶层、以获得全新身份地位的一大盛事,是宋代国家治理方式多样化的重要体现。科举和出仕在造就和维护士大夫精英群体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他们在科举上的追求与随之而来的权力、声望有很大的关系,进而利用科举和出仕来巩固增强他们在文化和社会上的支配地位。闻喜宴的举行及其所见的社会反响,可以说是此种行为的初见效应。通过体验和赞颂闻喜宴,宋代士人更加强化了他们作为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导者的地位。(60)张聪著、李文锋译:《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宋代通过举行包括闻喜宴在内的一系列庆祝活动而达到“上行下效”的国家治理目的,成效是显著的。宋代以闻喜宴为典型的科举庆酬活动,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举行的恩荣宴更是与之一脉相承,在凸显及第之后的荣耀和帝王恩宠方面一以贯之,蕴含其中的深层政治意旨与宋代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传承之际愈发彰显古人在治国理政中的智慧与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