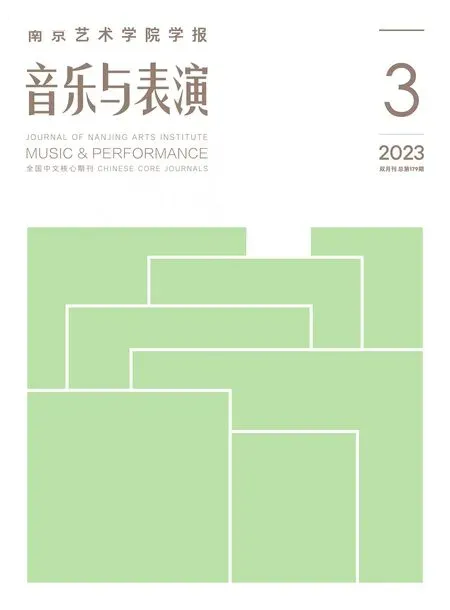认知民族音乐学①
2023-12-23欧阳平方
欧阳平方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北京 100007)(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关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如何制造、表演、记忆、理解、接收、感知、体验和使用音乐的问题,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关注的重要论域,即对作为文化的表演中的音乐认知研究,亦即认知民族音乐学(Cognitive Ethnomusicology)研究。认知民族音乐学是民族音乐学的重要分支,旨在将音乐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研究与人类认知研究相结合。其中,人的“先天性”(nature)心理生理因素与“后天性”(nurture)文化语境因素与之密切相关[1]3-4。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认识却非自始即有或一成不变,其随社会时代的变迁和研究范式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发展。梳析认知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渊源、研究进路、学科范式及其中国实践与未来探求,将会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该领域的理解与认识。
一、认知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界说
(一)何为“认知”:从语义分析开始
从词源学角度而言,“认知”概念是由英文词汇“Cognition”翻译而来,其词根“Cogn”源于拉丁语“cognoscere ”意为“to know”,即“知道”或“知识”[2]。从原文构词角度来看,“认知”(Cognition)是由词根“Cogn”(知道、知识)加上后缀“-ition”(行为及其过程)构成。可见“认知”概念作为认识论的关键词,不仅指涉本体论层面的知识,且涵括方法论维度之获取知识的过程内涵。此外,在《东西方哲学大辞典》中,“认知”被释义为“最广义的知识,既指认识活动或过程,又指知识本身,它包括知觉、记忆、直觉和判断”[3];《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将“认知”解释为“通过思维活动认识、了解”[4]等。
在上述概念释义中,“认知”常被暗指为存在于人头脑中形成的抽象思维、观念、记忆、言语、想象、经验、感觉、知觉等,与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及认知过程相关,涉及人认知事物的生物性本能(“先天性”生理心理因素)和文化语境(“后天性”社会文化因素)问题。前者与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实证量化研究相关②尤其是在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和演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等领域。,后者与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实践研究勾连,二者均与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密切相关。
(二)认知科学:从“离身认知论”到“具身认知论”
认知科学是一门随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之变革及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的介入而兴起的关于人类心智研究的跨学科交叉科学[5]。它发端于20 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充分肯定人类意识与心理现象的自主存在,并主张以控制论、信息论之模型对其予以建构与研究[6]。
20 世纪70 年代,认知科学正式诞生。1978 年,斯隆基金会报告(Sloan Foundation Report)提出了有关认知科学之跨学科交叉关系的“认知科学六边形”,即以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与哲学六门学科作为认知科学的主干[5]。认知科学虽是交叉科学,然整体上却奉行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7]1308-1309,即以“表征—计算主义”(representation-computationalism)作为主流的研究纲领,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H. Gardner)将其称之为“第一代认知科学”[8]6。
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受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主张的实证、理性思维影响而形成,将人的心智活动视作可独立于人的身体、可被操作的抽象符号信息的表征与计算,即“离身认知论”(disembodied cognition),其历史根源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身心二元论”。当然,认知科学家们很快即对其进行了反思与质疑,发现基于“表征—计算主义”的认知研究因排除了语境、情感、传统习俗等“干扰”因素[8]7-8,而面临对特定文化环境与背景知识的形式化计算和解释人类如何获取“意义”之机制等困境[7]1310-1311。例如,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G.Lakoあ)和约翰森(M. Johnson)指出“非具身”的哲学传统忽视了“身体”在人类认知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9]24。而正是基于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促发了20 世纪80 年代在认知科学领域出现的“第二次认知变革”,并催生了一种以“具身认知论”(embodied cognition)①“embodied”在中文翻译语境中,又做“具身”“体现”“缘身”“涉身”等不同的解释。为研究纲领的“第二代认知科学”(second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9]37。
第二代认知科学摒弃了“工具理性”的“表征—计算”,认为人作为心智活动的主体是一种自然、文化、体验、生物、感官且活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存在”,不存在独立于身体(大脑)的心智活动。同时,注重将人的心智活动与生物学、社会学因素相关联,倡导一种“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系统的”(dynamic system)认知观念,去探究人的认知活动是“如何基于、体现于和实现于身体的”[10],即“以身体为中心”。
追溯“具身认知论”的思想渊源,可知它同西方哲学领域兴起的反对“身心二元论”思潮相关,其观念出自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等人创立的“第一现象学”与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 Peirce)等人开创的“实用主义”传统,并充分吸收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与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人有关具身认知的思想。其中,梅洛—庞蒂提出的“知觉现象学”是具身认知思想最直接的哲学渊源之一,认为人类主体是一种“身体—主体”(body-subject),人类对外部事物的认知直接就是“我的身体的某种知觉”[11]538。
虽说梅洛—庞蒂倡导的“知觉”与“具身性”思想值得肯定,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对听觉问题的关注,强调的“知觉综合”难免存在“以偏概全”之嫌(即仍以视觉为主)。而这也孕育了以“听觉知觉”和“声音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声音现象学”(phenomenologies of sound)[12]6的出现。当然,上述国外哲学家有关“身心关系”的观念,均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强调“身心一体”之理念相吻合,亦即“身即心之身,心即身之心”。
(三)文化与行为的认知研究:一种认知人类学视域
认知人类学形成于20 世纪50 年代,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与思维之互动关系的交叉学科[13],旨在识别不同文化中的人之认知模式及其共同性与差异性[14]。“认知”作为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生物本能在早期阶段是无法依赖于文化因素的,但其在人类成长阶段的认知模式则受不同文化因素影响[15]。认知人类学注重强调文化之观念性本质,在美国人类学家古迪纳夫(W. Goodenough)看来,文化是指人们大脑中关于事物的形式,即感知或理解人类行为的模式[16]。此外,与认知人类学相关的民族志不再是传统民族志式的描述表象,而是以“新民族志”去“靠近”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他们自身周围世界表象背后的认知结构[17]。
认知人类学研究主要涉及语义学、知识结构、模式与系统、话语分析四大领域,其中与文化有关的认知模式与认知系统研究始终是认知人类学关注的热点[18]。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相关的认知分析不仅注重人们的言语(语言结构),且关注人们的身体行为与情感表达及相关文化语境,而这与美国阐释人类学家格尔兹(Cliあord Geertz)主张从不同文化语境中去关注人们认知与理解世界之方式[19]的观念是一致的。
概言之,认知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整体上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并行的研究范式。而当这种研究视域投至音乐认知研究领域时,前者往往注重从人的生物性本能出发去探究人对音乐的认知过程,后者则倾向于借鉴“理性主义”的实证量化研究方法去关注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如何形塑人的音乐认知,进而阐述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对音乐认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虽说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仍主要以“理性主义”(认知心理学)与“经验主义”(认知人类学)两种范式为基础[20],但它绝非二者的简单综合,而应是一种聚焦音乐、文化、认知、生态、生物属性等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多元研究态势。
二、聚焦生理心理因素的实证音乐认知研究
民族音乐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均有对不同文化中的人的音乐认知过程(即通过音乐来获取对“人性”的理解)的关注。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时期主要借鉴实证心理学(empirical psychology)研究范式,聚焦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去探讨人的音乐认知过程,侧重对人的音乐感知和记忆进行实证分析。
学界对人类音乐认知过程之生理心理因素方面的探索,同19 世纪出现的基于实证量化分析的科学心理学相关,这直接体现在其时心理学领域涉及的音乐感知研究。例如,德国生理学家亥姆霍兹(Hermann L. F. Helmholtz)提出了“听觉共鸣理论”(resonance theory of hearing)[21]。随着实证心理学理念在比较音乐学领域的应用,有关人如何处理、理解和记忆音乐的生理心理机制亦随之展开了初步的实证性研究。作为比较音乐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音乐学家施通普夫(Carl Stumpf)对人们的音高听觉体验进行了分析研究[1]3;美国音乐心理学家卡尔·西肖尔(Carl E.Seashore)通过实验测量手段将“音乐才能”测试方法(そe Measurement of Musical Talents)运用于音乐教育和音乐技能训练之中[22]等。
自比较音乐学时期以来,不论在欧洲学界还是在北美学界(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重新重视),人们对音乐认知过程之生理心理因素的探索从未止步。其中,第一代认知科学更是进一步助推了有关音乐认知过程的生理心理运作机制研究,相关研究主要沿着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发展:在理论方面,主要根据听觉的“神经感知肌肉互动”机制,结合实验测试、实证数据分析手段,研究人对音乐接收、理解与记忆的识别与反应等问题;而在应用方面,相关研究成果亦正运用于表演、创作、教育、治疗等方面[1]4-5。譬如,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多伊奇(Diana Deutsch)从实证角度对音乐与语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二者在大脑接受认知体系中关系极其密切[23]。挪威音乐学家戈多伊(Rolf Inge Godoy)指出动作是音响感觉与视觉感觉的媒介[24]等。
应当指出,上述有关人类认知音乐的普遍性生物本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构筑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之上去探索人类创造和接收音乐的生理心理机制(即生物学意义上的音乐认知过程),但其推论多是构筑在那些被“数据化”了的“冷知识”之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在音乐认知过程中的语境、情感与身体等因素。纵然在认知音乐心理学研究中也意识到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的作用,但其时对文化语境因素的研究实则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25]2。
三、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音乐文化认知研究
在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音乐文化认知研究中,语境、情感与身体行为体现等因素对人的音乐认知过程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范式强调社会文化、情感因素和身体行为如何形塑人的音乐体验与认知模式,并以“新民族志”的方式将局内人的音乐言语方式与身体行为作为认知研究的逻辑起点。
20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正式确立及其在北美发展过程中受“文化相对论”之影响,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融合了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交叉学科理论,其研究多倾注于人类学式的民族志个案描述,彰显的是不同文化主体的音乐认知差异。同时,该研究范式着重将音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强调通过参与观察与体验等方式,关注文化语境、情感因素和身体行为等因素对人类音乐认知过程的形塑及影响。
其中,梅里亚姆(Alan.P.Merriam)强调了“音乐概念化”研究的必要性,即如果没有与音乐相关的概念,音乐表演行为就无从发生,音乐声音也就不可能产生[26]33,认为音乐研究首先要对其概念体系进行界定。而概念体系是指一种宏观统筹层的解释体系,直接关涉人们运用什么概念体系来创造音乐,又是如何运用语言来言说音乐的,其与人的音乐认知思维休戚相关,亦即“没有对概念的理解,就没有对音乐的真正的理解”[26]84。此外,西格(Anthony Seeger)指出苏亚人的音乐分类方式正体现了他们的音乐观念与社会结构方式[27]。菲尔德(Steven Feld)发现卡路里(Kaluli)人是根据声音来辨识鸟类,认为鸟类世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隐喻,是当地人感受声音的观念性动力[28]79-86。内特尔在对Blackfoot 相关音乐思维和概念的研究中,应用了梅里亚姆的概念化研究模式,通过当地人对音乐的言谈信息、音乐表演行为去获取对当地人的音乐认知模式的理解[29]。日本学者山口修对贝劳人的音乐舞蹈分类、音乐中的时空观念、音乐用语及音乐形成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30]等。
民族音乐学倡导将“音乐作为文化”,其中与其“文化”最为密切的是其作为表达思想的语言,故用语言来“言说”音乐被视为文化语境中的音乐认知过程之映射,即音乐结构是音乐思维的一种体现。因此,通过对音乐局内人表演行为相关的语言表述方式进行收集与整理,阐释局内人如何用语言表达音乐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音乐认知过程,成了学界普遍认可的音乐文化认知研究路径。[31]例如,美国学者休斯(David Hughes)运用语言学的传递生成理论分析了爪哇甘美兰音乐的传递规则[32]。
透过上述的文献梳析,可见有关民族音乐学的音乐认知研究多是受梅里亚姆之“概念—行为—音声”模式的影响而倾向于对音乐的概念化研究。虽说音乐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与音乐认知是相符的,但二者定然是不能等同的。对此,赖斯(Timothy Rice)认为,梅氏提出的“概念”定义不能被“认知”一词取代[33]。在芬兰学者莫伊萨拉(Pirkko Moisala)看来,音乐认知涉及的领域包含了音乐文化的全部的认知特性,不仅涉及音乐概念化的内容,还包括音乐制造的动力、表演行为、形成过程、结构方式等,这些内容亦均体现在她对尼泊尔古隆人的音乐文化认知研究中[25]11。
应当说,长期以来的音乐概念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认知人类学思潮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布莱金(John 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在某种层面上属于认知人类学的分支学科,音乐是人的认知过程的综合结果,且是在文化中和人类的其他客体中显现出来的[34]。但需说明的是,纵然注重社会文化因素的音乐文化认知研究深受认知人类学的影响,但它肯定不同于认知人类学,因为它始终聚焦的是对作为文化的音乐的认知研究。当然,学界针对20 世纪中期以来学科在北美发展过程中因注重强调音乐认知过程中的文化因素,而忽略对人类所共有的生理心理之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如美国心理学家哈沃德(Dane L. Harwood)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探讨了不同文化中的人之音乐认知过程的普遍性(universals in music)问题[35]。
其实,生理心理与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音乐认知均不可或缺。布莱金认为,认知是从“文化性”和“生物性”两方面发展而来的[36]。对此,英国学者贝利(John Baily)提出对音乐认知的研究需将心理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主张[37]。但莫伊萨拉(Prkko Moisala)指出在认知民族音乐学领域,若仅统合人类学和心理学是不够的,应确立适合于把音乐的认知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发展模式、方式和技术,即“将音乐作为认知”[25]23。
四、注重音乐表演实践的具身音乐认知研究
人的身体经验和情感经验在音乐认知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身体经验体现了人对音乐的接收过程,也是音乐表演的重要媒介,它通过语言的隐喻而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20 世纪50 年代以后,民族音乐学界逐渐意识到了人的身体经验之重要性。其中,胡德(Mantle Hood)提出的“双重乐感”(Bi-Musicality)肯定了人的身体经验的意义,并倡导在“具身”参与实践基础上开展研究[38]。相较于胡德,梅里亚姆进一步论述了音乐行为(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唱奏表演行为)的四个维度,阐述了身体行为与音乐观念之间的关联性,并表明有关身体产生声音过程、音乐家表演姿态和观赏者身体反应在未来研究的重要性[26]103-110。但需指出的是,梅氏仍因时代之局限性——受制于当时身心二元论的哲学思潮影响,低估了身体行为体现的重要性,而将身体行为限定于概念之下。
对“作为文化的音乐”进行认知分析需面对的现实是,“音乐作为文化”强调的是社会文化语境,认知过程注重的是人在大脑中的思维模式,但我们不可能进入大脑中去探究其发生了什么,加之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口头传统的活态音乐。所以我们不得不将人类的用乐表演实践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回归至人类组织声音的呈现过程,即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音乐表演现场,并关联音乐的表演场景、行为体现和声音结构,以及与音乐相关的言谈信息等。因此,“具身认知论”和“表演理论”(Performance そeory)对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存在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民俗学家鲍曼(Richard Bauman)指出,表演是一种“说话的模式”和“交流的方式”,并注重“以表演为中心”去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生成过程[39]。作为口头传统的音乐,只有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得以存在和现实化,文化也只有在为人类所表演的过程中得以呈现。布莱金重视人的身体表演行为在音乐制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倡导从声音制造的“过程中”去探寻音乐[40]。莫伊萨拉认为音乐表演是被当作为一种文化的微缩模型,社会关系、文化价值、文化意义在其中均得以彰显,声音出现的刹那便是文化和声音被转化入音乐内部链接之中去的时刻[25]28,这亦正如美国学者赫顿(Marcia Herndon)所言之音乐表演是音乐文化认知的具像化表征,认知形式不仅体现在音乐场景中,也体现在音乐结构的骨干构架中[41],故需将音乐放置于与表演相关的语境及其行为过程中予以分析。
在音乐的表演实践中,人的身体经验(具身性)体现了人对音乐的接收过程。加拿大学者沃克尔(E.Margaret Walker)认为“具身性”是对“身体—概念”(body-mind)关系研究的重要维度,强调表演行为是思想观念与客观环境(音乐的声音)的媒介,人们通过具体的行为动作而赋予音乐以意义[42]。美籍华人荣鸿曾(Bell Yung)认为对于音乐经验的分析需要考虑听觉、视觉、肌肉运动知觉的综合因素[43]。英国学者克莱顿(Martin Clayton)指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与交流常通过特定的身体行为动作来完成,表演者的“具身”体现是声音呈现的一种延续与补充[44]。此外,赖斯认为对一种音乐文化传统的习得与认知实则是一种社会化、身体化的过程[45]等。
至此,音乐表演实践与“具身性”在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音乐表演民族志”的必要性,可见一斑。但对音乐表演的研究,确切地说,其研究对象并非聚焦于表演实践与风格、语境或其产物,而是作为文化的表演中的音乐[25]77。
五、从声音现象与听觉体验出发的多感官交互音乐认知趋向
人作为一种生物性存在,“身体”的感官与知觉(一种多感官交互的知觉综合)是人认识世界的根本途径。虽说听觉与视觉是人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然长期以来人们对事物与现象的认知与识别却多以视觉为主,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视觉主义”(visualism),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为知觉的听觉”和“作为听觉现象的声音”[46]。
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民族音乐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视觉主义”之影响,这一时期的音乐民族志写作多以视觉为基础的现象描述与阐释。当然,这与研究“他文化”音乐时所存在的“听”之困难有关,但究其哲学历史根源,则是与“视觉主义”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占据的主导地位相关联。即便在梅洛—庞蒂提出的“知觉现象学”那里,很大程度上仍以视觉作为“知觉综合”,认为“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11]6,而忽略了对听觉的重视。但是,“聽”一个社会往往会比看一个社会更能深入其现象学的实质,因此“聽”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认知的路径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47]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人类学界的“表述危机”深刻影响了民族音乐学的发展,相关学术研究旨趣亦随之发生转向,即注重倡导一种关注听觉感官、聆听体验、声音现象与生态环境为主的音乐民族志写作。其中,加拿大学者谢弗(R. Murray Schafer)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了“声音景观”(soundscapes)的概念和“声响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的研究计划[48],将以往在视觉认识论研究中被忽视的听觉感官和声音现象,放置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活世界中予以阐析,进而揭示声音体验和听觉感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态之间存在的意义,为声音现象、听觉空间与感官文化的研究拓展了新面向。
在谢弗的声景研究视域中,“声音”实则溢出了“听觉”,即凸显了声音的空间维度,而将声音现象视为一种与人切身接触的环境,将听觉活动视为一种空间中的生活实践与身体经验[49]。菲尔德从“声音民族志”(ethnographic study of sounds)角度意识到声音知识与听觉经验对卡路里(kaluli)人存在重要价值,故强调声音认知的重要性[28]7-12,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声学认识论”(acoustemology)[50]的观点,认为卡路里人对声音的体验既是“身体”觉受的,又是视听相关、动静相关、时空相关以及共时与历时相关的[51],强调了声音与其他感官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全息式”的身体感官认知经验。
值得提及的是,美国现象学家唐·伊德(D. Ihde)深刻批判了以往根深蒂固的视觉认识论,肯定了听觉感官体验与声音现象的重要性及其在现象学领域的不可或缺性。他以自己的听觉体验、聆听实践与声音感知及其相关反思为研究基点,围绕聆听与发声、理性与感性、体验与阐释,系统地构筑了一种走向声音、听觉感官经验的现象学路径。在他看来,对声音体验和听觉感官的强调并非另构建一种“听觉主义”,而是通过“整个身体”对声音进行感知[12]81,即身体感官之“通感”(多感官交互),亦即用“整个身体”来“听”[52]。
可见,国外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动态、多面向的发展态势。社会音乐文化的变迁,人的音乐认知模式亦随之生变,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动成了与之相应的研究策略。进入21 世纪,认知民族音乐学得以继续发展与扩展,相关研究在跨学科基础上更加强调音乐体验的文化与社会层面,涉及音乐、文化、认知、生态、生物属性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问题,如探讨音乐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音乐实践如何被社会与文化实践塑造、音乐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音乐表演中的即兴性所涉及的认知过程等。
六、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
国内学界有关音乐的文化认知研究多是未冠以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之“名”,但却有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之“实”,并聚焦于音乐用语表述与认知观念、音乐表演实践与身体感官认知、音乐结构与思维模式、理论范式与方法译介等研究取向,整体上体现了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中国经验。
(一)音乐用语表述与认知观念
中国传统音乐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音乐用语表述体系,除记载于历代音乐文献之外,仍多以口传之方式承传和应用在各地方民间音乐活动中,涉及传统音乐的分类体系、乐器形制、表演行为、习得方式、承传模式、创作体系、观赏关系、本体形态与认知体系等维度,是局内人音乐认知观念的体现。对音乐用语的关注成为理解音乐文化事象及局内人音乐认知观念的重要路径。国内学者对此多以局内人对“音乐”和“声音”概念的区分、本土音乐分类、特定音乐行为体现等方式切入对局内人音乐文化认知模式予以理解。
在中国民间音乐调查研究中,不乏对“原生性”民间音乐用语的记述与阐释。例如,程茹辛围绕“音乐本体”规律对民间乐语的收集与分析,并呼吁学术界对民间乐语进行收集与整理[53]。在少数民族音乐领域,如何芸、简其华、张淑珍于1959 年执笔的《苗族芦笙》《苗族民歌》[54]通过汉字借音、国际音标的方式较早对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歌曲、芦笙乐舞之民间表述进行了记录与分析。此后,沈洽对基诺人的“声音”“音乐”观念、音乐分类方式进行了解读[55],对音乐观念之民间表述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分析[56]。此外还有赵塔里木对蒙古族额鲁特人的音乐观[57]和中亚东干人的音乐分类方式及其表述体系进行了研究[58],以及何晓兵对白马人音乐观与表达方式的分析[59]等。
进入21 世纪,有关音乐用语与认知观念方面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樊祖荫指出,音乐术语是音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音乐的分析与描述需构筑在对传统音乐术语(包括民间习语)的学习、熟悉与运用,以准确表达用乐者的文化观念和对音乐的认知,正确反映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来面貌[60]。同样,萧梅认为“作为音乐概念与行为的高度抽象与凝练,‘术语’意味着观念与认知结构……是当事人主体对音乐的认知和实践经验的升华,是中国音乐‘民间知识体系’的源泉。对其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当事人主体的立场加深对传统音乐文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探讨”[61]。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音乐领域。可见,关注特定文化中的人之言说(表述)音乐方式的重要性、必要性与挑战性,而这正是我们对不同文化中的人之音乐认知观念予以理解的内驱力。
(二)音乐表演实践与身体感官认知
在民族音乐学的田野作业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特定文化中具有活态性、表演性、过程性的声音(音乐)文化现象[62],对其理解与认知不能局限在以“看”“听”为主的视听感知层面,而需置身心于其特定文化中“具身”参与表演实践,并通过身体综合感官之“体认”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局内人的音乐认知模式和音乐知识。对此,管建华强调了音乐人类学与哲学身体观念下的身体研究范式在音乐文化认知方面的重要性[63]。
研究者往往会通过田野作业中的“具身体现”(embodiment)和“具地体现”(emplacement)[64],以试图在多感官的基础上与文化当事人获得“通感”(correspondences)[65]。例如,萧梅阐述了“音声民族志”的“体验”问题[66],讨论了音乐学者在面对研究对象的体验、表述及其意义如何“缘身而现”的问题[67];她倡导“回到声音”和“从感觉出发”[68]。以“身”(body)作为“樂”之蕴体[69],并通过研究仪式与音乐研究中不同的身体观,提出了“缘身性”(具身性)在思想—行为的互向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70]。齐琨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声音经验的回归与身体感官之间的关系[71],并提出“声音建造—听觉感受”双向研究模式[72]。博特乐图立足以“表演为中心”对蒙古人的口传思维与认知模式进行分析[73],旨在探讨音乐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思维与行为机制[74]。此外,徐欣、高贺杰、矫英、李亚、朱腾蛟等人均从不同角度对音乐表演实践与身体感官认知方面进行了研究,而这些研究实践与近年来国内音乐学界兴起的“声音生态学”或“生态音乐学”,注重从生态视角去关照音乐表演、声音环境与感官体验的研究理念相关[75]。
另有学者对田野工作中的感官认知方法进行了学理分析,如黄婉指出“表演观察”的方法强调在“体验”中生成认知往往能探寻到“隐匿”的地方性知识,“学习表演”可获得局内的音乐性、音乐习得方法与音乐认知[76]。李萌瑜运用“学习制作”的田野工作方式,结合“感官转向”的观念,对新疆冬不拉进行了多重感官认知分析[77]等。
(三)音乐本体与思维结构
音乐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存在于人脑之中,本质上反映了人的思维结构与认知模式,音乐本体结构与人的思维结构存在密切关系。通过对音乐本体结构的分析,探寻音乐制造者的音乐思维模式是一条重要研究路径。
其中,樊祖荫立足中西多声音乐形态的思维模式,以“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分别就中西多声思维与结构差异进行了概括与分析,认为二者本质的差异是囿于中西双方对音乐“和谐”的认知思维方式之不同[78]。萧梅从表演切入对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与音乐形态关系进行探讨,指出通过对身体实践与表演过程的描写分析,捕捉传统音乐特征与局内人音乐认知,以拓展形态学之分析维度[79]。张伯瑜认为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音乐本体分析多是“局外人”的分析,而主张寻找一种“靠近”局内人的分析路径[80],即采用音乐制造者在音乐制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音乐结构[81]。应当说,这种研究理路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用乐文化主体的认知模式,亦在研究之中彰显了对音乐文化主体性的关注。
此外,杨高鸽从认知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山西省河津丧葬锣鼓的节奏构成模式进行了认知性分析[82];赵卓群将伊朗布什尔“赛之和达曼”仪式音乐的音乐本体、表演程序作为“音乐模式”并放置于音乐变迁的线索中探索“音乐模式”与“认知模式”的关联[83]。潘永华从局内人视角发现侗家人内部存在一种以“哎呜所”为划分标准的曲式结构,以此对侗家人有关侗族大歌结构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分析[84]等。笔者在对黔东南苗族音乐的“人声”与“器声”本体分析中,注重将其音乐本体构成关联到与之相应的音乐表演场景、苗家人有关音乐的言谈信息描述,通过“具身”参与苗族音乐表演实践,以尽可能获取对苗族音乐及苗家人“曲调认知模式”的理解,亦即试图进入到苗家人制造音乐的认知模式中去“挖掘”“贴近”他们制造音乐的“知识体系”[85]。
(四)对国外认知民族音乐学著述译介与理论读解
认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本土化实践过程中,与之相关的著述译介与理论读解是其重要领域。其中,赵志扬对意义的理论及其与音乐认知的关系进行了译介,指出在音乐结构中不存在固有的意义,而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浸染使其拥有的[86]。张伯瑜对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呼吁研究者需采用一种可用来分析与文化相关的音乐过程的方法进行研究[20]。杨民康认为在音乐民族志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带有认知音乐人类学—阐释(符号)学学术倾向的分析视角(或路径),即:始自语用学(语境研究)止乎于语义学的视角和始自语义学以形态学为终端的视角(或路径),而中国学者的研究现况则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上述两种学术路径及分析思维[87]。
当前,国内学界已翻译不少国外认知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经典著述①代表性译著如:《音乐中的文化认知——尼泊尔古隆人音乐的延续与变化》(2017)、《在那山水歌唱的地方——图瓦及其周边地区的音乐与游牧文化》(2021)、《Ethnomusicology 理论与方法英文文献导读》(2019)及其续编(2022)、《愿它充满你的心灵:体验保加利亚音乐》(2014)、《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12)、《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1999)等。,同时亦有不少学者对这些国外著作进行了评述,且评述者往往在通过那些著作去观察其中涉及相应族群的音乐认知过程时,会不自觉地反观自身所持有的音乐认知观念和检视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如张伯瑜对《音乐中的文化认知》[88]一书进行了全方位读解,加深了我们对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理论与范式的认识[89];博特乐图在《在那山水歌唱的地方》[90]一书中体察到图瓦人的音乐思维模式,即源自于牧民对自然万物的感受、认知、模仿、聆听、体验与阐释,并对该著的记述式写作方式进行了讨论[91]。又如,徐欣在对唐·伊德《聆听与发声:声音现象学》的评述中,指出声音的意义是在聆听中自行敞开,人对声音的认知体验并非单向度地作用于听觉,而是以整个身体来进行体认与感知[92]。另有李亚、郝苗苗、朱腾蛟等学者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界有关音乐表演与认知、身体—感官经验、歌唱表演与听觉感知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析与读解。
除上述以外,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有关作为文化的表演中的音乐认知研究还涉及音乐教育、传播、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领域的具身认知应用层面,它们共同展示了认知民族音乐学领域涉及的广度与多样性,并为音乐体验和感知的复杂性提供了新见解。
七、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思考与未来探求
透过中国学人对认知民族音乐学在本土化实践中所作出的积极探索与经验建构,可见相关研究视角、方法、过程及成果的丰富与多样,但其中也显现出一些尚需我们进一步加强、重视、思考与完善的地方。
其一,要重视音乐本体与思维模式的关联分析。音乐与思维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音乐本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人的思维模式。虽说这种认识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且在观念上亦逐渐达成共识,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却褪色不少。大多数的音乐本体分析仍无法摆脱借鉴西方音乐理论的分析模式来进行解读非西方音乐(或运用汉族音乐分析方法解读非汉族群音乐)的本体形态特征,即基本上是一种局外人的分析[80]。当然,并非说此类音乐本体分析毫无价值,因为对分析者所属文化内部的人来说也是有助于他们对特定音乐的理解,而我们似乎亦无法真正做到进入局内人制造音乐的思维之中,但此类分析之于局内人而言究竟有何价值的问题则仍需深思。
对此,有学者提出要尝试进入局内人的思维模式对音乐本体予以认知性分析[81],但音乐本体与思维模式的关联性究竟有多大?二者又如何关联与体现?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具有“本体论”“认识论”之意味。笔者认为,长期、深入田野工作是其必要的研究前提,而通过参与观察、感官体验、聆听实践、对话交流等方式,将音乐本体的呈现(制造)过程关联到相应表演场景、局内人言谈信息描述,再以“具身”方式去观察和学习其音乐表演实践,或许是一条“接近”局内人音乐思维模式的可行性路径。
其二,需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身体感官认知分析。对此问题的认识需将研究视域投至于我们的“身体”,或许我们均承认身体感官认知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重要性,比如歌是唱、喊出来的,舞是跳、动出来的,乐是奏出来的,与之相关的歌俗、舞俗、乐俗更是通过表演者的身体行为而呈现[93],并强调一种知觉综合的“身体感”。但在我们既有的音乐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实则仍缺少对中国传统音乐之身体感官认知予以分析的勇气和信心,而多是对其进行“结果性”“客体化”的音乐文本分析。对此,我们需要将“音乐”还原至“声音”,将其视作一种声音现象与存在过程,并用“整个身体”对其予以体认与感知。
其三,完善对中国传统音乐用语的收集、整理和语用分析。虽说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对“音乐作为文化”的理念已获普遍共识,但对如何将“音乐作为文化”的问题,研究者往往是将其“泛而化之”。其实,音乐用语是文化最为直接的外显,它蕴含丰富的传统音乐知识,也是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音乐用语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不仅有助于正确地还原中国传统音乐之面貌,且有助于中国音乐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总之,认知民族音乐学是一个丰富而复杂且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可以其跨学科方法对音乐体验之文化和社会维度的关注,以及探索音乐、文化、认知、生态、生物属性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其予以表征。当前,虽说与音乐认知相关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国内已受到学界同行的渐进关注,但学界对作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研究理论与范式的讨论及相关研究实践,实则仍处在一个需不断探索与完善的阶段。这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未来发展留下了较大的学术创新空间,同时亦明确了未来我们需予以继续关注、并为之努力深耕的学术研究阵地。
(感谢恩师樊祖荫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