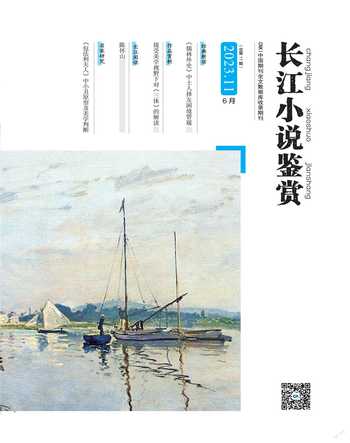从《母亲的岛》《寻暖》看女性自我价值追寻
2023-12-20何文琴
[摘 要] 陶丽群在《母亲的岛》《寻暖》两部拐卖题材的小说中,采用被拐卖的女性的女儿作为第一叙事视角,聚焦于被拐后的母女关系。被拐卖的女性被迫成为“母亲”,她的身上缺乏妻性的同时母性也不足,而女儿作为母亲悲剧的产物和见证者,深受拐卖的次生伤害,异化的母女关系和代际创伤正是拐卖造成的痛苦的延续。母女二人被压抑的自我感与现实中的失落感结合,最终引发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小说中的女性进行了自救与互救,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出走的方式开启了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自我追寻。
[关键词] 《母亲的岛》 《寻暖》 母女关系 女性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46-04
在拐卖的过程中,“中间人”或“媒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间人”将女性拐骗到手,再转卖给买主,一场交易就此画上句点,而被商品化、物化的被拐女性,要经历的痛苦才刚刚开始。《母亲的岛》和《尋暖》两部小说将拐卖事件的前端模糊化处理,把目光聚焦到被日常生活驯化的被拐女性与其子女身上。此时的被拐女性已经成为母亲,在拐卖的持续阵痛下默默隐忍地生活着,而被拐女性的子女作为母亲悲剧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本身正是拐卖的产物和目的,是致使母亲被拐、遭受痛苦的隐秘原因,也是被拐女性难以割舍的心理寄托。
母亲和女儿作为一对“同性异体”,称之为与生俱来的最亲密的同性关系也毫不夸张,然而,正如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中指出的,母亲与女儿之间也存在“厌女症”,实际上很难达到相互之间应有的性别认同与情感共鸣[1]。陶丽群在《母亲的岛》和《寻暖》两部小说中,将母女关系这一命题放置在拐卖的语境下,小说中拐卖来的母亲及女儿之间总是呈现出或淡漠疏离,或紧张分裂的情绪关系。母女间的代际创伤实则是拐卖造成的悲剧延续,母亲是在遭遇拐卖后被迫成为“母亲”的,女儿是母亲悲剧的产物和见证者,母亲抵拒“母亲”的身份枷锁而坚持追寻自我,女儿选择做“父亲的女儿”变得麻木缺爱,二者同时面临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由此可见,拐卖事件中母女关系深度异化,对母女造成的身心伤害是难以度量的,拐卖的悲剧会波及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和家庭,作者因此生发出对拐卖影响下母女间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当代女性自我价值的追问。
一、拐卖中的母女悲剧:异化的母女关系
1.被拐卖来的母亲
在拐卖的链条中,女性被物化,成为一件商品被人挑来选去、讨价还价。在“中间人”眼里,女性是赚钱的工具,在买主眼里,这些女性是生育工具和劳动力,拐卖事件的发生伴随着对女性个体价值的剥夺。女性在尚未成为“母亲”之前遭受拐卖,成为交易的商品,她的个体价值粗暴地被金钱衡量,而后成为“妻子”,受到丈夫的压迫剥夺,被迫成为母亲则是对女性价值的再一次剥削。被拐卖的女性总是被动地被男性和他者推上了指定的席位,对她们而言,成为妻子并不意味着幸福,人生走向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不是主动的抉择,而是被掠夺与被吞噬的过程。
在这一前提背景下,母亲在女儿面前总是沉默的、隐忍的。在此刻,母亲面临着内心的纠结和挣扎:是要继续争取自己的个体价值还是接受被他人强加的“母亲”这一身份,选择成为自己还是成为“母亲”。尽管此时母亲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已然被禁锢,然而选择成为“母亲”则意味着彻底放弃自我的存在意义,从此完全沉溺在被拐卖的事实中,放弃抵抗内心的痛苦。《母亲的岛》中,母亲对子女并不亲近,“母亲的话很少,对我们兄妹四个说不上很疼爱”,她面对女儿小妖也十分小心局促,表现为主动疏离的情感态度,“缺乏一对母女该有的自然和亲昵的感情”[2]。一方面,在被剥削的环境中,母亲处于这个家庭的最底层,她已经习惯了被人颐指气使,不仅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在子女面前也“抬不起头”;另一方面,被拐女性的“母性”是空白的,母亲内心对女儿始终是别扭的,她难以平和地面对并完全接纳自己的悲剧。
正是母亲对女儿的淡漠与疏离形成了母女关系异化分裂的缝隙。被拐来的母亲总是偷偷舔舐自己的伤口,而站在女儿的角度,“如若她肯把泪水和忧伤呈现给我,也许我们之间的隔阂不会那么大的”,因为“她的泪水和哀伤使我意识到她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彼此无可替代,我们的爱与哀愁如此息息相关”[2]。母亲和女儿之间存在天然的同性共鸣,只有当母亲放弃自我疏离的态度,认同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能从同性的角度出发,避免给女儿带来“拐卖”的次生伤害,才有可能走向母女认同。尽管,这也意味着她就此认同了“妻子”的身份和家庭关系。
2.作为母亲悲剧的产物与见证者的女儿
在受拐卖影响的“家庭”中,女儿往往深知母亲遭受的苦难,而自己正是母亲悲剧的结果,是某种意义上不洁、不堪的产物。结合母亲的态度,女儿必然会猜疑自己的存在是母亲所不喜的,在父权主导的环境中她失去了信任的依靠,不仅难以用“女儿”的身份定位自我,更会生发出对“女性”身份的质疑,面临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女儿由此产生的离弃感会在母女二人间发生相互作用,推动母女关系走向异化。
在成长过程中,女儿又亲眼见证了母亲在父权制“家庭”中被冷落、边缘化的现实遭遇,尤其是母亲与孩子之间天然的强弱依附关系在目睹了父母关系之后发生了改变。在孩子的人生中作为最初的绝对权力者登场的母亲,却受控于更为强有力的权力者,受到强力父权的牵制,以至于在女儿看来,母亲天生就是为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她们发现母亲是性别的弱者,于是承受着“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带来的绝望感和无力感。在这种境遇下,她们站在强权者的一边,抗拒成为母亲那样的女性,女儿往往选择做“父亲的女儿”,而不做“母亲的女儿”,于是很难与母亲产生共情。就像《母亲的岛》中“我”对母亲的痛苦处境极度麻木,“我们都是在母亲的哭泣声中长大的,已经见怪不怪了”[2]。女儿对待母亲的态度与父亲、哥哥们没有区别,“我”漠视母亲的存在,对母亲的苦难视若无睹、对父权的挤压无动于衷,因为此时在女儿面前的母亲只意味着“母亲”这一称谓和社会身份,并无法获得更多的、来自同一性别的心灵情感认同。
当然这种选择也有可能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强力的父权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从我未见过面的奶奶那里学到了对母亲的戒备……这种戒备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成为父亲的习惯,父亲的习惯又长期潜移默化我们几兄妹。”[2]奶奶教育父亲不能让女人有话语权,“尤其对买来的女人,更是不能对她掏心掏肺。也许奶奶在教诲她儿子时,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了”[2]。上野千鹤子指出“女儿的厌女症从母亲处学来”[1],实际上男性的厌女症也部分从母亲身上学来。奶奶在父亲面前显露出女性嫌恶时忘了自己也是个女人,而作为女儿的“我”在面对母亲几十年来受到的女性嫌恶时,也未展露出对母亲应有的性别认同与情感共鸣。此时的女儿如果认同母亲,则意味着她要站在受害者一方,对拐卖造成的苦难深恶痛绝,她会排斥父亲、男性,甚至对所处的父权制社会愤愤不平,与强大的父权作斗争;而如果站在父权这边,某种程度上也加入了施害者的行列。基于性别上的同一,女儿可能是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唯一的情感寄托,反之亦然。《寻暖》中小妖对母亲的不理解和疏离其实也是对自我的排斥,来源于对自我身份的难以认同与定位模糊,所以李寻暖的存在对小妖来说,是母女感情的寄托。李寻暖填补了母爱的空缺,也使小妖能够跨越与母亲之间的无力感,理解母亲内心的挣扎苦楚。直到母亲出走之后,女儿才发觉自己长期以来的漠不关心同样对母亲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我和我妈朝夕相处十几年,我从来没试图去理解他,从来不关心她内心的伤心和想法,从来没问她的老家还有什么人,她会不会想家,她是怎么到我们家里来的”[3],从此陷入悔恨的折磨之中。
3.拐卖悲剧的延續
女性被称为第二性,性别的弱势地位在家庭中更加突出,尤其是作为拐卖受害者的母亲,她处于整个家庭的最底端,缺失母性和对“家”的归属感;而作为见证者的女儿,面对母亲的痛苦既无法感同身受,又无力抵抗现实中的强弱依附,只能与母亲越走越远。母女之间的嫌隙日益扩大,演变为异化的母女关系。在异化的家庭关系中,“感觉自己就是一座孤岛”是母女二人的共同写照,母亲和女儿同时遭遇了女性价值与身份认同的陷落,这时的她们只能选择自救,于是母亲出走了,女儿在“李寻暖”身上安放自我。
母女关系的异化是拐卖悲剧的延续,最终引发女性的认同危机。拐卖对母亲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出走是母亲的必然之举,女儿承受的痛苦则是拐卖造成的次生伤害,不仅如此,原生家庭的情感异化更会成为女儿未来感情道路上的绊脚石。不过,正是母亲的出走唤醒了女儿对母亲的情感认同,当母亲将自己脆弱的内心摊开时,女儿才得以用同性的眼光理解母亲。面对外力对女性的层层挤压与掠夺,女性只能进行自救与互救,而母亲与女儿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结,她们应该打破异化的僵局,成为彼此的救赎,将对方从日常生活的苦难与自我价值的陷落中打捞出来。
二、女性个体价值的追问:寻找自我的“房间”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母女关系的代际创伤,尤其是在“拐卖女性”的大语境下,解放女性、获得同性心理认同,最终必须落在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上。女性主义认为,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是父权制社会给女性的指定席位,因此,“母亲的解放”与“女儿的解放”互不可分,两者都要从女性共有的身份认同出发,唤醒自我意识,找寻生命价值。女性如何确立自我的价值呢?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一个女性要想成为作家,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和足够多的金钱。”[4]“房间”是女性实现自我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空间、社会生存空间以及精神空间。
“房间”之所以对女性的个体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女性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父权制主导的社会理念所湮灭。父权社会认为母亲天生就是为丈夫和孩子存在的,母亲在家庭当中应是恭顺的、符合父权需求的,甚至连女性的社会性都被剥夺了。在父权占主导的社会中,生育功能和劳动能力被看作是女性的全部存在价值,这也是被拐卖的女性在买主眼中的全部价值,女性只是一件商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女性的社会性意义和个体发展的价值空间被完全抹杀。为摆脱这一性别困境,《母亲的岛》和《寻暖》中,被拐卖的女性及其女儿都开启了对“房间”的寻找,这里可以看出女性对自身话语的发现,她们逐步走向了自我认同与女性身份认同。
《母亲的岛》中,“岛”一方面是禁锢母亲的圈地,来自男性话语的束缚将母亲的身心隔绝起来;另一方面,母亲就像一座孤岛,与外界隔绝但情感独立,这也象征了母亲心灵的自留地。在毛竹岛上,母亲第一次出走到了小木屋,小木屋是母亲为自我搭建起的“房间”。小说多次写“我”作为女儿尝试进入母亲的“房间”,却遭到了母亲无意的“驱逐”,女儿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此时母亲的“房间”是一个纯个体化、私有化的空间,所以拒绝他者的进入,在异化的母女关系中,母亲和女儿没有达到心灵情感的一致认同。在这里,“房间”成为母亲自我疗愈、舔舐伤口的心灵领地,她在为走向更大的自由的空间做准备。母亲彻底出走之后,父亲住进了小木屋,一个人落寞地生活。这是父亲对母亲“房间”的哀悼式接纳,他最终接纳了母亲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空间和价值,蕴含着父亲/男性对母亲/女性身份的认同与接受。《寻暖》中的母亲虽然是在父亲与生活场的“冷暴力”下“被迫”出走的,十几年的委曲求全并没有使母亲得到家庭的认可,她的出走可以视作自我的解放,母亲放弃了做男性和家庭的附属,走向了自由的空间,这是母亲走向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而李寻暖与母亲不同,她拥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大胆追求自我的解放,借男性的帮助“被动”出走。然而,从拐卖中逃脱的李寻暖并没有出走成功,只能在幽暗的小巷子里拥有一个“不干净”的“房间”,这个房间实质上只是她的物质性社会生存空间,她的精神空间依然是虚无的。同时,李寻暖仅有的生存空间仍然是依靠男性获得的,从原生家庭的父母到买主再到其他照拂她的男性,她的个体价值被层层剥夺。李寻暖始终是迷失、飘零的,她把精神世界寄托在“我”身上,却最终没能获得真正属于她的“房间”和自由。“我”身上遗留着拐卖带来的代际伤害,在异化的家庭中成长,感受着浓烈的痛苦,无法接纳母亲的同时也难以进行自我认同。原生家庭中母爱的缺席以及母亲最终的出走,使“我”情感上深深失落,渴望在长辈身上满足情感需求,而这也导致了“我”恋爱中的盲目与婚姻的失败,由拐卖带来的悲剧阴霾一直笼罩着下一代人。当李寻暖去世,“我”失去了唯一的寄托,“我”最后搬进了李寻暖居住的房间,一如《母亲的岛》中父亲搬进了母亲的小木屋,标志着女性的生命价值得到了自己和他者的最终认同。
三、结语
将《母亲的岛》和《寻暖》结合起来看,读者可以发现两部作品在主题、情节、人物、地点等细节上的重合构成了一个发展的复调,二者形成互文,陶丽群通过对拐卖悲剧的揭露呈现出了女性争夺自我话语权与独立价值的不同道路抉择。《母亲的岛》《寻暖》两部拐卖题材的小说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书写与对母女关系别样呈现,带领读者郑重地思考女性的生命意义和个体价值。被拐卖的经历给被拐女性造成了无法逆转的悲痛,其悲剧还将延续到下一代,给被拐女性的子女带来持续的次生伤害。当拐卖的阴影分割了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亲密联结,母女关系的异化和分裂最终会引发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被拐女性及其女儿将在身份失落中踏上寻找自我的路。
身份认同感这一命题不仅存在于母女、同性之间,还存在于更广阔的视野中,认同感的获得并不以性别同一为基础。女性需要在社会中认知自我、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价值所在,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女人”而存在的价值。女性需要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是一个女性不会受到打扰的空间,是女性获得保护、自由和安全感的自留地。只有当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独立才有能力摆脱性别意识的束缚,只有当女性不再需要被保护的“房间”,才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2] 陶丽群.母亲的岛[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
[3] 陶丽群.寻暖[M].桂林:漓江出版社,2022.
[4] 伍尔夫.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M].周颖琪,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何文琴,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