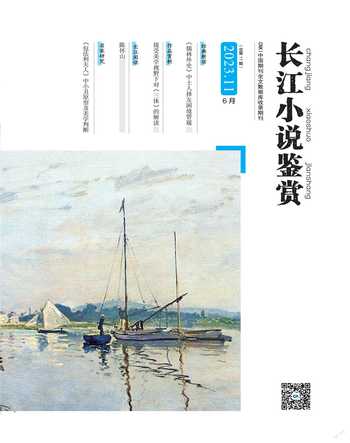论路易斯·厄德里克《爱药》中的地方感
2023-12-20聂亚楠
[摘 要] 地方研究一直是西方生态领域的关注重点,由此学界产生了对“地方感”的讨论。作为美国印第安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在其成名作品《爱药》中展现了印第安人以土地为基础的独特地方感和和谐生态观。虽然面临土地被侵占、人与土地分离的危机,但仍有一部分印第安人坚守在破碎的土地上,努力恢复部落失去的地方感,建构和表达自我民族身份。本文探索《爱药》中地方感的失落和建构,以期帮助读者了解印第安人的智慧,重新审视人类与土地的关系。
[关键词] 路易斯·厄德里克 地方感 《爱药》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獻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37-04
路易斯·厄德里克是美国印第安齐佩瓦族(Chippewa)著名女作家和诗人,也是“印第安裔美国文学复兴”重要的力量之一。她文风独特、叙事细腻,其作品植根于印第安居留地,涉及部落历史、自然、女性、身份等诸多主题,表达出厄德里克对印第安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坚守。
正如美国学者乔尼·亚当森所言:“在印第安文学研究中,观察作家研究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1]对于印第安人而言,土地不仅以物理空间的形式存在,更是其民族的象征和精神的家园,因此许多印第安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花费笔墨描写居留地的景观环境以及其对人物的影响。作为厄德里克的成名作,首发于1984年的《爱药》(Love Medicine)刻画了印第安人以土地为根基的地方感以及地方感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作品由十几个相互交织的短篇小说组成,细致描绘了居住于美国北达科他州龟山居留地的印第安人因白人殖民者的入侵而在城市和居留地之间颠沛流离的情节,地方感的丧失引发严峻的社会和精神生态危机。在困境中,以露露、玛丽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印第安人坚守自己的家园,在破碎的土地上努力恢复族群失去的地方感,重构民族文化身份。小说体现了印第安文化中独特的土地观及其对身份建构的意义。
一、北美印第安地方感
“地方”(place)是文学中的重要概念。生态学者劳伦斯·布依尔认为人们要让地方成为环境人文学者思考的必要概念。他区分了地方和空间两个概念,并提出地方更具有情感意义和价值,是“可感价值中心,也是个别而灵活的地区,社会关系在其中构成,并得到人们的认同”[2]。地方不仅仅具有物理性质,为事件的发生以及人类的活动提供背景,更承载着社会文化特性,具有其自身特点。随着对地方的研究深入,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个概念来说明人和地方之间经过社会文化改造过的人地关系,并用“恋地情结”(topophilia)来形容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当地方在人的体验中不断被赋予情感和价值后,它就成了人类自我的有机组成部分[3]。人类在与地方的相处中获得的地方感是自身身份建构的重要源泉。
在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印第安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了数千年。正如著名印第安评论家波拉·甘·艾伦所说:“土地与我们不可分割。”[4]对印第安人来说,土地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而且承载着精神力量,能够治愈族人的心灵并影响他们的成长。印第安人不仅热爱这块赐予他们丰厚回馈的土地,并尊奉其为“大地母亲”以及“神圣之地”。他们也尊重关心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生灵,认为自然万物都是自己的手足。所以印第安文化中的口头故事往往以居住地的具体地理环境为背景,表达了人们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同时,印第安人相信土地和人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同一的本质。土地里渗透着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是他们认识自我、塑造自我的地方。在数千年间与这片土地互动的过程中,印第安人形成了深深的地方感,它帮助明确自己在万物中的位置。
受到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影响,厄德里克将土地视为浸润着印第安人情感的整体,而非可掠夺的无意义空间。《我的归属之所:一个作家的地域观》一文中,厄德里克阐明了自己的土地观,她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有其所爱所恨之所”,而且“通过对这片地域的深入了解,我们才能认识到真实的自我,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起点”[5]。在厄德里克看来,不同于印第安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从别处迁徙来的白人一直对土地有疏离感,他们并未对这片土地抱有敬畏之心,反而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宰,无情地抢夺并摧毁了印第安人繁衍生息的土地,破坏了土著文化。部分印第安人在陌生的地域环境中缺失了原有的地方感,这不利于民族身份的建构。厄德里克意识到回归故土和传统对处于危机中印第安人的影响。她呼吁印第安作家“必须讲述当代幸存者的故事,同时保护和颂扬灾难过后遗留的文化核心,在这其中,包括土地的故事”[5]。《爱药》深刻体现了厄德里克作为当代印第安作家重写人地关系的使命。印第安居留地地域景观的描述贯穿全文,表明地方感对印第安族群在困境中寻根的重大意义。
二、《爱药》中地方感的缺失
厄德里克通过描述喀什帕、拉扎雷和拉马丁三个土著家族的故事,表达了自白人来到这片“新大陆”开始,印第安人便成为殖民者的牺牲品的观点。印第安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夺走,以土地为根基的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生存环境的改变和传统文化的消失让印第安人的地方感缺失,个人身份认同面临严峻的挑战。
布依尔指出:“没有对一个地方的综合了解,没有对一个地方的忠诚,那个地方独特的自然生态、自然景观就会被粗暴地改变,最终会导致毁灭。”[2]白人殖民者并非像印第安人一样持有朴素的土地观,他们深受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观点的影响,认为土地的作用是满足个人利益,可以随意占有和掠夺。为了侵占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肥沃土地,殖民者把他们赶去相对贫瘠的土地,强行剥夺了印第安人对故土的感情。作者借露露·拉马丁之口,表达了大批印第安人流离失所的窘状:“齐佩瓦人是从五大湖对岸搬到这儿来的,过去外婆常常说我们是如何被硬生生地赶到大草原这个孤寂的角落里来。”[6]为了合法侵占土地,政府又推行了所谓“土地分配政策”,迫使刚刚安顿下来的印第安人不得不又一次面临失去土地的残酷现实。小说中喀什帕家族的第一代女主人拉什斯·贝尔坚守在北达科他州的土地上,而儿女们却分到了蒙大拿的土地,因此他们要么迁过去,要么将土地卖掉,必须在远离部落和丢失土地之间做出抉择。“土地分配法案就是一场闹剧”[6],这是印第安年轻人艾伯丁回到居留地时看到大片土地被卖给白人时发出的感慨。同样,为了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殖民者还推行内部殖民政策,将印第安人的后代送进寄宿学校,迫使他们接受白人的土地观。最终这些印第安人成为殖民者抢夺土地的帮凶,殖民者摧毁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印第安部落的凝聚力。“用印第安人对付印第安人,政府就是这样花钱让我们窝里斗。”[6]拉什斯·贝尔的儿子尼科特从小接受了白人的教育,身为印第安人的他因受到歧视无法在白人社会立足,所以回到了居留地。尼科特深受白人殖民者的影响,不赞同印第安传统土地观。虽然成了部落酋长,但尼科特并没有保护自己的族人和土地。他大肆推行寄宿学校和工厂,并任凭政府以“非法占领土地”的名义抢占了族人的土地。在白人一次次的掠夺中,印第安人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更失去了民族团结。
殖民者抢夺了土地后,并没有像传统印第安人一样对土地抱有虔诚和感恩之心,顺应自然规律与土地和其他生灵和谐相处,而是大肆侵占动物的栖息地,修建现代化工厂。所谓的文明和工业化进程不仅破坏了居留地的环境景观,也影响了印第安人以土地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居留地充斥着灰尘以及现代生活垃圾,环境状况堪忧。由于土地的缺失以及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印第安人独特的狩猎文化正渐渐消失,他们对动物的感恩之心也不复存在。传统印第安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依靠土地生存的他们与土地保持亲密的联系。印第安部落往往在捕食前举行仪式,以表达对动物的尊敬和感恩,并在狩猎时节制捕杀,珍惜自己的所得,显示了印第安人遵守在大自然中“互尽义务”的准则。小说中老拉什斯·贝尔虽然将尼科特送往寄宿学校,但她偷偷地将自己的小儿子伊莱留在了家里接受传统印第安教育。作为为数不多的在居留地长大的印第安人,伊莱成了居留地唯一会下套补鹿的人[6]。其他印第安人由于林地的消失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已然丢失了捕猎的传统本领,选择到工厂维持生计。同样,印第安人对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尼科特的儿子高迪在醉酒之后不慎撞上一头鹿,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而是以一种功利的想法准备用鹿的尸体来换酒喝。正如白人女性林内特对伊莱所言:“他们得学学祖辈传下来的东西,不然您哪天没了,一切也都跟着埋葬了。”[6]土地不再对印第安人的生存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万物和谐互动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也受到了挑战。新一代印第安人不再对土地以及自然万物持有依恋和认同的态度,由此导致了地方感的消失。
印第安作家莫马迪曾经指出,世代居住的土地是传统印第安人的“一种精神财富”,因为只有在祖先的土地上,他们才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认识自我”[7]。白人对土地的侵略和传统土地观的丧失打破了一部分印第安人与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失去地方感引发了严峻的精神生态危机,阻碍了身份认同的建构。《爱药》中,一部分印第安人选择走出居留地到城市里生活,他们始终在“离家”和“归家”的路上徘徊。对土地的疏离让他们在居留地无法获得地方感,因此他们选择前往城市生存,而在城市这个陌生的地域中却饱受歧视得不到认同。无根的漂泊状态造成了自我的迷失。高迪的儿子金长大后前往城市求生,他每次回到居留地都精神极度不稳定,甚至酗酒后殴打自己的妻子林内特。林内特祈求金:“每次回家你都发疯了似的,我们回双城,回家去。”[6]两个“家”字体现了新一代印第安人家园意识的迷茫和对自己身份的困惑。金的母亲琼曾经被称为迷人的美国印第安小姐,她从小被遗弃在森林里,靠喝松树液幸存下来。她被伊莱带大,本应对土地抱有深厚的感情,但长大后琼选择在城市里维持生计。城市生活的不顺利让她颠沛流离,无法定位自己的身份。最终琼选择回到居留地,但她被冻死在回家路上的暴风雪中。琼的死因成了一个谜,因为她天生拥有动物般的本能,本应知晓风雪的到来,但琼并没有选择继续游荡,而是决定以死亡的形式结束失去地方感所造成的身份困惑与迷惘。总之,新一代印第安人游离在城市和居留地之间,地方感的缺失给他们带来了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和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
三、《爱药》中地方感的建构
地方感的消失是殖民主义给印第安人带来的苦果,挑战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和自我身份。因此代代印第安人不懈努力,以期“重新找到以源头和地方感为核心而建构的身份认同”[8]。在小说中,厄德里克通过塑造露露、玛丽等角色,描绘了老一代印第安人在面临年轻人普遍失去地方感的境况下的坚守,她们在自己的家园中重建族群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努力帮助族人们找寻缺失的地方感,整合破碎的历史身份。
作为拉马丁家族的核心人物,露露·拉马丁展现了印第安人与土地之间的深厚感情。虽然土地被政府用来修建工厂,但她决不妥协,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景观,实现印第安族群身份的认同。露露从小就具有反叛精神,一次次从白人的印第安寄宿学校中逃出来。回到居留地后,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影响了年轻的露露。后来露露选择到小岛上和印第安巫师摩西·皮拉杰一起生活,在那他们以最原始自然的方式和周围万物互动,摩西也用印第安语言为露露讲述古老的传统,增强了露露对于土地和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认知。露露“热爱整个世界,热爱世界上用雨露滋养的所有生灵”[6]。她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关联,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正是对土地的深入了解建构了露露的地方感,强化了她的印第安身份。当以尼科特为首的印第安事务管理局抢占自己的土地时,露露展现了捍卫家园的决心。她痛斥白人殖民者强盗般的无耻行径:“你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哪怕是摩天大楼的顶上,都是印第安人的。”[6]虽然露露的房子被尼科特烧掉,但露露带领自己的儿子们重建家园,并种植了很多树苗,体现了她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之后,年老的露露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选择坚守在居留地,反对政府破坏生态环境来修建无意义的纪念品工厂。她重新引进了野牛这种消失已久的古老动物,并不断教育自己的兒子莱曼·拉马丁尊重自然界的其他物种。露露坚持在破碎的土地上恢复族群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主张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野牛时代”,重构印第安人民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感。
虽然年少时面临身份定位的困惑,但尼科特的妻子玛丽逐渐在与土地的共生关系中汲取了力量,重新热爱认同土地。她与露露结盟,共同承担起保护土地和传统文化的责任。受到殖民者的文化观念的冲击,早期的玛丽并不认同自己的印第安身份,而是想要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遭受了修女利奥波德的虐待后,玛丽选择回归自己的部落。在和土地和谐互动的过程中,玛丽意识到了这片土地无穷的生命力,并渐渐找寻到了自己作为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和尼科特成婚后,玛丽生育并收养了数不清的孩子,她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通过土地的馈赠维持整个家族的生计。尼科特的出轨让玛丽身心俱疲,她并未立刻祈求丈夫回归家庭,而是选择削光了屋子里的所有土豆,让自己平静下来。土豆是大地给予印第安人的生存之物,是大自然的代表。在生活即将发生巨变之际,玛丽选择从自然中汲取无穷的力量。在与土地的亲密交流中,玛丽支撑着家族和部落的繁衍。她渐渐与土地融为一体,并成为部落“大地母亲”的象征。晚年的玛丽意识到了“天主教和印第安事务管理局这些新事物毁了她的孩子”,她与老情敌露露冰释前嫌,一起在居留地反抗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压榨[6]。她以戏剧性的方式砸掉了白人破坏环境后修建的纪念品工厂,捍卫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文化传统。在面临大片土地被夺走、部落人民地方感消失的困境时,露露和玛丽选择坚守在土地上,遵循着人与大地融为一体的信仰。她们的努力有利于恢复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热爱与认同,促使新一代印第安人在迷茫中找到自己的归属。
四、结语
《爱药》揭示了以土地为根基的地方感对印第安人的重要影响。在厄德里克笔下,土地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承载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指引着族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帮助他们认识和塑造自我。虽然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白人殖民者侵占,但仍有一部分印第安人在破碎的土地上坚持印第安传统和价值取向,帮助迷失的族人重建与土地之间的亲密联系,恢复消逝的地方感。《爱药》展现了厄德里克用文字的力量为印第安文化发声,帮助族人在困境中建构印第安族群身份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1] Adamson J.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Environmental Justice,and Ecocriticism:The Middle Place[M].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1.
[2] Buell L.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3] Tuan Yi-Fu.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M].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74.
[4] Allen P.The Psychological Landscape of “Ceremony”[J].Th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1979(1).
[5] Erdrich L.Where I Ought to Be:A Writers Sense of Place[M]//Wong H D S.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A Caseboo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 厄德里克.愛药[M].张廷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7] Coltelli L.Winged Words:American Indian Writers Speak[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
[8] 赵媛媛.论琳达·霍根《太阳风暴》中地方感的建构[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聂亚楠,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