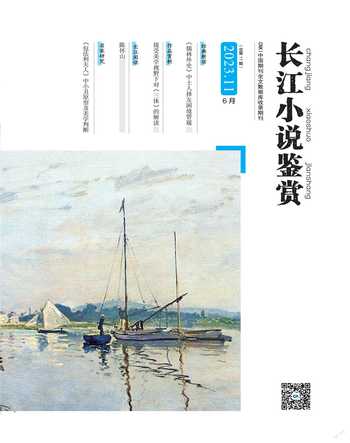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轻逸”与“沉重”:试论小说《宠儿》讲述创伤的两种叙事路径
2023-12-20曾新英
[摘 要] 小说《宠儿》的主题之一是讲述奴隶制度给黑人群体留下的心灵创伤,在创伤叙事上,《宠儿》采用了“轻逸”与“沉重”两种路径,其中“轻逸”表现为对人物创伤的隐匿书写和故事的寓言性色彩,是对人物创伤的委婉表达;而“沉重”则借助于不同人物对同一故事的复调叙述和人物身份设置的多重寓意,试图抵达创伤背后的历史真相。借由这两种辩证的叙事路径,小说揭示出残酷的奴隶制度在黑人群体心灵层面留下的难以抹去的伤痕,并积极寻找治愈创伤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宠儿》 历史创伤 轻逸 沉重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23-05
“黑奴历史”是美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笔下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一段历史带着血腥和眼泪,给黑人群体留下了永久的心灵创伤。莫里森借手中的笔在故事中描写这段历史给黑人群体留下的不同程度的创伤。
“创伤”一词原指人身体所受到的伤害和磨损,弗洛伊德曾对此做过解释:“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周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1]小说《宠儿》在文本层面上并没有直接反映宏大的黑奴历史,但这一历史语境的潜在身影所引发的黑奴精神创伤却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从文本来看,小说整体以一种轻逸迂回的笔调展开,而在描写人物时,小说的叙事则给人以愈加沉重的伦理体验。“轻逸”在此并非逃避过往,是作者在沉重历史的阴霾之下,探索如何治愈创伤的路径。
一、“轻逸”:历史创伤的迂回表达
“轻逸”作为一种叙事表达路径,是一个“减重”的过程。过往历史在人心灵留下的创伤本就是一种灵魂的重负,而“轻逸”的反映对于创伤性历史来说则体现为作者对历史创伤的隐匿反映和想象性建构。借助这样一种迂回路径,作者对于残酷历史的道德伦理批判也以一种更间接的方式呈现。《宠儿》中,作者对于人物在奴隶制度下生存的屈辱历史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呈现,表现为在讲述故事中多次设置人物失忆或对创伤避而不谈的情节,而在叙事方式上作者则引入了寓言化的想象。
1.失忆或隐藏:隐匿创伤的叙事策略
一段带有创伤性的历史过往对于个体来说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易提起的事情。《宠儿》中,每个黑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段带着伤痛的历史,而他们减轻伤痛的做法是试图“失忆”,将记忆封存或者避而不谈。
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甜蜜之家”的黑奴来说,“甜蜜之家”绝不是“甜蜜的家园”,相反,它带来的屈辱作为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在他们的心底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塞丝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在“甜蜜之家”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受到了无法忍受的伤害。她首先被剥夺了“人的属性”,“学校老师”给他的侄子上课,教他塞丝应该被归类为动物。这意味着在白人奴隶主“学校老师”以及他的侄子眼中,黑奴塞丝和栏中的母牛没有什么区别。继而她被剥夺了奶水,这是一个让塞丝的丈夫黑尔崩溃的场景:“学校老师”的一个侄子摁住塞丝,另一个趁机吮吸她的乳房,而“学校老师”则在旁边做着记录。对于这样一段无比痛苦和屈辱的经过,塞丝在此后给女儿丹芙说起“甜蜜之家”时,总是看似轻易地绕过这段,仿佛因为这是“隐私”,她就能忘记这段过去。“因为一提起过去就会唤起痛苦,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或者遗忘。”[2]对于塞丝来说,过去的一切就像灾难一样,她不断地逃离灾难:怀着丹芙逃离“甜蜜之家”,在路途中几近绝望;“学校老师”抓捕她,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免受奴役、逃离屈辱,她杀死了自己第一个女儿,用锯子割破了她的喉咙。这个女儿成了悲伤和愤怒的幽灵,守在她所居住的蓝石路124号。她已经无处可逃,记忆充满了痛楚,而塞丝,这个有着“铁的眼睛,铁的脊梁”[2]的姑娘,却在保罗·D面前,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避而不谈:
“你过得怎么样,姑娘,除了脚还光着?”
她也笑了,笑得轻松而年轻:“在那边把腿弄脏了,春黄菊。”[2]
保罗·D在这段对话中或许是想问候塞丝逃离“甜蜜之家”十八年来的生活,塞丝却避重就轻,只回答刚才的事:春黄菊把腿弄脏了。但保罗·D却从中感受到了塞丝心中的悲苦,因为他马上扮了个鬼脸,似乎在尝一勺很苦的东西。塞丝和保罗·D之间的委婉對话让塞丝心中的苦楚隐而不露,但他们之间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体谅,这种体谅缓冲了人物内心的伤痛。在作者的笔下,塞丝的创伤呈现得更为具象化:主人鞭打留下的伤痕变成了一棵苦樱桃树,开枝散叶甚至绽放出白色的花朵,随着苦难的累积年年生长,替塞丝留存她主观遗忘的创伤。
对于保罗·D来说,“佐治亚的阿尔弗雷德、西克索、学校老师,黑尔和他的哥哥们、塞丝、先生、铁嚼子的滋味、牛油的背景、胡桃的气味、笔记本的纸”这一切构成了他沉重的个人记忆,这些事物是他一次次被摧残的印记,他把它们“一个一个地锁进他胸前的烟草罐里”[2],并决定再也不让任何人撬开它。
塞丝的女儿丹芙听到母亲杀死姐姐的事实之后,无法承受这种恐惧,也无法理解事情背后的真相,于是选择让自己的耳朵“自动失聪”,隔绝外部的声音,并且在树林中找了一间藏着自己秘密的“屋子”:“五丛黄杨灌木栽成一圈,在离开地面四英尺高的地方交错在一起,形成一个七英尺高的、圆而空的房间,墙壁是五十英寸厚的低语的树叶。”[2]在这间“屋子”里,她与令她受伤的世界暂时失去了联系。
作者在小说中让人物的记忆呈现为散漫的游离状态,面对坚硬的沉重的历史时则让人物选择了一种迂回的避开方式,从而让读者在作为旁观者洞察过往的残酷瞬间时,体会到一丝轻逸的喘息。刘小枫认为,这种描写的作用是“消除世界带给个人的无法忍受的石头般的凝重,让人像植物——比如根深植在土地里的忘忧树——那样经受生命”[3]。因此苦樱桃树和烟草罐在小说中的诗意呈现,是对塞丝和保罗·D过往创伤的“去重”表达,和丹芙一样,他们的过往过于沉重,也需要一个地方来安放他们的创伤。封存记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更为轻松的解脱方式。因此,托妮·莫里森在小说情节上多次安排人物对创伤经历暂时失忆或避而不谈,是对人物创伤的“减重”过程。当人物失忆或试图避开言说创伤时,创伤真相被暂时埋藏。对历史过往的暂时性疏离,或许并不是逃避创伤的有效方式,但从书写层面来看,却是呈现历史创伤的一种迂回路径。
2.想象:寓言化叙事
托妮·莫里森在关于《宠儿》的创作谈中提到自己对于真实故事的想象和重新创造:“我插入了一个可以说话、可以思考的死孩子,她的影响——显现和消失——生产为一种奴隶制的哥特式伤痕。”[4]托妮·莫里森提到的“死孩子”就是小说中的一个叙事主体——宠儿。宠儿是黑人塞丝的第一个女儿,在她一岁多的时候,“甜蜜之家”的第二个奴隶主“学校老师”来到蓝石路124号,意图将塞丝和她的孩子抓回“甜蜜之家”。塞丝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遭受和自己一样的侮辱,决定杀死自己的孩子。此后,宠儿一直化为幽灵留在了塞丝和亲人所在的屋子蓝石路124号里面。宠儿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为无形的鬼魂存在,同时又让故事充满一种悲伤的氛围。当宠儿还魂为人重新回到塞丝身边时,她对塞丝索取爱的种种举动,以及她离奇的自我经历的叙说,都展示了一种魔幻性,是对现实的一种模糊和疏离。
鬼怪故事是美国非裔小说的一个传统,小说中作者的创造痕迹分外明显,因而故事的想象性质也极易为读者察觉。《宠儿》中,关于宠儿的言说脱离不开“幽灵”这样一种想象建构。对于读者来说,宠儿的存在很显然是一种作者的想象,当这样一种意识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中时,“塞丝为避免孩子重蹈受辱的经历而杀死自己的孩子,孩子还魂索求母亲的爱”这一悲剧现实本身带有的震撼性和冲击力被寓言化叙事的方式减弱,而这样一种减弱的过程是因读者和故事本身距离的缓慢拉开所产生的。
在小说中,宠儿还魂回到塞丝身边本身就是一种弥补创伤的描写。对于杀害女儿,塞丝一直在强调她渴求一个解释的机会:“但只要她出来,我就会对她讲清楚。”[2]当这样的愿望如愿以偿时,塞丝开始了漫长的弥补之旅,她不断输出自己曾经无法给予的爱。然而现实中,这个故事的原型却是杀死女儿的奴隶母亲不仅没有获得自我救赎的机会,甚至被继续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因为在当时,奴隶以及她的后代“都只不过是可定期贩卖的存货”[4]。现实中,迫不得已杀死自己孩子的奴隶母亲无法获得心灵的救赎。但在小说中,托妮·莫里森给了她弥补女儿的机会。现实或许无法改变,但托妮·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对真实故事进行的改写是对沉重现实的一种轻逸逃遁。
二、“沉重”:抵达历史创伤之旅
美国实行奴隶制度的历史充满了黑人的血泪,对其进行不同角度的言说应当立足于厚重的真实,对于历史的创伤性揭示也应该有真实的质地。“沉重”作为一种历史创伤的书写路径,就是从“真”的角度看待一段历史在人的生命里留下的痕迹。它“是一种‘加重的方式,是创作者对历史、国家、天下的关心与责任担当”[5]。《宠儿》中,作者并未提及奴隶制这一段较为宏大的历史,但它作为大历史背景而存在,其造成的历史创伤被故事中人物反复“指证”。另外,宠儿这一人物的隐喻性质也让潜在的历史浮出水面。
1.复调叙事:历史创伤的多视角证词
海登·怀特说:“历史本身是由一大堆有关个体和集体的活生生的故事构成的。”[6]《宠儿》中,作者并未直接反映一段连续完整的宏观历史,但文段中具有历史特性的名词如“1873年”“南北战争”“奴隶”等随处可见,指向具体的历史背景。也正是这些看似是小说作者不经意间提供的线索,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历史语境,让塞丝和宠儿的故事有了更大范围内的历史支撑。
作为小说文本,《宠儿》致力于以小人物的历史来反映和指涉大历史。《宠儿》中“甜蜜之家”的黑人受奴役的历史讲述由塞丝、保罗·D和贝比·萨格斯的回忆共同完成。在此期间,小说犹如一架摄像机记录了在场人物的言行,在人物回忆部分则转为内聚焦的叙事视点,深入人物内心。人物记忆的涌现如同翻开一本尘封的相册,回忆越是深入,历史创伤的真相就越是清晰。小说中,每个人的回忆组成了言说同一事件的不同声部,各个声部所组成的历史图景构成了揭示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痛苦和心灵创伤的有力证明。
关于宠儿被母亲杀死的悲剧真相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经由多个人物的回忆得到了完整呈现。虽然作者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但故事中的叙述视点却是移动的。叙事视点的移动让不同人物的不同记忆图景得以呈现。在第一部分里,叙事视点首先聚焦于塞丝,但塞丝的回忆总是在即将抵达“杀婴”事件真相前便戛然而止。很显然,对于塞丝来说,这是一段不想再提及的隐痛。随后叙事视点移动到祖母贝比·萨格斯身上,她的记忆营造出一股悲剧氛围,逐步引出悲剧发生的起始场景。但作者并没有借由贝比·萨格斯的记忆来完成这一次历史创伤的揭示,她将叙事视点从贝比·萨格斯的身上移开,又变为全知视角,描述“学校老师”的到来和塞丝杀死孩子的经过,在这一段经历的描述中,塞丝和贝比·萨格斯的身份模糊成了白人口中的“女黑鬼”和“老黑鬼”,明显带有身份指向特征的称呼让这段故事背后所指涉的奴隶制度下黑人和白人身份地位的不平等事实得以客观地呈现出来。完整的讲述最终由事件在场者斯坦普·沛德来完成,由于他和事件相关者的关系较远,他的回忆更为客观,为故事的讲述增添了一定的真实性。此后,在故事的第二部分,以塞丝、丹芙为言说主体的第一人称独白都对“塞丝杀害婴儿”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心灵伤害有所讲述。对于塞丝来说,不得已杀害自己的孩子,是难以弥合的伤痛;而对于丹芙来说,“母亲杀死姐姐”这个事实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在故事的第三部分,叙事视点再次转移到塞丝身上,由她的自我言说道出了杀婴背后的动机和缘由:“甜蜜之家”是个不安全的地方,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回去当奴隶。自此,“塞丝杀婴”事件的全貌经过故事中不同人物站在不同立场进行的回忆和言說得以还原。小说中,叙述视点的移动让不同人物的精神世界得以展现,而他们关于“杀婴”事件的看法,则成为他们创伤真相的复调证词。
2.负重的幽灵:身份的多重象征
宠儿在文中作为一个叙事视点呈现,本身带有隐喻意味。从故事发展的层面来说,她是曾被塞丝杀死的女儿的还魂体。随着宠儿还魂回到人间现身,塞丝刻意埋藏的记忆开始复活,曾经被遮蔽的事实开始浮现。她在给宠儿讲故事的时候提起了自己关于母亲的记忆:母亲因需要不停地劳作,所以和她相处的时间非常少,后来母亲不堪压迫试图逃走,被发现后被绞死。随后,塞丝不断解释自己对于女儿深刻的爱,但这种“爱”因为奴隶这一身份而得不到表达,甚至被扭曲,体现为塞丝为了保护女儿而将她杀死。从代际关系上来说,宠儿身上也有塞丝的影子,她们都是奴隶的女儿,关于母亲的记忆都带着痛楚。因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宠儿的命运象征着黑奴制度下黑人母女之间带着裂痕的爱。
此外,作为故事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叙事者,宠儿的自我言说让她的身份意义得到了延伸。从她的回忆中读者得知她来自船上。她回忆海上航行时的没有皮的男人、船上蜷缩的黑人等可怖的场景,让人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罪恶的黑奴贸易。而她在自我言说时的身份又是模糊不清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脸,我是你”等身份不断置换导致身份模糊的句子,她的外在形象又兼具大人和孩子的特征,这种描写使她的幽灵身份富有多义性。塞丝和丹芙的回忆聚焦于家庭,宠儿作为一个更灵活的身份象征,她的回忆关联的却是黑人群体的记忆。她的还魂经历也让她成了黑奴贸易受难者中的一员。于是宠儿就不仅只是塞丝的创伤了,她不幸的遭遇成了小说开头所说的“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黑人不幸的象征。她的悲剧暗示和指向的是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她的身份与塞丝、保罗·D、贝比·萨格斯的个人相关,同时又在隐喻层面上象征着残酷的黑奴贸易史和黑奴制度,而这些是故事中所有人物创伤记忆的潜在历史背景。
三、重构故事结尾:对抗“沉重”的“轻逸”
关于《宠儿》创作,托妮·莫里森说:“我创造了不一样的结尾,与玛格丽特·加纳的悲伤、不安、真实的生活不同的充满希望的版本。”[4]在原型故事中,塞丝的原型玛格丽特·加纳为了让女儿逃避被奴役的命运而将女儿杀害。历史事实让人物负重跌落地狱,但在小说中,托妮·莫里森却试图借助想象和虚构托举起跌落的人物,修补他们破碎崩溃的心灵。她在故事结尾以爱探求拯救人物残酷命运的可能,而面对已经造成的难以修复的创伤,她希望给人的心灵“减重”。
当得知塞丝杀死女儿的动机时,保罗·D说:“你的爱太浓了。”[2]面对这样的指责,塞丝说:“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2]正因为对孩子浓烈的爱支撑着塞丝熬过了那些充满磨难的时刻:怀孕时后背被鞭打、挺着大肚子逃离“甜蜜之家”、忍受着房子里女儿幽灵的纠缠和折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873年,此时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但奴隶制给小说中的每个黑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塞丝没有感受到来自母亲的关爱,而自己也因为奴隶的身份没有爱自己孩子的自由;塞丝的孩子丹芙一直生活在母亲杀女的恐惧之中,宠儿直接沦为罪恶制度的牺牲者;保罗·D作为男子汉的尊严被一点点践踏……过往的种种压得人几乎就要崩溃,而托妮·莫里森有意在沉重的故事背后尋找拯救的可能:就在塞丝因为幽灵宠儿快崩溃时,丹芙目睹了塞丝的愧疚,理解了母亲的爱并且自动担负起照顾母亲的职责。她勇敢地走出了蓝石路124号,努力寻找新的生活,最终在辛辛那提社区黑人群体的帮助下将幽灵宠儿赶跑,救回了塞丝。辛辛那提社区的黑人群体的帮助是群体之爱的回归。为弥补宠儿,塞丝快变得支离破碎,保罗·D的重新出现给塞丝带来了希望,他告诉塞丝:“我和你,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2]并且让塞丝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塞丝。你才是呢。”[2]正因为这样,当塞丝被创伤折磨时,保罗·D的爱将她拯救了。
正如作者所说:“我的叙述是关于包容之爱而非杀婴的野蛮行为。”[4]《宠儿》有别于故事现实结局的重构很明显地体现了作者的伦理倾向: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爱能够治愈创伤。在小说的最后,她让宠儿这样一个孤独而悲伤的幽灵讲述了自己的期待:“渐渐地,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被忘却的不仅是脚印,还有溪水和水底的东西。留下的只有天气。”[2]在一种充满诗意的想象中,作者以一种轻盈的笔调寻求治愈的可能,给读者暂缓沉重心绪的机会,读者也对现实抱有了向上的期待:人物因被爱包容,治愈不堪回首的创伤,寻找新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 Morrison T.The Origin of Other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5] 祝亚峰.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6] 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和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曾新英,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