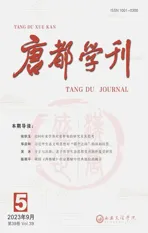唐代的清明改火、赐新火习俗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2023-12-20马荣良
马荣良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3)
改火习俗曾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改火之典,昉于上古,行于三代,迄于汉,废于魏晋以后,复于隋而仍废。”(1)转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2页。关于先秦时期的改火时间及次数,文献记载说法不一(2)据《管子·禁藏》《轻重己》等篇目记载,改火应在春季;而据《论语·阳货》篇记载,改火当在秋末冬初。《淮南子·时则训》称一年之中要四次改火,《周礼·夏官·司爟》称有五次改火者,详见汪宁生《古俗新研》,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147页。。至汉代,改火时期仍常变更。居延汉简保存有西汉宣帝时丙吉奏书,建议夏至改火(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后汉书·礼仪中》则云:“日冬至,钻燧改火。”[1]自汉代以降,改火仪式一度湮没无闻。
隋文帝采纳王劭的建议,恢复改火古俗,并在宫廷中推广开来(4)参见魏徵《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7页。。由隋代仲春寒食禁火三天的事实不难推知,其时宫廷春季改火当在清明日举行(5)参见马荣良《隋代寒食节的传承与创新》,载于《节日研究》第16期。。
至唐代,清明改火习俗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衍生出赐新火仪式,发展成为寒食节的重要节俗(6)关于唐代寒食节与清明之间的关系,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即唐代虽有以清明为节的意识,但清明并非独立的节日,而只是寒食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黄涛《清明节的起源、变迁与公假建议》,收入中国民俗学会等《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在传统社会,节日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满足民众敬天顺时、祈福禳灾的信仰需求;创造人际交往的空间,强化个人同家庭、社群的情感联系,满足个体对安全感、归属感的精神需求;调节社会运行节奏,满足民众放松身心的娱乐需求等方面。”[2]232清明改火、赐新火习俗不仅丰富了唐人的节日文化生活,增添了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更契合了唐人特别是统治者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及现实政治的需要,客观上有利于维系和巩固统治秩序,对唐代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于唐代清明的改火、赐新火习俗,学术界已经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参考(7)参见张勃《唐代的改火》,载于《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张勃《火燧知从新节变——唐代清明的改火习俗》,载于《中国文化报》2014年4月7日第8版。。但这些研究多停留在对民俗事项的描述上(这些描述也并不全面),对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尚需深入的挖掘与剖析(8)部分学者虽初步揭示了唐代清明钻燧改火习俗的文化内涵,诸如则天顺气、弃旧图新等,但并未展开论述。参见罗时进《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载于《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赵睿才《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0-651页。。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究。
一
在唐代,每逢寒食节,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贵贱,通常都要遵循禁火习俗(9)参见马荣良《唐代寒食节的禁火习俗》,载于《滨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而“节过藏烟,时当改火”[3]5490“改火待清明”[4]3055,随着清明的来临,“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4]1070的情形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改火、取新火。“清明日出万家烟”[4]3194“万井出新烟”[4]1498“田舍清明日,家家出火迟”[4]3390……,透过这些唐人诗句不难看出,清明改火、取新火之俗在大唐疆域内广为流行,蔚为大观。
每逢清明,在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千门尚烟火”[4]3891;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市),“榆火轻烟处处新”[4]8469;在平陵(今江苏省常州溧阳市西北),“火燧知从新节变”[4]3477;在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朝来新火起新烟”[4]2757;在锦州(今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郡内开新火”[4]4333;在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烟火满晴川”[4]1964。“自叹清明在远乡,桐花覆水葛溪长。家人定是持新火,点作孤灯照洞房。”[4]3680(10)权德舆《清明日次弋阳》此诗作于贞元二年(786)清明日。考权德舆生平履历可知,当时其家人在丹阳(今江苏镇江丹阳市)。参见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中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陶敏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严国荣《权德舆生平与交游考略》,载于《唐都学刊》1997年第4期。清明日,权德舆客居他乡,想象着此时远在丹阳(今江苏省镇江丹阳市)的家人也定会遵俗行事,生起新火。京师长安自不例外,“今日清明节,园林胜事偏。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4]6745贾岛一度寓居长安城东南青门附近的升道坊,这是一个“尽是墟墓,绝无人住”(11)李复言《续玄怪录》卷3,载本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的地方。“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朝炊”[4]4345,贾岛在此过着寒苦的生活,清明日也依俗改用新火。
有唐一代,清明日改火、取新火之俗在上层社会也颇为流行。唐高宗时,李峤在英王李哲府中任僚属,曾亲眼目睹清明日王府改火的情形。“游客趋梁邸,朝光入楚台。槐烟乘晓散,榆火应春开。日带晴虹上,花随早蝶来。雄风乘令节,余吹拂轻灰。”[4]695王侯府邸如此,宫廷禁苑亦可想见。至迟于唐中宗时,此俗在宫廷中已流行开来。“凤城春色晚,龙禁早晖通。旧火收槐燧,余寒入桂宫。”[4]560韦承庆的这首《寒食应制》诗,描绘的就是当时清明日宫廷改火的情形(12)韦承庆《寒食应制》诗一说作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寒食节,误。韦氏卒于中宗神龙二年(706)十一月,参见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武则天当政时,除了长安年间(701年10月至703年10月)曾暂居长安外,一直居于洛阳。这一期间,在朝中任职的韦承庆当随其往返于两都之间。又中宗神龙元年(705),韦承庆在洛阳,次年春因罪流放岭南。据此,此诗似作于武则天长寿年间(692—694)至中宗神龙二年(706)之间,韦承庆时在长安或洛阳。。
盛唐时此俗犹盛,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诗云:“寒食春过半,花秾鸟复娇。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改木迎新燧,封田表旧烧。”[4]957-958诗中所谓“改木迎新燧”,当指清明宫禁改火之事。流风所及,官僚士大夫也多依俗行事。“田家复近臣,行乐不违亲。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长会友,唯德自成邻。池照窗阴晚,杯香药味春。”[4]1336清明日,玄宗朝司勋郎中刘晃在自家别墅中生起新火炊爨,呼朋唤友,诗酒酬唱。降及中晚唐,此俗仍沿袭不衰。“寂寞清明日,萧条司马家。留饧和冷粥,出火煮新茶。”[4]4913元和十三年(818)清明日,时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家中改火、取新火,并煮新茶,送别贬谪虔州的韦侍御。
不唯世俗之人如此,化外之人亦不能免俗。“忽逢青鸟使,邀我赤松家。丹灶初开火,仙桃正落花。”[4]1647寒食节道士也要禁火,清明日方可取新火、重开灶。
二
清明日,唐人通常采用钻木的方法取新火。“钻火见樵人”[4]3522和“家人钻火用青枫”[4]2575等诗句,反映的就是清明日各地民众钻木取火的情形。据唐李绰《辇下岁时记》载,宫廷中也采用此法,“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5]547。
“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6]796古代中国钻木取火,不同的季节使用不同的木材,所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栆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梄之火,冬取槐檀之火”[6]796。不同季节使用不同的木材做燃料,本是一种现实需要,但后来经五行学说的改造,这些树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南朝梁代学者皇侃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7]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唐代春季清明取火所用的木材主要也是榆木和柳木。时人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清明千万家,……榆柳芳辰火”[4]3723和“木铎罢循,乃灼燎于榆柳”[3]7873。而尤以榆木为多,唐人诗文中也频频述及,如“槐烟乘晓散,榆火应春开”[4]695,“晓榆新变火”[4]3082,“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4]3189,“漏残丹禁晚,燧发白榆新”[4]3189和“榆烟将变旧炉灰”[4]6623,王起有赋题作《取榆火赋》,等等。除了榆柳,也有用其他木材的。“家人钻火用青枫”[4]2757,因楚地多枫树,清明日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民众多钻取枫木取火。
关于唐代钻木取火(主要是清明日取火)的情形,王起《取榆火赋》《钻燧改火赋》等文中也有着详尽描述。从中可知,唐人清明钻燧改火前,首先要选定木材,遣工匠斩而取之,继之以钻燧取火。钻火时,用手搓动木枝,急促而持续不断地施钻,“势若旋风,声如骤雨”[3]6473;紧接着“运手而绿烟乍起”,被钻之处首先生烟,继而“红星忽迸”“朱火既飞”[3]6473,迸出的火星被引成火焰,于是“丹焰发而炎精吐”[3]6473,“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4]1964和“出火煮新茶”[4]4913等,清明改火、取新火之后,唐人就可以重新开灶熬煮榆羹、新茶等食物及饮品,新的生活也随之开始。
三
中晚唐时,每值清明,宫廷中通常都要举行隆重的取新火、赐新火仪式。前引李绰《辇下岁时记》云: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者进上,赐绢三匹、金碗一口[5]547。随后,皇帝将钻取的新火赏赐给近臣戚里,以示恩宠。
从文献记载来看,清明赐新火之俗发端于唐代宗时。代宗大历九年(774),史延等人参加在东都洛阳举行的科举考试,同作《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备述其时清明赐火之盛(13)据《文苑英华》卷180、《登科记考》卷10等文献记载,史延等人所作诗歌均为大历九年(774)东都试帖诗。参见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第2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页。。另据唐李肇《翰林志》记载,兴元元年(784)唐德宗发布敕令,要求在重要节日颁赐翰林学士衣食等物品,其中寒食节赐“节料物三十匹、酒饴、杏酪、粥屑、饮啖”[8],清明日赐新火。在元和年间(806—820年)的某个清明,在长安任职的白居易蒙唐宪宗颁赐新火,遂作《谢清明日赐新火状》,以表感恩戴德之情。其状云:
今日高品官唐国珍就宅宣旨,赐臣新火者。伏以节过藏烟,时当改火。助和气以发滞,表皇明而烛幽。臣顾以贱微,荷兹荣耀。就赐而照临第宅,聚观而光动里闾。降实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倾葵藿之心。徒奉恩辉,岂胜欣戴![9]
降及晚唐,此俗犹存。“内官初赐清明火,……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4]8126唐朝末年,历经战乱的长安一片残破之景。清明之际,长安城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气息,一派热闹的节日景象,宫廷中依例将钻取的新火颁赐给近臣戚里。晚唐五代诗人和凝《宫词》诗云:“司膳厨中也禁烟,春宫相对画秋千。清明节日颁新火,蜡炬星飞下九天”[4]8478,亦为佐证。
关于唐代清明宫廷取新火、赐新火的情形,尤以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所述为详,其赋云:
国有禁火,应当清明。万室而寒灰寂灭,三辰而纤霭不生。木铎罢循,乃灼燎于榆柳;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由是太史奉期,司烜不失。平明而钻燧献入,匍匐而当轩奏毕。初焰犹短,新烟未密。我后乃降睿旨,兹锡有秩。中人俯偻以耸听,蜡炬分行而对出。炎炎就列,布皇明于此时;赫赫遥临,遇恩光于是日。观夫电落天阙,虹排内垣。乍历闱琐,初辞渥恩。振香炉以朱喷,和晓日而焰翻。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于时宰执具瞻,高卑毕赐。降五侯以恩渥,历庶僚以简易。暖逐来命,风随逸骑。入权门见执热之象,阅有司识烛幽之义。咸就地以照临,示广德之遐被。于是传诏多士,同欢令辰。将以明而代暗,乃去故而从新。均于庭燎,贶彼元臣。……群臣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捧煦育之温惠,受覆载之光泽。……方知春秋故事,未逾于我;周礼救灾,徒称变火。曷若赐于百官,万方同荷?[3]7873-7874
赋文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清明日宫廷钻木取火、颁赐新火的庄严而又盛大的场景。清明早晨天刚亮,有司就把钻取的榆柳之火奉上,随即皇帝下诏颁赐臣僚。“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3]7874“星流中使马,烛耀九衢人”[4]3190,宦官们骑马持蜡烛从宫禁出发,沿长安城内的通衢大道将新火传送至侯第之家。随着新火的到来,“灼灼千门晓,辉辉万井春”[4]3190,近臣戚里府邸之中无不“熠熠当门,烟助松篁之茂;荧荧满目,焰如桃李之春”,继而“各爨鼎镬,传辉膳官。争焚炉炷,竞爇膏兰”[3]7874,一派钟鸣鼎食、烟火繁盛的热烈景象。
流风所及,清明日一些地方军政长官亦有以新火赠僚属之举。据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清明日,宣歙观察使韦温将新火赠给观察判官郑处诲,郑处诲随即上表称谢,表中有“节及桐华,恩颁银烛”之语。韦温认为此语有僭越之嫌,非臣子可用(14)《南部新书》云:“韦绶自吏侍除宣察,辟郑处晦为察判,作《谢新火状》云:‘节及桐华,恩颁银烛。’”据考证,“韦绶”或系“韦温”之误,“郑处晦”当为“郑处诲”。参见梁太济《南部新书溯源笺证》,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448页。。不过,相关记载仅此一见,说明此俗在唐代地方官场中似乎并未普遍流行开来。
四
苏联学者巴赫金指出:“节庆活动永远具有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内涵。任何组织和完善社会劳动过程的‘练习’、任何‘劳动游戏’、任何休息或劳动间歇本身都永远不能成为节日。要使它们成为节日,必须把另一种存在领域里即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某种东西加入进去。”[10]10有唐一代,清明改火、赐新火节俗之所以如此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其能增加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是因为这些节俗活动具有则天顺气、辞旧迎新、君恩臣报等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契合了唐人特别是统治者的精神、心理需求及现实政治需要。
(一)则天顺气,遵循自然时序,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节庆是盛大的集会,它们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季节节律步调。”[11]我国古代的岁时节日礼俗具有自然伦理属性,岁时礼俗的伦理原则是遵循自然时令,人应天时,并以岁时礼俗活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年度周期的各个关节点即时节中,人们采取顺应、补救或转益等多种方式和手段,以满足群体与个人的生存、发展的精神及物质需要,并形成一套复杂的服务于民众生活日用的时日宜忌系统,使人事与自然相和谐,“不与阴阳俱往来谓之不时”[12]。
在唐人观念中,清明钻燧改火乃是则天顺气、遵循自然时序之举。所谓则天,即效法阴阳转换、四时更替的天道;所谓顺气,即顺应阴阳、五行变化之道。王起《钻燧改火赋》说得十分清楚:
乾坤设兮,其仪有二;寒暑运兮,其序有四。圣人则天而顺气,故改火而钻燧。……尔其始也,命工徒,案林麓。选槐檀之树,榆柳之木。斩而取也,期克顺于阴阳;钻而改之,序不愆于寒燠。……冠五行以斯用,审四时而是取。……新旧迭用,无乖于天时。[3]6473
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亦明确指出:“钻燧改火,春取榆柳之火,以顺阳时火气。”[13]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引唐《辇下岁时记》亦云:“唐朝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也。”[14]春季是阳气发动、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时节,清明日举行的鼓荡阳气的钻燧改火仪式,显示了唐人重视节气迁移,遵循自然时序,并通过岁时礼俗活动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心理积淀(15)。
(二)辞旧迎新、吐故纳新,憧憬美好生活与治世图景
“节庆活动永远与时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一定的和具体的自然(宇宙)时间、生物时间和历史时间观念永远是其基础。同时,节庆活动在其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10]10-11节俗的产生与节日在时间上重要的交替意义有关。新旧交替是历史与生命过程的重大转折关头,蕴含着死亡与新生的两种因素并存,通常意味着一种需要谨慎处理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存在,以及危机的处理与克服,应该就是寒食、清明节等节日的主要意义(16)参见郑文博等《“非典”北京:文化切入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在唐人心目中,清明钻燧改火同时也是“舍旧而谋新”[3]6472“将以明而代暗,乃去故而从新”[3]7874之举。李涪《刊误》云:“《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汉已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燧。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后。既曰:就新即去其旧。今人持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15]在唐代,改火只在春季寒食清明时节举行,寒食节所灭之火与清明所取之火被赋予了“旧”和“新”的不同价值(17)参见张勃《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144页。。唐人认为,新火和旧火不可相见,新火燃起之前,必须要灭掉旧火。旧火代表燃尽的死去的生命,新火则象征新的生命。这种从旧火消失到新火产生的转化过程,是辞旧迎新的交替,是大自然生命再生的神圣仪式,更是生命的新陈代谢(18)参见阎建滨《清明旧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寒食节禁火、灭旧火,清明日改火、取新火,新旧之火的更替,正是辞旧迎新、吐故纳新的生命更新过程。
“岂徒宣明于四海,固将贻范于百王。……诚国之美利,亦君之远图。”[3]6473不仅如此,清明新火的熊熊烈焰、炜煜光束,还寄托着唐人对美好前程和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表现了统治者对新的治世图景的企冀(19)参见罗时进《〈寒食即事〉诗寓意辨误——兼论唐代寒食清明风俗及其文化意义》,载于《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此点在中唐代宗、德宗朝体现得尤为突出。唐代宗即位以后,平定安史之乱,离间吐蕃、回纥联手入扰关陇、河右地区的行径,周边诸族和邻国又相继入贡唐廷,动荡的政局基本稳定下来。与此同时,重用刘晏、第五琦,改革江淮、江汉漕运和盐政、税制,减免赋役,恢复社会生产,国库渐渐充实。在平定叛乱、社会基本安定下来之后,革新图治,谋划振兴大唐帝国,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军心民心之所向。代宗主其社会沉浮,遇事沉思,宽而善断,政治漩涡中拨乱得意,生活中多情浪漫,善始善终交班应手,总算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彼岸(20)参见刘希为、景有泉《唐帝列传·唐代宗》“引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继位的德宗积极筹措,在经济上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废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作两税法,国库收支情况大为改善;在政治上不满于肃宗、代宗的姑息之政,颇思振作一番。尽管这两方面不久又出现很多弊病,甚至大违初衷,但“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生活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16]。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唐人一旦走出安史之乱后的低谷,在虚幻承平的气象中产生的享乐愿望是生生不息,无法遏制的。……君臣们是那样急切地肇建新节一展欢娱,在传统的节日中更是文恬武嬉,欢情毕露,人人含媚嘉悦。”[17]由此可以看出,清明赐新火习俗与仪式之所以在代宗、德宗朝兴起并大行其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种习俗和仪式及其意蕴契合了时人特别是统治者试图挽救危局、实现中兴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统治者以钻燧的熊熊烈焰、炜煜之光束炫耀高居皇殿的巨大声威,以榆柳新火表现对新的治世图景的企望。
(三)君恩臣报、上下一体,维系和巩固统治秩序
在唐人看来,清明所赐新火具有多重功效,既可“销冷酒之余毒,却罗衣之晓寒”[3]7874“更调金鼎膳,还暖玉堂人”[4]3190,更可增进君臣之间的融洽相得。
“荣耀分他室,恩光共此辰。”[4]3190对于君主而言,清明颁赐新火既是显示皇恩浩荡的手段,也是收服和笼络人心的好办法。君主藉此宣告自己愿意让臣僚分享其统治权力,并希望换取他们的忠诚和拥戴。“捧煦育之温惠,受覆载之光泽”[3]7874,“就赐而照临第宅,聚观而光动”[3]5490,对于臣僚而言,清明获赐新火、沐浴浩荡皇恩而为万众瞩目,乃是一种无上荣宠。在唐代,清明日获赐新火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仅限于“近臣”“侍臣”,“华光”是难及“小臣”的,更不会“怜寒士”(21)参见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云:“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郑辕《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云:“改火清明后,优恩赐近臣。”韩濬《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云:“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云:“谁怜一寒士,犹望照东邻。”窦叔向《寒食日恩赐火》诗云:“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参见《全唐诗》,第3190、3020页。。所谓“皇明如照隐,愿及聚萤人”[4]3190,只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罢了。职是之故,清明赐新火遂成为一种彰显皇恩的标志,成为达官贵戚荣贵的风向标。获颁新火者无不心怀感恩,并纷纷上表,表示愿以忠诚回报君主的恩宠和信任。“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各罄谢恳,竞输忠赤。拜手稽首,感荣耀之无穷;舞之蹈之,荷鸿私之累百”[3]7874;“既荷惟新之恩,更沐时珍之赐,将何以仰申裨补,俯效涓埃?惟当焚灼丹诚,激励愚鲁。”[3]5388这些表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受赐新火者感激涕零、愿以死相报的忠心赤胆。
质言之,作为一种节日礼典,清明赐新火仪式被唐代统治者加以装潢和粉饰,形成了一幕庄严、热烈的场面(22)参见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无论哪一种礼典,其具体仪式都是从统治阶级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只不过被加以装潢和粉饰,成为一幕幕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场面而已。”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意在营造出一种君臣同乐、君恩臣报、上下一体的融洽场景,以维系和巩固统治秩序。
综上所述,唐代是中国节日风俗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它既继承了前代的传统,同时又有所创新,此点在寒食清明习俗中上体现得也十分明显。如文中所述,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唐人将清明改火、取新火习俗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衍生出赐新火这一新的习俗活动。在节日里,“人们通过组织各种充满欢愉的世俗活动,表达信仰、渲染情感、调节身心、强化秩序。”[2]9清明日举行的改火、取新火及赐新火习俗及仪式,既增添了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更显示了唐人重视节气迁移,遵循自然时序,并通过岁时礼俗活动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心理积淀,又蕴含着他们辞旧迎新、憧憬美好生活与治世图景的希冀,并营造出一种君臣同乐、君恩臣报、上下一体的融洽场景,客观上有利于维系和巩固统治秩序,对唐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唐宋时期,在皇家的主导下,寒食清明节的改火、赐火习俗成为一种主导性时尚,极大提升了寒食清明节文化在中国风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23)参见安介生《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33-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