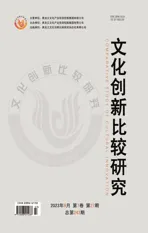浅探姜夔的诗学思想及其成因
——以《白石道人诗说》为例
2023-12-19陈若雯
陈若雯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姜夔(约1155—1221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 南宋饶州鄱阳人,其父姜噩,曾任汉阳县(今湖北武汉)知县。姜夔一生清贫,不曾仕宦,生活于高、孝、光、宁四朝,正是宋金媾和,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之时,二三十岁到过扬州、合肥等地,其《扬州慢》《昔游诗》表现“黍离之悲”,34岁后行迹主要在太湖流域,常住范成大、张鉴两家,晚年生计无着落,60余岁卒于杭州。姜夔工于诗、词、骈文,善书法,通音律,其诗初学山谷,后摆脱江西诗派藩篱,追随晚唐陆龟蒙,所著《白石道人诗说》(以下简称《诗说》)是其诗学观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姜夔诗词创作亦受文艺思想影响,现存80余首,善用精疏、清旷之余,意境高远,被张炎评为“野云孤飞,去留无际”。
1 《诗说》中的诗学思想
《诗说》是研究姜夔文艺思想的重要著作,里面蕴含了姜夔的审美理想和文学创作观念。《诗说》从美学思想、创作论、鉴赏论等各方面阐述了作者的诗学观。
1.1 兼具“浑厚”和“飘逸”的审美理想
《诗说》开篇即从“气象”“体面”“血脉”“韵度”4个方面概括了诗歌创作的标准,提出了“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的审美理想。“气象”是对外在结构、章法、布局的要求;“体面”是追求诗的整体结构宏大,气势恢宏;“血脉”要“贯穿”是指诗的内部结构要紧凑,一气呵成;“韵度”则是要求诗歌的语言要含蓄婉转,“要眇宜修”,留有馀味。姜夔所追求的审美理想是内涵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希望通过雄浑开阔的意境气势、宏大深邃的体面内涵、浑然一体的脉络及飘逸优美的韵律节奏,使诗歌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出众的形式美感,达到气势与格调、内容与形式、内涵与外在的高度统一。具体来说,气势不可太俗,应雄浑开阔;体面不可太狂,应宏大深邃;内涵不可太肤浅,应贯穿始终;韵律不可太轻,应飘逸灵动。诗人通过这种统一的审美追求,反对只重内涵或只重外在形式的极端倾向,提倡诗歌创作兼具渊博内涵与精妙绝伦的形式之美。
1.2 讲究“法度”与“活法”的内在统一
“法度”在这里一般也称作“诗法”“诗格”,指的是创作诗歌所遵循的一整套创作方法、技巧和规范。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对法度极为推崇。黄庭坚曾在《论作诗文》中说道:“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度,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1]而他所主张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理论都试图为后人形成一套作诗的法则。姜夔师承江西诗派,用他自己的话说“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就他在《诗说》中所云“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守法度曰诗”等内容,他认同作诗必须遵循法度的主张。但姜夔对于诗法并不是盲目地遵循,由于黄庭坚等人过于推崇“承词”传统,模仿和套用前人诗词非常严重,导致创新性不足。另外,江西诗派追求语言的隽永,也导致诗歌语言晦涩难解,脱离现实。姜夔在吸收吕本中“活法”说、杨万里“诚斋体”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度”与“活法”的统一。“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这段话强调写诗要适可而止,要懂得掌握运用学识的分寸,语言要精练准确,叙事中加入说理,使作品既严谨又不失生动。对于破除江西诗派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则是强调写诗创作要灵活多变,变化虽不可极尽,但要遵循诗歌的内在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法度”。
1.3 兼具儒家的诗教观与道家崇尚自然的风格
姜夔在诗学观念上融汇了儒家诗教理念与道家意境理论,形成了兼具雅正与自然的独特风格。姜夔虽然一生未曾仕宦,但从他晚年向朝廷进献《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和《圣宋饶歌鼓吹十二章》之举可以看出,他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这一点在《诗说》中也能证实。他认同儒家的诗教观,认为诗歌语言要庄重简练,反对绮丽伤感的风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又提出“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这一点也是沿着儒家的“诗言志”传统而来的。他继承了儒家“兴、观、群、怨”诗教功能论,强调诗歌的教化意义,许多作品体现出对儒家伦理价值的追求。同时,他又深受道家自然意识影响,倡导意境自然写作,反对修辞与辞藻的浮滥风格,“沈着痛快,天也。自然学到,其为天一也”“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表现出自由灵动、复归自然的艺术追求。姜夔体风格简单自然、内涵丰富,既体现儒家诗歌雅正传统,又呈现道家意境的天然高妙。姜夔通过吸收儒道精髓,打破前人之藩篱,开拓出一种新颖的诗风,这种风格即为张炎所标举的“清空”“骚雅”。 “清空”和“骚雅”两者实为相通,“清空”使得意旨远,“骚雅”使得格调高,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白石词的独特风格。
1.4 追求意格,讲究韵度
《诗说》中有好几次提到了“意”与“格”的关系,如“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通俗来讲,“意”指的是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意旨,它反映诗人的情感和思想;“格”指的是诗歌的风格、格调,反映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手法。这两个字经常放在一起,但姜夔却在这里有意分开,强调“意”和“格”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文论史上是首创”[2],两者都含有抽象意味,只不过“意”是指内容,“格”是指形式。他还提出“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表明创作者不应只追求字句的工巧,而要从整体意格的构思入手,使句子既有深远的意境和格调,又有明快优美的语言,两者相结合才能成为好作品。真正杰出的作者在意境和语言上都能达到较高的境界。除此之外,姜夔还反复提到“韵度”一词,如“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他也曾在《题梅溪词》中评价张镃的词“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意家,会句意于两得也”[3]。可见“韵度”是姜夔诗论中的评价标准之一。“韵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关于诗词音乐美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主要指诗词在声音组合上的和谐美感。不管是唐代定型的格律诗,还是和曲而作的宋词,诗词这两种文体本身就富有与音乐相关的属性,因此“韵度”也成了衡量诗词美感的重要因素。姜夔这里所讲的“韵度”可以理解成作品的音乐性,“韵度欲其飘逸”就是说诗歌的韵律要灵活舒展,而不是过于死板。韵律可以体现每个作家的独特风格,“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亦无矣。鸡林其可欺哉”,这种“韵”也就构成了作品本身的独特韵味。那么姜夔所讲的“韵度”与司空图的“韵味”又有没有相似之处呢?答案是肯定的。司空图的“韵味”本身就包含对于作者本身精神品格的品评,“韵味”来自作家深厚的修养和个性品格,是其独特的审美情志的表现。姜夔推崇陶渊明,认为其“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恰恰证实了姜夔认为写诗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不是一味效仿前人,而风格的形成既与自身天赋有关,也与创作者的个性情趣相关,换句话说,诗歌所展现的风格意蕴便是诗人精神风貌、审美情趣的外化。
2 姜夔诗学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宋代文化中心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以靖康之难为分界线,完成了由北向南转移。以都城临安(今杭州)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是南宋文化的标志,特征是文人心态趋于雅化,无论从文学、音乐、书画、瓷器的发展,抑或瓷器隆盛、饮茶之风盛行皆可窥探。南宋光宗时期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序》[4]有证:
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研,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姜夔生活于南宋中后期,30岁以后其行迹遍布太湖附近,42岁移居杭州,后定居于此至死。受到雅文化的浸染愈发深厚。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载《姜尧章自述》所言,他与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朱熹、京镗、谢深甫、辛弃疾等当世名流结交,朱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姜夔当时被作为高雅之士,得到认可。其词《湘月》序云:“丙午七月既望,声伯约予与赵景鲁、景望、萧和父、裕父、时父、恭父,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坐客皆小冠綀服,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笔搜句。”颇有苏子逍遥人间的惬意洒脱,从侧面印证了他雅致的生活方式。这种尚雅、崇雅的志趣不仅限于人品与生活情趣上,还体现在他文艺创作的追求中。
“雅”出自《毛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5]。雅,原本就与政治相关,是儒家积极入世人生观的体现。姜夔虽终生未仕,但生于官宦之家,早年习儒,青年时期曾4次参加科考,其文艺思想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较深,他与朱熹交好,尤其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提出“中正”“醇雅”的审美理想。朱熹《诗集传序》论“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6],姜夔在《诗说》中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二者都继承了孔子“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观。“无邪”即“归于正”,“思虑悖礼违义之事为邪念。邪念者,过而不正也。”[7]姜夔在《诗说》中反复强调“中正”之论:“《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这与《诗大序》中“主文而谲谏”的核心是一致的,即诗歌可以用以针砭时弊,但其方式需委婉含蓄。关于诗歌的创作他提道:“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指出在“雕刻”和“敷衍”中取中的道理,强调作诗要秉持中道,不粗拙不鄙陋,恰到好处。“雅”还与“俗”相对,体现高雅的情趣和创新的精神。《诗说》中多处流露出作者别出心裁、超尘拔俗的诗歌审美理想。“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从选题着手强调内容和素材的新颖;“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则从创作论出发讲如何使诗歌创作不落俗套;“若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8]则是强调诗有“馀味”,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标准。姜夔词曾被张炎评为“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9]。“清空”与“质实”相对,“清”既可形容人的品格高洁,又可代表文学作品的风神意境,“空”乃佛家用语,有脱离凡俗、超世绝伦之意。“清空”二字准确概括出姜夔其人清高狷介、疏宕不羁的性格品性及其作品古雅峭拔、空灵俊逸的特点。
3 姜夔人生经历与其诗学思想形成的关系
少年失怙,无缘仕途,寄人篱下,居无定所,人生经历和个性才情成就了姜夔孤傲狷介、娴雅淡泊的品格。姜夔出生于鄱阳一个落魄官宦之家,父亲姜噩曾任汉阳县令,姜夔自幼便随父亲宦游,家庭背景和宦游经历给予姜夔良好的教育,亦为他的博学多才打下基础。15岁时姜噩卒于汉阳官次,姜夔只能依姊居汉川。姜父的早亡让姜夔发出“吾少孤贫”的感叹,寄人篱下的生活也让姜夔少年老成,性格敏感疏宕。他精通诗文、熟谙音律,才情极高,但在“举业”方面却显得迟钝。成年后姜夔曾4次返饶州参加应试,均未果,后便放弃进入仕途。淳熙十三年(1186年),白石随肖德藻寓吴兴,从此至庆元初八九年间皆在吴兴,开始了一生漂泊、靠人接济的生活。后通过肖德藻引荐交识杨万里、范成大等人。40岁左右与张纳交,后因肖德藻离开湖州,白石眷属无所依靠,又移居杭州,受张氏兄弟资助。姜夔的人生经历挫折,但政治经历却是一张白纸。他交往的都是名流巨儒,如他在自述中所言“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他在艺术层面的才华是受到上流人士认可的,但他从未任过一官半职,不曾深入官场参与政治风云,亦没有深入底层体察民生疾苦。34岁后他的行迹基本不出太湖,每日生活内容也都是研词作曲、酬唱交和,狭小的交际圈与简单重复的生活内容决定了他的作品内容只限于抒发自我的身世感慨,始终走不出自我的小世界,即使触及政治类型的作品,也无法像苏辛一样揭露深刻的社会矛盾、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的整体风貌。
生活窘迫和过高的才情形成巨大反差,形成了姜夔清高孤傲、洁身自好的个性。南宋中期江湖游士盛行,他们将文字作为生存和干谒的工具,许多落魄文人靠着给游士写文作词来过活,大多数江湖文人的生活状况并不像他们作品里所展现出的那般潇洒恣意,反倒是经常生活窘迫。在此情景之下,许多文人丢失了自己的仙风道骨,为求荣华富贵不惜趋炎附势、曲意逢迎,如宋谦父一见贾似道,得楮币二十万,便建起了阔房子(见方回《瀛奎律髓》)。而姜夔虽一生寄人篱下,却始终保持狷介清高的品性,与他交往的肖德藻、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等一众南宋名士对他的人品评价甚高。张钅监更是与他“情甚骨肉”,不仅自愿割田赠与姜夔,还主动提出为他“输资以拜爵”,但姜夔却“辞谢不愿”[10],由此可见姜夔傲骨卓群,未曾改变。
姜夔词偏爱写梅,梅亦是姜夔心性人品的象征。梅花傲寒而开,又因其冷冽幽香,常被赋予卓尔不群、超世脱俗的人格气节。姜夔爱梅、慕梅,据夏承焘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统计,姜白石写梅花的词共有18首之多,占其词作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梅花被寄予了白石的身世之感,是其人格品性和精神追求的象征。《卜算子》中“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惆怅西村一坞春,开遍无人赏”[11],看似在写梅花的独自幽香、无人垂怜,实则是自悯身世,抒发怀才不遇的忧闷。梅花是姜白石的人格写照,清高自守、避世尘嚣、适性自乐又不萦外物,环境和个性的双重影响使其注定难以在官场上施展抱负,终身不仕。姜夔向往当一名隐士,常以陆龟蒙自比 “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松作客归”(《除夜自石湖归苕溪》)“沉思只羡天随之,蓑笠寒江过一生”[12],却因无资购田正只得靠人接济,漂泊一生。
4 结束语
姜夔生活在南宋中期,这是一个国势衰微但文化相对昌明的时代。姜夔出生书香门第,少年即以词才见长,但因4次科场失意,无法通过仕途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他只能寄人篱下靠他人接济度日,其生活圈也局限于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这使得他的作品内容不直接涉足政治,主要抒写个人情怀,较少针砭时弊的内容。南宋雅化的文化环境及与文人学者的密切交游使姜夔得以汲取众家之长,丰富自身的创作经验和技巧。尽管上承江西诗派,姜夔却能“从诗法进一步超出法,并告诫诗人不要拘泥于法度,且更深一层谈到韵味,将诗歌同人相比,注重灵气”。此外,少年失怙、长期依靠他人援助的生活处境增加了姜夔对外在环境的敏感与不安,其本身清高狷介、不求名利的个性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寻求心灵寄托,通过建构一种异于世俗的文人空间来追求个人的闲逸和情感的表达。尤其是他的词作,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特色,通过融入自身的艺术感知和审美情趣,运用空灵、超逸的笔调,抒写京洛遗踪、桃花源深处的意境,形成独特的“幽韵冷香”风格,将宋词之美推至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