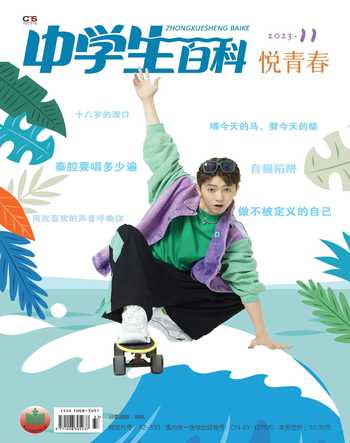名字暗示了一种缺乏
2023-12-14陆隐
陆隐

我不喜欢我的名字,仅仅是不喜欢,如此而已。
母亲给我取名字时想得很多,她听人说我命里缺水木,便找了大量“梓溪”“洛梵”“楠汀”之类的名字,体面并且诗意,如同旧时穷人家给孩子取名“富贵”“大富”等。这些名字暗示了一种缺乏,如内衬的补丁,看不到但够暖和;诗意是外部的美化,不保暖,但够浮华。在这样的语境下,名字成了填补空缺的事物,仿佛是一张贫困列表。后来据说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与她在一棵大树下走失了,她难过万分,便给我取名为“树”,全名李树。与最初的取名逻辑并无二致,我的名字照样是一种“担心缺乏”,前者担心不足,后者担心失去。
人们喜欢他人喊自己的名,像我,习惯别人喊我“树”或“阿树”。一个熟识之人连名带姓地喊我,会让我觉得有一种陌生感和距离感。如果一个经常喊我“阿树”的友人有天突然喊我“李树”,我会怀疑我们之间出现了某种异常,以至于他主动在称呼上抹掉了我们之间原有的亲密。按理说,姓与名一样,都是自己的,被完整地称呼,应该会倍感亲切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姓会给人以严肃感,产生一种似乎难以逾越的隔离。
我也不喜欢我的名字,从小时候开始。直到现在,在任何形式的点名环节上,我常常忘记答“到”。我的名字被点到时,我觉得别人是在喊一个局外人。这种疏离感和陌生感常常使我感到恐惧。名字,似乎不过是一个符号,签到时它和ABCD并无不同,是人们试图通过統计名字这一符号来统计我的存在。
说到符号,如今的人们喜欢加大认同或者表面认同名字的符号性,然而说这话的人往往有一个平庸之名,说这样的话只是一种开脱。即便是大肆宣传“名字不过是符号”的文人,照样会给自己取一个意义非凡的笔名,来与可能俗不可耐的本名保持距离。当然,说一套做一套是不用修辞手法的。
就算是普通人,网络通信工具上的名字也经常更换,随着时间更换,随着一件小事更换,甚至随着心情更换。名字是别人给的,而笔名或网名则是我们自己取的。从这一点来说,笔名或网名的存在照样是一种“缺乏”的暗示,缘于现实的恐惧,缘于真实姓名的匮乏和我们自己对它的偏见。
像我,就时常更换笔名。对于写作,我是恐惧的,因为大部分天才之外的人没有“提笔就老”的天赋——他们写作,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像幼儿学习走路、吃饭,这不是天赋,而是生存的技能。随着时光渐逝,学习中的写作者会发现之前作品的不足,拿起一篇曾经自我认同而今却不忍直视的作品,不修改吧,显得过去太愚昧太自大,若重新书写,则背弃了一段时光。因此,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换一个笔名,仿佛换了名字就会成为另一个人,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名字是有记录性的,它记载了一段时光、一段历史。正如历史是不能篡改的,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存在的实质。就像现在的我,仍旧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但从不拒绝它。它代表了两代人之间的希冀与交换。身体发肤,还有名字,都是受之父母的。我逐渐习惯了我的名字,在相对的美丑之间。
后来,我试着在作品里为“我的孩子”取一个可能会让他觉得美的名字,甚至会在不同的作品里使用同一个名字让他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这,也是一种成长。对名字的匮乏的认同,显示了一个人成长的足迹。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青春小说里,有很多很好听的名字,如未央、简生、齐铭等。如今,我不再读青春小说,随着阅读的进步我可能忘记了那些作者的存在,但依旧记得那些人物的名字。它们展现的,是青春稍纵即逝的匮乏,错过了,就是永远地失去。
名字如掌心的暗纹,终将伴随一个人走过一生,甚至更远。有一天,当我们不在了,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历史全都化为时光这个巨大手掌的浅浅暗纹,或许一个熟人的孩子或是一个陌生人会在水边桥头提起我们的名字。在很久很久以前……听,多美,我们的那些平庸之事也成了别人眼里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