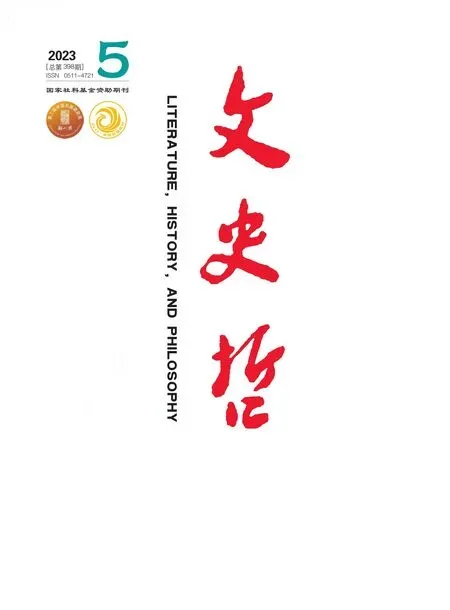范式与问题:美国的唐宋思想转型研究
2023-12-13葛焕礼
葛焕礼
自宋代以降,唐宋之际学术思想的转型即受到东亚学人的关注,现代学术建立后,更是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二战后美国汉学界受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对宋史尤其是宋代思想史研究致力颇多,积累起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除对此课题的专题论著外,很多思想史成果因探讨宋代新儒学的起源和性质,也关涉到唐宋思想转型问题,而且相关研究在范式和议题上不断出新,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术传统,在欧美宋史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中一些观点,近些年来甚至对东亚的宋史研究产生了反向影响。对此学术传统的构建和评述,田浩(Hoyt C. Tillman)《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宋代思想史研究》(1)田浩:《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宋代思想史研究》,江宜芳译,《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第3卷第4期,1993年,第63-70页。,吾妻重二《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最近的情况》(2)该文原刊于《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6卷,1996年;译文见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9页。,许齐雄、王昌伟《评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兼论北美学界近五十年的宋明理学研究》(3)许齐雄、王昌伟:《评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兼论北美学界近五十年的宋明理学研究》,《新史学》(台北)第21卷第2期,2010年,第221-240页。等文,已有所涉及。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对代表性学者论著的解读,从历史角度对美国唐宋思想转型研究的范式变迁和观点认识进行述评,以期深化学界对此学术传统的认识。限于篇幅,所述学者和成果难免挂一漏万,尚请方家教正。
一、观念史的研究:从赖肖尔到狄百瑞、陈荣捷

在1955年据其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圆仁在唐代中国的旅行》一书中,赖肖尔认为“9世纪是一个新局面的转折点,那是‘一个伟大的形成期’,‘最近几个世纪里西方所接触到的那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根本特征,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4)狄百瑞所述赖肖尔此书中的认识,见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页。。这些特征包括:“新儒家哲学,近代的渊博学术,伟大的风景画和陶瓷产品,主要是基于土地而非人头的新的税收制度,商业财富与国家财政间更为紧密的关系,大的商业城市和东南沿海港口海外贸易的繁盛”(5)Edwin O. Reischauer, 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5), 8-9.等。这一认识,显然受到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所代表的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历史分期说和“唐宋变革论”的影响。


赖肖尔早年讲授的“东亚历史概况”课程,对狄百瑞产生了重要影响。1986年,狄百瑞受邀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赖肖尔讲座上演讲东亚文明传统时,“承认了这种早期的受惠”(14)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序言”第2页。。在据此演讲内容而出版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15)Wm. Theodore de Bary,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 Dialogue in Five Stag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一书中,狄百瑞将东亚文明(以中国为主)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二、三阶段分别为“佛教时代”和“新儒家阶段”。这两个阶段的转换,发生在唐宋之际。他坦承这一解释,是从“经过了几十年”“深入、专门的研究”的唐宋变革论入手的:就佛教而言,一方面自8世纪末以后随着“唐朝本身的瓦解”,“大的寺院体制和各个教义派别衰落了”;另一方面,代之而起的禅宗和净土宗都不能解决晚唐五代的政治、社会失序问题。因此,“在与本国传统的对话中,必须发现新的答案,必须设计新的机制和运载工具”。宋朝建立后,极其强调与武功相对立的文治,“鼓励各种有关形式的学术和世俗教育”,“出现了一个新的文人阶层、一群官僚的和文化的精英”,同时,“文官考试制度扩大了,官吏的来源有了相对公开的渠道”,这就提高了对教育的要求并使人越来越注意到需要有培养相关人才的学校。正是由于企图解决这一教育的需要,便诞生了新儒学(16)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第38、43、47、48页。。
由上述可见,从赖肖尔到狄百瑞,对于唐宋思想转型的叙事可谓一脉相承,即他们都认为是从佛教转向新儒学,且都在唐宋变革论的论域内进行解释。狄百瑞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唐宋思想转型后的思想形态——宋明新儒学,他从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的思想入手,上溯被黄宗羲所珍视并作为其思想渊源的宋明新儒学,有《心学与道统》(17)W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中国的自由传统》(18)Wm. Theodore de Bary,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道学与心学》(19)Wm. Theodore de Bary, The Ma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等著作。狄百瑞为学的基本路数,是“紧扣宋明儒学中具有关键性的‘单位概念’(罗孚若所谓unit ideas)如‘为己之学’‘自得’‘自任于道’等,进行观念之史的追溯及其发展过程的爬梳”。这种观念史的研究,虽然也关照由于缺乏创新性而被哲学史研究所忽略的著名思想家(如朱熹)之后学的思想,但其“将概念抽离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网络中,进行孤立的解析”的主要研究进路,实与哲学史研究方法类似,被黄俊杰称为“内在研究法”(20)黄俊杰:《战后美国汉学界的儒家思想研究(1950-1980):研究方法及其问题》,《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狄百瑞为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着重探究新儒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最初吸引他踏上“新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研究之途的,是黄宗羲思想中的民主观念。在二战后兴起的世界性反儒学思潮尚未退歇的20世纪80年代初,狄百瑞就深刻指出,像中国六七十年代那样力图抹杀儒学以求得“从过去中彻底得解放的做法最终已证明是徒劳的”,“正视过去并接受它当是更为合理的做法”;“现在是时候将其视为一种古代积极的教育力量而非一种消极、束缚人的正统观念来重新评价儒学了”(21)Wm. Theodore de Bary, “Prefce”,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可以说狄百瑞毕生为学都贯穿着从中国乃至亚洲其他文化传统中探寻现代价值这一主线。他的新儒学研究亦如此,如《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集中讨论了宋明新儒学中“那些渊源于传统儒家但同时也朝着‘近代的’‘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观念”(22)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页。。他对新儒学的这种现代诠释,从思想史上论证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被评论者认为“人们(从中)能够辨认出内藤湖南坚持认为中古时代也明确无疑具有现代性这一论断的解释性遗迹”(23)詹启华:《在倒塌的偶像与高贵的梦想之间: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札记》,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第37页。。
协助狄百瑞确立起新儒学的这种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是与他有着密切学术合作的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陈荣捷于1929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高校,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他“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也是国际汉学界新儒学与朱熹研究的泰斗”(24)陈来:《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序》,陈荣捷:《朱子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自1949年起,陈荣捷与狄百瑞持续合作30余年,成为推动宋明理学逐渐受到西方汉学界重视的最主要的力量。
陈荣捷对唐宋思想转型问题的认识,可见于他编著的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25)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中译本由杨儒宾等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93年、2006年出版。。该书第22至26章、第27章至34章,分别选译、论述唐代佛教重要宗派的代表人物和中唐儒学复兴代表人物以及宋代新儒家的文章和学说思想。从此篇章安排来看,陈荣捷遵循了注重“创新性思想”的中国哲学史的通常编纂理路,用“谱系学”的方法呈现了唐宋时期从佛教到新儒学哲学的转型。关于新儒学的起源,他认为韩愈和李翱“是在11世纪发展的新儒学之先驱”,“大大地决定了新儒学的方向”;周敦颐则是“真正开拓新儒学之视野并决定其导向者”(26)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90、397页。。这些认识也都相合于此前冯友兰等所构建的中国哲学史叙事。
作为哲学史家,陈荣捷研究新儒学的方法,首先是“重观念史的分析”。他对新儒学重要概念的内涵都做过深入分析,由之“探讨学派流变”,隐约构建了“以‘唯心’(传统所谓‘心学’)与‘唯理’(传统所谓‘理学’)为宋明儒之两大主流”(27)黄俊杰:《出版前言》,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第16页。的解释框架。其次,“不忽视史实考证”(28)陈来:《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序》,陈荣捷:《朱子学论集》,第4页。。陈荣捷对新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等,尤其是朱熹的事迹和门人,都以专题的形式做过系统考证。义理与考据并重,是陈荣捷为学的显著特点,但他考证事实的目的,主要是探寻真相,并无结合事实以论析思想的取向,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影响他的新儒学思想研究属于观念史研究的定性。
狄百瑞对唐宋思想转型和新儒学所作的观念史阐释,得到了陈荣捷新儒学哲学研究的支撑和强化,从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内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史研究范式,但他们基于西方哲学概念的新儒学思想阐释,以及“将‘中国思想’还原为儒学”一元性的做法,被批评完全脱离了本土语境和历史语境(29)参见詹启华:《在倒塌的偶像与高贵的梦想之间: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札记》,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第34页。早在20世纪80年代,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余英时已就明代思想史的研究,分别对狄百瑞和他的弟子钱新祖的著作所体现的“将思想和思想家从历史的环境与脉络中抽离了出来”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可参见Frederick W. Mote, “The Limit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Ming Studies 19(1984): 17-25. Yu Yingshi,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ited,” Ming Studies 25(1988): 24-66.。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以狄百瑞、陈荣捷为代表的新儒学研究先后受到三种“为中国思想观念的历史填充语境”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这些挑战分别来自:1.刘子健等学者着眼于新儒学正统地位确立的政治文化史研究;2.余英时、田浩等学者探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思想存在的文化史研究;3.包弼德(Peter K. Bol)等学者基于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P. Hymes)的唐宋精英转型说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二、渗入政治、社会的思想:刘子健“两宋之际转型”说和史乐民等“宋、元、明过渡”说
刘子健是美国宋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与日本宋史学界有着相当密切的学术联系。正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唐宋变革的意义及其后的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和论战,引发了他对唐宋变革问题的关注。1964年,他在《亚洲研究学报》发表《中国历史上的新传统时期:纪念已故雷海宗教授短札》(30)James T. C. Liu, “The Neo-Traditional Period (ca. 800-1900) in Chinese History: A Note in Memory of the Late Professor Lei Hai-tsu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105-107.一文,就唐宋变革问题,反驳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说、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承之而持的“近代早期”说,提出公元800至19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新传统时期”说。刘子健认为,无论是“文艺复兴”说,还是“近世”或“近代早期”说,都来自欧洲历史经验的内涵,并不符合中国历史演变的实际;“新传统”表示旧传统被有选择地延续,新出现的一些因素与延续下来的旧传统一起整合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此“新传统时期”至少有三个特征:1.新传统渗入平民社会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旧传统,因而更为稳定、坚韧和持久;2.仍然有发展变化,但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循着在旧传统之下新传统得以形成的那种模式;3.竭力抵制任何突然、剧烈或根本的变革,更不用说革命。
尽管作了特征说明,刘子健所提出的“新传统”的内涵仍嫌宽泛。1973年,他在《东西方哲学》发表《一个新儒学流派是如何成为国家正统的?》(31)James T. C. Liu, “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3.4(1973): 483-505. 中文版相似的内容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为题,发表于《文史》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148页。一文,将“新传统”的内涵由理学笼罩下的国家政教体系及其运行方式化约为其引领成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这样,他一反自宫崎市定以来日本学者注重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论证唐宋变革及其后社会性质的做法,而明确将其视为一个思想史的问题,即在政局变动中新儒学正统的确立问题。沿此理路,刘子健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即1988年出版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32)James T. C. Liu,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8). 中译本由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2012年再版。。此前,“大批前近代史料和20世纪的东西方学者都习惯于一枝独秀的叙述模式,太过关注某些显赫的哲学派别,特别是新儒家学派”,刘子健则抛弃了这一路径,转而以“儒家的政教观”为研究视角,围绕南宋前期的皇权政治及其与新儒家的关系,论述以12世纪新儒学思潮的空前壮大并在宋末被树立成国家正统为表征的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型。刘子健将形成这一转型的基本历史脉络概括为:南宋初高宗和长期独掌朝纲的权相秦桧压制异见,形成了“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政治;“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新儒学得以在朝廷之外发展;南宋后期,“朝廷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危机的不断加剧”,使新儒学的政治地位不断获得抬升,最终于1241年被朝廷正式宣布为国家正统;然而,“新儒家本身却转向了内在,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实。调整和创新仍然存在,但都只是量的增加,而非方向的转变与开拓”,他们与专制的国家权力相互作用,“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藩篱,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立论说:“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33)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126、145、146、147、148页。
简言之,刘子健所持的“两宋之际转型”说的主要依据,是理学在南宋前期被专制皇权政治压制、在朝廷之外得以创新发展并逐渐在朝野扩展其影响,乃至在南宋末年以后被朝廷树立为国家正统的历史,即理学影响下的新的国家政教系统的确立。这就将唐宋思想转型叙事中作为对比方的宋代思想,由北宋新出现的理学思想,转变为南宋以后在政治、社会、文化中得到制度性落实的理学思想。这一视域转移,不仅在“唐宋变革论”下开启了“两宋之际转型”说,而且在思想领域成为后来史乐民(Paul J. Smith)等学者提出的“宋、元、明过渡”说的先导。另外,刘子健得出的理学与国家权力相互作用“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的结论,实质上是从思想文化角度论证了由内藤湖南提出而被赖肖尔、费正清等所继承的中国“近世发展停滞说”。刘子健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学者,上述研究是他对中古以降中国历史进程的反思,旨在呼唤传统中国实现从制度到文化的变革,所以他的停滞说与内藤湖南的相比显然有着不同的意旨(34)虽然谷川道雄、傅佛果(Joshua A. Fogel)等学者另有解释,但已成为学界共识的是,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发展停滞说”是其“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有着为日本入侵和统治中国张目的意旨。参见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5-236、240页;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陶德民、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3-259页。。
史乐民等学者的“宋、元、明过渡”说集中体现在他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合编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35)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一书中。在该书序言中,史乐民对此说作了论证:过渡的时段是从南宋起始的1127年直至1500年左右,主要表征有:1.期间中原与草原地区周期性的战争造成了此过渡最显著的特色:人口和技艺集中到唯一免遭破坏的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2.江南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舞台,其他地区直到16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才得到恢复;3.该时段内的国家与唐宋及清朝全盛时期相比显得更为消极被动,而社会政治精英则更为独立自主,政治重心已由11世纪的集权国家转向受过教育、拥有土地的地方精英所形成的“士绅统治”;4.道学为新兴的富有自我意识的地方士绅提供了意识形态,并对精英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制度产生渗透(36)参见史乐民:《宋、元、明的过渡问题》,张祎、梁建国、罗祎楠译,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7-285页。。
此“宋、元、明过渡”说并未否定唐宋变革论,而是基于地域视角,将此过渡视为唐宋变革所产生的新因素植入历史实践并发展成熟的过程,即作者所谓的“不妨把宋、元、明过渡看作是唐、宋转型时期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趋势在江南的地域化”(37)史乐民:《宋、元、明的过渡问题》,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第254页。。就理学而言,作者对它在此过程中与政治相结合、政治地位显著上升的认识,与上述刘子健的论述一致,而对理学所引导的地方社会运动兴起的认识,则与下文所述包弼德所引领的道学社会史研究相辅相成。
三、探寻历史情境中的思想真实:余英时和田浩

自1999年秋开始,因为德富文教基金会标点本《朱子文集》写序之机缘,余英时对朱熹的“历史世界”进行了深入研究,于2003年出版《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该书虽以“研究朱熹时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为主,但视野不限于朱熹时代,作者借鉴年鉴学派“中时段”的研究方法,上溯至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以呈现包括其“创世纪”在内完整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因该书乃基于儒家的思想和行动论述士大夫政治文化,故与其宋代政治文化历经三阶段演变的论述相因应,余英时勾画出了宋代儒学思想的演变脉络:第一阶段为“从柳开到欧阳修的初期儒学”,即“宋初古文运动”,“这是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直接延续”,“对韩愈的道统观进行了有力的传播”,但“内圣”之学尚无建树,政治上以回向“三代”相号召;第二阶段则始于王安石,他“发展了一套‘内圣’和‘外王’互相支援的儒学系统”,“获得‘致君行道’的机会,使儒学从议论转成政治实践”,同时期的程颢、程颐、张载等创立道学,“新学”是他们“观摩与批评的对象”,受其激发而发展出儒家的“内圣”之学,从整体上完成了对它的超越;第三阶段始于12世纪下半叶的朱熹时代,当时道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界”,取代“新学”而成为儒学的主流,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型范开始发生变异”,“但与第二阶段之间的延续仍远大于断裂”。经历这三个阶段,宋代儒学思想的重心“从前期的‘外王’向往转入后期的‘外王’与‘内圣’并重”,其间“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儒家要求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3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9、40、42、46、47、56、45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儒学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也就是理学的起源问题上,作者一反哲学史界惯常所持的“近承韩愈、李翱”说而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从儒、释互动的角度给出新解:北宋初、中期,佛教中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重视世间法,关怀人间秩序的重建”,一些高僧大德如智圆、契嵩等“精研外典,为儒学复兴推波助澜”,他们“最先解说《中庸》的‘内圣’涵义,因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谈辩境域’(discourse)。通过沙门士大夫化,这一‘谈辩境域’最后辗转为儒家接收了下来”。同时,《中庸》及《大学》又“通过好禅的试官而进入贡举制度”,传遍天下,进而被理学家所接受(4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82、96页。按,20世纪40年代钱穆曾论及禅宗对理学之生发所起的引导作用,认为禅宗为“隋唐宗教师”和“宋明儒”间的过渡,“主张本分为人,已扭转了许多佛家的出世倾向,又主张自性自悟,自心自佛,早已从信外在之教转向到明内在之理。宋明儒则由此更进一步,乃由佛转回儒,此乃宋明儒真血脉”(钱穆:《宋明理学之总评骘》,《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06页)。。作者隐约呈现了这样的影响脉络:士大夫化沙门→好禅的士大夫→王安石→二程等理学家。
如多篇书评所指出,该书内容的最大特色,是摆脱“将注意力集中在理学内部的理论构造”的哲学史研究范式,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深入具体的历史情境,来探讨宋代“理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从而集中呈现了理学家的“外王”思想和政治实践。余英时指出,作为传统“道统论大叙事”现代化身的哲学史聚焦于“道体”的理学研究,“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这样做虽然符合了哲学史学科的要求,结果却造成了这样的普遍印象,即“理学所处理的主要是不在时空之内的种种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与当时实际政治的关系仅在若有若无之间”。余英时对宋代理学的政治性的解读,有助于消解这一偏颇的认识,而更引学界关注的是他由此厘定了理学的性格,即秩序重建是理学最主要的关怀,“‘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4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8、183页。。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的主旨,即是以朱熹为中心来论证理学的政治性格。为此,余英时一方面从“事实世界”入手探讨朱熹等理学家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另一方面着力论证王安石时代与朱熹时代在最高权力结构及运作方式、士大夫政治文化上的延续性。此延续性表现为:南宋权相与皇帝的“权力关系及运作方式”,乃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中移步换形而来”;自神宗朝至朱熹时代,“宰相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对‘国是’负责,也就是与‘国是’同进退”,“而在位的士大夫则‘视宰相为进退’”;自神宗熙宁至理宗宝庆年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的观念持续了150年之久,未尝断绝”;“得君行道”作为王安石变法时代出现的士大夫群体意识,在南宋“由理学家承当了下来”,他们“热烈地参与了孝宗末年的改革部署”。因为前后两个时代有此包含多重因素的延续性,余英时称朱熹的时代为“后王安石时代”,因而才有了这样的思想史叙事:“朱熹的历史世界不是从南宋开始的,它的创世纪必须上溯至熙宁变法。”(4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249、258、327、161、249页。
就理学家而言,“后王安石时代”的指称强调了这样的认识:即使在理学成熟的南宋时期,理学家仍然怀有以“得君行道”为旨归的政治期望,“随时待机而动”。这一论述,反证了学界两种流行的观点:其一是前文所述刘子健提出的以新儒家(社会精英)致力于“修身和内心的思想”为表征的南宋文化“转向内在”说。此说的形成与哲学史研究所造成的理学与现实政治无关的“普遍印象”密切相关,余英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明确反驳云:“即以最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如朱熹和陆九渊两人而言,他们对儒学的不朽贡献虽然毫无疑问是在‘内圣’方面,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更重要的,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作准备的。”(43)余英时:《自序二》,《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11-12页。因此从理学家整体来看,重建秩序才是他们最主要的关怀,不能仅看到其在“内圣”上的努力和成就便认定他们“转向内在”。
其二是下文所述美国宋史学家郝若贝、韩明士、包弼德等所持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说(44)许齐雄、王昌伟亦曾指出,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除明确表示“不认同‘大叙事’典范下的研究”外,“没有点破的另一个批评对象就是北美学界的社会史学者Robert Hymes”。见许齐雄、王昌伟:《评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 ——兼论北美学界近五十年的宋明理学研究》,第221-240页。。余英时指出:“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如即使被韩明士当作“地方化”的南宋精英之“原型”的陆九渊,“在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期间有过‘得君行道’的深切期待。他正是因为想步王安石的后尘,从中央改革全社会,才被‘小人’逐出临安”,他的“许多门人如徐谊、杨简、袁燮等都参与了孝宗末年的改革部署”(45)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附论二,第897-898页。。南宋士人的秩序重建虽然包括家族和地方建设,但是“‘治道’——政治秩序——则是其始点”,因此从整体上看不存在精英的致力方向“由国家转向地方领域”的趋势。
另外,对理学为封建皇权服务、理学家是专制皇权辩护士的说法,余英时也作了有力的反驳。关于宋代以后皇权专制愈加强化的说法,一方面来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他们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宋代出现的‘现代’因素最后无法实现”的问题(46)参见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王昌伟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刘子健也认为“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发生了“专制权力的扩张”的决定性变化,其“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47)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第78页。。另一方面来自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中国历史分期说,他们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的起始时代,“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更为严重的时代”,理学是支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工具。余英时认为,在思想上,“朱熹一方面运用上古‘道统’的示范作用以约束后世的‘骄君’,另一方面则凭借孔子以下‘道学’的精神权威以提高士大夫的政治地位”(4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35页。,理学“‘天理’‘太极’之类的观念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构成了对‘君’的一种精神约束”(49)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附论二,第889-890页。;在实践中,儒家士大夫中出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乃至与皇帝“共定国是”“同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并有不少信奉理学的大臣践行之。这些都彰显了宋代理学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和理学家“与皇权相抗衡”的政治主体意识。
总体来看,余英时的这项研究在材料引释、论说细节方面或有可议之处,但在修正学界对宋代理学的一些偏颇认识,尤其在呈现理学的历史存在形态上,贡献卓著。他从个体人物的事实世界入手探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思想”的研究路径,也具有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范式意义。早于他而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宋代理学的,是他的弟子田浩。
田浩于1976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余英时和卡罗琳·拜努姆(Caroline Bynum),其博士学位论文以《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50)Hoyt C. Tillman, 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2).中译本由姜长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2012年再版。为题,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于1982年出版。在该书《中文版序》中,田浩坦承“结果一直对中国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宋代思想的主要转变”吸引了他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注意;作为一名思想史家,他为学的旨趣是努力“‘如其原貌’地理解过去”的思想世界:“西方目前的一些历史理论强调不可能‘如其原貌’地理解过去。尽管我意识到认识过去是多么困难,但我依然认为,这样刻苦努力地去做是历史学家的起点。”(51)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姜长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序”第1、2页。
该书从人物身世、阅历、交往、性格等方面论述了南宋陈亮与朱熹的思想论辩,动态呈现了两人思想的异同。相较于此前北美汉学界对转型后宋代儒学的研究,尤其是狄百瑞和陈荣捷的“新儒学”叙事而言,该书的学术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二,不囿于《宋史·道学传》所限定的道学传统以及学界基于此而形成的看待道学的静止视角,揭示出南宋“道学”流派有一个历史性的构建过程。作者指出,“二程思想在12世纪的实际涵义与他们在后来被显示的思想之间有区别。在12世纪的背景下,他们的思想广泛而无清晰界限”,而“朱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综合(包括对二程思想的诠释)后来湮没了对立解释,后辈只看到12世纪程颐思想的狭小部分”。因此历史地来看,12世纪的道学流派远较《宋史·道学传》的记载宽泛,“包括那些与二程有基本相同的伦理、学术观念的人”。就陈亮而言,从他“后20年及前30年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经历了一个自我与程颐紧密相连的阶段;而且,这一阶段对陈亮思想的发展来说非常关键”(52)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12页。。因此,至少在陈亮一生中的某些时段,他或是道学弟子,或可归为道学家。这揭示出12世纪道学流派的复杂性。
其三,指出陈亮和朱熹论辩的内容以及他们所阐述的思想学说的中心问题,多属于儒家理论中的“文化价值”层次,而非此前学界所着力阐释的属于“哲学思辨”层次的形而上学。作者认为,“一个像朱熹这样的宋代儒家学者所做的事更直接关乎实践而不是试图解决一个西方形而上学家认为基本的本体论问题”;陈亮则“极为珍视政治价值”,“他不忠诚于抽象的伦理价值,而是通过特殊的政治目标来判断效果,并且推崇更为具体的规则”。两人是“从价值层面而非形而上学角度去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即使对道之性质的辩论,实际上也“是价值取向问题的一部分”(53)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139、138、140页。。就全面呈现宋儒的思想学说而言,作者的这一论断无疑会动摇此前哲学史研究方法和阐释方式的合理性,确立起思想史研究的适用性和必要性。
田浩的研究体现了其回归理学历史语境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他发表论文与狄百瑞进行辩论,质疑狄氏所使用的“新儒学”概念之于宋代新儒学思想的适用性,主张“在历史原有的意义上使用‘道学’这一概念”以代替之(54)Hoyt C.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u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1992): 455-474; Hoyt C. Tillman, “The Uses of Neo-Confucianism, Revisited: A reply to Professor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1994): 135-142.。这是讲究“历史语境”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与狄百瑞所代表的观念史研究范式就宋代理学研究问题发生的首次正面交锋。
《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出版后,田浩继续从“与朱熹之关系”的角度,对当时与朱熹有着重要学术交往和思想交流的学者进行研究,其成果即《儒学论争与朱熹的正统》(55)Hoyt C. Tillman,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该书被作者译成中文,并经历了数次较大幅度的增订,以《朱熹的思维世界》为名先后多次出版(56)其版本有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2008年增订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2019年增订版。。其内容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将朱熹放回南宋当时的情境中,透过朱熹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学者如张栻、吕祖谦、陈亮、陆九渊以及其他人物的关系或交往以进行考察,进而了解朱熹本人在这种交涉中逐渐发展凸显出的思想观念”(57)夏长朴:《增订版序二》,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二是通过对南宋道学演变历程的分期梳理,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具有共同关注的一群儒家学者所组成的道学‘团体’,是如何发展演变成自成一家的思想学派,乃至南宋末期正式成为政治思想上的正统学说的”(58)田浩:《作者的话》,《朱熹的思维世界》,第1页。。该书对于突破观念史研究认知、揭示南宋道学的历史实态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将朱熹放置在与同时代学者的关系或交往中来考察其思想观念的形成,“威严的朱熹不再作为一个无血无肉的‘哲学家’或‘圣人’出现,他被看作一位思想家”(59)史华兹:《序》,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第8页。,揭示出其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曾受到所交往学者的激发和助益这一事实。这样便从形成历程的角度把朱熹思想还原进了历史情境和人际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朱熹的文化权威形象——由宋代以后帝制中国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并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的哲学史研究模式所延续——的去魅化。
其二,通过论述宋初胡宏、张九成以及与朱熹同时代的张栻、吕祖谦、陈亮、陆九渊等学者的学说思想,尤其是他们的思想与朱熹的相异之处及其与朱熹的论辩,进一步论证了12世纪道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内涵多元的道学在成为“朱熹化”正统的过程中,除了朝廷的认可、扶持和后学的宣扬外,作者着重强调了朱熹本人在剔除异见、确立正统乃至塑造自身文化权威上所作的努力。这样便揭穿了为后世学人所看重的“朱熹化”道学乃由学者本人和国家权力等多方面力量构建而成的底细。
田浩对道学在南宋迈向正统之过程的论述,虽然也涉及政治因素,但主要着眼于学者在思想学说方面的努力,这与前述刘子健基于政治运作的论述不同;而他对学者思想学说的阐述,虽然也涉及“哲学思辨”层面,但重点在于“文化价值”和“现实政论”,这又与前述狄百瑞、陈荣捷等侧重哲学思想的论述不同。由此,田浩在呈现唐宋转型后儒家思想主体——道学的历史存在形态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四、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从郝若贝、韩明士到包弼德

这一脉络的研究对唐代政治精英演变的认识尚承旧说,对宋代政治精英群体的身份划分及其演变历程的构建,则具有独创性。郝若贝弟子众多,他们大多继承师说,其中作进一步深化研究而成就最著者,当属聚焦于两宋之际“职业精英”向“地方士绅”转变问题的韩明士。1986年,韩明士出版《官僚与士绅:两宋之际江西抚州的精英》(61)Robert P. Hymes, State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一书,以抚州地方精英为研究个案,认为北宋至南宋之际,精英的“关注点和自我观念经历了一个大转变:大体而言,其兴趣从国家转向地方领域。这个变革不仅标志着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62)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这就从地方史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发展了郝若贝的两宋之际精英转变说。
值得注意的是,韩明士从狄百瑞对南宋道学兴起的认识入手,试图将南宋精英的“地方化”转变与当时道学的兴起结合起来考察。狄百瑞在1953年发表的《新儒学再评价》一文中认为,朱熹思想中对道德和个人的强调,可视为南宋道学家鉴于王安石变法导致灾难性党争,而对其北宋先驱所作的基于朝廷的政治、制度改革努力的有意背离(63)Wm. Theodore de Bary, “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 in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eds. Arthur Wrigh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这一对两宋道学家努力方向从中央政治转向个人道德的解读,与郝若贝和韩明士所主张的两宋之际精英的“地方化”转变相契合,从而被韩明士认可。他进而指出,南宋道学家的三项制度性举措——办书院、立社仓和乡约,都是基于地方而开展。由此他强调了南宋道学对精英“地方化”的影响:虽然道学家的关怀并不限于地方,而且其“哲学中难以发现‘地方主义’”,但是“通过三项制度性的改革举措,朱熹给地方士绅提供了一套可以在地方范围内从事实际社会活动的路径”(64)Robert P. Hymes, State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135.近二十年来欧美学界对南宋精英“地方化”说的批评和发展状况,包括韩明士对该说的修正,可参见王锦萍:《近二十年来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邓小南主编:《宋史研究诸层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06-138页。。
真正着眼于唐宋思想演变而将其与上述“精英阶层转变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是包弼德。在西方汉学界,包弼德是对唐宋思想转型问题研究最为着力、影响最大的学者。他的专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是西方汉学界关于唐宋思想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被称为是“自1950年代狄百瑞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以来最为重要的关于宋代思想起源的研究之作”(65)Richard von Glahn, review of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by Peter K.B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4(1993): 976-977.。
该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公元600至1200年间士人价值观基础的转变,以及士人是如何确立价值观的。它有两个特色鲜明的研究视角,其一,就研究对象而言,作者关注的核心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思想,而是“斯文”——“首先指称源于上古的典籍传统”,“包括了诸如写作、统治和行为方面适宜的方式和传统”(66)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在《历史上的理学》一书中,包弼德对宋代以前历史上所积累的“文”的多层意义作了更为明晰的总结:“它是宇宙运行过程的具体显现(所谓的天文学,就是对天的“文”的探究),是人类社会的具体形式(人文),是在三代和经典的基础之上层层累积的文献传统,是政治与社会的价值所在,是圣王用于教化的文化形态(文教),最后,也是个人文学上的成就。”(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46页),是“士学”而非儒学,尤其是最受当时士人重视的文学,故该书“将文学作为核心,所讨论的许多重要思想家,主要是文人”;其二,该书“通过阐明思想以及思想所赖以发生的历史世界,来澄清思想价值观的转变与实践转变之间的联系”(67)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6、100页。,为唐宋思想转型构建了一个用来解释转型原因的社会历史背景。
包弼德将公元600至1200年间思想的演变,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唐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学者将文化价值观具象为可用作榜样的“文化形式”,包括“所有那些属于‘礼’的范畴的东西,过去的文献遗产,以及文学创作(文章)”;755年至唐朝末年,伴随着安史之乱所导致的唐朝政治危机,士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出现危机,一些士人倡导古文,强调写作为公共道德服务,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写作必须建立在作者独立思考的“圣人之道”的基础上;宋朝初年至1044年庆历新政被废罢,为文标准出现了分化,以范仲淹为中心的古文家“坚持认为士应该以圣人之道作为学的核心,并将写作当成实践道的一种努力”;1044年至北宋末年,文学及其话题渐不被重视,学者致力于“探求一种可以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提供基础的道”。这四个阶段中,士人的价值观虽然都建立在“宇宙和历史”基础上,但把握方式却发生了从信仰政权所支撑的“文化形式”到独立思考“圣人之道”,再到个人独立于权威而解悟“天地之道”的转变,即“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的转向”。之所以将唐宋思想转型的历程结束于苏轼和程颐,因为在作者看来,苏轼标志着中国思想史的两个时代——源自中世的“文化综合体”的文章观时代和始自韩愈延续至11世纪的“寻找圣人之道”的古文时代——的结束;程颐则标志着唐宋数百年间思想转型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和道学新文化时代的开始。
除论述以上四阶段的文化、思想演变外,作者还单设一章,专门论述唐宋间士的身份属性转变问题,即从唐代的门阀转变为北宋的学者官员,再转变为南宋的地方精英。然而遗憾的是,作者对唐宋思想转型阶段的论述,并未与士阶层的转变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论析,这不免带给读者疏离之感,可以说作者力图用唐宋士阶层的转变来解释思想转型的做法并不成功。因此,该书的主体内容仍然是基于文化特征和思想创新性而构建的唐宋思想文化演变之逻辑脉络(68)葛兆光亦曾指出“本书中比较多地讨论的却是文本中的‘思想’”(葛兆光:《文学史:作为思想史,还是作为思想史的背景?——读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7页)。,由此可以理解作者为何将转型历程结束于程颐,而未涉及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道学。这一论述方式以及作者对作为思想“正统”的程颐道学的重视,导致该书被批评仍未摆脱由狄百瑞、陈荣捷建立的中国思想史“家谱编撰学”的研究模式,“它的说服力恰好只有在陈荣捷和狄百瑞所提供的特殊的说服语境之中才是成立的”(69)詹启华:《在倒塌的偶像与高贵的梦想之间: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札记》,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第33页。。
与“将文学作为核心”的研究视角相一致,作者给出了新的唐宋思想转型模式:“应该将唐宋士人的思想变迁了解成从文学转变到道学而不是从佛学转变到儒学。”(70)周武:《唐宋转型中的“文”与“道”——包弼德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第91-100页。这是对前文所述赖肖尔和狄百瑞“从佛学转变到新儒学”的唐宋思想转型叙事的反动,无疑丰富了学界对此转型复杂性的认识。尽管作者将研究对象规定为“士学”,因而从文化形态浮沉的角度为这一新模式找到了看似合理的历史逻辑,但它仍有可商榷之处:其一,在中国古代,文学一直都为士人所高度重视,隋唐以降,科举考试中最受推崇的进士科要考诗赋和策论,这使得士人凭文学才能不仅可博取名誉,还可获致官宦利禄。宋代道学兴起后,道学家中出现了排斥“文学”的现象,但是这些道学家并不代表所有士人,崇尚“文学”的士人仍占绝对多数。也就是说文学即使在道学兴起之后,仍是一个存续的为士人所致力的传统。其二,即使就道学家而言,他们排斥“文学”,针对的主要是“浮艳”文风,却肯定、支持根基于道、文辞质朴、文风平淡自然的“文学”。如有学者指出:“尽管在‘文’‘道’的关系上,南宋理学家仍然承继了北宋时期‘文以载道’的思想,含有‘道本文末’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把‘文’与‘道’完全对立起来,而是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它们的一致性。”(71)叶文举:《南宋理学与文学:以理学派别为考察中心》,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331页。再如程颐因朱长文“心虚气损”,致书奉劝他“勿多作诗文”,而朱长文复函称作诗文乃“为学之末”,程颐又回信正告他说:“苟足下所作皆合于道,足以辅翼圣人,为教于后,乃圣贤事业,何得为学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责?”(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朱长文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1页)可见他支持作“合于道”的诗文。由此二点,足以说明道学兴起后,文学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不存在被道学替代的问题。因此,虽然包弼德系统而深入地呈现了唐宋士人价值观的转变历程,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将唐宋思想转型解释成“从文学转变到道学”,便嫌勉强。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出版后,包弼德对唐宋变革、理学思想等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并将研究范围向后延展至明末,糅合郝若贝、韩明士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说,用文化史的方法从理学承载者——士的社会存在的角度论述宋至明末理学的存在形态和演变状况,著成《历史上的理学》(72)Peter K. Bol,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or,2008). 中译本由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一书。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唐宋变革所形成的新的历史环境,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之,理学即是王安石新学之外回应这一时代需求的“另一种选择”,同时,理学也是唐宋思想转型的产物和标志;宋元明时期的理学,除了是一种“学说立场”外,也是一种“身份认同”,还是一种“社会运动”。
从“身份认同”和“社会运动”的角度阐释理学的历史存在,包弼德至此完成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圆融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理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由此呈现了历史上理学的社会存在机制和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其研究和认知,他对学界某些关于理学和宋代以降历史的著名论说作了反驳:
其一,“理学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支柱”说。包弼德认为,“宋代的政治制度不是专制而是一种‘士大夫政治’”(73)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12页。,理学与皇权所代表的政治体制之间保持着相当的张力:其一,理学家在传统的政治权威之外,确立起道德权威,将包括皇帝在内的个人道德修养,看作是转变政治、社会的根本方式,从而树立并提升了理学家独立于政治的地位;其二,理学家支持“行政系统的分权,减少中央政府的收入与开支,让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灵活性”(74)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25页。,同时“敦促那些受到正确教育的文人学者组织,在地方生活中扮演领导的角色,一方面维护坚持其立场所必需的制度(例如学校体制),一方面主动维护和造福于公共社区”(75)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3-87页。。也就是说,理学家在理论上确立起的道德本位主义,实践上主要面向地方社会的“自发主义”活动,都表明理学并非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而是“旨在转变个人与社会的哲学”,有着相当的独立性和自由度。
其二,“中国在12世纪之后进入长期停滞阶段”说。如前所述,从内藤湖南到赖肖尔、刘子健都信持此说,虽然其意旨或有不同。包弼德认为,源出自中世纪“旧基督教”的历史发展观,即认为“历史是朝着既定的方向行进,有其预先注定的进程”,遇到自17世纪以来始自西欧的“现代化”发展这一“特殊的历史状况”后,形成了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单一历史发展理论,其基本预设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是在同一道路朝着同一目标赛跑”。在这种历史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初以来“将‘现代’中国与之前的‘传统’中国相区别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些学者遂断言“中国在过去一定时期停滞了”,或将停滞的起点定在理学开始流行的12世纪。这种停滞说,完全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以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历史发展观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的产物。其实,世界上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假如历史终止于16世纪,此停滞说便断然不会出现(76)包弼德:《论停滞与失败——思想意识形态与历史:两个初步的问题(之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5-15页。。
其三,余英时“后王安石时代”说。包弼德认为,王安石新政“猛烈抨击了地方精英(王安石称之‘兼并之家’)的经济立场与社会地位”,“试图将以国家为主导的命令型组织强加在地方社会之上”;而朱熹“呼唤皇帝加强本人的道德修养,并接受道学的学术理论,与此同时,他又呼唤地方士人精英为地方社会负起更大的责任”(77)包弼德:《对余英时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程钢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第92-102页。,即在不依赖朝廷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办书院、立乡约等举措来改变社会。前者重视政府在改变社会中的作用,后者呼唤士人面向地方社会的“自发主义”活动,两者致力的重心和路线完全不同,不可互相比附。
结 语
由以上论述可知,美国的唐宋思想转型及转型后的思想形态——“新儒学”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生了由观念史研究变为历史主义研究的范式转移。赖肖尔继承并在美国宣传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但在唐宋思想转型问题上,他借用了中国哲学史界从唐代佛教转向宋代新儒学的思想史叙事,以弥补“内藤假说”在此问题上的缺失。这一叙事借用,直接影响到狄百瑞。狄百瑞对唐宋思想转型、新儒学的阐释和脉络构建,又得到陈荣捷新儒学哲学研究的支撑和强化,从而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史研究范式。

从范式意义上对狄百瑞的观念史研究提出更大挑战的,是余英时及其弟子田浩以探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思想”为基本路径的文化史研究范式,和包弼德所引领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学者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都从“将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实际经历关联起来”的角度研究理学;对理学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和自由度的辩护,也表明他们对唐宋思想史上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着一致性。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根本差异在于:包弼德继承了郝若贝、韩明士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转变说,更多地将道学视为地方士人主导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因而注重从士人阶层的“社会生活”角度来探讨道学;余英时不认可此精英“地方化”说,认为南宋与北宋士人有着一脉相承的以“重建政治秩序”为始点的关怀,注重从“个人经历”(处境)的角度探讨道学,强调南宋道学的政治追求。
重视国家权力对思想文化的决定作用,从政治活动中探讨道学的沉浮,强调朱熹的政治关怀并将他和王安石相提并论(78)刘子健将王安石和朱熹并列为“主张彻底改革”的代表人物(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第43-46页)。,这是余英时与刘子健的一致之处,但余氏并不认同刘氏的两宋之际“中国转向内在”说。田浩有着与余英时一致的从“个人经历”角度探讨道学的取径,但也重视社会史的视角,并不排斥南宋精英“地方化”转变说。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及其所含括的有着复杂异同认识的问题,以及背后的概念阐发与思想语境化、一元化与多元化思想等理念间的张力,使得思想史成为美国的中国中叶史研究领域颇具活力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