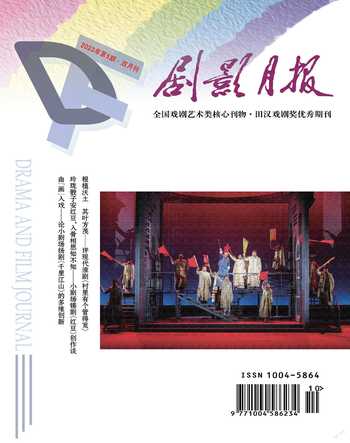作者论视域下的简·坎皮恩电影“作者性”探析
2023-12-12郑一笑
郑一笑
“作者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法国新浪潮时期弗朗索瓦·特吕弗和安德烈·巴赞等人在法国电影杂志《电影手册》上的争论,支持一种更个人的电影和导演,强调导演在电影制作中作为作者的权威性。美国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则基于法国作者论进行了系统性的完善与批评,提出了“三个同心圆”的电影作者标准和前提,即分别是“技术能力”“可辨识的个人风格”和“内在意义”。而另一位美国的影评家宝琳·凯尔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作者论进行质疑。
首先,安德烈·萨里斯认为“作者论的第一个前提是导演作为价值标准的技术能力”,被可视化为三个同心圆的最外层,是导演身份的最基本的前提。在萨里斯的“作者论”中,电影导演首先应该被视作一位“技术人员”,能够“处理主题、剧本、表演、色彩、摄影、剪辑、音乐、服装、装饰等等”各方各面的技术。而作为首位获得金棕榈奖最佳故事片的女性导演,简·坎皮恩的技术能力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电影《犬之力》也分别斩获银狮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甚至在她早期学生时代的短片作品《果皮》中,她作为导演、编剧和剪辑师的技术能力就已经初具雏形并初露锋芒。作为该短片的导演、编剧和剪辑,简·坎皮恩赢得了1986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最佳短片,同样成为第一个赢得该奖项的女导演。即使是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她对主题、剧本、编辑、色彩、构图和声音的巧妙操作也都已经彰显出她作为一名作者导演精湛的技术能力。
在这部仅仅9分钟的短片《果皮》中,观众被迅速带入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紧张家庭氛围之中。在高速公路上,一个行为不端的男孩粗暴地从车窗里扔出橘子皮。因此,他的父亲把车停在路边,命令男孩取回果皮,但男孩不情愿。男人的妹妹也不耐烦地等待,每个人都充满怒火。电影中高度风格化的视听表达正是她娴熟技巧的有力说明。在影片中,为了渲染家庭关系的紧张气氛,简·坎皮恩采用了快速切割的蒙太奇剪接,比如在场景之间插入其他超速行驶的汽车的镜头,以渲染人物的焦虑情感。声音的设计同样非常独到,如片头出现的快节奏的橘子撞击的声音,加上刻意混乱的快速剪辑,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电影令人不安的基调。此外,简·坎皮恩还在摄影和构图中格外强调感官上的视觉冲击。例如,影片结尾对几个人物极端的面部特写镜头放大了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愤怒。通过用直线分隔整个构图以放大人物之间的距离,简·坎皮恩再一次增强着人物之间的隔阂感。汽车内外三个人物的排列也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三角构图,暗示着三个人之间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从编剧的角度来看,影片凝练而敏锐地描绘了生活的一个碎片式的片段,没有给予复杂的背景或任何多余的对话却展示了简·坎皮恩作为导演和艺术家的敏感而敏锐的洞察,尤其是它揭示了她对家庭关系中的控制和权力的思考。而这些技术在简·坎皮恩后来的长篇作品中也不断精进,使她成为一位卓越的电影作者导演。
然而,对一位导演或电影工作者来说,仅仅有“学问精深的构图,复杂的灯光效果,一流的摄影”是远远不够的。宝琳·凯尔甚至认为技术技巧并非必不可少,因为“唯一值得拥有的技术是你为自己发明的技术”。这种原创的技巧在这里也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作者独特的个人风格。这就可以引入萨里斯的“作者论”的第二个关键前提:“可辨识的个人风格”,也就是同心圆中间的第二个圆。它要求导演在他的电影作品中“展览某些循环特征的风格,作为他的签名”,而电影也同样“与导演的想法和感觉有一定的关系”。这也与安德烈·巴赞所强调的“艺术创作中的个人因素”不谋而合。也就是说,“作者论”认为只有当一个导演的作品重复包含相同或可比的个人风格,或对特定主题表现出反复的痴迷或兴趣,才能被视为电影作者导演。而简·坎皮恩的电影中,独特的电影风格和主题表达也正呈现着某种非常显著的一致性,进而构成其“可辨识的个人风格”。
强烈的感官视觉风格便是她最明显和最主要的视觉风格之一。正如简·坎皮恩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她“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感觉、感觉和微妙之后”。这种风格则与劳拉·马克斯提出的“触感视觉”的概念不约而同。马克思认为“视觉本身可以是触觉的,就像一个人用眼睛触摸电影”,它“倾向于在物体的表面移动来辨别纹理”,“更多涉及身体”和“优先考虑图像的物质存在”。在简·坎皮恩的电影中,同样有这种倾向,展示非常微妙的细节、纹理、身体或皮肤,提供非常微观化的视角,迫使观众在影像和观影中获得一种触摸银幕的身体感官体验,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情动。
除了之前讨论过的短片《果皮》,电影《明亮的星》的开场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简·坎皮恩采用极端的特写镜头去捕捉对主角范妮·布朗(阿比·康沃什)缝制的布料的纹理细节,让观众在一开始便更接近这位女主人公,巧妙地暗示虽然电影讲述的是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本·卫肖饰)的浪漫故事,但故事核心和视角将更多集中在他的爱人范妮身上。简·坎皮恩也特别热衷于使用面部和手部的特写镜头来呈现皮肤表面的纹理。例如,在《钢琴课》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当艾达的丈夫发现她的不忠后,在雨和泥中砍断了她的一根手指,镜头再次提供了艾达的脸和沾满泥的手的特写镜头。整个画面的阴影投射出一种绝望的氛围,赋予观众一种痛苦、寒冷、肮脏和潮湿的触感体验。
通过高度感官的表现,简·坎皮恩进一步“沉浸在极简主义的美学中”,通过最小的对话来表达极端的情感成为她另一种独特的风格。正如简·坎皮恩自己所说,“我的语言能力不如视觉能力强”,她更习惯于通过视觉效果和表演来表达情感,而不是依靠对话。例如,在《犬之力》中,菲尔·伯班克讨厌他的嫂子罗斯·戈登,因此在精神上百般折磨她。这种折磨不是言语上的暴力,而是菲尔对罗斯的一种无声、更具伤害性的精神虐待。例如,当罗斯在钢琴练习上遇到麻烦时,菲尔通过在楼上流畅地弹奏出同样的曲子来嘲笑和干扰她。摈弃了言语上的妙语连珠式的讽刺和调侃,取而代之的是音乐所建立起的强烈而引人入胜的极简主义美学。
不仅仅是在《犬之力》中,音乐在简·坎皮恩的电影中一直有着至關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作为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还是电影中一个美丽的插曲,无不彰显出简·坎皮恩对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在视听美学中的痴迷和出色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坎皮恩对音乐的出色利用也反映了她的电影的高度感官风格。例如,钢琴经常作为她作品中非常突出的象征或隐喻:它是《钢琴课》中沉默的艾达的自我表达的媒介,是《犬之力》中罗斯的自卑情绪的外化,也是《一位女士的肖像》中伊莎贝尔·阿彻的吸引力和错误地信任梅尔夫人(芭芭拉好时)。简·坎皮恩也经常以优美的音乐开场和结束她的电影,比如在《明亮之星》中,电影以缓慢、轻快的音乐开始,以本·卫肖朗诵约翰·济慈的诗人《夜莺颂》结束,以类似的旋律,给观众留下无尽的唤起体验。
除了这些一以贯之的独特的个人美学风格,简·坎皮恩所有的故事片在主题上几乎也都保持着某种一致,成为她“可辨识的个人风格”的关键部分。在简·坎皮恩的作品中,她“总是讲述同样的故事”,即“关系、爱情和性”的故事,描述“女孩和妇女的生活因为外表(如果不是完全的身体残疾)或个性怪癖而以某种方式被主流人群隔绝”。例如,艾达在《钢琴课》中是沉默的,被安排嫁给一个严厉的农民。珍妮特·弗雷姆则是《天使与我同桌》中一个奇怪的、低自尊,敏感和害羞,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的胖女孩,困苦于超过200年电击治疗。《一位女士的肖像》中的伊莎贝尔·阿彻则是一个渴望独立的自命不凡的女孩却被困于婚姻阴谋。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挣扎,自我对独立的探索和渴望,唤醒了对爱和性的渴望,以及女性的身体都被坎皮恩微妙地描绘出来。例如,在《钢琴课》和《一位女士的肖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女性欲望的去男性化凝视的生动描绘。
然而,正如凯尔曾经攻击萨里斯的第二个前提是“没有发展的重复是衰落”,风格和主题并非一成不变。例如,《犬之力》就是一个例外。主人公从以往的女性角色成为被有毒的男子气概压抑的男性主体。菲尔在电影中是一个狂野的强壮的牛仔和一个有权威的牧场主。然而,他的男子气概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和一颗微妙的女性之心。简·坎皮恩仍在讨论异性恋、父权霸权秩序下对欲望的抑制,但这次她把它从女性扩展到了男性同性恋者。因此,简·坎皮恩的工作既有一致性,又有发展性。
家庭中的创伤、失语和交流也经常出现在简·坎皮恩的电影中。其电影中的主角或多或少遭受了来自家人的创伤。比如,《天使与我同桌》中的珍妮特年轻的时候,她的父亲禁止她在晚餐时讨论性问题。当初潮来临时,她的母亲对她的恐惧和尴尬漠不关心。之后她最亲密的两个姐妹也相继去世。家人的失语与关爱都对塑造她害羞和敏感的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简·坎皮恩的主人公的父母,尤其是他们的父亲往往不在场或情感上不在场。同时,缺失父亲的孩子经常出现,如《钢琴课》中艾达的女儿、《明亮的星》中范妮的妹妹图茨(伊迪·马丁饰)、《一位女士的肖像》伊莎贝尔的继女亨丽埃塔(玛丽路·易丝帕克饰),他们作为最亲密的人见证着主人公的不幸,同样可能成为主人公内心情感的延续与投射。因此,不仅是《钢琴课》中真正沉默不语的阿达,简·坎皮恩电影中的许多其他角色也处于一种脱离实体、压抑和沉默的孤立的生存状態,且他们都试图将一个物体作为媒介进行交流和表达自我,比如艾达的钢琴、珍妮特的诗歌、范妮的针线,以及菲尔的皮绳,都成为沉默的主人公的情感出口的关键象征和隐喻。
萨里斯进一步指出,“作者论的第三个,也是终极前提,涉及内在意义”,成为三个同心圆的内圆,这意味着要求解决“导演的个性和他的材料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里的“个性”可以指萨里斯的第二个前提——独特的个人风格,而“材料”可能与商业生产行业有关,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的制片厂系统。由于“大多数作品都是由电影制片厂控制的,电影公司导演不能沉迷于自己的虚构世界”,在自我表达和制作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简·坎皮恩也提到,“这本质上是一种在不影响业务的情况下制作好电影的坚定理念”。
然而,正如萨里斯自己的反思,这样的概念可能是非常模糊的。凯尔在她的著名文章《圆与方》中抨击了萨里斯的“作者论”观点,认为其“贬低了作者——导演——他们是使用电影媒体进行个人表达的最佳位置”。凯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内部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坎皮恩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作者——导演”,因为她几乎有一半的作品都是她的编剧作品,她的电影倾注着她的个人表达。
然而,萨里斯提出的“材料”的概念或许也可以被理解为改编电影中的原始文学材料。对于坎皮恩剩下的改编作品,个性和材料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人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坎皮恩非凡的自传体性质,她在改编作品中常常“用第一人称说话”。例如,之前讨论过的关于家庭创伤的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简·坎皮恩的自传体表达和自我的投射,例如她在一次采访中提道:“我震惊地发现她(《天使与我同桌》中的珍妮特)是多么的正常,我的童年感觉是多么像她的。”虽然这部电影是改编自澳大利亚作家珍妮特·弗雷姆的自传,但它也属于坎皮恩的童年回忆。当坎皮恩在13岁时读到珍妮特的书,她立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她的童年也深受她抑郁的母亲的影响。尽管有这样的改编,但它投射了许多来自坎皮恩的个人记忆和情感,而不仅仅是忠实地复制原始作品。
(作者单位:英国爱丁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