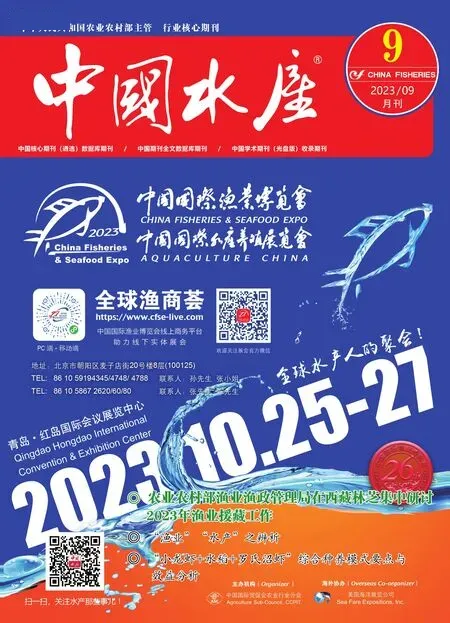要食物 求发展 永和谐
2023-12-12吕俊霖
◎ 文/吕俊霖
江河湖海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为自然界和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水生资源和生存环境。本文探讨了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分析了江河湖海对生命的重要性,回顾了人类渔业的发展历史,指出人类应该珍惜和保护江河湖海,基于大食物观理念发展高质量低消耗的水产养殖模式,建设海洋牧场、营造蓝色粮仓,保障食物安全和改善营养结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是一个亘古以来即被重视的话题。不仅是自然界的动植物,人类亦须借助于江河湖海维持自身。江河湖海与我们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自然界中,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是许多生物赖以生存的手段。众所周知,地球上海洋与陆地的比例约为7:3,海洋是地球上含氧量最高的生态系统,算上江河与湖泊,江河湖海深深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活动。江河湖海不但是水循环、气体交换的重要载体,也深深影响着地球上的气候,维系着地球大环境,给予了众多生物容身之所。
从低等单细胞生物蓝藻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开始,地球逐渐固氧,生命从此开始新一轮的繁衍进化。我们通过考古研究和对化石的分析得知,生物进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也就是说,陆上生物本质上是江河湖海中生物经过繁衍与变异所得基因积累产物,实际上本源皆来自江河湖海,亦有大量陆上物种以江河湖海中的生物为食。数亿万年积累过后,食物链逐步形成,能量自下而上层层传递,在重组的、错综复杂的食物网中,各种生物形成彼此相依、环环相扣的关系,每一层生物既以别层生物为食,又被其他生物所用,整个生态系统被置于江河湖海大背景之下。在这种情形下,底层分解者直接利用江河湖海中有机物,而上层消费者间接利用江河湖海谋生。江河湖海中稳定的生物关系构筑了欣欣向荣又不断自我完善、不断毁灭又时刻新生的水圈环境,深深影响着地球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
自然界生物因江河湖海而生,同时也在改造江河湖海。所谓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实际上不仅仅是索求,在索求被反馈的同时,江河湖海的面貌也被一点点改造,被生物重塑为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塑造满足生物的长远利益,是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的长期策略。在短期地、不连续地、任意性地对江河湖海的索取中缓慢积淀能量以形成更佳的环境,让自身的存活更具可持续性。在这种选择模式中,“要食物”主观上是谋求生存,但从客观上看,也构成了对江河湖海的改造。在历史长河中,江河湖海孕育的水产品,极大一部分为人类捕捞、采集、食用甚至于作为用以审美的装饰物。古代人类滨水而生,逐水而居,临水而筑,甚至就江河湖海产生相应的神明崇拜,凭着江河湖海的滋润,人类文明开始踉跄前行。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处于原始社会早期的人类就在居住地附近的水域中捞取鱼、贝类作为维持生活的重要手段。如1万年前山顶洞人的捕捞物中就有草鱼和河蚌,以及可能是通过交换得到的海蚶。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捕鱼技术和能力有了相当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出土的各种捕鱼工具可以推断此时已有多种捕鱼方法。沿海地区除采捕蛤、蚶、蛏、牡蛎等贝类外,也已能捕获鲨鱼那样的凶猛鱼类。商周时期即有“东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而甲骨文中的渔字形象地勾画了手持钓钩或操网捕鱼的情景。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铜鱼钩,还有可以拴绳的骨鱼镖。滨水而居的百姓也各有其神灵崇拜,如河伯、冯夷以及湘君等,为远古渔业笼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让江河湖海不仅仅成为祖辈的生活所安,更寄托了祖辈的精神祈愿。无数人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每日早出晚归,下江下海,向江河湖海要食物以谋生。对他们而言,水域不仅仅是食物来源,更被赋予了生活的希望,有了江河湖海,就像是得到了安定、丰足和富饶的承诺。
新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作为奋斗目标。1978年10月18日,一篇题为《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保障水产品供给、解决“吃鱼难”问题的信号。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农牧渔业部《关于加速发展淡水渔业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必须在抓住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畜牧和水产业,逐步而适度地改变居民的食物构成。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面的利用”。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我国解决了城乡居民“吃鱼难”问题,水产品供给日趋充裕,至今保持了国内水产品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保障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和食物安全、有效改善城乡居民营养膳食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水产养殖主要生产国,连续三十二年居世界第一。可以说,在保障食物供应、保持蛋白质摄入量上,中国渔业生产功不可没,为提高中国人身体素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说农业是支撑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的话,那么渔业,则是这个稳定器和压舱石的重要砝码。
然而,长期粗放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对土地的浪费和对水体的污染,近海高强度捕捞也造成了渔业资源枯竭。
水产养殖需要用到连片水体,粗放的养殖方式投喂了过量饲料,为了控制疾病传播,又可能播洒大量药物,这样一来,对邻近水体的污染也在所难免。另外,由于水循环运行,还造成了地下水和土地污染,有些地方因为养殖抽取了大量地下水,导致土地塌陷等次生灾害。
过度捕捞,是中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另一难题。据2021年统计数据,我国小型渔船数量接近30万艘,占全国渔船总数的79%,哪怕这些渔船仅仅是为了讨生计,但比例如此之大,分布如此之广,必然深深改变了人类与江河湖海的生态环境。大量幼鱼被提前捕捞,不但影响这些鱼类自身的生殖和繁衍,还威胁到海洋里大型生物的食物来源和海洋食物链基础。在近50年以来,由于过度捕捞,现代渔业捕获的海洋生物已经超过生态系统能够平衡弥补的数量,整个海洋系统生态退化,许多重要渔场渔汛已经趋近消失,为此一些捕捞船队不得不将作业范围扩大到专属经济区外以满足市场鱼类消费需求和贸易出口。
随着人类无序开发和长期掠夺,江河湖海生态环境在逐步恶化,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越发脆弱,岌岌可危。我们要看到,人类命运与江河湖海的生态息息相关、唇齿相依,保护好江河湖海就是在保护人类自身。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的更好方式,是改善江河湖海的大环境,发展高质量、低消耗的生产方式,促进生态系统的良好循环而不是凭借人类的强力去恣意破坏。
这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保生计与护生态之间,在大开发和永发展之间,需要有一种长远目光,并为之计谋深远。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大禹发布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季节性禁渔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吕氏春秋》就有对竭泽而渔的谴责:“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这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观念。江河湖海是人类的起源,人类是江河湖海所孕育的孩子,自须合理地利用水生生物,而不是肆意捕捞和挥霍资源。
这要求我们树立大食物观的观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在当前这种情景下,秉持大食物观,就是保障生态功能基线,守好环境质量安全底线、控制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从人类本身、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更高维度思考,从而更好地发展自身,发展人类文明,建设更加和谐、绿色、美丽的地球环境。
2019年4月,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公布了72项2019年农业主推项目,其中包括对虾工厂化循环水高效生态养殖技术、池塘“鱼—水生植物”生态循环技术、淡水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化综合治理技术等七项水产养殖主推技术,为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当前,水产养殖模式变革已呈现向集约化和生态化发展的趋势。集约化,即设施化和智能化方向,强调用先进的养殖设施和传感器来进行养殖的精细调控。生态化,就是向绿色有机和生态环保方向发展,减少对水体的大量消耗和污染。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和研究单位还探索出另一条路子,那就是建设海洋牧场,营造蓝色粮仓。
海洋牧场,就是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生态养殖等措施,构建或者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者避敌所需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模式。智能网箱和多功能海上平台都属于海洋牧场的实现形式。经过近十年发展,我国海洋生态牧场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因海制宜”,实现了南北方海洋牧场生态环境从局部修复到系统构建的跨越;“因种而异”,实现了生物资源从生产型修复到生态型修复的跨越;“因数而为”,对海洋牧场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预报,实现了海洋牧场从单因子监测评价到综合预警预报的跨越。在海洋牧场的建设过程中,海洋生态逐渐修复,渔业资源明显增加,养殖品质得到提升,证明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科技推动社会进步,靠“大食物观”发展人类自身,在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的过程中求得发展,在发展中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是我们渔业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