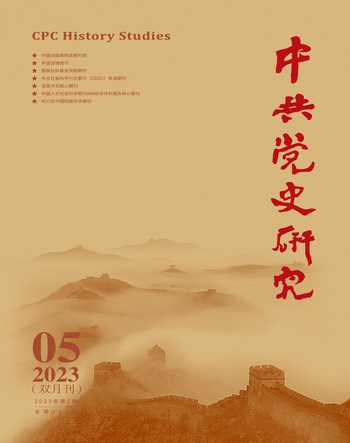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信贷、财政及其调整
2023-12-11林超超
林超超
〔摘要〕想要理解基层“大跃进”的制度邏辑,应该关注信贷管理体制变革与信贷资金使用偏差。一方面,“大跃进”时期超定额流动资金的需求激增,推动了“全额信贷”“差额包干”的出现,从而为预付、赊销等占用流动资金和各种挪用流动资金的行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大量本应用于增加商品流通的流动资金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从而造成财政账面盈余、商品物资却异常紧缺的矛盾现象。而早该发现的巨额财政赤字被银行信用膨胀长期掩盖,以至于持续多年才被彻底清算。
〔关键词〕“大跃进”;信贷管理体制;财政赤字;流动资金;预付赊销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5-0075-11
Credit, Finance, and Policy Adjustments from 1958 to 1962
Lin Chaochao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t the grassroots, emphasis must be placed on the transformative shifts in credit management and the changes in credit fund alloc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overquota operational capital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full credit” and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s for deficits,” making it convenient for activities such as prepayments, deferred payments, and various misappropriations of circulating funds. Simultaneously, an extensive amount of liquidity, destined to augment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was reallocated to fixed asset investments, engendering a contradiction whereby there was a surplus in the fiscal accounts but a severe shortage of commodity goods. The consequential fiscal deficit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discovered, remained long hidden due to the longterm bank credit expansion and the sustained inflation of banking credit that lasted for several years before being resolved.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浮夸风”几乎已成为“大跃进”的代名词之一。至于浮夸风的兴起,层层加码的工农业生产高指标被认为是直接原因,而调研和统计工作的失真则使得真相被掩盖。直至高征购等错误决策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浮夸风才得到了纠正。(参见黄根兰:《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4期;戴清亮:《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探析》,《学术界》1996年第2期;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从浮夸风导向“大跃进”的失败,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这些浮夸的统计数字被采信了。但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对于违反常识的高产“卫星”不可能全都信以为真,相关宣传更多的是出于对民众“热情”的肯定和鼓动,希望通过高指标激发出生产的“潜力”(参见高其荣:《毛泽东与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5期;罗平汉:《试析1958年毛泽东对待粮食高产“卫星”的态度》,《现代哲学》2008年第6期。)。也就是说,高指标和高产“卫星”都只是一种手段,提高工农业生产实绩、尽快实现工业化目标才是中央领导层的本意。那么,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生产部门放出“卫星”后,又是如何应对商业部门的如数收购,继而完成利润上缴,转化为财政收入的呢?这些环节在“大跃进”的既有叙事中常常被忽略。
事实上,伴随着工业管理权限的下放,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权限也被下放,财贸部门在“大跃进”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商业部门在“大购大销”中与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工厂随意签订合同、预付货款,向农村人民公社大量赊销生产资料,财政部门对各级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发放信贷资金上的放任,都在很大程度上为生产“大跃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对“大跃进”的解读,如果缺少了信贷与财政关系视角,将是不完整的。
一、银行信贷与工农业“大跃进”
如果没有大幅增长的资金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根据资金周转的不同特点,生产资金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固定资金是指可以较长期地在若干生产周期中发生作用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劳动手段。它们的价值随着磨损而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通过产品的出售逐步收回。流动资金指原料、材料、燃料等,以及支付工资的货币。它们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全部消耗,其价值也一次性全部转移到产品之中。除了生产领域的流动资金,还有处在流通领域的流动资金,如以产品形态存在的待售产品,以及准备为下一生产过程购买原料、材料、燃料和支付工资用的货币。(陈胜昌等编:《常用经济学名词解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4页。)
从1955年开始,国营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实行财政和银行分口供应。其中,定额部分按照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进行核定,由财政拨给;超定额部分,即因季节性原因,或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变动等临时性原因形成的超过定额的那部分物资储备所占用的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支持。1958年,以钢产量为核心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逐步提高,并通过“三本账”的方式层层加码。国家计划的多变客观上要求企业流动资金的拨付方式向“全额信贷”过渡。1958年3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关于国营企业和中央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定额信贷的三项具体规定》和《关于增拨地方企业定额流动资金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规定自当年起,国营企业按照全年平均需要核定年度定额流动资金,并由人民银行参与30%的定额信贷发放。地方企业1958年需要增加的定额流动资金,30%由地方预算拨付,70%由银行贷款解决。(广东金融学会、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建国以来经济金融法令、制度、大事要略》,1984年印行,第172—174页。)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对国营工业企业的贷款利率调整为月息6厘(原为月息4.8厘),与国营商业部门的贷款利率持平(《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289—290页。)。银行信贷在企业流动资金的供应中所占比重开始扩大,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1958年“大跃进”伊始,中央就调整经济管理体制,主动向地方下放权限。中央各工业部将所属的大多数企业下放地方管理,下放企业利润的20%归地方所得,80%归中央所得。在工业、商业、财政管理全部向下放权的既定方针下,各地银行仅接受上级总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对信贷资金的调剂使用。从1958年3月开始,人民银行多次召开会议,强调紧跟“大跃进”形势,对于企业扩大生产和流通所需的流动资金,要大胆支持、充分供应(《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人民银行向分行发出指示,强调“商业是第一性的,信用是第二性的,商业放款办法应当首先适应商品流转情况和需要”。对商业部门支援增产、收购工农产品、增加库存所需的流动资金,如超过信贷计划时,仍应予以支持;对地方国营、合营工业和手工业增产所需流动资金,也应给以相应放款。总行对商业放款只掌握总方针和政策,具体做法授权各分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著:《中国货币金融史大事记》,人民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85页。)信贷管理权限实际上已经开始下放。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规定》,明确对财政和银行信贷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银行所有存款,除中央财政、国防、中央企业和机关团体的存款外,其他各项全部划给地方作为信贷收入来源。银行所有的贷款,除中央管理的少数企业所需贷款外,其他各项全部划归地方管理。存款与放款的差额由地方包干使用。“差额包干”改变了以往把存款与放款活动分开管控的办法,可以极大突破贷款发放指标,满足地方工业“大跃进”对资金的需求。(《中国货币金融史大事记》,第386页。)地方银行为了增加贷款发放额度,可以想方设法吸收储蓄存款,以实现存贷平衡,但存、放款间的差额是实时变动的,当各地办工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机关团体、企业的银行存款及农村信用社存款被大量提取,存、放款间的差额将迅速发生变化。存、放款间缺口的扩大,意味着信贷资金投放的扩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改进信贷管理体制意见的报告》(1958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6-2-360。)虽然《规定》指出,银行原则上不发放基本建设贷款,但文件一出,各地银行就纷纷改变信贷资金供应办法,“企业需款就贷,要多少就贷多少,哪里要就哪里贷”(《建国以来经济金融法令、制度、大事要略》,第198页。)。据统计,1958年全年,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增加近190亿元。其中,财政拨款增加9亿元,其余皆为银行贷款。工商企业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获取流动资金,本是为了方便购置生产资料和商品,以满足周转性和临时性的需要。但是,“大跃进”当前,各地方、各部门从中抽去了大量资金搞基本建设,包括大炼钢铁。调查发现,湖南省商业系统企业的流动资金被抽去9600萬元花在基建上,天津市河北区抽走26个工厂的67万元流动资金建设钢铁厂。各部委从所属企业抽走流动资金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冶金部和煤炭部,前者从各企业抽走6000万元流动资金,后者抽走了5200万元。(《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76、78、232页。)这些流动资金被抽走后,大部分搞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这势必挤占计划内大中型项目的资金和物资。
大量的流动资金占用还发生在预付货款和商品赊销上。前者是一种“先款后货”的商品交易方式,后者是一种“先货后款”的商品交易方式,交易资金都来源于银行信贷。商业部门预付货款的主要对象,一是地方工业、手工业,用于工业生产和购买生产资料;二是农村人民公社,用于发展工业、农业、副食品生产和多种经营。1958年以来,由于货源紧张,商业部门往往主动向供货单位预付货款以抢购产品,这是其争取货源的常用手段之一,由此增加了潜在的商业风险。如辽宁省抚顺市百货经营管理处预付给河北化学玻璃丝厂25万元货款,但该厂无法立即提供货品,需待扩建厂房投入生产后才能交货。换句话说,企业将商业部门购买商品的预付款先用作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如此一来,信贷资金回笼周期将大大延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项目没有物资保障,不免因物资供应不足而半途停工,最终并不能增加货源。有的收款单位直接将收到的预付款挪作他用。如河北省唐山市煤建公司为获得更多煤炭货源,向农村人民公社预付121万元,资助其建设小煤窑,结果公社用这笔钱归还农业贷款和商业赊销、发放工资和福利,真正用到小煤窑上的只有30万元左右(《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233页。)。还有的收款单位实际上并无生产条件,如上海市化工原料采购供应站预付货款支持大、中学校勤工俭学工厂土法试制硫酸,但这些工厂技术条件不足,长期未能成功出酸,化工站因此收不到货品(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清查商业流动资金运用情况的报告》(1959年2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3-1592。)。据统计,1958年全国商业部门预付货款中,有15.8亿元最终没有增加商品库存(赵学军:《中国商业信用的发展与变迁》,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针对农副产品的预购也存在同样问题。农业合作化以来,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预购,以将其生产纳入计划,此举对工业原料的供应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起到了保障作用,同时也能帮助农业社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需求。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公社的资金积累有了较大增长,经济力量大大超过农业社时期,原来对主要农副产品的预购办法开始向长期的、全面的购销合同制发展。但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少地区想要实现“跃进”式发展,仍需国家通过预付定金的办法给予支持。因此,预购又普遍发展起来。国务院对全国预购定金总额和发放预购定金的对象作了限制:首先照顾贫穷山区、受灾地区和粮食产区,然后才是其他地区;可以预购的农副产品为茶叶、麻类、土纸、生猪、活羊、土糖、干鲜果、干菜等供应尚不充足的商品。事实证明,各地并未严格把控预购定金的使用,且随意增加,这些流动资金最后也都花在了农业生产以外的用途上。(《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233、728页。)
商品赊销主要发生在商业部门与农村人民公社之间。为适应农业“大跃进”的形势,农村财政贸易体制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即通常所说的“两放、三统、一包”。“两放”指将财政、银行、商业、粮食等部门设在农村的基层机构的人员和资金下放给公社经营管理;“三统”指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一包”指包财政任务,由公社按财政收支差额包干上缴(刘鸿儒主编:《经济大辞典·金融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302页。)。实行“两放、三统、一包”后,银行营业所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成信用部;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社的资金、商品、经营、人事管理权全部下放给公社,公社将其与原有的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公私合营商店,以及农业社的供销社合并成公社供销部。公社供销部在生产大队设有供销分部(分销店或门市部),在生产队设有供销站或临时供销组。(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第146、147页。)不少地方的供销部、信用部与公社(农业社)合并办公,供销部对于公社、生产队生产上急需却暂缺资金购买的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予以赊销。尤其是生产季节,原本就需要较大数量的资金投放,而在“大跃进”中,公社为了取得高产更是要加大资金投入。
由于信贷资金使用已远超计划,在城乡贸易中,采购站和贸易公司不得不向公社赊销生产资料。部分赊销是商业部门有意为之。为减少库存压力和运输成本,防止种禽、种畜、秧苗等死亡或变质,商业部门会将一些生产资料直接拨给公社,但公社经常对货品不满,或并不急需,导致商业部门不能及时收回货款。(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加强商业流动资金清理和管理的报告》(1959年6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4-1165。)在部分省份,赊销欠款占用的流动资金比例非常高。如河北省商业系统1958年有5.75亿元流动资金未用于增加商品库存,其中赊销欠款占到44.5%,湖北和山东两省的比重也达到38.1%和24.3%(赵学军:《中国商业信用的发展与变迁》,第127页。)。赊销的方便之门一旦打开,生产资料的购置就不受资金限制了。有的公社自有资金很多也要赊账,有的公社赊购的商品远超需求量。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开始以后,水车、动力机械等水利工具需求量激增,山东各地公社要求以赊销形式购买的水车计50万部,动力机械计4000部,但省供销社连30万部水车、2500部动力机械的货源都无法落实,其余更无从谈起。赊销的蔓延不但加剧了商品供求紧张,同时也在变相地增加农业贷款。(《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714页。)
二、供给失衡与财政清查
1958年以来,各地通报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各行各业竞相放“卫星”,“刷新”历史纪录。但是,城乡居民却没有因此感到生活物资富足,相反,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农副食品和日用商品供应紧张。1958年下半年,市场供应紧张已初露端倪;1959年春节过后,情况加剧。这一时期,国务院秘书厅人民接待室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反映百货脱销问题。如山西省阳泉市从1959年2月开始,市面上已少有肥皂、碱面、糕点、糖果供应,3月以后毛巾、白洋布、粗线、球鞋、火柴、灯泡、白纸等不见踪影,到了4月,皮鞋、布鞋、线毯和各种针织品也没有了,5月就连鸡蛋、肉类和豆腐也停止了供应。辽宁省一些县、市的市场上不仅买不到鱼肉,一般的蔬菜和水果也很少见。原本农历三月和四月是海鱼供应的旺季,但福建省福州市的市民反映,现在想买一条鱼都很难。江西萍乡自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猪肉、糖、糕点、雨伞先后脱销,火柴、煤油、肥皂、鞋子几度断供,需要婴儿奶粉和代食品的居民只能到长沙、宜春等地购买,后来连这些地方也都买不到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由于各地均無法保证本地市场供应,致使上海等工业城市的粮食调入计划难以完成。上海市的生猪调入量不断减少,1958年为10.29万吨,比上年减少24.5%。1959年第一季度,各省调沪生猪9896吨(平均每天4000头),仅完成中央下达计划的41.2%;4月情况更不容乐观,仅剩1841吨;5月以后,每天的生猪到货量只能维持在500头左右,无法保证每人每月6两的供应量。1958年鲜蛋调入量是7759万斤,比上年减少约4%。到了1959年,前4个月调入仅274.8万斤,只完成中央下达计划的22.3%,较上年同期减少85.4%。(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党委:《关于当前副食品市场供应情况的报告》(1959年5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1-430。)鱼类从3月起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1.5斤的标准。其他如金针菜、木耳等南北货,以及咸蛋、皮蛋、香肠等以主要副食品为原料的商品,在市场上已断供多时。上海市只能通过扩大蔬菜种植、增加水产捕捞,来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2—353页。)
与市场供应紧张相伴而来的是物价上涨和质量下降。浙江杭县的市民反映,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蔬菜、鱼类以及燃料的价格均上涨1倍至2倍。上海青浦的水产品同样如此,黄鳝从0.2元/斤普遍涨至0.4元/斤以上,最贵时要0.7元/斤。糕点售价的涨幅更大。安徽蚌埠市场上售卖的饼干从0.14元/包涨至0.3元/包,面包从0.1元/个涨至0.3元/个,点心从0.56元/斤涨至2.6元/斤。即使很多商品并未涨价,厂商也往往以次充好或偷工减料,如往糕点里掺入玉米面,往面粉里掺入杂粮和豆腐粉渣,同一价位的商品品质大为下降。(《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128页。)
市场供应紧张更直接导致黑市活跃。辽宁省阜新市黑市上售卖的萝卜、白菜、豆腐要高出一般价格1倍至3倍,即便如此,依然十分抢手,不少市民甚至愿意出钱预订。沿海居民也发现,黑市上的鱼货远高于0.2元/斤的一般市价,涨至3元/斤。一些商贩通过长途贩卖获利颇丰。江苏省铜山县张集公社的社员将南瓜种子运到西安市贩卖,售价是进价的10倍,每次倒手都可获利1000元至2000元。河北省献县韩村公社的社员将鸡蛋、鱼虾等售往天津,每个鸡蛋可获利0.08元,每斤鱼虾可获利超过1元。即便被罚款300元,他们也不在乎,因为获利远不止于此。黑市售价畸高加剧了市民的担忧和恐惧,常常发生排队抢购的情形,很多并不紧缺的物资也被抢购一空。为了阻断商品流入黑市,各地国营供销社收购站强行收购农民手上的少量副食品,被戏称为“抢购站”;公社干部在车站搜查往来旅客,强行收购旅客随身携带的鸡蛋、红枣、花生、白糖等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市场管理所则对旅客捎带的较多物资直接予以没收;一些商业局和供销社还规定,居民购买煤油、毛巾、香皂、火柴等日用品均要以鸡蛋进行换购(《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127—128页。)。
市场供应的全面紧张,不禁让人对1958年工农业“大跃进”的成果产生怀疑: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如果说1958年支持大炼钢铁,副食品供应不足还情有可原,那么1959年以来市场供应愈发紧张,则让整天排队争购食品的民众渐渐失去耐心。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抱怨,现在购买任何一样食物都要排队,但他们没有时间。上棉一厂的夜班工人索性带着菜篮上工,到了清晨下班马上赶到菜场排队买菜。上海港务局第四装卸区搬运工人也有同样的苦恼,以往他们上班时总能在十六铺码头买到各种早点,夜里下班也有流动小摊贩提供夜宵,现在都没有了,只能前往食堂就餐,而食堂供应的饭菜却大不如前。上钢三厂党委宣传部道出其中原因:商业部门过去每日能给厂里供应猪肉900斤,1959年以来日渐减少,到5月底,每日只能供应200斤左右荤菜,其中还混杂了内脏和禽蛋,导致食堂做不出很多荤菜,工人吃不饱肚子。(中共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区有关工厂工人、里弄居民、商店店员对当前市场供应的意见和要求》(1959年5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1-430。)
为搞清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所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组织商业部、财政部调查组到各地调查,很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财政“窟窿”。据商业部初步估计,1958年商业流动资金增加111亿元,但商品库存只增加了40多亿元。也就是说,投下去的近70亿元资金并没有用在商品生产上。在李先念的建议下,1958年12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清理商业资金和商品库存,搞清财政账面盈余颇丰但商品物资供应极度紧张的原因,当时将这一行动称之为“捉鬼”。(《李先念传(1949—1992)》(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49页。)各地经过清查发现,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从银行借来的贷款,有80亿元没有增加商品和物资库存。其中有10多亿元本是工业部门的流动资金,被挪作基本建设投资。这就混淆了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的使用界限。银行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是用作商品周转和生产周转的短期性贷款,是要及时收回的;而基本建设资金贷款最终形成固定资产,不需要收回,本该作为国家的财政支出。将流动资金用作固定资产投资,而不计入财政支出,可能会造成财政结余的假象。另有64亿元是从银行借来的商业贷款,其中16亿元商业资金被工业部门抽去使用,商业部门自己办工业也用了5亿元;商业部门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占用23.2亿元,预购定金未收回的部分占用5.8亿元;其余14亿元商业资金也有部分办了基本建设。这就等于在财政收支以外,通过工业和商业信贷的渠道,把一部分资金使用出去了,财政结余实际上已经预支,工业和商业库存则并未增加。(《当代中国财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152—153页。)
1959年2月,李先念根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报告,起草了《关于清理商业资金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央。这16个省、市、自治区1958年底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等占用商业资金在四成以上,抽去办工业(包括大炼钢铁)和搞基本建设等占用资金在二成以上,这些资金均没有及时或实际已无法收回。《报告》建议,对已经赊销、预购的产品,限期清缴完毕,不能按期交货的,退回货款,今后非经批准不得赊销、预购;对抽调商业流动资金用作基本建設和其他用途的,凡是尚未使用的部分,全部交回,已经使用的部分,按照“谁抽谁补”“抽多少补多少”的原则,由省、专区、县偿还,今后对基本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分别管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197—198页。)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并同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商业流动资金使用情况的清查。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对所属6个中央站(原华东大区各专业公司的上海采购供应站)、7个市级专业公司和14个区的零售企业的清查结果显示,1958年末约占用流动资金14.8亿元,较年初增加1.3亿元,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银行借款。而由于大量流动资金被用于预付货款等无法兑现的支出上,商品库存没有增加。(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清查商业流动资金运用情况的报告》(1959年2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3-1592。)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所属单位也存在同样情况。该局分管全市副食品采购供应和饮食服务业,大量预付赊销发生在与农村人民公社的交易过程中(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加强商业流动资金清理和管理的报告》(1959年6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4-1165。)。
在清查商业资金的同时,商业部门也在着手增加市场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商品供应。城市农副产品与日用品供应紧张,固然与城市工业人口大量增长、消耗量剧增,以及手工业社升级全民所有制以后,满足市场需求的品种大为减少等因素有关,但若没有银行信贷的掩护,财政赤字等问题将更快暴露出来,从而引起重视(参见《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除了信贷透支导致财政亏空,商业部门在商品收购中的“大跃进”也变相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损失。工农业生产部门为了完成高指标,不顾产品质量,只求提高数量,而商业部门“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致使质量低劣或货不对路的产品也被收购进仓库。商业部门完成了收购,生产单位就获得了销售收入,随即上缴税款和利润,成为财政收入,但这部分财政收入代表的只是一些质次价高或根本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国家的财政支出远多于此,甚至于花了钱却没有收到商品。(《当代中国财政》(上),第154页。)如商业部财会局调查发现,河南省商水县商业局下放到城关公社的收购站为配合公社放“卫星”,以做假账的方式从公社收购商品总价526万元,谎称加价出售给公社,从中获利17.9万元,但实际上并无此商品,也没有盈利。为了蒙混过关,他们又谎称从利润中支出4万元搞基建,其余部分动用银行贷款上缴财政。(《李先念传(1949—1992)》(上),第450页。)河北省琢县17个公社所属537个供销部,商品库存38万元中有5万元是白条顶替的。其他县市亦有类似情况,根据河北、山东等地材料估算,平均商品库存中约有1.63%是白条顶替的。从全国来看,预计存在3亿元至4亿元的虚假数字。(《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199页。)
随着各地商业资金清理工作的进行,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但只要持续“跃进”的势头不减,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59年,为支持地方工业“大发展”和全民大炼钢铁,银行和财政部门加速资金周转,简化企业流动资金拨付手续。国营企业所需流动资金,不论定额流动资金还是超定额流动资金,都改由人民银行以放款的方式供应,即实行“全额信贷”。其中定额流动资金由财政部门统一拨给银行,再由银行供应企业;超定额流动资金的部分,由人民银行根据实际情况贷放。已拨发的流动资金作为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也如数转作人民银行的贷款。公社所属企业需要增加的定额流动资金,则由公社财政部门在公社预算中拨出一部分资金,交信用部统一贷放。针对1958年出现的各地方、各部门普遍抽调流动资金的现象,国务院重申了企业流动资金的使用范围,即只能用来满足生产周转和商品流转之需,不能用于基本建设、购置固定资产和财政性开支,也不允许将工業、农业、商业贷款互相调剂使用,并对预付、赊销等行为严加限制。(《中国货币金融史大事记》,第389—390页。)
但是,实行“全额信贷”后,流动资金的供应不再经过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而是直接由基层企业和银行办理,对资金的使用实际上缺少经常性监督,特别是在超定额流动资金的使用上少有约束。许多商业部门一面收回此前预付、赊销的货款,一面又继续预付、赊销。因此,各地收回欠款的进度很慢。至1959年5月底,黑龙江等16个省份收回欠款占应收回总额的40%至60%,山西等6个省份收回欠款占比30%至40%,河北等3个省份甚至不到10%,还有些地区的欠款反而继续增加(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秘书处:《关于商业流动资金清理情况和今后意见》(1959年7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4-200。)。1959年1月至5月,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所属单位收回的预付和赊销货款分别为1929.5万元和1361.1万元,但同期新增的预付货款和赊销货款仍高达623万元和1812.5万元,并以82.7万元流动资金投资工业和基本建设(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加强商业流动资金清理和管理的报告》(1959年6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4-1165。)。当年上半年,全国各行业占用银行贷款、商业资金和自有流动资金,将其作为财政性开支或用于各种不符合规定用途的资金多达85亿元(《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204、224—228页。)。
1958年底中央关于清理商业资金的指示下达后,直接的赊销、预付等行为有所收敛,转为更加隐蔽的变相挪用商业流动资金等做法。山东省69个县的公社以各种名义向供销部(信用部)借款共计1155万元,如长清县许寺公社以预付棉花款为由,一次性向供销部借款20万元;益都、诸城、高密、五莲、昌邑、昌乐等6个县的公社当年11月、12月以财政包干为名预抽利润,但实际利润比预期少了90万元,也相当于是借了一笔钱。新的欠账不断发生,也源于旧的欠账无法偿清。在1958年至1959年公社和生产队欠商业部门的赊销款、预付货款和预购定金中,用于兴修水利、搞基本建设、发放社员工资、上缴财政任务和归还农业贷款等方面的资金占到90%以上。大部分资金没有直接用于生产,也就无法在短时期内创造收益。至1959年6月底,湖南省供销部赊销、预付的款项仍欠9667万元,约占银行贷款3.7亿元的26%。据平江长寿公社、常德东风公社供销部反映,二者分别从银行借款174万元和75万元,无力归还,同时大量资金因向公社赊销和垫款而被占用,分别达到70万余元和55万余元。长寿公社于1958年10月至11月期间3次向供销部借用现金32万余元,用作发放工资和放财政“卫星”;长寿公社工交部也向供销部借款7877元,用于建化工厂;长寿镇人委会修公共厕所、修街道、搭光荣台的用款,以至召开人代会的费用、社会肃反费用,都向供销部和合营商店借用,到1959年6月底仍欠6455元;供销部向公社工业预付和借出的款项还有2.7万余元未收回,可这些工厂现已停办。由于赊销、预付及借出的款项过多,供销部还要负担沉重的贷款利息。(《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199、721页。)
1959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商业系统信贷资金投放。商业系统财务计划和信贷计划的审批权限,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集中掌握、统一管理,不再下放到专区和县。商业系统的贷款分为商品储备贷款、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农副产品预购定金贷款和特种贷款四种,采取专款专用。各级银行未经上级批准,不得发放没有物资保证的贷款。(《中国货币金融史大事记》,第391页。)此前信贷资金管理上的混乱,还在于定额流动资金难以确定,以至于财政部门不能及时将企业需要增加的定额流动资金拨交银行。财政部要求各企业主管部门在1959年7月底前,根据财政部门核定的数字,逐级核定基层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并将数字通知有关银行,银行据此发放定额资金贷款。各级银行对企业的定额资金贷款和超定额资金贷款分别管理,超定额资金贷款需限定用途、定期归还。其中定额资金是企业正常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凡属于季节性、临时性、特别储备和为新厂开工备料所需要的资金,都不应计算在内。库存物资中超定额的占用部分,不论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其价值也不应计入定额资金。(《建国以来经济金融法令、制度、大事要略》,第204—205页。)
1959年7月底,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财政金融工作方面的几项决定》,继续强调划清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的界限,并要求对过去的账目进行一次清算,限9月底前完成。《决定》强调,要坚决停止计划以外的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凡性质上属于财政开支的部分,一律用财政款项归还。1958年抽用的资金,原则上由地方财政结余和企业留成收入负担一部分,中央财政负担一部分。1959年抽用的资金,由各地方、各部门在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和企业留成收入中归还。(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73、179页。)1959年8月,财政部成立清理资金办公室,最终于10月底将账目基本清算完毕。1958年,各地方、各部门动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用于财政性开支的款项共计67.4亿元,还不包括商业部门占用流动资金进行赊销和预付的30亿元。67.4亿元中,用1958年财政决算已经处理了26.5亿元(补贴大炼钢铁21.2亿元,其他财政性开支5.3亿元),尚未处理的还有40.9亿元:从使用的方向看,花在基建上18.6亿元,补贴大炼钢铁18.8亿元,其他财政开支3.5亿元;从资金的来源看,属于动用银行贷款的有20.9亿元,属于动用企业流动资金的有11.8亿元,属于动用企业物资折款的有2.2亿元,属于占用公社资金的有2.6亿元,其他如动用财政周转金的有3.4亿元。1959年,各地方、各部门补贴冶炼钢、铁、铜、铝的资金计24亿元,动用银行贷款用于财政性开支的计8.6亿元,合计32.6亿元。这32.6亿元中,除了冶炼补贴部分已在当年国家预算安排解决以外,其余动用银行贷款的部分主要用于基本建设投资。1958年和1959年,各地方、各部门动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用于财政性开支(包括冶炼补贴)共计100亿元。(《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207—208頁。)
三、信贷收缩与经济调整
相较于工农业生产中的“浮夸”,财政中的“虚假”具有一定隐蔽性,它由银行信用膨胀所掩盖,实际上是依靠货币超发来维持。1958年末,中央批准了人民银行在已发行6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再增发20亿元,以满足市场流通需求的请示。当时认为国营商业物资库存空前丰盈,发行货币主要是用来收购农产品,如果发行的货币暂时超过市场需要,多余的货币可通过商业系统出售库存商品回笼,这也不能算作坏事。但实际上,货币发行量远超商品库存价值,也就是说大量的货币发行背后并没有对应的商品作为保障,市场物资供应紧张,通货膨胀由此形成。虽然中央很快发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商业资金和商品库存,但到1959年10月,中央之前批准当年发行的80亿元人民币已经无法满足各地方、各部门的贷款需求,因此,中央又批准了人民银行关于当年再增发20亿元人民币的申请。增加货币发行对于发展生产是有益处的,但问题是如果货币投放出去,却没有相应地拿回物资(增加农副产品的收购量),主要商品和物资的库存减少了,就意味着货币无法回笼。1958年和1959年两年,扣除回笼的货币后,实际超发22亿元(《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643—647页。)。
1960年一开年,为实现新的“跃进”目标,国务院批转人民银行《关于信贷管理体制问题的报告》,继续肯定在信贷管理体制中实行“差额包干”的做法,并作了补充规定:(1)在管理年度包干计划的基础上实行“一年两包”的办法,即总行对分行一次确定上半年和下半年两个差额;(2)省、市、自治区分行在总行核定的上半年包干计划内,自行安排本地区第一、第二季度信贷计划,在下半年包干计划内,自行安排本地区第三、第四季度信贷计划;(3)在半年包干计划内,省、市、自治区可以多存多贷,计划包干差额确实不足、需要超过时,报请总行修改包干计划;(4)总行拨给省、市、自治区分行一定数额的后备款,用于解决国营工业、商业贷款的临时需要(《中国货币金融史大事记》,第394页。)。这一年,人民银行实际超发的货币达到20亿元。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超发货币42亿元,平均每年14亿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货币超发量的近3倍。根据过去的经验,市场货币流通量同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大体是1∶8或1∶9,也就是说每增发10亿元人民币,都需要准备增加80亿元至90亿元的商品,否则增发的货币便不能完成回笼。(《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645—646页。)
1961年初,“大跃进”已难以为继。由于燃料和原料匮乏,许多工厂停工或减产,财政收入锐减。当年1月,上海市财政收入仅有2.5亿元,较上年12月下降64%以上;全国财政收入也只有27.5亿元,同比下降50%。全国财政收入减少后,地方财政分成收入不够地方开支的一半。许多省份都反映银行周转货币紧张,如果收支差额继续扩大,势必要增加货币发行。(《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649页。)1961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当前紧缩财政支出、控制货币投放的补充规定》,要求严控预算外开支和预算外项目上马,停止一切非生产性购置,年内压缩集团购买力30亿元至40亿元。与此同时,为了尽快回笼货币,中央决定在稳定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供应,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即在全国范围内敞开供应高价糕点和糖果。1961年全年共计销售高价糕点3.9亿斤、高价糖果4.1亿斤,回笼货币33亿元,占当年全国消费品购买力的5.9%。(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第209页。)
要实现紧缩银根,“大跃进”期间的信贷管理体制必须改变。196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改变信贷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不再实行“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即“差额包干”的办法,改为由总行按季度核批分行的信贷计划,分行按照总行批准的季度计划放款,超过计划时,须事先报总行批准,各项放款指标不得相互流用。5月,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报告,修改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办法,要求除了超定额流动资金仍由银行放款外,定额流动资金改为大部分(80%)由财政部门通过企业主管部门拨款,作为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小部分(20%)由财政部门统一拨给人民银行,由银行向企业发放定额流动资金贷款。(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第211、219頁。)之后,由于财政部门仍无法及时足额地将资金拨给银行,自1962年1月1日起,银行不再参与20%的定额贷款。凡是实行由银行参与20%定额信贷的企业,一律按1961年12月31日定额借款的账面数额,转作企业自有资金。(上海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取消国营工业、交通企业银行定额信贷的通知》(1962年1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2-2-971。)
1962年2月,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会议上用大量数据披露了当时财政经济面临的困难处境,对通货膨胀有了明确说法。陈云表示:“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随着中央逐渐明确国民经济大幅调整的方针,对货币发行的管控也愈加严格,甚至比1950年统一财经时更紧。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1)收回几年来银行工作下放的一切权力,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2)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不得随意在计划以外增加贷款;(3)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包括用于基建开支、弥补企业亏损、发放工资、缴纳利润,以及职工福利开支和“四项费用”开支(“四项费用”,指企业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银行发放贷款须以能按期偿还为前提,一切非偿还性的开支,只能使用财政预算资金;(4)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不准携带现金抢购物资,不准开空头支票,不准相互拖欠,不准赊销商品,不准预收和预付货款;(5)各级人民银行必须定期向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报告货币投放、回笼、流通,以及工商贷款、工资支付、企业亏损及弥补等情况,并报告违反制度把银行贷款挪作财政性开支的情况和其他重要情况;(6)必须严格财政管理,谁的支出谁安排,谁的漏洞谁堵塞(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第225页。)。
1962年4月,中央对财政经济困难程度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经过计算,上年财政赤字足有30亿元,是靠银行信贷弥补的,此外挖商品库存20亿元,动用黄金、白银储备1.7亿元,对外贸易中增加欠账6亿元,共计57.7亿元。如果加上1958年至1960年的财政赤字,当时初步估算已达200亿元以上,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当年要消灭财政赤字,必须做到三点:货币不再增发;主要消费品库存不再减少;农产品收购计划如数完成。(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第230—231页。)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除了下决心大力削减基本建设投资、精简工业人口,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出:增产日用品20亿元,以增加财政收入4亿元;将原来的高价糕点和糖果从城市扩大供应到所有县城、农村较大的集镇和集市,糖果的销售价格在大中城市工矿区需高于5元/斤,在县城、集镇和农村需高于4元/斤,糕点的销售价格一律高于3元/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关于迅速开展高价糖果高价糕点下伸工作,进一步扩大供应的通知》(1962年3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98-1-1097。)
并增加针织品、自行车、手表、茶、酒和高级副食品等7种高价商品的供应,以回笼货币20亿元左右,增加财政收入10亿元左右(《中国货币金融史大事记》,第404页。)。
继发出“银行六条”以后,中央又作出《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即“财政六条”),着手堵塞银行信贷资金的漏洞:(1)切实扭转企业大量赔钱的状况;(2)坚决制止一切侵占国家资金的做法;(3)坚决制止各单位之间相互拖欠货款的做法;(4)坚决维护应当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5)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6)切实加强财政监督。1961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一度多达125亿元;经过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到1962年8月,市场货币流通量降到84.1亿元,回笼货币40.9亿元,即回笼了市场货币流通量的1/3。即便第四季度收购需要投放一些现金,财政也要增加一些必要的支出,到1962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仍可以比1961年底减少20亿元左右。(《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654页。)
1962年底,历史欠账基本理清完毕。虽然1959年以来,中央几次要求清理资金,但乱拉乱用的情况没有完全停止下来,直到1961年底,欠账仍在增加。据计算,1958年至1961年国营工业企业的物资盘亏和呆账损失,以及各地方、各部门平调集体经济的资金和挪用的银行贷款,需要由国家财政核销、退还和补拨的,共有348亿元。其中,国营企业物资盘亏损失、银行发放贷款中收不回来的呆账损失,以及商业部门发放的预购定金、赊销商品和预付款中收不回来的呆账损失等部分,属于钱和物资已经用掉或损失掉的共有212亿元,大约相当于1962年国家预算收入300亿元的70%。(陈如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第239页。)
四、结 语
自1958年开始实施的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地方的投资冲动;而随之下放的信贷管理权限,则极大助长了投资扩张行为。信贷资金与财政赤字的发生有着直接关系,正是信贷资金的管理漏洞造成了“大跃进”时期财政盈余的假象,并在短时间内没有被发现。一方面,“大跃进”时期超定额流动资金的需求激增,推动了“全额信贷”“差额包干”的出现,从而为预付、赊销等占用流动资金和各种挪用流动资金的行为提供了方便。各地、各部门抽走企业的流动资金后,再用银行的信贷资金补上,这就又增加了信贷需求。另一方面,大量本应用于增加商品流通的流动资金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从而造成财政账面盈余、商品物资却异常紧缺的矛盾现象。而早该发现的巨额财政赤字被银行信用膨胀长期掩盖,以至于持续多年才被彻底清算。从信贷与财政关系的视角观察问题,可以解开基层“大跃进”的密码。这也部分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央何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整顿——因为需要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
“大跃进”以后,中央重新调整经济管理体制,收回了此前下放的包括信贷、财政在内的经济管理权限,但混淆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使用范畴的行为并未杜绝。1965年的调查发现,四川、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南、内蒙古、江西等地有135个工矿企业挪用流动资金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等行政性开支,金额高达880万元(《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248页。)。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所言,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虽然特定的制度条件和中央经济政策会改变投资的紧张程度,但是投资紧张是一种常态。投资紧张是由短缺感带来的,同时又加剧了普遍短缺。投资越紧张,人们就越感到需要把资源从其他领域转入投资领域,由此形成了投资紧张与短缺之间的恶性循环。(参见〔匈〕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等译:《短缺经济学》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06—208页。)这些投资转向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银行信贷得以实现的,中央对此缺少经常性监管,而地方对于信贷膨胀造成的货币超发又缺乏整体认知。当问题被发现时,这些投资往往已经形成固定资产而无法追讨,最后不得不启用财政资金堵上缺口。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