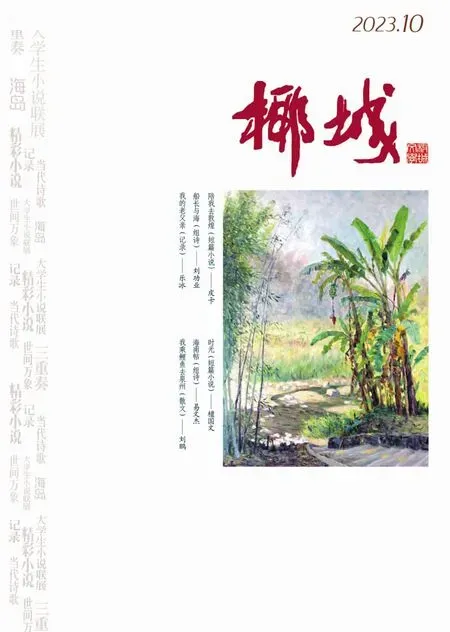生命之轻
2023-12-11◎金戈
◎金 戈
生命看似沉重,步履蹒跚,实则轻如薄纸,禁不住一阵风吹,飘飞于虚空。
在乡下小住,安闲而富足,每一个夜晚都很沉静,睡眠显得格外温润可感。九点的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从酣睡中醒来,阿妈告知:“小宇家那边有人哭,刚炸了三个鱼雷炮,可能有人过了。”不一会儿,村长在微信群里发信息:“兄弟们,小宇老爸刚过世,大家到小宇家帮忙,砍柴火,搭凉棚,摆桌子,安灶台,杀鸡宰猪。”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怎么可能呢?”我心里想。我不肯相信这是真的。毕竟,小宇的老爸很年轻,才69岁,除了风湿病导致腿脚行动不便,拄着拐杖走,或骑电动三轮车代步,身体并无大恙。
对于小宇父亲的突然离世,我是很痛惜的,因为我家和小宇家向来很亲近。按黎族亲属关系,从我父亲这边来算,我叫小宇父亲为叔叔(表叔),因为小宇父亲的母亲是我爷爷的妹妹,我父亲是小宇父亲的表哥,自然的,我也是小宇的表哥;从母亲那边的关系,我得叫小宇父亲为大伯——这和汉族叫法有所不同,黎族叫小舅为小舅,而大舅则叫大伯。我总叫他大伯。我们两家不仅是双重亲戚,住得还很近,关系较好。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村现今所在地,还是一片茅草青青的野地,我们两家是最早从老村那里搬出来到此居住的,两家相距不过一百米远,父亲和大伯平时会相邀饮酒,我和小宇总在一旁听大人聊天。记得有一次,月明之夜,父亲带着我从大伯家喝酒回来,路上发现一条银环蛇——黎族地区叫甘蔗蛇,差点被父亲踩着。那是一圈黑、一圈白,黑白相间花纹的一种蛇,常在夜间出没,黎族人看见此蛇视为不吉祥,必须将它打死方能化凶为吉——若是在白天看见,则要请法师做法驱灾。父亲眼疾手快,从草丛里抓起一截棍子,把甘蔗蛇敲死,带着蛇返回大伯家,说又有了下酒好菜。大伯从屋后的鸡窝里抓出来一只正在孵蛋的小母鸡,杀了和蛇肉炖煮。我和小宇也欢欢喜喜地和大人共享了这道稀罕的美味佳肴。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木匠,手艺很好,制作的家具很是精美。他特意搭了一间茅草屋,那是专门用来制作家具的工坊。他加工木材时,刨出许多刨花,工坊里的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有时没过膝盖,人走进去,松松软软的,仿佛置身于由刨花形成的波浪中,且发出轻柔的沙沙声,很是好听。我和小宇总爱到工坊里去玩,捡一些木材的边角料,当玩具玩;有时把刨花当做海浪,钻到里面去,玩捉迷藏。大伯从没有呵斥,也从不担心我们妨碍到他的工作,只是一再叮嘱我们,刨刀很锋利,不要拿来玩耍,不要靠近锯子和刻刀。但我对那些工具感兴趣,趁大伯不在,就和小宇溜到工坊里去,仔细观察木匠的工具,有时忍不住拿来一把小锯子,找来废料,亲自体验锯木板;有时拿出刨子,在木板上刨着玩,看着自己刨出的刨花兴奋不已;有时拿出墨斗,在板材上弹线。当时远近村的人家,用的床、衣柜、餐桌、板凳、靠椅、书桌,还有打谷子的木制谷箱、吹谷子的手摇风箱,也由村里的木匠打造。我家的餐桌、衣柜、床还有菠萝蜜树格做的靠椅,都是大伯亲手做的。
大伯为人善良,平时总见他和颜悦色,说话轻声细语的,在酒桌上既不和人争辩抬杠,也不论人是非,倒是善解人意,爱替人说好话。村里有个“傻子”,人们叫他“山神”,因为他喜欢独居,独来独往,默默干活,一个人住在野外的山寮里。“山神”其实不傻,只是看起来有些愚痴,爱被村里人拿来开玩笑,成为逗乐的对象,而“山神”从不计较,总是跟着笑,乐呵呵的。大伯见人们开玩笑过了度,就替“山神”说话:“你们不要嘲笑他,他并不傻,只是不和你们计较罢了,他是个善良的人,也很勤劳,老实。”“山神”提起酒杯敬大伯:“呵呵,不碍事,随便他们,我无所谓。”在路上见“山神”,大伯会停下三轮电动车,顺便载“山神”一程。
听闻父亲死讯,小宇从省城赶回来,下午到家,泪眼迷蒙地看过父亲的遗容,开始料理后事。族中、村中的长辈和兄弟,按黎族风俗习惯,依例行事,不须交待就各自忙开了。
傍晚时分,唢呐队也请了过来,坐在屋前的门边,一边饮酒,一边吹吹打打,奏着哀乐。小宇花了近万元从县城棺材铺买了一副加大号的陆军松木棺材。小宇说宽敞些好,让父亲躺着舒服。入殓时,空间余留很大,亲属给死者盖了许多件衣物。亲近的亲人,也都纷纷掏出钱,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不等,塞进棺材里。女亲属轮番哭灵,唱着悼词作道别,啼哭阵阵,听得人伤心。
入殓前,伯母要给死去的大伯抹脸。死者头对着门,裹着被子,躺在草席铺着的地板上。亲属们可以掀开被子,看死者最后一眼。屋里突然传来闷雷破空似的一声哀嚎,屋外的人吓了一跳,纷纷探头往屋里看,只见“山神”趴在地上,抱着死者痛哭,伤心欲绝的样子。他哭着哭着,也躺在地上,哭声减弱,仿佛要静静地和死者同眠。有人说:“这家伙又发酒疯了,捣乱来了,快拉他出来。”但也有人说:“就让他哭吧,他才是真的伤心呢,谁能有他这样认真啊?”人们于是任由他哭了一阵,陪死者躺了一阵,到快要入殓时他才带着哭腔走出来。都说“山神”傻,我倒觉得他不傻,他只是和大伯一样,不想跟人争。他真诚、有爱、善良,他对善待他的人是如此掏心掏肺,虽然,在大伯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给过他什么钱财和物质,但是给了他尊重和理解。村里人认为的“傻子”,原来是最真、最善的,他干活不嫌脏,不嫌臭,不嫌累。
小宇是个孝子。家里就他一个独苗,大姐二姐已经远嫁汉人,一个在海口,一个在文昌。大姐和丈夫带着一个儿子回来奔丧,但二姐的丈夫没有回来,听说是因为文昌地区有避丧的习俗,不便回来。前几年,小宇家也盖了政府扶持的一栋60平米的平房,但房间小,偶尔大姐二姐回来,地方不够住。小宇很上进,在外面承接一些电子设备安装之类的活,赚了一点钱就往家里采购钢管和装修材料,他决定在平房顶上自建铁皮房。房顶虽是铁皮的,但内部装修精致,四边墙用的是防火板材,东面还特意做了一面落地玻璃窗,采光极好,外观也装修得很时尚美观,人们都说小宇家盖了别墅。
可是,谁曾料到,才享了几天清福的父亲,竟然不告而别了。“人生忽然!”我脑海里蹦出这四个字。在丧礼进行的间隙,我和小宇谈到大伯的死因。
小宇说:“我老爸身体很好,没什么病。他们说,昨晚上还看见他在村委会小店那里看人家打牌,还和人说说笑笑的。我叔也说,白天的时候,他还自己骑他的三轮电动车到乡里去领取补助金。”
我看见树下停着一辆全新的小四轮全封闭电动车,问道:“你给他新买的电动车吗?他开过没有?”
小宇眼眶湿润,叹了口气说:“是啊,前段时间他说他的三轮车旧了,我就给他买了这辆,能给他遮风挡雨。可惜,他才开过几次。”
我本想安慰他,说“节哀顺变”,可总觉得这种话真是太不人道了。亲人离世,如何能节哀,如何能顺变,此时此刻就该悲痛,就该哭,悲伤过后才能释怀。
小宇说:“我多想他多活个二三十年,让他好好享福!其实,我今年是要结婚的,都定好了,过两天还打算去拍婚纱照的,却怎么也想不到,他等不及了!要知道今天这样,我就早一点办婚礼,让他亲眼看见,喝上我的喜酒,看看他的儿媳妇。”
大伯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伯母抹着眼泪哭诉:“早上四点多我起来煮饭的时候,他还跟起来,关了外面的灯,然后又回去睡觉了。早上八点左右,他还没起床,我走进去才发现,他在抽搐,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话。”
哎,生命无常,又有谁能够预料?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活蹦乱跳、嬉笑欢乐的,今天说没就没了。这是“人生忽然”!忽然之间,亲人便要阴阳两隔,甚至来不及说一声“再见”,来不及叮嘱一句“你们要好好生活”。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要送大伯上山。我那天的工作是负责记账收钱,原本可以不跟随送葬的队伍去的,可是当大伯的灵柩被青年们抬起来,缓缓走出院门,走向村口,一种悲伤压着我的胸膛,我的心命令我:“要送大伯一程!要送大伯一程!”那时,我的脑海浮现大伯生前在酒桌上的玩笑话:“不要等大伯走了,到时你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赶忙把账本让同岗的一位小兄弟保管,也跟着送葬的队伍送他到山上。
在途中,要轮换抬棺人,我顶了上去。这是我第一次抬棺!有一段路是山路,坡陡路滑,崎岖坎坷,抬得很艰难,同行的青年都加入进来,有几双手顶起我肩上的担子。我和几个人在后面双手抬起棺木,憋足了劲,气喘吁吁的,坚持抬到了墓地。
大伯得以入土为安。人们的心却有了一些波动。回来的路上,几个青年在谈论死亡。他们说的时候是带着笑的。有的说:“尽孝要趁早,不要等父母过世了,才想着弥补,悔不当初。”有的说:“人生要及时行乐,谁也想不到明天会怎样,总之过一天算一天,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过。”
一个人死去,在众人的玩笑里画上了句号。人生一世,不如秋草,草枯可复生,人死不再来。生命一开始就奔向死亡,只是,有的人离开得太迅速,太不应该,就像我这位人好心善的大伯——只愿他在天堂往生极乐世界吧!
生命真是太轻、太轻、太轻了!轻飘飘如梦幻,抓也抓不住,留也留不得。生命之轻,如一缕烟,如一片雾,如一句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