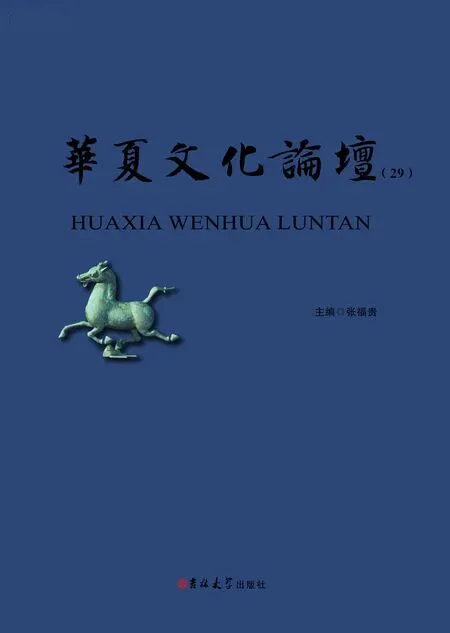家训体的形成及其文体之确立
2023-12-11刘军华
刘军华
【内容提要】随着家族、家庭的出现和宗法制度的建立,家训、家诫行为也随之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而且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把早期的口头的教导训诫的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书面家训(即家训、家诫文)。以《尚书·无逸》为代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专题性的家训体论说文。后来随着词汇的双音化,以及人们认识到“诫”体专门的义指和适用范围,家训体著述除了以“诫”(戒)为题名外,多称为“家诫”“家训”(还有“家约”“家规”等异称别名)。通过考察家训类文章著述的实际,史传记载中的家训体著述名称及文体类分观念,以及古代文论、序跋、类书和诗文总集中家训体的名称及文体归类,史志和目录学著作中的图书著录与文体归类等,都可以看出家训体存在的事实以及时人的文体辨析、文体类分观念和做法。家训体有其自身的文体特征和适用场合,在文体类分观念中家训体著作单独立体,家训体可以独立称体。
家训,也称为家诫,在古代有多种名称和说法,现在人们习惯上一般都使用“家训”,因此本文行文主要采用“家训”这一名称。实际上,在指称文体名称时,“家训”等同于“家诫”,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按照诗文二分法的文体分类,家训体著作有的是韵文体的,有的是散文体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家训体著作大多数是散文体的(也有一些是韵文体的),但是早期的家训著述多是韵文体的,尤其是在口头训诫的时代。由于口头文学时代的韵文体的家训家诫很多都没有流传下来或缺乏记载,难以知晓。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有文字记载的或者说是凝定为文本的家训著作。
在专门的研究家训、家诫史或家训思想的著作中,可能由于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或者说不需要特意强调其文体名称和文体属性,因此行文中经常把家训体著作都笼统地称为“家训文献”①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家训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存在,或者说家训体是否具有自身的体性,在当今的文体学著作的文体分类中,也难以见到其名称、概念及作为独立文体类别而存在。因此考察家训体文体产生的实际,辨析其名实的确立,有着文体辨析的理论意义和文体区分的现实意义。
一、缘事成文:家训体产生的条件及形成的事实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处理具体的社会生活生产事件的需要,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具体的文章。人们已经用此类文章来处理社会事务了,之后才给它归纳出一个适当的文体名称。即先有文章著述之“实”,再有文章著述之“名”和文类文体之“名”。
在未有文字之前,人们之间就有教导训诫的行为发生,通过口头表达来实现。即使在有了文字之后,绝大多数的时候,教导训诫也是口头进行、口耳相传的。只要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知识经验的传授、道德礼仪的教化、立身处世的教导等,就有口头教导训诫的发生。因此口头的教导训诫行为的出现是很早的,早期的文献也有记载。伪《古文尚书》中记载有《五子之歌》②[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7,199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6-157页。,因为夏禹之孙、夏启之子太康沉溺于游乐田猎不理国事,他的五个兄弟心生怨气,于是追述先祖大禹的训诫,作《五子之歌》。记载《五子之歌》的文字虽为后世伪托,但事或有据,不可否认夏禹对其子孙有训诫行为的发生。从《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的追记来看,尧对舜进行过考察和训导,舜对禹也进行过劝诫,颛顼对儿子也进行过训诫,“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③[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3页。。《史记》中虽追记了训诫本事,但由于相隔时代久远,未能追记当时教导训诫的具体言辞和内容。
家训家诫就是在家族或家庭内部,长辈对晚辈、长对幼或夫对妻的训导、训诫,以及族法家规等,有明确的规范家族或家庭成员的目的,具有劝导、约束的性质。虽然起初限于一个家族或家庭之内,但有的家训影响力很大,其训导教育的内容具有普适性或普及性,因此又被别的家族或家庭所接受,不仅具有“范家”(规范一家一族成员)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范世”(作世人模范,规范世人)的作用。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治家家书》等。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中说,“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④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页。,但由于其普适性与影响力,后来被很多人所接受,产生了“范世”的效果。
在早期的训诫行为中,根据训诫的主体与客体(训诫行为的发出者与接受者)双方关系来确定,双方关系为亲属或社会关系范围在家族或家庭范围之内者为家训。家族、家庭是家训产生的社会基础;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建立,助推了家训家诫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发展丰富完善。在先秦时期,虽然没有“家训”或“家诫”的名称和概念,但事实上,随着家族、家庭的出现,家训家诫逐渐形成并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一个家族(家庭)由族长(家长)来领导和管理家族(家庭)事务并教育其家族(家庭)成员,族长(家长)的思想在西周时已经产生,族长(家长)是家训、家诫的主体。①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38页。《诗经·小雅·斯干》“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②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47页。,《诗经·大雅·生民》“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③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04页。,家室、室家的概念和家长思想都已经出现。《周易·家人》:“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④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1页。《家人》中这段话主要体现的是家室的家教思想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宗法观念。父母亲是家教的主体,家教、家训是父母的职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道,先正家室然后可以安定天下。到战国时期,家族、家庭的思想观念更加普及。《管子》卷八《小匡》:“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⑤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1页。《墨子》卷二《尚贤中》:“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⑥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8页。家族、家庭的思想观念的出现是家训、家诫行为产生的基础和背景,宗法制度是家训、家诫行为普遍施行的制度基础和推手。
历史从“历史事实”发展到“历史话语”,就是历史的记忆化、文字化。⑦参[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把早期的口头的教导训诫的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书面家训,即我们所说的家训、家诫文。最初的训诫、教导的社会行为,经过记录或文字加工,凝定为一篇文章(甚至一部著作)、一种文体。书面家训形成后,并不排斥或排除口头家训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书面家训形成后,也可与口头家训并存。比如有些家族、家庭内部的族规、家规,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写定的书面文字,有的也是代代口耳相传的。
家训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随着家族、家庭的出现,家训家诫著述逐渐形成,而且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姑且不论众多湮没消散于历史长河中的口头家训家诫,在书面的历史文献中,《尚书》中已经有了篇章结构完整的文章,其中《无逸》篇就是早期较为完整的专题性的家训体论说文。考察《尚书·无逸》的训导场合、训导双方的关系、训导目的与主题、语言风格、篇章结构等,得出其符合家训体文的基本文体特征:《无逸》中的训导场合、训导双方的社会关系和身份,是在家族之内,周公以家族长辈的身份对成王进行的训导。通篇围绕“毋逸”这一中心话题,劝诫、训导成王不要沉溺安乐,从立身处世、治国理政方面进行教导。《无逸》全篇都是周公一个人的训导之辞,而且“据题抒论”,主题明确,是一篇结构较为完整的早期专题性的家训体论说文,且具有从口头家训向书面家训过渡的特点。①参刘军华《〈尚书·无逸〉的文体特征及文体学意义——兼谈口头家训的发生与文本的凝定》,《求是学刊》2022年第2期,第152-160页。
二、因文立体:家训体著述之“实”与“名”
考察有无文体辨析、文体类分观念和做法,“实”与“名”是其关键。“实”即此类训诫行为和训诫文章著述的实际,“名”包括著述之题名(有的题名就具有文体类分的性质②著作名、篇章名与文体名称有所区别。有的篇章或著作题名具有文体指向的功能,能反映出文体名称,有的题名不反映文体名称,二者不是相合或对应的关系。)和该文体文类的命名(包括异名和别称)。
上文已论,家族的训诫行为很早就已经出现,而且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据《史记》追记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的记载,颛顼有训诫儿子的行为,夏禹有训诫子孙的行为和言辞。西周时期,周公即将还政成王,训诫侄子成王的文辞凝定为家训体的文章《无逸》,并流传至今。
虽然家训体文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但是在汉代之前,家训体著述没有标志文体的类名或文体指向的题名,也没有特有的文体名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唐代孔颖达以回溯的方式,提出《尚书》有“六体”,家训类著述《无逸》被追称为“训”体,但并不意味着在西周或先秦时期家训类著述的文体名称本来就称为“训”体。孔颖达《尚书序》:“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③[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199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4页。《尚书·尧典》篇题下孔颖达疏:“《无逸》戒王,亦训也。”④[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199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7页。孔颖达《尚书》“六体”的观点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篇《书与诗》:“《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是称六体。”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页。虽然《无逸》被归为《尚书》“训”体,但不具有文体类分的意义。孔颖达在《尚书·尧典》篇题“疏”中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⑥[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199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7页。章学诚也认为《尚书》篇章命名依据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⑦[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页。。《尚书》六体中的“训”体具有其特指性和特殊的指称范围,不是后来文体细分之后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名称,不能等同于后来作为文体类别、文体名称的“训”体。如任昉《文章缘起》中所标立的“训”体,不是训诫之文,而是祭祀祖先时所使用的祝颂之辞。《艺文类聚》中列举的“训”体与潘岳的《两阶铜人训》,非训诫类的文章,而是颂赞之辞,与“颂”体接近。
到了汉代,既有家训家诫体产生之“实”,也有其特属之“名”。指称发生在家族(家庭)之内的训诫行为,有的称“家训”,有的称“家诫”,还有的是其异名或别称,如“家约”“家规”“诫”(通“戒”)等。《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①[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51页。“任公家约”,就是指任氏家训,《史记》此处引述仅概述其最核心的内容。蔡邕《与何进荐边让书》:“陈留边让,字文礼,天授逸才,聪明贤知,纂成伐柯,不远之则,龆齿夙孤,不坠家训,始任学问,便就大业。”②[汉]蔡邕:《蔡中郎集》,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娄东张氏刻本。蔡邕此信中夸赞边让“不坠家训”,可见“家训”是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的现象。
家训体在汉代多称为“诫”(通“戒”),家训体著作往往以“诫”或其异称别名(如“戒”“训”“敕”等)为题名。戒,告戒,指通过语言来告戒。通过语言告戒这种行为而产生形成的文体,即“戒”(诫)体。在此意义上,“戒”通“诫”,萧统《〈文选〉序》所谓“戒出于弼匡”。因此指称训诫行为作“诫”或“戒”,文章著述题名多作“诫”,少数题作“戒”。“训”是“诫”的异称,《玉篇·言部》:“训,诫也。”③胡吉宣:《玉篇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51页。“诫,警也,命也,告也。”④胡吉宣:《玉篇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58页。“家诫”即家训,“女诫”即女训。汉高祖刘邦有《手敕太子》,“敕”就是“诫”,因尊长告诫后辈故称“敕”。汉代产生了很多以“诫”为题名的家训体著作,如东方朔《诫子》、韦玄成《诫子孙诗》、刘向《诫子歆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张奂《诫兄子书》、班昭《女诫》、杜笃《女诫》、荀爽《女诫》、蔡邕《女诫》等。
汉代之后,家训体的著述越来越多。随着词汇的双音化,人们认识到“诫”体特属的、专门的义指和适用范围(家族或家庭之内),因此家训体著述除了以“诫”(戒)为题名外,多称为“家诫”“家训”(还有“家约”“家规”“家范”“家教”等异称别名)。三国时期有曹操《诫子植》、李秉《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王肃《家诫》、嵇康《家诫》、王昶《戒子》等。东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的观念更加浓厚,尤其世家大族更加重视子弟的教育,家训家诫体的著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成书于隋的颜之推《颜氏家训》已发展为成熟的家训体专著。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家训体著述越来越丰富多样,成为我国的家族(家庭)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由于《颜氏家训》的重大影响,此后更多的家训体著述以“家训”为题名,逐渐具有了文体指向的功能,并由此而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
三、史传记载中的家训体著述名称及文体类分观念
史传记载中,家训体在汉代多称为“诫”(通“戒”),家训体著作往往以“诫”或其异称别名(如“戒”“训”“敕”等)为题名。《史记》人物传记中把家训行为称为“诫”。《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吾即没,若必师之。’”①[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300页。《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张)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②[汉]司马迁:《史记》(修订本)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80页。如果把孟釐子训诫其嗣懿子、张负训诫其孙的言辞辑录为文,即孟釐子《诫嗣懿子文》、张负《诫孙文》。
《汉书》人物传记中把家训行为多称为“戒”(通“诫”),家训著述题名也多用“戒”。《汉书》卷四〇《陈平传》:“(张)负戒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8-2039页。《汉书》卷九〇《酷吏传》:“(尹赏)疾病且死,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④[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75页。《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大司马护军褒奏言:‘……惟(王)宇遭罪,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经》。”⑤[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65-4066页。不仅用“戒”指称家训行为,而且用“戒”来指称家训文。《汉书》卷七七《郑崇传》记载的郑崇进谏言辞中的指称更加明晰,“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艰难,唯耽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⑥[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55页。郑崇谏言引用周公所著为《尚书·无逸》中的话,把《无逸》篇直接称为“戒”,具有指称文体的意义。
《三国志》人物传记中也把家训行为多称为“戒”(通“诫”),家训著述题名也多用“戒”。《三国志》卷一九《魏书十九·任城陈萧王传》:“太祖戒(曹)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⑦[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5页。《三国志》卷二七《魏书二十七·王昶传》:“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吾复何忧哉?’”⑧[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44-747页。此即王昶《戒子》。《三国志》卷一一《魏书十一·邴原传》:“永宁太仆东郡张阁以简质闻。”南朝宋裴松之注:“杜恕著《家戒》称阁曰:‘张子台,视之似鄙朴人。……体之不如也。’”⑨[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4页。裴松之直接称引杜恕的家训著作题名为“《家戒》”。
《后汉书》人物传记中指称家训行为、列举汉代人物著述的文体,往往称为“诫”;列举家训著述题名,也多用“诫”,少数用其别名“训”。《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阯,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①[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4页。“诫”是马援训诫兄子的行为,其言辞以“诫”名篇为《诫兄子严、敦书》。《后汉书》卷六五《皇甫张段列传·张奂传》:“(张奂)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②[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44页。明确将“诫”与铭、颂、书、教、述志、对策、章表这类文体名称并列,张奂有《诫兄子书》,也是以“诫”名篇。《后汉书》卷八〇上《文苑列传·杜笃传》中将“女诫”与赋、诔、吊、书、赞、七言、杂文这类文体名并列,既作为篇名,又作为文体名看待,“(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③[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09页。。同样,《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曹世叔妻》:“(班昭)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④[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86页。《女诫》既以“诫”名篇,“诫”也是文体名。在《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列传》中作“女训”:“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⑤[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07页。“女训”就是女诫。《后汉书》所记蔡邕《女训》,《文选》卷五六张茂先《女史箴》“人咸知饰其容,而莫知饰其性”句下李善注引作“女诫”,“蔡邕《女诫》曰:‘夫心犹首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人心不修善,则邪恶入之。人盛饰其面而莫修其心。’”⑥[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1977年影印清胡克家刻本,北京:中华书局,第768-769页。
随着词汇的双音化,以及人们认识到“诫”(通“戒”)体专门的义指和适用范围(家族或家庭之内),因此后来的史传中也多称为“家诫”“家训”。《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房玄龄)治家有法度,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各取一具。”⑦[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57页。此后的史传记载中基本承袭,将家训体称为“诫”(通“戒”)体、“家诫”“家训”或其异名,而且与其他文体名称并列列举,体现出较为明确的文体类分观念。
古代的文论和文集序跋中,家训体著述也常以“诫”来名篇,归于“诫”体;有的还说明阐释该类文体的特征、适用场合等。类书和诗文总集中把“诫”体单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选录的文章也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家训体著述,对于家训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归类的认识是比较清晰的。⑧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此外,图书著录分类与文体辨析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史志和目录学著作中对于家训体著作的著录归类,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出时人的文体认识与类分观念。全面考察家训体著作著录归类的源流及其演变的整个历程:《隋志》开其源,立其本。《隋志》把家训体著作归于“集·总集类”的认识和做法,被《旧唐志》之后的史志和目录学著作舍弃。《隋志》把家训体著作归于“子·儒者类”的认识和做法,为后来的史志和目录学著作所承袭,成为主流的认识和做法。到《四库全书总目》总其成,总束为一部(子部)两类(子·儒家类、子·杂家类),对家训类著作性质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延续到现在,《中国丛书综录》统一归为一个类别(子部儒家类),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对于家训体著作的性质和文体分类的认识。①参刘军华:《史志和目录学著作视角下家训体著作的性质与文类》,《文学研究》第8卷(2022年)第1辑,第1-10页。
通过分析家训类著述缘事成文的产生条件和形成事实、因文立体的文体分类做法,考查家训类文章著述的实际,史传记载中的家训体著述名称及文体类分观念,以及古代文论、序跋、类书和诗文总集中家训体名称及文体归类,史志和目录学著作中的图书著录与文体归类等,都可以看出家训体存在的事实以及时人的文体辨析、文体类分观念和做法。家训著述形成较早,大概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在汉代有了自己文体类分的名称,之后一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存在,这就是家训体确立的事实。家训体有其自身的文体特征和适用场合,在文体类分观念中家训体著作单独立体,家训体可以独立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