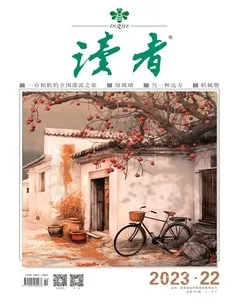葡萄叶绿
2023-12-10徐国能
☉徐国能
甜的葡萄来自童年的泪水,酸的则是欢笑。没有人会质疑,一串葡萄中,每一颗都是既酸又甜的。
浙江大学的江教授寄给我诗人冯杰二十年前的旧作《童年的葡萄向这边遥望》:“多少年不闻那种月光的勃动/想必人间的葡萄都睡熟了/在星星松软的蓝巢之中/葡萄都躺在外祖母的童话深处/如此幸福。”
这首诗更让我确定了,每一颗葡萄,都是一次幸福的回忆,童年的故事或许是一首经常被遗忘的诗。
从前,父亲与弟兄们在小院子里搭了木架,姐妹们撒下种子,让绿叶慢慢地爬满木架。有一天,大家都说:“长出葡萄了。”我仰头一望,一小串青绿色的葡萄挂在藤上。
终于有一天,我不再仰望葡萄,四处漂泊的日子让我与《伊索寓言》和无云的晴空阔别多年,生命里好像也有了一些乡愁。再次相逢,葡萄已经酿成了酒。
在一次次宴会上的水晶杯里,绅士们轮流传递着葡萄酒的种种传说,争辩着关于葡萄酒的许多解释。我不懂那些品种、阳光与水文对葡萄的意义,但我发现那也是一种信仰。我静默着让馥郁的气息唤起难以分辨的记忆,而我想那灯下的暗紫光影的确是值得沉醉的:“所有的葡萄藤都是月光的软梯,一夜纷纷坠下。”
如果我告诉绅士们,真正影响葡萄滋味的,是我们童年的心事,或许他们又要笑我标新立异了。但顺着酒意,或许真能回到童年,攀上那藤的软梯便可在月下荡秋千。唯我不曾醉过,《鲁拜集》里面的醉歌吟唱着:“忍教智慧成离妇,新娶葡萄公主来?”于是我便成了永远的醒客,徘徊在寒食与花朝。
现在,妻子便是我的葡萄公主,她去年不知吃了多少斤葡萄。有一次,我们将葡萄籽随意丢在阳台上的花盆里,不知不觉,竟有藤芽在夜里钻出来。
藤蔓在暗中攀附着窗格,我们发现时,它已变成一队绿叶,横在陈旧的花格铝窗前。最大的绿叶近乎手掌大小,有些则长成三个尖。天晴的时候,那叶子绿得透明,在风里摇曳着一首古老的诗。
当茶花盛开时,我奄忽体会到诗人写下“遗身愿裹葡萄叶,葬在名花怒放中”的感受,毕竟我们都是在葡萄园里工作的人啊。
近来孩子常问我:“我们家真的会长出葡萄吗?”我重新把那些古老的故事与歌谣搬出来,让那温驯的狐狸坐在我们的窗下,让哲学家一般的蜗牛慢慢地享受绿叶间的阳光。我还准备了一个空瓶子,把一些细琐的交谈、微小的秘密与点点滴滴的心情全部装进去。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想酿一瓶酒,也许有一年我们可以围在麝香的烛光中一起品尝,那时我想和你们一起回忆必须溯游时光才能返抵的童年,童年的那一杯夜光。而我们终究也是要被装进那个瓶子里酿成酒的,因为我们都是别人在童年时无心种下的葡萄,甜的来自泪水,酸的或许是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