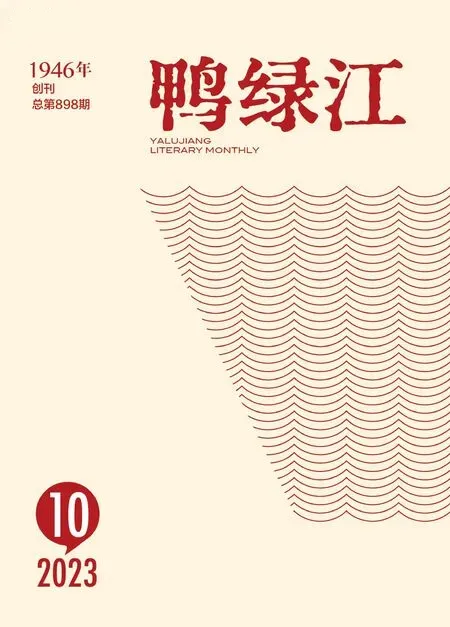花痴吴一拍(外一篇)
2023-12-10胡炎
胡 炎
“吴一拍”这个雅号,是老吴55岁后得来的。
老吴迷上了拍照,一部手机,得闲就拍。街边、公园、湖畔、郊野,别的不拍,独钟情于花。也不讲究技法,更不分花色品种,“咔咔咔”,拍得过瘾。拍完就发朋友圈,自得其乐。
同事说:“老吴,看不出,你还有点浪漫情怀呢。”
老吴笑笑,不答。
其实大伙儿都知道,老吴不是浪漫的人。一辈子老实巴交,脑袋不开窍,在机关混了几十年,才是个主任科员,虚职。家里负担又大,老伴所在的企业不景气,退休后在街边摆小摊。儿子大学毕业,考公务员落榜,屈就于一所乡村小学。父母兄弟呢,都在山区老家种地,时不时需要接济。多少年,老吴连次客都没请过。自然,大席小宴,也很少有老吴的份。
私下里,同事评价老吴“不会来事”,说狠了,老吴窝囊。
可大伙儿却不知道,老吴和一个大领导是老同学,私交甚笃。老同学不提,老吴更是守口如瓶。否则,若让同事知道,那就不仅是窝囊了,背靠这么棵大树,却不晓得乘凉,不说他缺心眼儿才怪。
偶有闲暇,老同学会来他家中小叙。二人品茶,忆旧。聊起同窗趣事,仿若回到当年,解颐大笑。只一样,工作上的事,谁也不说。这是多年的默契。
临别,老同学打趣:“吴一拍,明天还要拍花啊,养眼养心。”
老吴说:“少不了,不拍手痒。”
老同学说:“人活着,就得学会给自己找乐。”
老吴说:“知足常乐。”
老吴这么说,老伴可不这么想,说,咱老两口窝囊就窝囊了,儿子总不能不管吧?给你老同学搭个话,他还能不念旧情?老吴说,是乌鸡是凤凰,凭他自己本事,邪门歪道的事,免提。
“那可是你亲儿子!”老伴的嗓门,不亚于河东狮吼。
老吴一叹,儿子的事,他岂能不挂心?可他拉不下这张脸。一辈子,没啥出息,就这张脸金贵。再说,老同学的为人,他比谁都清楚,不光是能臣,还是廉吏,一年到头忙活,干巴老头儿似的,落了一身病,他怎能再给人家添累?
为了这个,老吴和儿子有嫌隙。有就有吧,老吴照旧,八小时内低头干活儿,八小时外做他的“花痴”。
第二年,老同学视察一个重点工程时,突发脑出血,溘然长逝。老吴把自己关在屋里,落了半天泪。后来,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图片是一丛野菊,上写一行字:清风两袖,人淡如菊。老同学千古!
老伴叹息,儿子往后更没指靠了。老吴不吱声,心里针刺般疼。
转眼,老吴退休了。手续办完,老吴突然对老伴说:“我也要去练摊。”
老伴嘴一撇:“就你?等着喝西北风吧!”
老吴笑而不答,挨着老伴,在街边摆了个小花市。老吴一不吆喝,二不揽客,自顾拍花发朋友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收摊时,一盆花也没卖出去。老伴故意挖苦他:“挣了多少?能买俩馒头吗?”
老吴讪笑:“万事开头难,不急。”
一连几天,老吴的花摆多少,收多少。他还真灰心了,对老伴说,明天最后一次出摊,再没生意,他就不干了。老伴说,你也就这点出息。
没想到,第二天,生意竟出奇地好。老伴奇怪,问他使了啥高招,老吴诡秘一笑,说,降价一半,立竿见影。老伴拿食指戳他的眉心:“敢情是赔本赚吆喝呀,二百五!”
可就从这天起,老吴的小花市火了,价位也渐渐上来了,连老伴都嫉妒。老吴颇为得意:“眼红了吧?这叫花喜鹊落头上,时来运转。”
半年后,老吴鸟枪换炮,开了间花房,白天忙得不亦乐乎,晚上笑着数钱。这还不算,还有更大的好事:儿子到底憋着一股劲,公招一路闯关,终于得偿所愿,进了大机关。老伴扬眉吐气,老吴心中,也是一块石头入池塘,溅起了一片小浪花。
一晃五年,老吴的花房变成了花卉大世界。儿子表现突出,仕途顺利,被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上。
一日,来了两个大客户,极是慷慨,光定金就是五万。不仅如此,嘴还特别甜,一口一个“叔”地叫着。老吴正庆幸财神降临时,忽听他们说:“您是吴主任的父亲吧?”
老吴猛地一个激灵:“你们认识我?”
“可不嘛,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就是冲着您老来的。”
老吴当即沉下脸:“这花我不卖了。”
“为啥?”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为啥,”老吴的语气又冷又硬,“不卖了就是不卖了,你们走吧!”
很快,老吴把花卉大世界转让了。
老吴又像从前一样,游游逛逛,做他的“花痴”。人见老吴的朋友圈花团锦簇,花丛中,老吴还偶尔玩自拍,但见他笑眯了眼,脸红扑扑的,也像一朵花。
驴头面具
路灯稀释了脆薄的月光,我骑着电动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有一刻我产生了幻觉,感到前妻就坐在我身后,前胸贴着我的后背,两只胳膊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腰。这多么可笑,前妻在一年半前就离开了我,傍上了一个有钱的半大老头儿,留给我的,只有上初中的儿子。
但我没理由恨她,我这个小工厂的失业工人,能给她的只有粗茶淡饭和满身的臭汗。走吧,走了好,省得劳累一天后还要承受那些含讥带讽的唠叨,倒也落得耳根清净。
夜风揪扯着我的头发,此刻,我或许像一株移动的草。没错,像我这样的人,不过就是城市里的一株草而已。
回到家,清锅冷灶,满屋狼藉,连狗窝都不如。想起今日业主家的复式楼,客厅大得可以开舞场,水晶吊灯照亮了满屋的豪华。即使这样,还要再做装修。这个世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好在业主是个慷慨人,额外给了我200元小费,我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惭愧。因为,这更像一种施舍。
老同学林建春的电话来了:“钱凑齐没有?铺面已经找好了,咱们得抓紧。”
我迟疑一下,说:“我尽快。”
我要和林建春合伙开一爿驴肉店,这个计划已经酝酿了大半年。眼前打工的装饰公司并不适合我,我对设计一窍不通,只能干一些卖力气的杂活儿,累成死狗也挣不到几个钱。我不想一直这么潦倒下去。老实说,我也想住进业主那样的高档小区,耸立的高楼像是大地的獠牙,更重要的是有那么多探头,对每一个闯入者虎视眈眈。别说住,就是在这里站一站,都觉得腰杆子硬了几分。
但现在,入股资金我还有两万元的缺口。没办法,只有逼上梁山了。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朝父亲家驶去。这里是煤矿的棚户区,前妻和我离婚后,儿子就和父母一起生活。为了讨好老爷子,我狠狠心买了一只猪耳朵和一个口条,老爷子喜欢这一口。
但我并没有直接进家,而是坐在了后面的山坡上。从这里可以俯视父亲的瓦屋。房顶的红瓦有多处凹陷,支撑它们的木檩被岁月压弯了。我想象着待会儿父亲吃猪耳朵和口条的样子,他应该还会喝两杯。母亲一准儿不停地为我儿子夹菜,正是长个儿的时候,他吃两个大馒头绝对没问题。五月的日头和我父亲一样,喜欢吹胡子瞪眼,日光已经有些焦辣。我索性把灰色夹克脱掉,团起来垫在脑袋下,眯起眼睛打了个盹儿。直到听见前妻在梦里叫我:“起床了,懒狗。”我才鼓了鼓勇气,慢吞吞下山。
母亲出门了,家里只有父亲。不出所料,父亲脸色阴暗,对我的到来报以十足的冷漠。从小到大,我和这个倔老头儿似乎是天生的仇人。我知道他用煤矿工人的拳头一心想把我修理成人中龙凤,但我辜负了他。
“你来干什么?”父亲瞪着我。
我向他赔笑:“这不是来看看您二老吗?”
“不需要!”他的右手在旧沙发上使劲拍了一下。我看到了他手背上那道蜈蚣形的疤,那是他年轻时在矿井下留下的。
我坐下来,感到难堪。当我终于横下心道明来意后,我的头已经垂到了裆下,只恨自己不是一只蚂蚁,否则我一定会钻进水泥地板的缝隙里去。
这样尴尬地待了一会儿,父亲只说了三个字:“你走吧。”
“我……”
父亲狠狠地瞪我一眼,一个人进里屋了,我听到很响的摔门声。还能怎样呢?我走出门,机械地跨上车。也许,这就是命,那些不着边际的妄想,对我来说永远是个白日梦。
我没想到,父亲竟追了出来。“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儿子,连个老婆都看不住!”
我拼命咬着牙,老爷子这句话,带给我的不是羞惭,真的,羞惭对我来说已经麻木了。我感到疼痛。
我把电门拧到底部,急速离开。刚驶出几米远,父亲吼道:“站住!”
我停下来,头也不回。
父亲走过来,把一个皱巴巴的旧信封塞给我,转身回去了。我狐疑地打开信封,里面居然是一张存折。信封的背面写着密码,正是我的生日。
顷刻,我的眼前雾蒙蒙一片。
驴肉店开业那天,我们特意搞了个仪式,让一些人戴着租来的驴头面具在门前迎客。等忙完了客人,我走到店外透了口气。戴面具的人拿了钱都已散去,我突然发现马路边竟还有一个晃动的“驴头”,向往来的路人散发着传单。
我心里一热,向他走了过去。
“你怎么不走呢?”我问,其实还有句潜台词,我们没有“加班费”。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仅没有回答我,反而掉头而去。
蓦地,我看到了他手背上那道蜈蚣形的疤……
“爸!”我追了上去。
他一个激灵,停下了脚步。
“忙你的去,”片刻后,他把手用力一挥,长长的驴嘴巴对着我,“等你小子赚了钱,老子天天来这儿吃驴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