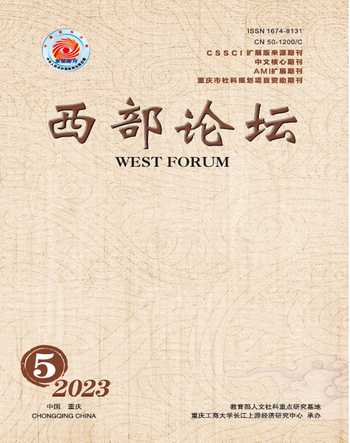双重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
2023-12-04王宇昕余兴厚陈亚惠
王宇昕 余兴厚 陈亚惠



摘要: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则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其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显著正相关,与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负向作用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表明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明显。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财政纵向失衡;财政压力;经济赶超;经济增长压力;地市级政府
中图分类号:F812.2;F29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3)05-0066-14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必须实现各地区各领域各主体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方面之一,推动实现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则不但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路径,也是地区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的具体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然而,一個地区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来提供,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进而财政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情形下,要实现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必须依靠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机制。
王宇昕,余兴厚,陈亚惠:双重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作为联结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纽带和衔接财政收支的主要桥梁,转移支付在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矫正地区间财力差距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英家 等,2022;吕冰洋 等,2019)[1-2]。作为一种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援助,转移支付具有直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促进地区间财力均等化的功效(徐明,2022)[3]。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性问题,进而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也是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王瑞民 等,2017;Dreyer et al.,2015)[4-5]。因此,通过转移支付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优先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措施。然而,由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不同,不同地方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郝春虹 等,2021)[6]。一方面,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能直接缓解因其自身财力不足而造成的财政压力,有效地弥补公共服务支出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产生救助预期和依赖,而这种无成本或较低成本的财政收入容易使得地方政府陷入软预算约束的“激励陷阱”,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甚至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应进行现实性考察。
目前,较多文献探讨转移支付对地方财力均等化的影响,并大多认为转移支付具有财力均等化效应,但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有所差异(贾晓俊 等,2015;马海涛 等,2017邱强,2019;董艳玲 等,2022;刘晓明 等,2022)[7-11]。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强地方财力来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但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曾明 等,2014)[12],因为,财政支出结构也可能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选择(缪小林 等,2017)[13]。如果地方政府在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后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那么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就具有直接的激励效应。而在财政分权体制下,财税收入竞争和政治晋升竞争成为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吴柏钧 等,2021;龚锋 等,2022)[14-15],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往往会呈现出明显的“重经济建设,轻民生改善”倾向,即相较于科教文卫等软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更愿意把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财政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领域(亓寿伟 等,2015;郑垚 等,2018)[16-17],这将会大大弱化转移支付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在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其机制。
鉴于上述,本文从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第一,将财政分权导致的纵向财政失衡(即由财权与事权失配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程度视为地方政府面临的“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将促使地方政府实施经济赶超战略的地区经济差距视为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赶超压力”,进而在分析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的基础上,探究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转移支付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还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下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有助于深入认识转移支付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机制。第二,有别于既有相关文献主要基于省级层面进行经验分析,本文以地级市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能够为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而有效促进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以及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不同于将经济分权与政治分权同步推进的西方联邦主义国家,我国的财政分权在制度设计上采取了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方式(储德银 等,2017)[18]。中央政府一方面将财权上收,另一方面將本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央地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表现出“财权上移,事权下沉”的特征,这种非对称性分权所形成的财力缺口导致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吉富星 等,2019)[19]。由于现行的分权体制只是规范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因而省级政府通常比照中央与省的财政分权体制来设计省以下政府的财政分权体制,这会使地市级政府面临更为严重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陈文美 等,2018)[20]。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受制于其有限的财税收入,进而对其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形成约束。而转移支付则是缓解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能够通过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促使其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直接加大了地区公共服务投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会促使其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进而产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
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发展环境因素会对转移支付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李永友 等,2017)[21]。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的发展环境不同,因而可能具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倾向,表现为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对于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除专项转移支付外,不同地方政府也可能有不同的投入方向,从而产生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对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从财政分权体制来看,其带来的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即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程度不同,表现为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的缺口规模不同。财政纵向失衡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越大,就越会将财政资金(包括得到的转移支付)优先投向能够在短期内直接或间接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领域(如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实体经济发展补贴等),以缓解其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而对于在短期内难以产生财政收入增长效应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则往往是支出倾向较低。第二,从政治集权体制看,地方官员的晋升或连任与其政绩考核紧密相关,而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GDP标尺或GDP增速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性指标(吴延兵,2017)[22]。根据财政竞争的资本流动假说和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假说(Keen et al.,1997;Weingast,1995)[23-24],在地区间激烈的横向经济增长竞争中,地方政府为了能够获胜势必会更加注重财政支出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越希望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赶超,这种经济赶超压力(即经济增长压力)会使其更倾向于将财政资金投入经济建设领域,以期能在短期内迅速地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进而获取较好的政绩。因此,虽然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同样都会为其带来财力增强,但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也会将财力增量相对更多地投向更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领域,进而产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较小;而当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较小时,地方政府则会将财力增量相对更多地投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产生较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越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越小,即存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门槛效应。
实际上,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本身也会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政绩考核压力和地方财政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因素(胡斌 等,2018)[25]。一方面,地方政府享有对财政收入的剩余索取权以及经济增长的政绩红利,当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增大时,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成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收支不平衡和缩小与其他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佳选择,因而其会缩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用于更多地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包括招商竞争、管理权竞争、晋升竞争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竞争等,相较于前三种竞争而言,后者处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地位(王宇昕 等,2022)[26]。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越大,越不利于其提高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对于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全部投资于经济建设领域,必然会有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而且随着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得到缓解,进而有可能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因此,转移支付会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即会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此外,由于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显著地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而对经济赶超压力的作用较为间接并可能不明显,因而转移支付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作用的调节效应可能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增加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负向影响,转移支付对这种负向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即转移支付增加会弱化该负向影响),其中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的负向影响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三、实证方法设计
1.基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为检验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构建基准模型(1):
expi,t=α1transferi,t+α2Xi,t+ui+vt+εi,t(1)
其中:被解释变量(expi,t)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表示城市i在t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核心解释变量(transferi,t)为“转移支付”,表示城市i在t年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水平;Xi,t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的“宏观税率”“资本边际产出”“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等;ui代表个体(地区)固定效应,vt代表时间(年度)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1)被解释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相关研究中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衡量通常采用投入指标(在相关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或产出指标(如中小学的师生比、万人拥有的医师数等),本文选取投入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各地区将财政支出转化成公共产品的效率存在差异,私人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供给能力上也有所不同,用投入指标更能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倾向,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涉及的内容较多,仅选用部分产出指标可能无法代表公共服务供给的真实水平。为了进一步考察转移支付对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本文采用了4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教育服务供给”“医疗卫生供给”“社会保障供给”;同时,为消除不同城市人口差异所带来的影响,采用人均指标来衡量。具体来讲,“教育服務供给”采用“财政教育支出/地区常住人口”来衡量,“医疗卫生供给”采用“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地区常住人口”来衡量,“社会保障供给”采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常住人口”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上述3项之和。
(2)核心解释变量“转移支付”。借鉴郑浩生和李东坤(2016)、王宇昕等(2019)的方法[27-28],同样使用人均指标,即用“(预算内财政支出-预算内财政收入)/ 地区户籍人口总数”来衡量转移支付规模水平。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测算采用地区常住人口数不同,人均转移支付规模水平的测算采用地区户籍人口数,这是因为当前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主要是与地区户籍人口数量挂钩。
(3)控制变量。一是“宏观税率”,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区GDP”来衡量。作为地区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能够为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有效保障,通常宏观税率较高的地区更有实力也更有可能提供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资本边际产出”,参照何强和董志勇(2015)的做法[29],采用“地区GDP/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替代变量。资本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这也是影响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城镇化水平”,采用“地区非农业人口/地区年末总人口”来衡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有效破解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失衡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地区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有效手段。四是“人口密度”,采用“地区常住人口/行政区域面积”来衡量。人口密度不但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人均成本有关,而且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有关,进而会影响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门槛效应检验方法
为考察在不同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同影响,进一步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来进行检验。构建门槛效应模型(2),其中,I(·)表示门槛指标函数,Z为门槛变量,设置“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赶超压力”“双重压力”3个门槛变量,分别用以分析在不同压力的动态变化中转移支付规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异质性影响。
3.调节效应检验方法
4.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平台各省区市的县市统计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补充。限于EPS数据库和统计年鉴地市级公共财政分类支出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样本为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甘肃等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同时,由于我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在2007年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了避免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选取的样本时间段为2007—2018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基准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2。Hausman检验的P值接近于0,拒绝原假设,因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表2的Panel A显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教育服务供给”“医疗卫生供给”“社会保障供给”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会带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显著提高,即转移支付资金通过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正向激励效应,而且这种激励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均存在。考虑到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进一步使用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1期项来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的Panel B,各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明显改变,表明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由此,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
2.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采用门槛模型回归估计前首先需要对门槛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各门槛变量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门槛效应模型(2)的检验结果见表4。需要说明的是,在基准样本分析(表3和表4的Panel A)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两种稳健性检验:一是剔除样本的异常值,即对基准样本进行双边1%的缩尾处理,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的Panel B;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借鉴刘贯春和周伟(2019)的做法[31],使用相对量指标“各地级市所获得的转移支付额与其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转移支付1”)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表3和表4的Panel C。3种检验的门槛个数以及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显著性水平和数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表明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槛变量变化阶段上,“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扩大确实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比各阶段“转移支付”估计系数值的大小可以发现,随着门槛变量值的逐渐增大,系数值逐渐变小,这意味着随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加大,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
3.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表5为模型(8)(9)(10)的检验结果。其中,(1)列在基础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2)列进一步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3)列则是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对(2)列的内生性处理结果。考虑到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使有的地方政府更加依赖输血式财政援助,进而影响其转移支付水平,导致双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与转移支付规模相关程度较高但与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水平相关程度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具体来讲:借鉴袁航和朱承亮(2018)的做法[32],“地区产业结构水平”采用“第一产业占比×1+第二产业占比×2+第三产业占比×3”来衡量;借鉴周密(2020)的思路[33],“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GDP之比”来衡量。(3)列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与(1)列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信。
从表5的回归结果来看:首先,各模型中“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转移支付制度确实具有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的政策效应。其次,“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增大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具有抑制作用。最后,Panel A中“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转移支付对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会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面影响; Panel B中“经济赶超压力×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转移支付对经济赶超压力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Panel C中“双重压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转移支付规模增加可以弱化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抑制作用。由此,研究假说H3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决定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因而地方财力的不均衡会导致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地方财力均等化,但其能否有效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还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倾向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1)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增加会激励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而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增大会抑制其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增加。(2)随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增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而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抑制作用。可见,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有效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但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更好地发挥其政策效应,进而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在提升各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同时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设计方面,应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实现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科学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并重点围绕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努力程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努力程度等方面设立相关的激励指标。对于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应设置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底线标准相适应的最低保障线;对于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城市,尤其是暂时面临经济增长困难的城市,也应适当增加转移支付规模。
第二,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当前,地市级政府的财政压力普遍较大,仅靠财政转移支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事权方面,要合理划分地市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如果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不明确,那么与其相对应的支出责任也就无法清晰地界定,事权的不清晰与支出责任的不明确则会导致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缺口无法被精确计算,进而直接影响到转移支付的激励效果。在财权方面,要适度下放省级政府的税收权限,逐步提高地市级政府对共享税的分享比例,有效增強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从而避免其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
第三,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要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容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针对各地区的发展实际差异性化地设置各项指标的比重,加快推进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本文从财政和经济双重压力的视角拓展和深化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应研究,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但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能只追求数量增加,还应追求质量提升,因此未来还应针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效应展开研究;另一方面,转移支付除了能通过影响地方财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直接作用外,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来提升地方政府的“造血能力”,进而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作用(马光荣 等,2016)[34],对这种间接效应的研究也很有价值。
参考文献:
[1]王英家,张斌,贾晓俊.财政推动共同富裕——基于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分析[J].财经论丛,2022(9):25-34.
[2]吕冰洋,台航.国家能力与政府间财政关系[J].政治学研究,2019(3):94-107+128.
[3]徐明.财政转移支付带来了地区生产效率提升吗?——基于省际对口支援与中央转移支付的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22,39(9):88-103.
[4]王瑞民,陶然.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基于县级数据的评估[J].世界经济,2017,40(12):119-140.
[5]DREYER J K,SCHMID P A. Fiscal federalism in monetary unions:Hypothetical fiscal transfers within the Euro-zon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2015,29(4):506-532.
[6]郝春虹,王英家,贾晓俊,等.分好“财政蛋糕”:对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效应和效率的考察[J].中国工业经济,2021(12):31-49.
[7]贾晓俊,岳希明. 我国不同形式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效应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44-54.
[8]马海涛,任致伟.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均等化的作用[J].财政研究,2017(5):2-12+113.
[9]邱强.省以下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研究——基于福建省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35(6):110-120.
[10]董艳玲,李华.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来源分解及动态演进[J].财贸研究,2022,33(03):51-64.
[11]刘晓明,康慧芳.转移支付与县域财力均等化研究[J].经济问题,2022(8):65-71.
[12]曾明,华磊,刘耀彬.地方财政自给与转移支付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门槛分析[J].财贸研究,2014,25(3):82-91.
[13]缪小林,王婷,高跃光.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分组比较[J].经济研究,2017,52(2):52-66.
[14]吴柏钧,曹志伟.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引资竞争[J].上海经济研究,2021(6):118-128.
[15]龚锋,陶鹏.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竞争——来自中国县级层面的证据[J].经济评论,2022(3):39-55.
[16]亓寿伟,胡洪曙.转移支付、政府偏好与公共产品供给[J].财政研究,2015(07):23-27.
[17]郑垚,孙玉栋.转移支付、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8):18-27.
[18]储德银,韩一多,张景华.中国式分权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预算内外双重维度的实证考察[J].财贸经济,2017,38(2):109-125.
[19]吉富星,鲍曙光.中国式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中国软科学,2019(12):170-177.
[20]陈文美,李春根.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影响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8(11):94-101.
[21]李永友,张子楠.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J].经济研究,2017,52(1):119-133.
[22]吴延兵.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J].经济研究,2017,52(6):137-152.
[23]KEEN M,MARCHAND M.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7,66(1):33–53.
[24]WEINGAST B R.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95,11(1):1-31.
[25]胡斌,毛艷华.转移支付改革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8(3):63-72.
[26]王宇昕,余兴厚.转移支付对重庆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与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2.
[27]郑浩生,李东坤.省以下分权改革促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吗?——来自四川省“扩权强县”改革的经验证据[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4):42-52+153-154.
[28]王宇昕,余兴厚,黄玲.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及结构效应研究——基于川渝地方政府的经验数据[J].财政研究,2019(12):48-60.
[29]何强,董志勇.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J].经济学动态,2015(2):56-65.
[30]EYRAUD L,LUSINYAN L.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advanced economi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3,60(5):571-587.
[31]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08):60-77.
[32]周密,趙晓琳,黄利.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南方经济,2020(05):18-33.
[33]刘贯春,周伟.转移支付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支出偏向[J].财经研究,2019,45(06):4-16.
[34]马光荣,郭庆旺,刘畅.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16(9):105-125+207-208.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Fiscal Transfer Payments o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under Dual Press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37 Prefecture-level CitiesWANG Yu-xin, YU Xing-hou, CHEN Ya-hui
(a. Research Center for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se River; b.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Differences in the fiscal resour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determine differences i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region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balancing local fiscal resources,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can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its differentiated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 Fiscal pressure and pressure for economic growth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iscal spending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eldom considers the influence of this dual pressure when exploring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effect of transfer pay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creased financial resources brought about by transfer payments will encourage local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their fiscal spending 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region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mismatch between fiscal power and office power caused 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ts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the pressure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while the relative la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uts pressure on local governments to catch up. These two pressures prompt local governments to allocate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areas that are more conducive to revenue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n turn has a dampening effect o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reg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 sample of 237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in 16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confirms the above view. The per capita transfer payments receiv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 capita fiscal expenditure 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cluding education expenditure, health expenditure, and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while the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pressure and economic catch-up pressure fac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 capita fiscal expenditure 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shows that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fiscal transfer has a threshold effect of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pressure and economic catch-up pressure, manifested as the incentive effect gradually weakens as the pressure increases. The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transfer payments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pressure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o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regions, bu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transfer payments o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conomic catch-up pressure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suggests that transfer payments can directly and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while the effect on economic catch-up pressure is more indirect and may not be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the pressure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nd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catch-up o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region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ransfer payments are analyzed,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ransfer payments in stimulating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is examined.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ransfer payments for the supply of public products. Moreove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s a sample can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sub-provincial fiscal transfer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regional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fiscal transfer fund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fiscal and tax system that integrates the powers of provincial and lower level governments to alleviate the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alleviate the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fiscal transfer payments; basic public service; 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fiscal pressure; economic catch-up;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prefecture-level government
CLC number:F812.2;F299.23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3)05-0066-14
(編辑:刘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