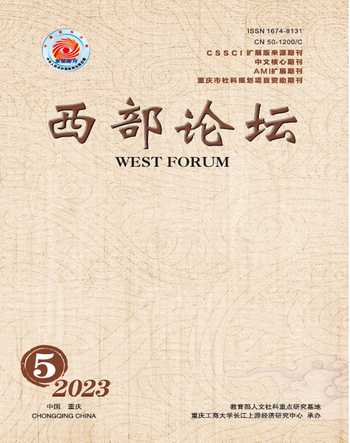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2023-12-04王彦芳王恺涛陈则霖姚景民
王彦芳 王恺涛 陈则霖 姚景民



摘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关键词:数字鸿沟;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化水平;社会网络;创业行为;消费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126.1;F06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3)05-0036-16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各个方面。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2年中国5G基站点达231万个,上网用户达10.67亿。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2022年网上零售额达13.79万亿元,是2014年的4.9倍,数字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然而,由于各地区經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及居民受教育程度等存在显著差异,数字不平等问题逐渐凸显。目前,中国还存在以老年人、农民工、残疾人、边远山区居民等为主体的信息弱势群体,这类群体数字素养较低,缺乏网络信息接收端口且信息处理能力匮乏,无法平等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红利,从而形成数字鸿沟。为弥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趋于扩大的数字鸿沟,2021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国发〔2021〕29号),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的利企便民服务体系,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计划,培养全民数字消费意识和习惯。
王彦芳,王恺涛,陈则霖,姚景民: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数字鸿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互联网、通信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城乡间、区域间、企业间、家庭及居民间的分布不均导致数字不平等(任保平 等,2023;贺唯唯 等,2023)[1-2],并加剧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平等问题(Sanders et al.,2021)[3]。数字鸿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众多文献基于不同视角分析了数字鸿沟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应对策略等(陈梦根 等,2022)[4]。从经济主体维度来看,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鸿沟对家庭(居民)、企业、产业、地区及城乡等层面的影响,其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于数字经济及数字鸿沟影响家庭行为和发展的研究日益丰富和深入。目前,国内文献从家庭层面对数字鸿沟的经济效应分析主要集中在收入(尹志超 等,2021;李五荣 等,2022)、财富(粟勤 等,2021;张楷卉,2022)、消费(黄漫宇 等,2022;杨碧云 等,2023)、投资(张正平 等,2021;李胜旗 等,2022;刘艳华 等,2023)、创业(张要要,2022)等领域[5-14],但各领域的研究均有待拓展和深化。
单就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家庭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展开,而对消费不平等的关注不够。黄漫宇和窦雪萌(2022)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6年和2018 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城乡数字鸿沟通过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数字技能差异阻碍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减弱这种负面影响[9];杨碧云等(2023)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7年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可支配收入、强化信贷约束以及削弱社会网络等渠道抑制了家庭(居民)消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够缓解该负面效应[10]。贺建风和吴慧(2023)的分析结果也显示,数字鸿沟对居民总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来促进居民总消费[15]。杨碧云等(2023)采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CHFS的数据,从家庭消费不平等的视角研究数字鸿沟对消费鸿沟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鸿沟通过扩大家庭收入不平等和削弱家庭消费平滑机制等加剧了家庭消费不平等,并表现出区域和家庭异质性[16]。
总体而言,已有文献对数字不平等影响消费不平等的经验分析还较为薄弱。“不平等”更多的是对群体状态的描述,而从群体中的个体来看,数字不平等表现为其面临的数字鸿沟(即个体与群体中其他个体数字化水平的相对差距),消费不平等表现为其受到的消费相对剥夺 “相对剥夺”的本意是指个体以群体内其他个体为参照进行横向对比而内生出的一种不公平(权益被剥夺)的主观心理状态(Runciman,1996)[17],也用于描述导致不公平心理产生的客观状态,比如导致个体产生自身消费被剥夺心理的相对较低的消费水平。(即个体与群体中其他个体消费水平的相对差距)。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家庭层面探究数字鸿沟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与杨碧云等(2023)的研究相比[16],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拓展:一是在影响机制上,杨碧云等(2023)基于数字鸿沟对家庭收入和消费平滑的影响分析了数字鸿沟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路径,本文进一步从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角度探讨数字鸿沟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机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数字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关系;二是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杨碧云等(2023)基于“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分析了数字鸿沟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区域特征异质性和家庭特征异质性(包括是否贫困户以及户主的学历、金融素养和年龄4种),本文则基于家庭消费行为的差异从是否线上支付、城乡差异、抚养比高低、户主性别4个方面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异质性影响;三是进行了分年度的实证检验及异质性分析,为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由于个体及群体差异的显著存在,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着数字鸿沟的形成与演变。从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看,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搜寻成本,帮助生产者精准识别产品受众从而增加消费适配度,最终刺激家庭消费;而且,随着数字金融服务安全性和便捷性的不断提升,互联网理财等线上金融服务受到更多家庭青睐,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日益普遍,缓解了金融交易摩擦,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张春玲 等,2023;田鸽 等,2023)[18-19]。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普惠性的消費促进效应。然而,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个体间的禀赋差异导致信息网络、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的高度分化(贺唯唯 等,2023;Zhang et al.,2020)[2] [20],从而形成数字鸿沟,并导致数字红利实现的不平等(侯瑜 等,2023)[21]。一方面,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数字公共服务可及性较高(陈梦根 等,2022)[4],居民具有数字技术接入与使用的优势和便利性(张金林 等,2022)[22],能够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多元化商品并借助用户评论筛选优质产品,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相反,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数字技术与服务的可及性与普惠性不足,尤其贫困地区居民无法均等地享受数字红利,与发达地区相比从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获益较小,在消费上则表现为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杨碧云 等,2023)[10]。
进一步从家庭层面来看,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家庭可以较好地利用信息优势提高其消费水平,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由于信息渠道匮乏以及缺少数字知识和技能而无法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来改善其消费(李宝库 等,2018)[23],从而导致两者的消费水平产生明显差距,这种消费不平等会使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产生消费被剥夺的心理,降低其主观幸福感(Sanders et al.,2021)[3]。因此,一个家庭的数字化水平在群体中与其他家庭之间的差距越大,其消费水平与其他家庭的差距往往也越大,从而产生更大程度的消费相对剥夺。
本文将一个家庭与群体中其他家庭之间在数字化水平上的相对差距定义为数字鸿沟,将一个家庭与群体中其他家庭之间在消费水平上的相对差距定义为消费相对剥夺,由此提出假说1: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
2.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的中介作用
数字鸿沟能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化水平不同的家庭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获得的消费红利不同,因而可以基于数字化转型对家庭消费的作用路径来探究其内在机制。家庭消费除了取决于收入水平外,还受到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两个方面探讨数字鸿沟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路径。
从社会网络来看,家庭的社会网络是指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是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状态的反映,对家庭的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社会网络的拓展和强化对家庭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孙海刚 等,2021)[24],而数字技术、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拓展和增强劳动者(家庭)的社会网络(罗明忠 等,2022;丁述磊 等,2022)[25-26]。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家庭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宽原有的社交边界,实现高频次网络社交互动,扩展家庭原有的社会网络(于乐荣 等,2023)[27],并促使家庭亲情维护、工作学习交流、日常生活应用、休闲娱乐等各圈层社交得到系统升级。同时,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有利于家庭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姜扬 等,2023)[28],并实现线上社会资本的价值变现,进而刺激家庭消费。相比之下,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社会网络同质性较高且趋于固化,数字鸿沟的扩大使其社会网络的拓展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相对缓慢(张要要,2023)[29],最终扩大消费不平等,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从创业行为来看,创业家庭的消费特征与非创业家庭具有显著差异(徐佳 等,2021)[30],创业可以显著提高家庭消费(杨碧云 等,2021)[31]。自2014年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创业氛围和示范效应持续强化,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创业机会和工作岗位,网店、自媒体、网约车、外卖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多信息交流机会和知识获取渠道,有助于家庭掌握金融知识,获取并解读真实市场信息,进行更合理的资产配置,增加投资收益,进而促进家庭消费。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家庭能够对各种风险有更系统全面的认知和评估,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创业不确定性,并更有动机和机会通过“互联网+传统产业”进行家庭作坊式创业,从而促进其创业和投资行为(刘艳华 等,2023;张要要,2023)[13] [29]。高数字化水平家庭往往能够利用信息优势发现创业机会并从中获利,而低数字化水平家庭由于缺少信息来源而更多地表现出风险厌恶(陈晓洁 等,2022)[32],不利于家庭风险投资和创业,导致两者具有不同的创业行为。相对来讲,面对同样的创业环境,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家庭投资创业的概率比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家庭更大,因而数字鸿沟的扩大可以通过对两者创业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来扩大两者在消费水平上的差距,最终导致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2:数字鸿沟的扩大会通过对家庭社会网络改善和家庭创业的抑制效应来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
三、实证检验设计
1.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为检验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本文设定如基准模型:
In_consumption(c)it=α+βDig_divit+γXit+μi+λt+εit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家庭和年份,μt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家庭)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个体和家庭层面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2017和2019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该调查的样本范围涵盖全国29个省份(不包括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地区层面的数据来自全国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为避免异常值影响,删除收入、消费及总资产小于0的样本,并对家庭经济数据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以2014年为基期获得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共有32 190个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进一步比较不同年度各地区的数字鸿沟平均水平及其城乡差异,可以发现(见表2):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数字鸿沟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2015—2017年降幅明显,但2019年部分地区(如北京、浙江、河南等)出现了回升;农村家庭的数字鸿沟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家庭,表明城镇家庭的数字化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城乡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基准模型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采用全样本进行基准模型回归的结果见表3的Panel A 本文样本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附近,但并不堆积于零,故而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同时也采取了Tobit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数字鸿沟”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家庭与群组内其他家庭的数字鸿沟越大,其受到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越高,假说1得到验证。为验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将家庭消费分为基础生存型消费(食品、衣着和居住)和发展享乐型消费(文娱、旅游、保健、教育和交通)两类,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的Panel B;此外,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仅保留户主年龄在18~65岁的样本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的Panel C。上述检验中“数字鸿沟”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假说1。
为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尹志超等(2021)、鲁元平和王军鹏(2020)的做法[5][35],采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和“家庭邮电通信费(取自然对数)”作为“数字鸿沟”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检验。一方面,互联网普及率可以反映数字信息技术在样本家庭所在地区的使用和渗透情况,邮电通信支出则反映家庭通过数字工具与外界交流的密切程度,两者与家庭的数字化水平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个体家庭消费支出受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较小,邮电通信支出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占比较小,滿足外生性要求。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家庭邮电通信费用采用CHFS中“家庭平均每个月话费、上网费、邮递服务费等通信支出”题项的数据来衡量。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见表4,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Cragg-Donald Wald F值大于临界值,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以及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且不存在过度识别,说明2个工具变量均有效。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2个工具变量均与“数字鸿沟”显著负相关,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拟合的“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数字鸿沟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的结论依然成立。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进行分年度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结合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1)无论是全样本还是3个年度的分样本,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总消费、基础生存型消费、发展享乐型消费的相对剥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具有普遍性;(2)“数字鸿沟”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估计系数均明显大于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估计系数,表明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的发展享乐型消费具有更强的相对剥夺加剧效应,这也与杨碧云等(2023)的研究结果一致[16]。发展享乐型消费所对应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更复杂,对消费者数字化素养和技能的要求更高,因而,家庭数字化水平的差距会带来更大的消费水平差异。
2.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选取以下2个中介变量:一是“社会网络”。尹志超等(2021)使用节假日支出和红白喜事支出来衡量社会网络[5],但节假日收入和红白喜事收入更能反映家庭的有效社会关系,因而本文采用CHFS问卷中“去年您家庭因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收入(包括压岁钱、过节费)和红白喜事收入(包括做寿、庆生等)”之和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样本家庭的“社会网络”。二是“家庭创业”。借鉴尹志超等(2021)的做法[5],将从事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工商业的家庭视为创业家庭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分别检验“数字鸿沟”对2个中介的变量的影响以及2个中介变量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数字鸿沟”对“社会网络”和“家庭创业”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鸿沟扩大会抑制家庭社会网络的改善,并降低家庭创业概率;“社会网络”和“家庭创业”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估计系数均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家庭社会网络改善和家庭创业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上述分析结果说明,数字鸿沟的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假说2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检验
不同特征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和行为,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特征家庭消费的影响也不同,因而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本文基于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显著差异的角度,选择从是否线上支付、城乡差异、抚养比高低、户主性别4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第一,是否线上支付的异质性。相比传统消费的线下支付,网络购物和线上支付的便利性推动了居民消费革命。互联网消费和线上支付能够有效避免使用现金,减少消费过程中货币支出的视觉冲击,增加消费者的消费冲动(尹志超 等,2019)[36]。采用线上支付方式进行消费的家庭通常具有较高的数字化水平,且能够充分利用花呗、借呗和京东白条等消费信贷产品来弱化现金不足对其消费的限制,从而更好地满足家庭消费欲望(田鸽 等,2023;王小华 等,2022)[19][37]。而未采用线上支付的家庭往往数字化水平较低,不能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来缓解消费约束,因而数字鸿沟的扩大会进一步拉大其与其他家庭的消费差距,产生更强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
第二,城乡异质性。《2022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74.4%,但乡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8.8%,城乡之间在互联网接入方面仍存在较明显的差距。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参见表2),农村家庭的数字鸿沟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家庭,表明城镇家庭的数字化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等的城乡差距依然显著存在并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此,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会导致农村居民获得的数字红利较小,而城镇居民获得的数字红利较大(杨碧云 等,2023;郑国楠 等,2022)[10][38],数字红利的城乡非均衡性在家庭消费上则表现为城乡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差距拉大,从而加剧农村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此外,从基础生存型和发展享乐型两类消费来看,发展享乐型消费的城乡差距比基础生存型消费的城乡差距更大,而数字鸿沟扩大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比基础生存型消费更大,因而农村家庭的数字鸿沟扩大会产生更强的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
第三,抚养比异质性。家庭中少儿和老年人等非劳动人口的多少会对家庭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高抚养比家庭与低抚养比家庭在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上都具有明显差异(罗光强 等,2013;姚青松 等,2016)[39-40]。相比抚养比较高的家庭,抚养比较低的家庭负担较轻,更有动机进行文娱、旅游、保健、教育和交通等发展享乐型消费,因而数字鸿沟扩大对其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可能更大。
第四,户主性别异质性。根据《2022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男性消费能力高于女性,但消费意愿低于女性。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中,女性的消费支出相比于男性多集中于食品、衣着、居住等家庭基础生存型消费(王岳龙 等,2023;邓金钱 等,2023;侯冠宇 等,2023)[41-43],而男性在发展享乐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更多。因此,相比于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数字鸿沟扩大对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可能具有更强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
针对上述4种异质性,本文采用分组检验的方法进行验证。进行以下4种分组:(1)依据CHFS 2017年问卷中“购物是否选择通过手机、pad等移动终端支付”题项将样本家庭划分为“使用”移动支付和“未使用”移动支付2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的Panel A。(2)根据家庭户籍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2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的Panel B。(3)采用家庭中非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来计算抚养比,其中非劳动力人口包括14岁及以下的少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抚养比小于等于0.5的家庭划归“低抚养比”子样本,抚养比大于0.5的家庭划归“高抚养比”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的Panel C。(4)根据户主性别将样本划分为“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2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的Panel D。
根据表7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1)在所有模型中,“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对于不同类型的家庭数字鸿沟均正向影响消费相对剥夺,再次表明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具有普遍性。(2)从系数大小比较来看,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在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的家庭、户主为男性的家庭中,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更强。
六、结论与启示
虽然由数字技术进步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普惠性,但由數字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不同经济主体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等形成的数字鸿沟也导致数字红利的分配不均,从而会加剧经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居民消费活动更加便利,并降低了交易成本,有效促进了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因数字化水平的不同而不同,从而会加剧数字化水平较低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本文从微观家庭层面探究数字鸿沟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采用2015、2017、2019年CHFS数据的分析表明:(1)家庭在群体中面临的数字鸿沟扩大会增强其消费相对剥夺程度,数字鸿沟扩大对家庭发展享乐型消费的相对剥夺加剧效应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的相对剥夺加剧效应更大;(2)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抑制家庭社会网络改善和降低家庭创业概率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3)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也表现出影响强度的异质性,对于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的家庭、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具有更强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启示:一是加快弥合数字鸿沟,尤其要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数字素养、数字技能差距,同步推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一方面,因地制宜做好乡村网络基站建设,增加农村网络接入端口,从网络硬件上缩小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差距;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城市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升城市网络服务能力,提高用户互联网体验。与此同时,基于不同类别数字弱势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数字技能培训与应用场景宣传,减少其心理抵触和技术恐惧导致的数字壁垒。二是为数字技术应用滞后家庭、农村家庭、低抚养比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等建立个性化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并通过虚拟现实、实景模拟等科技手段提升重点群体在实践中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信心,培养数字消费意识和习惯,缩小数字不平等。三是除了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外,还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经济社会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比如,帮助和激励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拓展和改善,促进其社会资本累积;继续鼓励大众创业,应用数字技术降低创业门槛,增加灵活就业岗位供给,为家庭创业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任保平,李培伟.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六大路径[J].经济纵横,2023(7):55-67.
[2]贺唯唯,侯俊军.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改革,2023(5):41-53.
[3]SANDERS C K,SCANLON E. The digital divide is a human rights issue:advancing social inclusion through social work advocacy[J].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Work,2021,6(3).
[4]陈梦根,周元任.数字不平等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2(4):123-139.
[5]尹志超,蒋佳伶,严雨.数字鸿沟影响家庭收入吗[J].财贸经济,2021,42(9):66-82.
[6]李五荣,周丹,李雪.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0):116-127.
[7]粟勤,韩庆媛.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37(9):80-96.
[8]张楷卉.城乡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财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2):69-74.
[9]黄漫宇,窦雪萌.城乡数字鸿沟会阻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9):47-64.
[10]杨碧云,王艺璇,易行健,等.“数字鸿沟”是否抑制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23(3):95-112.
[11]张正平,卢欢.数字鸿沟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57-70.
[12]李胜旗,徐玟龙.数字鸿沟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J].金融與经济,2022(10):3-15.
[13]刘艳华,余畅婉.数字鸿沟阻碍农村家庭金融投资了吗?——基于2018年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OL].财贸研究:1-16(2023-06-1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093.F.20230615.1445.002.html.
[14]张要要.数字鸿沟与农户家庭创业[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2):103-114.
[15]贺建风,吴慧.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45(3):43-55.
[16]杨碧云,王艺璇,易行健.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J].经济学动态,2023(3):87-103.
[17]RUNCIMAN W G.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18]张春玲,范默苒.科技驱动数字营销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中国科技论坛,2023(8):9-11.
[19]田鸽,黄海,张勋.数字金融与创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23(3):74-92.
[20]ZHANG S ,LI F ,XIAO J J .Internet penetration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2020,44(5).
[21]侯瑜,袁鹏妞.“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J].西部论坛,2023,33(2):96-110.
[22]张金林,董小凡,李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22,48(7):4-17+123.
[23]李宝库,赵博,刘莹等.农村居民网络消费支付意愿调查分析[J].管理世界,2018,34(6):94-103.
[24]孙海刚,冯春阳.社会网络与居民消费支出——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证据[J].社会科学家,2021(7):81-87.
[25]罗明忠,刘子玉.数字技术采纳、社会网络拓展与农户共同富裕[J].南方经济,2022(3)1-16.
[26]丁述磊,刘翠花.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43(7):97-114.
[27]于乐荣,张亮华,廖阳欣.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J].西部论坛,2023,33(4)1-16.
[28]姜扬,郑怀宇.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2018数据的研究[J].人口学刊,2023,45(4):57-69.
[29]张要要.数字鸿沟影响相对贫困吗[J].农业技术经济,2023(7):4-18.
[30]徐佳,韦欣.中国城镇创业与非创业家庭消费差异分析——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1):43-60.
[31]楊碧云,毛钦兵,易行健.创业能否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证据[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6):32-38+45.
[32]陈晓洁,何广文,陈洋.数字鸿沟与农户数字信贷行为——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J].财经论丛,2022(1):46-56.
[33]栾炳江,陈建,邹红,等.城镇家庭负债存量与消费不平等[J].南开经济研究,2022(10):92-108.
[34]李晓飞,臧旭恒.“多轨制”养老金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J].经济评论,2022(4):130-147.
[35]鲁元平,王军鹏.数字鸿沟还是信息福利——互联网使用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20(2):59-73.
[36]尹志超,公雪,郭沛瑶.移动支付对创业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3):119-137.
[37]王小华,马小珂,何茜.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11):21-39.
[38]郑国楠,李长治.数字鸿沟影响了数字红利的均衡分配吗——基于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22(9):33-50.
[39]罗光强,谢卫卫.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J].人口与经济,2013(5):3-9.
[40]姚青松,赵国庆.抚养比、年龄结构与我国居民消费:1995~2014[J].金融评论,2016,8(2):39-48+124-125.
[41]王岳龙,蔡玉龙,唐宇晨.房价升值预期、财富幻觉与家庭消费——基于《国六条》的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9):116-137.
[42]邓金钱,刘明霞.数字乡村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来自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J].管理学刊,2023,36(2):10-24.
[43]侯冠宇,胡宁宁.支付数字化能否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2023,37(1):20-28.
The Aggravating Effect of Digital Divide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WANG Yan-fang1, WANG Kai-tao CHEN Ze-lin YAO Jing-min
(1.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Jiangsu,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ese Financial Studi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Sichuan, China;
3.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hil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to residents lives, it has also created a prominent problem of digital inequality. Despite Chinas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establishing the worlds large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superio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households has not diminished. The widening digital divide has suppressed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intensifie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Simply improving the universality of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is not enough to alleviat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families digital literacy.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bridge the family digital divide and identify the key objects and pathways of digital literacy promotion plans ar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in 2015, 2017, and 2019,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ts impact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household consump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r tool use. It is found that the digital divid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resulting in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 Specifically,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on basic subsistence consumption weakens while its inhibitory effect on luxury consumption strengthens. The relative degree of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is greater in households with low dependence on male heads of household, mobile payment, rural areas, and low dependency ratio.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divide intensifi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mainly by weakening family social networks and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starting a family busines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the main expansions and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focusing on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family digital skills, analyz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from the micro level, and revealing the main focus points of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public service inclusive work; (2) focusing on the typic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amilies, such as “men in charge of the outside, women in charge of the inside” and “old people and young people at home”, explor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igital divide and answering which famil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deprived of consumption; (3) in line with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relative bala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measurement of digital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dopts the relative concept and accordingly chooses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s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so a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bridge the family digital divid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effects and pathways of the digital divide from the micro-household level, and reveals that the key targets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promotion plan are male household heads, families with low dependence on mobile payment, rural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s with a low dependency ratio. The key to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is to jointly improve the family digital literacy and the inclusive level of region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Relying on digital platforms to expand social networks and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his paper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clusive sharing of digital dividend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divid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 of digitization; social network;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consumption inequality
CLC number:F126.1; F062.4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3)05-0036-16
(編辑:黄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