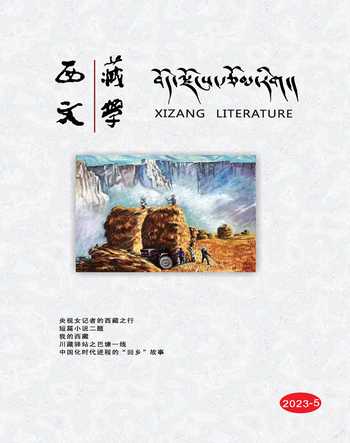中国化时代进程的“回乡”故事
2023-11-29高磊周晓艳
高磊 周晓艳

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模式中多有“农村人进城”的叙事模式,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母题,这种叙事模式贯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之中。从王统照、箫军、柳青、路遥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中均能看到“农村人进城”的叙事模式架构,这种叙事模式架构在如今社会中让文学受众者们感到即便在进城之后仍然感到“精神贫困”,对自我产生怀疑,企求在地域文化的根源——家乡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回乡”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另一种“进城”叙事,人物在进城之后无法寻得精神家园所给予的自我精神栖息空间,产生与“进城”叙事相反的“回乡”叙事,对现有文化现象产生逃离,尼玛潘多新作《在高原》通过对同一时期文学创作中藏族女性“回乡”模式的探源,剖析新时期藏族女性在回乡过程中受到的制衡之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身为一名女性作家,尼玛潘多从创作伊始便将藏族本土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心理转变置于作品之中,在“无意识”之中肩负起女性写作的重任,正如其所说:“在藏族作家的笔下,很少呈现农村女性的心灵世界,我特别关注这一块”“正是因为没有人给她们发声,农村人的内心世界鲜有人关注,所以我更想写一些农村人。”①也正因如此,2010年《紫青稞》的诞生被看作是藏族女性在时代转型中表象的开创性之作。②在经过十数年的沉淀之后,其新作《在高原》包含“时代的发展变迁,作品既有人的发展,又有历史的阵痛”,①在其中可以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女性形象仍然是其不可绕过的生命体验,细观尼玛潘多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女性生存的命运与家庭密不可分,按照荣格所说:“本能和原型是相互决定的”,③原生家庭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在白玛措吉人格塑造的过程中,为其夯实了心理基础,这也正是白玛措吉在经过自我诘问:“我的指路星在哪里?”的心理斗争之后,选择回到塔金的文化原型根源。
一、“回归”之因:地域符号路径的根源
在学者薛晨《日常生活的意义世界:一个符号学的路径》中曾提到符号学与日常生活的息息相关。正是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在以创造思维和潜意识思维中创造了一个精神的栖息地,相比现实世界,这个精神的世界中的一切事物真实性远超外界,在作家看来这个世界正是脑海中对现实世界模仿出来的理想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可以用卡西尔“符号世界”的概念来进行映照,由符号创造的对象非日常生活世界,其最大的特征在于:非日常的生活世界建立在纯自然的人类思维之中。④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尼玛潘多极度关注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命运选择,无所适从到选择归属的情感线索贯穿在其作品之中,所以在《紫青稞》和《透进病房的阳光》中,尼玛潘多打造出来两个文化符号的精神栖息地“普村”和“协噶尔村”,尼玛潘多在“普村”和“协噶尔村”这两个文化符号的栖息地中倾注了所有的情感,包括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社会变迁的思考以及各类人心境转型的思考成为这两个精神栖息地的现实文化根源。作为尼玛潘多笔下第三个文化精神的根据地“塔金”,拥有着特殊的文化使命和文化内涵,作为一个文化地域符号,它承载着白玛措吉的心灵归属,这也正是白玛措吉返回塔金的原因之一。
塔金在现实世界中无从可考,这是独属于尼玛潘多心灵的归属,塔金的命、魂、灵在尼玛潘多的笔下“化入身体”,自我哲思被转嫁在文章之中成为地域和心灵的符号。正如文章中白玛措吉所想:“塔金是隐修者的圣地,遍布着修行的男女,他们想以赤心归于自然,不喜不怒不争不抢,可最终到底有几个做到了呢?她真的希望能看到他们当中某人的传记,她想知道没有欲望的人生真的存在吗?”⑤尼玛潘多关于塔金的哲思,通过白玛措吉在身份转型时期的迷茫思考中展现出来。此外关于塔金地域符号的思考在古时就有所展现,塔金“隐修者”正如中国传统道教中的“隐士”身份,远东诸山在晋宋之际未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⑥其所处皆为人迹罕至之所,故灵运注有:过石桥,渡楢溪再无人迹,然其中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风,云雾缭绕的山峦密林,使这一带犹如仙界,成为佛道隐修者的避世圣地。⑦但不同的是,尼玛潘多笔下地域符号塔金的“隐修”,不同于中国传统认知中的“隐士”形象,以陶渊明《山居赋》中中国传统隐士形象所求“周圆之美”、“隐幽之趣”、“水路通阻”⑦来看,尼玛潘多笔下塔金的“隐修者”更像是佛教的苦修者:“不喜不怒”“无欲无求”,这更符合西藏地区佛教传承的社会背景,这种影响在潜意识中将“佛理”融入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在此背景下成型的地域符号塔金,也正是影响其所处地区人民的文化意蕴。白玛措吉脱离塔金在拉萨求学的经历,只能是其生活生命中的部分体验,正如八九十年代“文化寻根”一般,白玛措吉的根就在塔金,与之相应的是:塔金作为地域符号的本质已经深刻的栖居在白玛措吉的肉体和灵魂之中,这种思维成为其思考过程中的灵魂,也正是塔金这个地域文化符号的影响,白玛措吉在“地域——自我”的空间圈域中选择回到塔金,回到自己的文化栖息地。
二、“回归”之因:原生家庭中“父亲”原型的影响
塔金在白玛措吉出生前就已经存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也成为了塔金文化组织、运转的基本规则,朗杰多吉作为拉萨下乡定居塔金的青年,即便已经成家数十年仍然有着无所适从的文化归属感。作为“人类”的个体,朗杰多吉有着生命和社会两种发展历程的体验,对于类同他们一类的知青团体来讲,他们的人生是充满遗憾的,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的约束条件,后者也能做到理解。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拉萨对于各地区的藏族人民的意义是厚重的,正如文章中所描述:“拉萨是遥不可及的梦,是一座虚幻的城市,所愿所望都在那里。旧时塔金的高僧大德,向往的终极是拉萨,拉萨的三大寺,是他们眼中的日月星辰”⑤“拉萨开在一朵八瓣莲花上”⑤,朗杰多吉作为拉萨人,在其他地区的藏族人民看来本质上是高人一等的,但是朗杰多吉却在政策的洪流之下来到塔金扎根,在他心里自己是与塔金这片地方格格不入的,此外与他一同下乡的其他知识青年已经在各地有所成就,而他却囿于塔金这个地域符号之中,由此产生了不断逃离的生命愿景。
塔金的风季正如同其所孕育的“隐修”文化,即便是非隐修者身份的本地居民在这段风季也无法忍受,“无休无止的风,把塔金人的好脾气磨到不时擦出火星子,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塔金人的另一种修行,不喊杀不骂天,就算修行到家了。”⑤恶劣的自然气候让生存在此的牲畜也难以忍受,相比于拉萨的自然气候,塔金相差甚远,这也正是朗杰多吉想方设法逃离的原因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朗杰多吉本身是在拉薩市区长大的,本身所接受的教育高于周边其他人,在面对白玛措吉度过小学,到了与同龄人接受中学教育的年纪时,她被朗杰多吉送到拉萨读书就可以看出朗杰多吉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妻子梅朵曲珍的质疑声中他反驳道:“只看得见鼻尖的人,怎么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⑤正是自 我本身接受过教育,所以才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朗杰多吉来到塔金做知青时年龄甚至不如白玛措吉,这也正可以看出其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在朗杰多吉看来要想从塔金走出,就必须让白玛措吉接受其应有的教育;第三就是地区文化认同之因,不同于塔金纯粹的地域文化符号,拉萨作为西藏地区的中心,“大包容”的特点正是其社会特征。朗杰多吉在拉萨见过世面之后,即便与梅朵曲珍成婚定居塔金,也有着无法适从的文化归属感。文章写朗杰多吉在刚成婚的时候与家人喝醉的场景:“朗杰多吉喝醉酒是要哭的,乡里人保守,他没法抱着梅朵曲珍哭,就把脸埋到双腿间,边哭边说:‘我没处说话。‘那么多人在这里,怎么没处说话呢? ‘你们听不懂。 ‘你大声一点,我们就听清了。 ‘你们不懂……”,⑤朗杰多吉的这种认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认同,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找和肯定。朗杰多吉即便身处塔金,家庭、亲情都无法阻断拉萨文化和自我身份联系的纽带,在塔金长久的生活中他对自我精神身份认同产生了迁移,自我的身份出现了危机,但是塔金的文化在时间的发展中对他还是产生了影响,所以为保证自我与另一地域的联系,只能不断地在“出走与停留”的模式之中徘徊。“他有什么都藏在心里,更不会说出要走出塔金,可一举一动不都透着想走的意思吗”“一定要学习好表现好,想方设法留在拉萨,千万不要回到塔金”“朗杰多吉却一次次发电报:请勿回来。”⑤通过以上的表现即可发现朗杰多吉将自我“出走”的愿景寄托在自己的女儿白玛措吉身上,自女儿出生后二十几年的心灵慰藉产生了危机,让朗杰多吉不由得对自己不断追寻的自我身份产生断弃的念头,“我是谁”、“我在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思在朗杰多吉的身上得以贯穿,朗杰多吉的行径正是“对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探究,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⑧朗杰多吉作为“父亲”的家庭原型在白玛措吉的人生经历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囿于父亲形象的原型,白玛措吉无法正视自己的心迹,成为在面对选择中矛盾的个人集结体,这也正是白玛措吉选择回到塔金的原因之一。
三、“回归”之因:个人生命的体验
白玛措吉不同于父亲朗杰多吉,十数年的生活经历积淀在塔金,塔金既是故乡也是其生命之根所在。在来到拉萨接受中学和后来到内地接受大学教育之后,白玛措吉于塔金培养的文化建构体系得到了冲击,拉萨社会模式中的生活交往方式对于生在塔金的白玛措吉短时间内造成的文化冲击是难以改变的。“封闭——开放”、“稳定——剧变”⑧的社会模式变化让白玛措吉虽身处拉萨,但身心却扎根在塔金的地域文化符号之中。正如学者崔新建所说:“现代性昭示了文化认同的真正根源。”⑧
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文化——心理结构”中曾提及“积淀”是一种文化性的心理过程,在塔金文化的滋养下,白玛措吉面对新式文化的冲击感到无所适从,所以归其原因来看,正是长久的积淀下白玛措吉承认了其内心深层次的塔金心理结构。在李泽厚先生看来:“长远的社会(主要是种族)经验在人脑结构中留下生理的痕迹,形成了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它们不断遗传下来,成为生而具有的‘集体无意识,它们是超个人的。”⑨运用李泽厚先生的观点来谈白玛措吉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正是塔金的生活经验在其脑海中留下无意识的生活原型,超个人的体验让白玛措吉在新的社会文化中难以适从。面对父亲朗杰多吉从小到大的指引,她在这种无所适从中产生了“异化”感受,在她看来“每个人不就是风中的经幡吗?随风起舞,随波逐流。有几个人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撒哈拉的故事》中:“我虽然掌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但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静静闪烁的指路星,却是我的神。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有的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⑤在白玛措吉看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过自己的选择,被动地承受来自父亲和家庭的生活经验,以至于自己变成了矛盾的集合体,想要突破但囿于生活的困境,以至于发出“我的指路星在哪里?”的心声。
在没有毕业前,身为学生的身份让白玛措吉在学校中畅享着毕业后的未来安排,父亲、家庭、地域的影响抛之脑后,急切的心理让她不由得憧憬未来生活。与之相反的是来自内地的夏荷因为地域、文化、心理的不同,从小培养了极强的个性心理,养成了个人的主见,她的心理正是一名青春期大学生所应有的探求欲,“未知的未来才刺激才好玩,如果什么都清楚了,还有什么动力去奋斗呢?那时的夏荷,已经做好了到沿海城市打拼的准备,她甚至劝白玛措吉也跟着去闯荡。”⑤白玛措吉在未曾面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她的心路历程正如夏荷一般,懵懂躁动的心让她有了对于现实冲击的探索热情,故土故人的限制未曾明显的展露出来。但是到了毕业前真正面临选择的时候,白玛措吉内心深处如父亲的期待、家人的盼望、地域文化的影响、个人的心理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她还是对夏荷的提议选择了背道而驰,“破天荒”的描述手法也正说明了白玛措吉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恪守规矩,即便在某方面对于部分传统有突破,但是真正意义上看来,白玛措吉仍然没有走出“自我”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圈。“大山的孩子应该回到群山间,我不适合沿海,更不适合漂流,倘若你混不下去,也可以来群山间找我,我们一起在塔金隐修,那里是隐修者的圣地。”夏荷满脸红晕,晕晕乎乎地举着杯子说:“人的一生,一定要去闯荡,一定要去争取。”⑤从两位挚友的毕业小聚上的对话可以看到,二人再次相见的可能性甚微,两种不同现代意识的碰撞让两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路径,原始的生活体验也就是原始的经验与两个客观存在之间相互作用,在某一方面形成了契合,并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固化或者强化,化为较为稳定的心理结构,从夏秀的文学主张中可以分析:白玛措吉和夏荷的两种文化地域的生活体验,让客观存在的两人在两个方面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回归”、“探索”,这两种文化心理在两人的求学经历中进一步得到了固化,形成了特有的心理归属结构和精神空間,这也让二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所以说白玛措吉选择回到塔金、夏荷选择去沿海进行体验,正是二人生命体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结语
《在高原》不仅是尼玛潘多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更是其关注当代藏族女性发展的呕心沥血之作。小说通过白玛措吉的“回乡叙事”展现了“家庭——个人”模式之下,新一代藏族女性的价值追求和符号求索,从出走到回乡的叙事,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藏族女性在现代性冲击之下的心路历程,通过白玛措吉的求学经历将新时代藏族女性自我寻找、确认的过程展示在社会之中引起读者的反响。歌德曾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时代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崛起密不可分,女性精神恰恰是这个时代发展所需,容纳、柔和、反暴力的女性特性正是社会正向的生命本能,尼玛潘多从始至终的女性细观体验正是其对于社会发展所需的把握,藏族女性的命运、价值是藏族文学以及中国文学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正是尼玛潘多对藏族女性生活、命运的把握让文学受众者们看到了其本真的社会价值。
(基金项目: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项目“西藏革命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研究”(项目号:2022-TFSCC-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赵丽:《为沉默的农村女性发声——尼玛潘多访谈录》[J].《西藏当代文学研究》2022(01):76-84.
[2].李美萍,范友悦:《女性书写中的“城乡故事”——解读尼玛潘多的〈紫青稞〉》[J].《名作欣赏》2011(32):127-128+137.
[3].冯川、苏克编译:《荣格: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4].薛晨:《日常生活的意义世界:一个符号学的路径》[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第41页。
[5].尼玛潘多:《在高原》[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
[6].孙绰:《游天台山赋》选自:《历代骈文名篇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第104页。
[7].晁元君.:《谢灵运因任自然的地理空间思想》[D].东北师范大学,2017.
[8].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102-104+107.
[9].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高磊,男,陕西榆林人,西藏大学文学院21级中国现当代硕士研究生,热爱西藏文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当代诗歌。
周晓艳,女,湖北公安人,博士,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兼《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