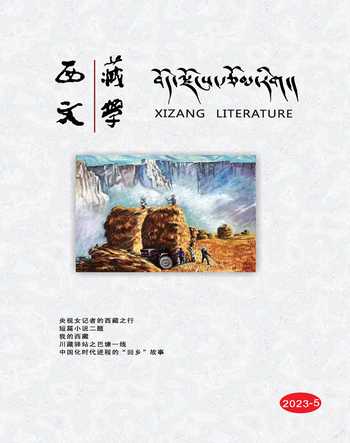大地上的身影
2023-11-29曹林燕
曹林燕
在广袤的田野上,我曾看到过一种热爱,它们是一片固执的绿色,苍青、浓郁。阳光稠密的时候,它们也稠密;阳光稀疏的时候,它们依然稠密。它们像阳光一样常年住在大地的骨子里,以生活的正面或者侧面反复出现在一个村庄的周围。当时间用情绪不断搅动着原野的安静时,当一片土地显得心事重重时,它们的身影便在大地上开始浩荡而行了。
它们可能是一片森深的树林,大地赋予了它们不同的树种:杨树、槐树、柳树、柿树、榆树、椿树、杏树、桃树、梨树、松树、柏树、橡树、漆树、栗子树、梧桐树、苹果树、核桃树、花椒树......
它们可能是一片葳蕤的草丛,拥有世间最平凡普通的名字:猪殃殃、狗牙根、牛筋草、马唐草、节节草、棒槌草、狗尾草、鬼针刺、拉拉秧、剪刀草、风车草、马齿笕、婆婆纳、车前草、马刺蓟、艾蒿、猫眼、苦苣、地丁、蛇莓、水蓼......
它们可能是一片茂密的庄稼,人们稀罕地将它们称为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稻子、荞麦、谷子、棉花、花生、芝麻、油菜、红薯、土豆......
它们可能是一片葱郁的蔬菜,因实用可爱而被冠以美名:萝卜、白菜、辣椒、豆角、西红柿、茄子、黄瓜、韭菜、卷心菜、菠菜、蒜苗、葱、香菜......
当然,如果它们有脚的话,它们也可能是一群悠闲的牛羊,可能是一片跳跃的灰雀,或者是一条条潺潺的小河,抑或是一缕缕袅袅的炊烟......而我最终以为:它们可能就是一群土质的农民。
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总是感觉到童年的故乡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了。我常常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困惑和迷茫:我为什么会将一种曾经绿色的热爱,最终想象成一群土质的农民呢?
(一)
当一个季节被阳光反复陈述时,原野的风正安然地吹荡着树影,光斑灌满了树梢,灌满了纹理密布的骨身和叶脉,也灌满了高低不平的坡岭和大大小小的沟壑。布谷鸟的叫声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细碎和殷切,田畈里的麦子正在渐渐泛黄,麦芒上闪着耀眼的光亮,彰显着一种昂扬的姿态和诱人的质感。无疑,这是一年之中土地最富性感的季节。风吹麦浪,草木弥香,农人的热爱将一拨一拨地化成汗水和炙烤,在大地上传诵、播撒......
他们粗质的眉脸,像河川一样一览无余地荡在风中,佝偻的身影齐刷刷地跟在卑微后面,像一片成熟的庄稼,跌跌撞撞地迈向风景的深处。田野的空旷,增加了时间的密度,带着体温的农具替他们发出了声音:嚓,嚓,嚓……那是一种常年惯有的声音,让土地和镰刀有了纠缠不清的秘密,然后通过他们粗粝的手掌和沉重的脚步,严丝合缝地完成了一个季节与另一个季节的交替。
那時,太阳和影子同时发生。
麦秆在麦田里发出“铮铮铮”的炸响声,那声音不断传达着一种急促和迫切,使得包裹在麦壳里的颗粒瞬间鼓胀起来。芒刺直挺挺地刺向天空。翻滚的麦浪在风中脉动起伏,扑向滚烫的阳光。影子与汗水相互扶持着,被溽热的空气不断冲击并吞噬。
蚂蚁无孔不入,它们可以随便在影子上咬个洞,豆大的汗水便会叭叭叭地掉进洞里,洞和影子随着沉重的脚步贴在地上,缓慢移动……在村庄和村庄之外,没有谁会在意影子的长短和汗水的多少,也没有人仔细计算过影子和汗水给予一个季节所付出的重量。人们只在意各家的麦场上今年积攒了多高多大的麦垛子,各家的麦垛子下能打出多少斤粮食。
当落日终于弯腰,暮色愈来愈浓,一个村庄的滚烫白天被他们土质的身影拖到了傍晚……
月亮在天空渐渐升起,黑夜替代了白天,虚构了一切。村庄再也摸不到白天的身影,只能从月光下发出的沉重脚步声中辨识他们。他们在白天放倒了一大片麦浪,并用长的麦秸秆打了许多麦腰子,把一大片金黄的麦子扎成一个个麦捆,装上架子车运回麦场。从傍晚到黑夜,他们一直在小路上踉跄往返着。时间依附着土地,在弯曲的腰身中遁入一种寂寞,然后,寂寞交织着寂寞,淹没了脚下的田野、沟坡和山峦。寂寞同样牵引着一条乡间的小路,小路像某种密语,被两旁黑压压的庄稼和草木押解着,不断地淌着热汗,不停地喘着粗气,偶尔会有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像极了某些身影的衰老器官,在和贫穷抗争的岁月里,竭力地做着许多克制和隐忍。
堆在麦场上的垛子越来越高,它们的身影高过了房屋,高过了炊烟,也高过了大山的山顶。
当一位皮肤黧黑的父亲,手握一柄大竹叉,站在高高的麦垛上,认真指挥一家人搬运麦捆的时候,他一生所遭受的所有苦难,都被汗水浸润的笑容,瞬间融化了。
带着芒刺的麦垛,先后经历了摊晒、碾压、翻场、起场、扬场、揉搓、簸筛、晒场、装袋,最后终于颗粒归仓。而完成这个虔诚而辛劳的过程,使得一些农具反复地在忙碌的身影里出现:竹叉、碌碡、扫帚、刮板、木锨、簸箕、筛子、推车等等,它们的作用不容小觑。因为受了汗水的包浆,它们在长期与人的躯体接触和磨合中,也慢慢有了人的灵性和温度。
在一个季节发出成熟的呼吸时,农具们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它们被农民引领着,在乡村的麦场上尽职尽责。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又单薄得微乎其微。
这是它们与一个村庄纠缠不清的关系,也是它们与一群土质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土地让它们具有了思想,也具有了生活的惯性和韧性,是生命,也是宿命。
它们是乡间活的身影。
而夏收后的麦场上,只剩下柔软的秸秆和坚硬的麦糠,在太阳底下熠熠发光,人们将它们分别堆压成一座座小山,以备平时做饭生火或者冬天烧炕的时候用。
那些静默的小山被人们称作草垛,忠实地守候在村庄四周。它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身影去拱卫村庄,而村庄也习惯了用另一种身影去拱卫土地。土地拱卫着万物的身影,所有身影最终成为大地上觅食的蚂蚁。
当归仓后的麦子通过暴晒、淘洗、粉碎、搅拌、揉擀、刀切,以及沸水煮烫的华丽变身,最后演变成为舌尖上的一道劲道面食时,人们往往已自行忽略了一切与之有关的忙碌和倦意。岁月在嘴唇一张一合的满足中得到磨砺和滋养,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全为一种甜美所稀释。孩子们日益增长的个子和日益强壮的身体,让清苦的乡村生活悄然凝固成一种恬静的时光,父母在田埂上躬身耕作换来的饱满,足以让一家人欣慰一个整年。
这是乡村最简单的一种幸福。
(二)
秋天快要接近尾声。
阳光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季节的需要,与谷物打成一片,在乡村努力营造出一片壮阔的光影画面。大地散发着成熟的气息,草影和树影通过色彩的变化,清晰地将密匝的庄稼从田野里分割出来。物与象在时间的界限里自然抵达并且集结相融,像思绪延伸的秘境,在风景的深处铺展着一场抒情的叙事。
只有人与庄稼、村庄与庄稼会在默契中共同呼吸,共享一种丰收的喜悦。
秋天的沉甸与丰厚通过农人的身影传递在一个村庄的周围。这个过程带着无比鲜明的饱满和耐力,将土地与村庄的内质深埋在时间之中。
玉米上了木头搭的横架,一层一层,黄灿灿地挂在农家的小院里。几串红辣椒随意地吊在屋檐下。悬挂稻草把子的一根细铁丝被两棵胳膊粗的白杨树牢牢地张在半空。低矮的院墙头上晾晒着一些还沥着潮气的黄豆秆,熟透的豆角还在上面未曾摘取。院子中的大片空地上铺着几张竹席,席子上全摊着白花花的棉花团朵儿。一些抖了粒的芝麻捆整齐地放在墙根下,心有不甘的鸡群们伸长了脖子在芝麻秆下搜寻,试图从芝麻壳中捕捉到几颗遗漏的芝麻粒。它们歪着脑袋,豆眼十分专注,忽然发现藏着的颗粒,尖而硬的喙猛地探进芝麻秆上的硬壳里去啄取,弄得那些芝麻捆在墙角沙沙沙作响。
谷穗和稻子已经铺到了大场上进行晾晒,为了防止牲口家禽以及鸟雀的偷食,由小孩去看场。小孩一会坐在一张小木凳上,低头看自己的影子,好像很矮,小孩不高兴,又站起来看,自己的影子很长,长过小木凳,一高兴,脱了鞋,在谷穗上踩,軟软的,脚底直痒痒。稻粒有些硌脚还粘脚,不好玩。不过影子好玩,随着小孩的移动也发生着有趣的变化,影子追着小孩在大场上跑来跑去,小孩子和自己的影子玩耍,一点也不寂寞。
秋天的收获有时是交替进行的,而秋收、秋种在时间的维度里也有着相对的缓冲性,尽管它们的过程依旧很辛苦。
腾空了谷物的田里,只剩下黑的泥土和一些残碎的枯叶。地的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湿气,某些酱状的植物软软地贴着地面,远远望去,毛茸茸的一片。
农人迈着坚实的步子,在上了肥料的田地里播撒麦种。他们的手脚配合得如此默契而富有韵律和动感,手臂在一抓一扬的挥洒投放间,熟稔干练,收合有致;他们的脚下踩着与手臂动作协调一致的踏点,一进一停,整个身体很有节奏地稳步移动着......那时,他们的身影和劳动的姿态显得无比的从容和自如,仿佛他们不是在劳动,而是踏着音乐的鼓点在田间舞蹈。麦粒从他们宽厚有力的手掌中均匀抛出,在低空中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形成欢快跳跃的扇状画面,然后纷纷散入土中,在随之而来的犁铧下面滚落、深埋......
犁铧经过的地方,黑土翻涌,沟痕深陷。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新泥清香,混合着化肥刺激扑鼻的味道,充斥着一个秋天的早晨或者傍晚。
响鞭不停地在空中挥舞,伴随着耕种人的吆喝声,负重前行的耕牛拉着犁铧踩着犁沟,一步一步在田间劳作。人和牛在常年的患难与共中,相互陪伴,相互扶持,形成了情感上的统一认知和行为上的默契配合,在劳动的过程中,他们具备了同样的耐性和耐力,由一张犁铧牵引着,顺着生活的方向,在辽阔的大地上努力开拓着,他们的身影连同一片土地,往往被一个季节定格成一种生活的背景,在乡村的日暮中不断呈现、延续......
然而,土质的耕作仍是世间最卑微最枯燥的劳动。
当人和牛终于困乏时,没有谁会去安慰他们疲惫的身影,他们必须学会自己安慰自己,学会用一种虔诚料理一片土地带给他们的劳累和饥渴。
人会独自坐在田垄上休息。或者他会点燃一根烟,默默地抽,默默地望着远方。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常常喘不过气来,不过现在还好,他在这个秋天的早晨或者傍晚,还能偷空歇息一会儿,静静地抽一阵子烟,望望远方,想象一下种子入土后的希望。
牛大口大口的喘息后,终于可以和主人一样在田间地头偷空休息一会。主人在放下皮鞭宣布休息之后,从路边抱了一大捆带着新鲜叶子的空棵玉米杆喂它。它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时牛不再羡慕山上那些居高临下的羊群,羊群需要自己去觅食,而牛现在得到了与付出相应的劳动报酬,它吃得心安理得,大量的白沫正从它的嘴里不断流出来。它“咔嚓咔嚓”地吞咬着、咀嚼着,那声音带着一种脆亮和满足,湿漉漉的、热乎乎的,粘着泥土的气息向村庄飘去......
(三)
乡间的日子里必有一块菜地。
蔬菜是庄稼和田地的缝隙,依然属于村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块菜地,面积虽然不大,却仍需经历一个除草、打土疙瘩、筢拉平整、施肥、播种及浇水、拥土的劳作过程。饥馑年月,蔬菜可以当粮裹腹,肚子能够填饱的时候,蔬菜便成为调节肠胃的重要食物。
乡村给予蔬菜的尊重,往往多由女人来完成。但一块菜地的选址,却取决于男人。男人将更多的田地用来种庄稼,留一块距离村子最近的自留地给女人种菜。女人在把自己活成乡间的一株庄稼的同时,充分利用了节气的属性,不失时机地完成一畦蔬菜的茁壮生长和茂密覆盖。
当然,有些事也非一成不变,为了不影响田野的庄重,蔬菜有时也会躲到庄稼下面。比如玉米行子里可以套种些豆角,女人完全可以做这个主。有时蔬菜能卖上好价,女人和男人商量着在河滩种萝卜。
河滩上的萝卜地,不缺水,也不缺阳光,只要肥料上足,手脚勤快,自然长得好。乡下的日子里需要这片河滩地的萝卜。
当大片的庄稼被收割,当大片的空地被耕种,乡间的果蔬成了坐拥田野的招摇宠物。
那片萝卜地,情绪高涨,光影生动。茂盛纷披的缨子,鲜嫩碧绿;呼之欲出的萝卜,绿腰白身,头顶努力撑开一张蓬伞,竭尽一身苍翠,在深秋殷切地铺设着一种萃聚生机的场境。霜降过后,萝卜到了该收割的时候。女人早早起来,做好早饭,喂了猪,给牛槽里再添些草料,就收拾出门了。
一条被露水打湿的田间小路,几乎全让杂草给遮盖住了。女人的鞋子、脚面和裤腿也湿了。早上雾大,空气里湿漉漉的,带着一丝寒凉,看不清远处的南山,只有空旷的田野朦朦胧胧地横在眼前。
女人小心地摸到河滩上,她看见那片萝卜的绿叶上缀满了露珠,亮晶晶的一片。她走近了,弯下腰,轻轻地抖了一下脚边的一棵萝卜缨子,刷刷刷,缨子上的露珠立刻滑落下去,女人的手湿了。
她开始收萝卜,连根带叶一起从土里往外拔。早上露水虽然大,但土层相对松软,好出萝卜。女人从地头开始拔。先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将撑开的萝卜缨子收拢,再抓住裸露在外的萝卜头,前后左右摇晃,等萝卜在土里松动了,便使劲往外一拔,一个身躯白胖的萝卜便离开了坑窝,被女人稳稳地托在手中。
女人嗅了嗅,萝卜带着泥土的清香和水汽,味道很好闻。她去了根部的泥,提着长长的绿缨,把它放在空地上,接着去拔第二棵、第三棵……
太阳从地平线上慢慢升起,地气蒸腾,浓雾渐渐散去。南山眉目清嘉,身影端庄。
女人已经在河滩地里出了一半的萝卜。她浑身湿透了。身上沾着泥、沾着水,也沾着汗。一绺头发从她清秀的脸上垂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用泥手拨了拨,继续弯腰干活。她身后的地里,整整齐齐地摆放了很多带缨的萝卜。太阳出来,萝卜缨子需要敞一敞,有些露水还留在上面。
女人有些累了。她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身,用衣袖擦去额头的汗水。她望着河滩上的那片柿子林,柿子树上的柿子已经红透了,叶子也红得像火,有些叶子已经落了,树下厚厚的一层。
她忽然听见男人的脚步声,回头一看,男人正推了木轮子的推车,车上放着一个大荆笼,朝这边走来。
男人是到河滩上来运萝卜的。
女人和自己的丈夫打了招呼,便帮他装车。他们提着萝卜缨子,把萝卜头朝上放进大荆笼里。装满了一车萝卜,男人拿起牛皮做的车襻,将车襻两边的铁钩分别扣在推车手把的铁环里,然后半蹲下身子,将固定好的车襻绕过头顶襻在肩上,两手抓住木车把的同时,身子从半蹲状态慢慢站立起来……男人脚下踩实了,身子也站稳了。他顿了顿气,然后鼓足了劲,在女人的帮助下,顺利地将一车子新鲜萝卜从地里运到小路上,他缓慢而稳健地推着第一车萝卜回家了……
女人站在地头,目送着丈夫的背影,她知道他将那一车萝卜安全运回家后还会再来河滩上装运萝卜。她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完剩下的那些萝卜。
她重新弯下腰,继续出萝卜。有些萝卜长得不大,却扎土很深,她必须借助手中的小手锄去刨。女人背着晨光,动作麻利地干着,堆在她身后的萝卜越来越多……
她终于出完了河滩上的那一大片萝卜,在这期间,男人也来回往返了好多次……
院子里堆满了萝卜,像小山包一样。男人只管将地里的萝卜连根带叶运回来,剩下的全是女人的事了。
女人坐在院子里,用菜刀一一将萝卜上的绿缨切掉。她挑了些品相较好、个头较大的萝卜,将它们储放在地窖里,准备藏一个冬天,等年关到来时再取出来拿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剩下的萝卜,除了平时包包子、炒菜用,吃不完的,切成片晒成萝卜干或者腌制做泡菜,也可以埋到院中的土里存放着慢慢吃。总之,所有的萝卜放在农家都是宝贝,连那些小得可怜、满身是根须的都不能扔掉,家里的母猪吃得可是津津有味的!
嫩绿的萝卜缨子在女人眼里是做浆水酸菜最好的材料。
女人将它们淘洗干净,切成小段,放在热锅里,用开水轻轻焯一下,除去菜叶中的苦味,把它们装进菜瓮里,放些提前准备好的酸浆水作为菜引子,再倒入掺了面粉的熟的稀面汤,用细竹竿做的长筷子不停搅拌,然后封了瓮口。两三天后,女人打开瓮盖,再次搅拌,让菜叶在酸浆和稀面汤的催化下,迅速发酵,颜色从青绿色慢慢变成黄褐色。为了防止菜酸在发酵过程中溢出瓮口接触空气产生坏的白菌花,女人给瓮里压了一块大小适中的干净石头后,最后才将菜瓮口严实封好。
大约一周左右,用萝卜缨子做的酸菜就可以吃了。馋嘴的孩子们早早就围了上来,每人手里拿双筷子,捧个洋瓷碗,眼巴巴地瞅着菜瓮。在母亲打开瓮口的那一瞬间,一股清冽扑鼻的酸香迎面袭来,女人挑了一筷子酸菜出来,淡白色的酸浆像长线一般顺溜溜地垂挂在菜团下面,刚出瓮的萝卜缨子色泽明亮,带着一种温热,惹得孩子们都争着抢着把碗伸到母亲面前。
女人脸上泛起淡淡的微笑,却装作嗔怒的样子:“猴急啥呢,一个一个来!”她一边说着一边捞着,给每个孩子的碗里都放了一筷子酸菜。
孩子们狼吞虎咽,嘴里发出吸溜吸溜的响声,年龄大的直喊爽,年龄小的却直喊酸,嘴巴歪咧着,眼睛挤成一条缝,那模样十分的滑稽好笑。
女人在一旁看着他们的吃相,自己也被逗乐了……
男人翻了一个上午的自留地,扛着锨走进院子里,女人赶忙吩咐孩子们泡茶端水递毛巾。
男人放下锨,洗了手,用毛巾擦去脸上的尘土和汗水,然后接过孩子端来的热茶,坐在房檐下的石墩上喝茶。他需要缓一缓,休息一会儿,喝完热茶,还要抽一阵子烟。
女人在这个空档,麻利地烙了一个大锅盔,迅速用刀把它切成三角形的块儿,趁热端上来先让家人垫肚子。锅盔外黄内白,油亮酥软,还没张嘴,孩子们的口水就像哈喇子一样流了下来……
女人熬好熱粥,盛在大家的碗里。粥是用今年新打的玉米颗粒磨制成的细糁做的,黄亮亮黏糊糊的,飘着淡淡的香甜味,很诱人胃口。
她从菜瓮里捞了一小盆酸菜,在菜板上切碎,在菜盆里放了调料和油泼辣子,撒了些芫荽碎叶和蒜末,再沥些芝麻香油,搅拌后让孩子们将热粥和酸菜端上饭桌。
一家人围着一张简陋的饭桌,大口大口地咀嚼着油锅盔,吸溜吸溜地喝着玉米粥,吧唧吧唧地就着萝卜缨子酸菜,在清淡、简单、充满幸福和烟火气息的乡间岁月里得到一种生活的满足。
(四)
乡间一年的故事被风算完了。
风从春天刮到冬天,从冬天刮到第二年的春天,又从第二年的春天刮到第二年的冬天……它像一位老谋深算的吹鼓手,吹老了田野,吹老了山坡,吹老了河流,吹老了村庄,也吹老了村庄里的人们。
风拽着时间,到处奔跑。
庄稼收了一茬又一茬,树木绿了一季又一季。葱密的草丛喂养了多少牛羊,贫瘠的土地填饱了多少肚子,清澈的河水滋润了多少村庄,沉重的脚步背负了多少身影……只有风和时间知道。
当一位父亲的锄下淌满汗水的时候,当一位母亲的锅底填满青烟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里正居住着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身体里正居住着一些故事,故事的身体里正居住着大地,大地的身体里正居住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身影一直在大地上行走,一直未曾离开过土地和村庄。
风引导着他们的身影,在广阔的原野上忙碌奔走。他们栽树打草、放羊赶牛、耕种浇灌、拉粪锄地、收割运送、碾场晒粮……为了不影响一块薄田的庄重,他们弯腰屈身,早晚守候着土地和村庄,让荒芜给粮食让路,让农具给庄稼命名。
那时,林木画影为地,沟壑坐幽成阴;那时,羊群在山坡上互相挤兑,黄牛在河滩上静静发呆;那时,云雀从空中飞过,蚂蚁在暗处搬家……它们都是乡间的主人,为了一个村庄的生存,将各自的身世转化成影子,各布其景,各司其事。
风盘活了村庄,村庄抚慰了身影,身影唤醒了土地,土地流淌着血液,血液凝聚着情感,情感记叙着生活的背景。
当尘和影徐徐降落,村庄的耳朵里灌满了许多过往,那些被风吹皱的脸庞,那些被岁月掏空的身躯,那些衰老和消失的背影,那些鲜活和跳跃的新生命……都是固执的绿色、土质的热爱。
他们是大地上的词条,来自我们的故乡。他们曾经拥有过一片土地,曾经拥有过一个村庄。
他们灵魂的深处曾经拥有过风景的深度,他们广阔的胸怀里曾经拥有过大自然的坦荡。
他们从一棵庄稼开始,在大地上认知世界、改造世界;他们饱尝了生活的苦难,也呼吸了丰收的喜悦。
他们执着、勤劳、质朴、善良;他们粗粝、卑微、乐观、坚强;他们是一群农民,是一片土地,是一个村庄,是一种无以替代的生活背影。
当时代试图篡改一种记忆,当今天试图复制昨天,当一代人已经忘记了一种精神,那些曾经出现在大地上的热爱和身影,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地一直都在那里,这是泪流满面的事实!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