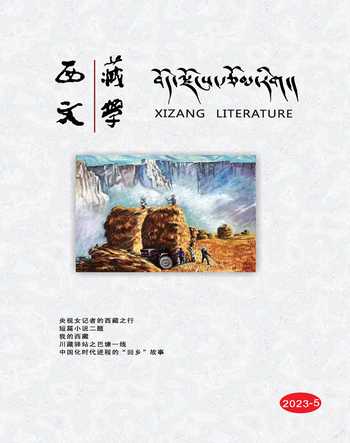川藏驿站之巴塘一线
2023-11-29汪涛

历史上进入西藏的线路有三条,称为康藏驿道、青藏驿道和滇藏驿道,康藏驿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川藏驿道,它从京师的皇华驿,经居庸关外,穿陕西、甘肃到四川,由川康道入藏。在打箭炉的东俄洛,也就是今康定的新都桥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称入藏官道,北线为商贾捷径。而我的家乡巴塘就是南线进入西藏的最后一段,作为四川的西大门,是南线进入西藏的重要门户。
驿道又称官道,巴塘人称“拥郎”(官方修建的路)、“甲郎”(大路)、“这郎”(客行之路)。1958年9月20日,全长386公里的川藏公路南线东(俄洛)巴(塘)段建成,在巴塘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巴塘结束了无公路历史,而318线从理塘县由海子山、德达乡一线入境,也让曾经的川藏驿道巴塘段归于了沉寂。直到2012年,县城通向波密乡格木村的公路通车,虽然当时是土路,却让格木村事隔54年,再次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后来省道459线也沿着曾经的驿道修建而来,在巴塘的茶树山与318线汇成一线,让驿道重新焕发出生机。
据《义敦县志》记载:“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廷由于军事需要修筑了四川至西藏的驿道,并在沿途设置驿站,运送军用粮饷和传递官府文报,西路由理塘治所,行经头塘,拉尔塘,喇嘛垭,三坝,大溯塘,崩察木,小巴冲,直扺巴安今巴塘至西藏。”
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川藏驿道巴塘段曾经的古道和驿站遗址还能看到,其中理塘县的喇嘛垭和巴塘县的三坝、大溯塘三地,就是如今格聂风景区的核心区域,三坝和大溯塘属现在的巴塘县波密乡格木村。按文献记载,巴塘县城到理塘县分界线之间的驿道上,共有四个驿站,分别是小巴冲、崩察木、大溯塘和三坝。这期间义敦县几经设立和撤销,也让大溯塘和三坝一会儿归巴塘一会儿归义敦,也给这条驿道增加几多的故事。
到了巴塘县城后向南沿金沙江经牛古渡、竹巴龙两个渡口,过江就到了西藏的地界,当年这两个地方也是驿站,竹巴龙是川藏驿道四川段的最后一站,作为川藏咽喉,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古人用自己的双脚在横断山脉中踏出了一条足以让史家绝唱的驿道,不仅加强了中央对涉藏地区的管理,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进了区域间人员的流动,促成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密切交流,可以说川藏驿道对于康巴地区人文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坝——以桥为名
三坝位于格木村的夏季牧场所在地,称为“热体”。“热”为藏族的四大姓氏之一,以此为部落名,也读作“咱”。在这里可见海拔6204米高耸入云的格聂山,虽然已是七月,但山上仍旧是冰雪覆盖。它是康南第一峰,在四川境内的众多高峰中仅次于贡嘎山和四姑娘山。
三坝所在地又称“立登三坝”,在藏语里“立登”为宝藏之意思,“三坝”是桥的意思。热体河从这里流向理塘县境内,河上架有三座桥,都在目及范围内,一座为藏区常见的伸臂式木桥;一座为水泥桥墩,上面铺有劈成方料的原木;一座为省道459的路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座桥代表着三个时代,从桥在热体河上的演变历史进程,可推断此处自古以来就是进出巴塘的重要通道。
在《巴塘縣志》和《义敦县志》中记载有三坝厅建厅的情况:“1908年,赵尔丰把理塘土司辖地毛垭和曲登以及巴塘土司辖地格木三地划出设三坝厅,为义敦县治之始,治所三坝桥。”三坝厅就是义敦县的前身,根据当地人的说法,“三坝”和“义敦”这两个名称,都缘于“立登三坝”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义敦就是“立登”这个词的音译,只是所用汉字不同。
再结合当地人的传说,当年的三坝厅可能就设在木桥上方的台地上,由于这一代自古以来是游牧地带,居无定所,因此可知三坝厅办公点就是牦牛毛帐篷,时光如梭,如今已找不到一丝痕迹了。而“三坝”一词,也有人是这样理解的,当时划归的毛垭、曲登和格木三地都有大草坝,因此命名为“三坝”,只是这一种说法无从找到出处。
到了1911年,又将巴塘土司辖地冷卡石划归三坝厅管理;1913年,撤厅改县,三坝厅改为义敦县,取“立登三坝”中的前两字,治所也由“立登三坝”所在的“热体”,迁往格木的大溯塘,办公场所为黑牦牛毛帐篷;1919年,陈遐龄废义敦县,以临卡石、格木划归巴塘,毛垭、曲登仍归理塘;1939年义敦县复治,临卡石、格木、毛垭、曲登复归义敦;1951年成立义敦县人民政府,治所茶洛乡宗马贡村;1954年治所移到措拉区沙溪乡;1978年,撤销义敦县建制。
也就是说三坝厅从建到改为义敦县,再到撤,又恢复又撤,存在了短短的一甲子。其中县府从三坝迁往大溯塘的原因我们已不得而知,而三坝作为驿站,对当时运输物资,传递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应该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溯塘——老虎经过的地方
大溯塘是个草坝子,属于格木草原的一部分,格木草原是四川十大最美草原之一,2020年8月29日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大溯塘是藏语“打雪通”的音译,意为老虎从草坝的低处经过。当地人还称这个地方为“打雪宗”,“宗”为县之意,这个称呼也成为这里是义敦县治所的一个证据。
另一个证据是两张照片,当年都是在义敦县照的,第一张照片很多人应该都看到过,是民国时(1939年)摄影家孙明经先生为义敦县县长彭勋所拍,彭县长背后的草皮坯垒的房子都快要垮了,仅由一根圆木支撑着土墙,可以想见县长的不容易。我拿这张图片,和大溯塘西北方向的大山作对比,这座山和县长彭勋背后的雪山极其相似。当时彭勋县长还为孙明经先生题过字,写的是“川藏之间,古称瓯脱,功比张骞,遍历西域。”
第二张照片是一张合影,1939年11月孙明经和同样是摄影家的庄学本,在西康考察时在义敦县遇见时的合影,也是以那座雪山为背景,我对照着照片上的背景,在现场照了一张相片,通过两张照片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俩背后和左侧的山几乎和现在一模一样。因此通过“打雪宗”一词和两张照片可以确定,义敦县最早的县治在这里,也就是大溯塘,如今已经物是人非,曾经简陋的平房和旗台早已消失在青翠的山野中。
听当地的人讲,当年的驿站所在地和马帮的歇脚点也都在这里,从雪山流淌下来的溪水、依稀可辨的古道,还有这繁茂的牧草,我相信村民所言非虚。
同时文献中也说当年义敦县到巴塘县需翻越大朔山才可到达,“大朔”一词应该也是来自大溯塘一词,只是不同字罢了。这座雪山前有一条路,就是曾经通向大朔山的驿道,大朔山在藏语中称为“扎哇拉”,是小坝村和格木村的分界点。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面对空旷的草原,根本不敢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县的县府所在地。只有草地上还藏着些许的秘密——那些依稀可以辨认出的房屋基础,想到彭县长背后快要倾倒的县政府办公房,可以想象当年治县的艰难与艰辛。
听格木村中84岁的平措曲批老人讲,军用粮饷和文报运送,是以各地支差的形式完成的,从三坝到崩察木由格木人负责护送。而经拉萨、察木多(昌都)一线下来要上报北京的官方文书或军事情报,则是一人飞报,沿途只换马不换人。
还听老人讲马帮等在此宿营有个规矩,三天之内路过住宿是不会有人过问的,但超过三天还没离开,本地人就会来收取相关费用。
后来义敦县府从大溯塘迁到茶洛的宗马贡村,老人也道出了缘由,是由当时的县长曲麦多吉一手操控的,他为了将治所从大溯塘搬迁至他的家乡临卡石宗马贡村,给在格木的官员和村民讲,大溯塘太小了,气候恶劣,人口也不集中,县府搬到茶洛的宗马贡村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不熟悉情况,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才知道上当了,宗马贡村并没有他说的那样大、那样好。
后来我在《义敦县志》看到,曲麦多吉是临卡石宗马贡村人,解放前,出家在亚所寺为僧,父亲死后还俗,任临卡石甲本即土百户,为义敦县第一大头人,能调动五个头人,400人枪,曾任义敦县临卡石区区长,1951年任义敦县人民政府县长。而义敦县也称为措拉县,就是从县治所搬迁到临卡石开始的,因为临卡石也叫措拉。
格木人以游牧为主,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定居点,从大溯塘沿459线向北拐个大弯就可以看到定居点和学校了。
七八月是格木草原最美的时候,县城里的人会利用周末到这里打卡游玩。我也曾为这里的美景赋诗一首——
格木,我来了!与你相约在七月里,无尽的绿在眼中畅游,我的心从骏马的眼里跌出,如风般在草甸上飞驰。
格木,我来了!花海在风中起伏,漫过了定曲,延伸至山脚,与高大的云杉,构成仙境般的画卷。
格木,我来了!我的眼镶在了高山间,我的心跌落在花海里,我被风定格在时空里,这样的美谁能复制。
茶马古道是唐代以来因茶马互市逐渐形成的,是以人背、畜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商品贸易和传递文书的通道。从这里到巴塘县城有两个路线,一条是官方的驿道,就是翻越大朔山;另一条是民间马帮经常走的路线,需要翻越冒拉山。听平措曲批老人讲所需时间差不多,但冒拉一线可以穿越整个格木村的定居点,因此在修建省道459线时,为了更方便格木村人的出行,就选择了冒拉一线。
也因为这,格木有许多关于康巴南路茶马古道的故事,《葱本阿来》就是其中一个故事。葱本是商人之意,葱本阿来即商人阿来,当时他已经是拥有九十九匹骡子的大商人了,可他还是不满足,盯上了他请的拉多(马夫)仅有的一匹骡子,一心想把拉多的那匹骡子据为己有,让自己的驮队变成一百的整数,一路上他都在算计着这件事。
到了途中休息的时候,葱本阿来对拉多说:“我俩打个赌,谁能爬上对面那座高山,在山顶点上烟火,那么对方的骡子就归自己所有。”得到拉多的同意后,葱本阿来的贪念涌上心头,便要求先去爬山,为了不迷路,他沿路采集花朵,在峭壁上做了记号,为让自己的驮队的骡子变成一百的整数,葱本阿来用尽全身力气爬上了山顶,并在山顶上点起了大火,浓浓烟雾在山顶冒起,拉多想自己输定了,可就在此时,天空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霎时下起了冰雹,作为标记的花朵也被风吹散,被冰雹打落了,葱本阿来在下山时无法辨认路线,加之冰雹的袭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等了一夜的拉多见他未归,就赶着一百匹骡子回家了。
从那以后人们称这座山为“葱本腊”,如今它雄踞在冒拉一线的群山之中,非常壮观。传说过往此地的商人,在山脚大声喧哗或心存贪念,山上就会降下冰雹,警示人们不可贪婪,要学会知足。
崩察木——闪光的草地
翻过大朔山或越过冒拉一线,海拔高度就会逐渐下降,至此一直到小坝村才会看到村落。
从高山草甸逐步过渡到原始森林。在森林中听到流水淙淙声时,会看到一条小溪,小溪前有一块草坪,那里就是崩察木,意为鲜花盛开的草地,也可以说成是“闪光的草地”。
此处作为驿站早已废弃多年,当年的遗迹有点模糊了,还好经过几番找寻,知情人讲的嘛呢堆还在,用柏木做的“锁心”(中心木)还挺立在嘛呢堆中,据说由柏木做成的中心木会历经百年不腐。
由嘛呢堆我们可以大概推断驿站的位置。驿站也叫台站,《巴塘县志》中对驿站的作用作了详细说明:“1719年,因为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岳钟琪西征,清廷在打箭炉至巴塘一路设置台站,专作军政行人和传书公差住宿之用,每站设台书一人,专司看守和办理往返公文收发事宜。”驿站又分尖站和宿站,文献上说“三十里一尖站,六十里一宿站。”尖站,只在这里吃饭、稍作休息的地方,如果是马匹跑不动了还可换马,崩察木就属于尖站。宿站用于投宿的,驿站所在地往往和民间马帮的宿营地是同一个地方。
听扎多洛绒讲,从三坝到崩察木,驮运货物的主力是牦牛。崩察木的古官道要寬阔很多,越野车在此行进应该不在话下,长满杂草的驿路一直伸向原始森林的深处。
小坝村——得名于巴塘
沿古道一路下山,当看到掩映在苍翠树林中的藏房时,我们就到了江巴顶,它是小坝村一个自然村落,也意味着离巴塘县城只剩下一站的距离了。
小坝村的名称和巴塘的地名来历有关。传说巴塘的先民寻找栖息地时,迁徙的人们赶着羊群经过这里时,头羊的叫声不大,并没引起迁徙人们的注意,可一到巴塘县城的坝子上,头羊的叫声特别响亮,让人们听出了头羊对这片土地的满意和依恋,于是决定生活在这里,并以羊声定地名,为“咩”,后谐音为“巴”。鉴于小坝村的羊叫声要小于在县城坝子上的叫声,因此得了“小巴”之名,也就是说小坝村是藏语“巴邛西”音译加意译的结合体。
它是由江巴顶、梦林顶、小坝村、林多、扎多、各拥贡、哈戈西七个自然村组成,因此“小坝村”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同时我发现,这段驿道上的地名由于书写者和记录者的不同,文献上所注地名也略有差别,例如:小坝村,不同的文献上就有小巴村、小坝冲、小巴冲等不同的写法,但都是同一个地方。
七个村子中的江巴顶、梦林顶、小坝村和哈戈西就顺次位于这条驿道上,其他三个村子都在小坝村上方的山中。小坝村面对喇嘛多吉山的正面,我们在县城看到巴塘八景之一的巴山积雪,就是这座山的背面,因为这座山面朝外而背对县城,所以巴塘人认为这座神山主要是护佑在外打拼的巴塘人,因此在外的巴塘人对它有很深的情结。当年我曾从这里出发,用了13个多小时翻越了这座高山到县城,这也算是年轻时一件引以为豪的事。
听扎多洛绒讲,当年小坝村和官府对接支差的有十三户,称十三差户,这十三户就要负责崩察木到小坝村这段路的运输任务和运输安全。但驿站的真正所在地不是在这个自然村,而是在另一个自然村,叫梦林顶。
过江巴顶就到了梦林顶,其意是在一片铜镜大的地方上。当年的驿站之主叫“梦林阿乃”,也是本地的头人,到巴塘的物资到达梦林顶后,由“梦林阿乃”派人到巴塘传信,巴塘的衙门或商行得信后,组织毛驴和骡子来驮运。
梦林顶通向崩察木的老路还在,古道旁还保存有一道石墻,苔藓在石上留下斑驳的印迹,可以看出这里很多年无人扰动,我在苔藓上那一圈一圈的印迹中穿梭,仿佛在解读一个久远的故事。
这段古道得以留存下来,是因为这里坡度较大,省道459从古道下方转了个弯向南,再转弯通向山中。
位于山下古道旁的这座藏房就是“梦林阿乃”家的房子,这座房没翻修前,门是朝后开的,正对着“梦林甲挂”,“甲”是一百的意思,“挂”有圈、围的意思,“甲挂”可理解为“可以圈很多牲口的地方”。由此可知这里就是当年马帮歇脚的地方。
村子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岔路口,西侧靠着巴曲河的这条路是通往巴塘县中咱镇的又一条线路。没通公路前,这条线路是县城通向中咱的一个重要通道,到了中咱,离得荣县和云南的香格里拉县就很近了。途中要翻越藏巴拉,它是红军长征时翻越过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垭口。从梦林顶的地盘大小和所处的位置来看,它成了两条线路的交汇点,我想这就是它成为驿站和马帮落脚点的真正原因。
过梦林顶二十多分钟就可到小坝村,在《巴塘县志》中对当时交通有这样一段描述:“由县治东行经小坝冲、崩察木,大朔山至义敦县界,计120里。”这句话给我们指明了当年出县的线路及里程。
最先听说小坝村是驿站时,我是质疑的,因为我1992年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小坝村村小任教,从县城到村小,当时不通公路,路上走快点,不耽搁,步行只需两个小时,就推想,这么短的路程怎么会设成驿站。
后来通过田野调查,才知道自己忽略了很多东西,一是给几十头上百头的牲口上鞍、上驮、卸驮、下鞍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二是每头牲口驮的货物都是上百斤,会走得很慢;三是当年很多的路段大多艰险难行,又是长途跋涉,因此驮队行进的速度也不会很快;四也是最重要的,牲口每天都需要补充能量,驮队要让骡马、牦牛等有吃草、饮水和休息的时间。因此驮运货物的驮队基本上是行半天,歇半天。这也是为什么把每个驿站间的里程定在30里左右的原因。
当年小坝村也是村小的所在地,只有十几户人家,事隔30年往事仍历历在目。如果说不忘初心,我的初心就在这里,就是想通过知识改变山里孩子们的命运,可以说高山阻隔的小坝村就是我记忆中的桃花源,有我最美的青春。我写的散文《在小坝村的日子》,再现了我在乡村的教育生活经历,其中四篇刊登在《贡嘎山》杂志2021年第六期上,并荣获《贡嘎山》2021年年度散文类优秀作品。感谢小坝村人当年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现在村民都已搬迁到县城里了,只剩下村中这些挺立的核桃树,还能告诉我们,这里曾是一个村落。
鹦哥嘴——东南第一关隘
从小坝村的哈戈西村到县城这一段路都处在高山峡谷中,东隆山和喇嘛多吉山就隔着巴曲河水耸立在两侧,形成了陡峭的地势,开凿出来的路大多狭小、险要,其中有两段路是从山岩上凿出来的,有上岩路和下岩路之说。
虽然省道459线沿着曾经的驿道修建而来,但有些路段因为通行困难,就把线路改在了巴曲河对岸,这让岩路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在上岩路段,看着上方突兀的岩石,就让人心惊胆战,走在上面亦是战战兢兢的,鹦哥嘴石刻中的《修路记》中有一句“徕者惴恐”,意思是让往来的人心生害怕,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路吧!
鹦哥嘴这一段是当年进出巴塘的一个重要关隘,因为地势状如鹦鹉的嘴而得名。今天我们在省道459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石刻群下的古道,是处在悬崖峭壁之上,极其险要,加上下面滔滔的巴曲河水,此处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险峻的地势,当年的驻藏大臣凤全一行在此被伏击,全部遇难就不难想象了。“凤全事件”由此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巴塘和周边地区历史的进程,在《川藏高原深处的石刻群》一文中已讲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说到这里,如果当年在鹦哥嘴题写《孔道大通》和撰写《修路记》的吴嘉谟先生穿越到今天,看到古道对面宽阔的省道459,老先生恐怕会惊掉下巴,他可能从没想到过,路能修成这样的宽阔平坦。可能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孔道大通竟然如此大通,百年之后国运如此兴盛,正是我之心愿,喜哉!赞哉!”
过鹦哥嘴,我们继续沿着东隆山脚向西北而行,转过一个山角就能看到虎头山了,当年山顶有一座碉楼,正对着山口,与三家村头和鹦哥嘴下方的碉楼互为犄角,封锁了进入巴塘县城的通道。
山脚下,柳树成荫的地方就是巴塘八大景之一的温泉沐浴,巴塘人称它为“茶却卡”。到了垂柳青青时节,巴塘人会呼朋唤友或携家人到这里洗澡、春游,可惜的是,由于水温下降,它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这里也是观赏巴塘八景之一巴山积雪的最佳位置,一百多年前,古人就有诗赞曰:“久被太阳熏不化,时时当作水晶看。”
此处离东隆山下的日登村也不远了,从村口一直到老街,以前都是用扁平的石块铺就的石板路,有些石头上能清晰地看到骡马留下的蹄印,我不知道,需要经历多少次的踩踏才能形成这样的印迹?
巴塘——茶马古道重镇
巴塘县城所在地为夏邛镇,古为白狼国地,1978年甘孜考古队在县城东北的扎金顶村发掘古墓葬九座,证实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白狼部族遗迹。
相传远古时期的巴塘为一片湖海,中有一条黑龙兴风作浪,为恶巴塘,让生活在此间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布达拉宫的一名高僧得知后,他派座下的金翅大鹏鸟前去降伏黑龙,大鹏到巴塘后又累又饿,反被黑龙偷袭,困在沼泽中,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大鹏忽然奋力一啄,啄死了黑龙,自己也力竭而死,其身化为巴塘的山川林木,也造就巴塘县城的地势状如大鹏,因此巴塘又名鹏城,“夏邛”在藏语中就是大鹏之意。
在改土归流前,它属土司管辖之地,但已建有军粮府,有粮务委员在此任职,还有绿营官兵驻防,说明清朝政府已经加强了对川边地区的管理,也让地处川滇藏三省通衢之地,有着地理优势的巴塘,开始活跃在川边,不仅促进了人员和物资的频繁流动,也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发展,讓它成为了茶马古道重镇。
从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二百多年间,这里先后建有关帝庙、清真寺、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这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巴塘不得不说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也是罕见的。
如今除关帝庙外都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是涉藏地区最早修建的关帝庙,巴塘人称为格萨拉康,也就是格萨尔王庙,1727年开始修建,历时37年才修建完成,它见证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也是这条川藏驿道所起到的作用之一。如今,我们仍能从残存的壁画、雕镂、梁下的龙头和鸱吻上,感受到当时庙宇的气派;除此之外还有1904年建立的官话小学,是巴塘县人民小学的前身,据说是涉藏地区第一所百年老校;1938年建成了涉藏地区唯一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广场;1942年修建了涉藏地区唯一的抗战纪念塔;1949年建立了涉藏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巴安地下党”;还有出名已久的巴塘苹果,是1911年经传教士引种在县城的架炮顶,引种时间仅次于山东烟台。种种迹象无一不在述说着巴塘的包容与开放。
古镇上的老街还有一些房子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据史料记载,1727年时就有来自川、滇、陕的客商在这里经营,最多时有八十家汉商,藏语称为“葱巴甲且”,已成为巴塘民间的固定称谓,关帝庙中也有相关记载,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当年作为边地的巴塘古镇上这条老街的繁荣景象。
老街东西向,300多米长,两边有很多小巷子,将夏邛古镇上的四个村子——泽曲伙、拉宗伙、坝伙、孔打伙连成一片。小时候,这些巷子是我和伙伴们追逐打闹的最好地方。以前老街两边的建筑融合了好几个民族的建筑风格,只是现在不多见了。
如今老街上有一组茶马古道的雕像,有骡马组成的马帮,有至此的洋人,还有撑着牛皮船的船工,述说着曾经的故事。
街口有两棵高大粗壮的并蒂槐,也不知生长了几百年,比旁边的七层楼还高,依然郁郁葱葱,这样的槐树在县城中还有七棵,它们是巴塘活的文物,是巴塘高原江南风貌的代表,也是巴塘灿烂文化的一部分,见证着老街的历史。
夏邛老街作为川藏驿道巴塘段的中转站,不仅是往来人员的休憩地,也是货物的集散地。因此不管到康定、雅安、成都还是到昌都、拉萨,起点都在巴塘夏邛古镇这条老街上。但大型的马帮是不会歇在古镇上的,只有到郊区才能为几十上百头的牲口提供足够的草料。
而今的巴塘县城建设得越来越美,2020年、2021年巴塘连续两年荣获甘孜州最美县城称号,看,五月的巴塘,在月季花的装扮下越发美丽。
南门——巴塘城垣的见证
夏邛古镇作为进出西藏的重要驿站,历史上,因军事防御修建了城门,通道设于城楼下。据《巴塘县志》记载:“1912年4月,藏军进犯川边,顾占文率众垒卡御敌,连接民房,镶以墙壁,又建四门,此为巴塘形成城垣之始。”
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一样,夏邛镇也以巷子为特色。老街可经泽曲巷、小南巷、曲学巷、孔打伙下巷、坝伙巷通向南门。其中,孔打伙下巷离南门最近,直走便达,大队骡马也可以轻松通过。
南门,也称南大门、老南门,巴塘藏语称“敲赤”。它是在原址上重建的,已成为巴塘的地标性建筑,是巴塘人的集体记忆。站在门下,近观远眺,仿佛还能听见驮着茶包的骡马穿城而过的叮当铃响。虽然它比不上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城门高大、雄伟,但看到它,却能让人在史海钩沉,心潮澎湃。
根据白尚文先生于1942年前后撰写的《巴安县县志资料初集》记载:“城分六门,东为中山门,西为中正门,南为建国门、天祥门,北为复兴门、定远门。”书中还有中山门、中正门和一段城墙的照片,该书现存于巴塘县档案馆。
后听扎西次仁老人讲,其中的天祥门是小南门,定远门是小北门,最早东门又叫皇华门,西门叫度支门,根据这些门的位置我们也知道了当年县城的轮廓,只是这些名字已和我们渐行渐远。
南门作为巴塘仅存的一个城门,它见证了历史。当年的官员、商人和朝佛信众,还有马帮,都从这里出发,前往西藏。1950年,十八军进军西藏时,巴塘人民在南门欢送解放军出城,那年巴塘儿女用团结包子招待人民子弟兵,并积极支前,踊跃参军,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巴塘县档案馆还保存有一张老南门的照片,南门上方建有土碉楼,是守门士兵休憩的地方,小窗子作瞭望和防守用。门前的这条路叫“学撒腊”,1989年洪灾前仍是石梯,通向桥边,路面和老街一样,铺着大小不一的扁平石块,古色古香。桥边这片地也叫“曲科上卡”。当年沿河北岸这一带都有水磨房,形成的村落也因磨房而得名,称为“曲戈西”,分为上磨房和下磨房。
古镇上的人视巴曲河为母亲河,时光荏苒,它依然奔流不息,水磨房却已不复存在,成为名副其实的“水磨乡愁”。
这里最早建有一座简易木桥。1719年,岳钟琪进军西藏时重修此桥,后被命名为岳公桥。桥墩为石砌,桥面为木质结构,后破损,又在旁边新建一桥,叫团结桥,后因洪灾损毁。现在的桥为洪灾后重建,桥面抬高,与南门下的路面平行,既方便出行,又能達到防洪目的,“学撒腊”就此成为历史。
走过桥,我们沿“道冉呷”向西南而行。“道冉”就是桃园村,“呷”是藏语,水渠的意思,即“通往桃园村的水渠”。
一直到原巴塘园艺场门口,这里是百年华西医院的遗址,里面种植的苹果多为美国传教士带来的老品种,现为夏邛镇卫生院。再一路向南,过桃园子、茶树山,可到“枯优腊”。
“枯优腊”——扼守金沙江的险关
在桃园村,有巴塘八景之一的桃园可以赏花,还能看到曾经的驿道。听洛布老人讲,沿驿道向南翻过“谢玛腊”,经茶树山的“枯优腊”就可以看到金沙江了。距离古道西侧一百多米就是国道318线。
如今知道“枯优腊”这个地名的人越来越少了,当年却是南行西渡前的一个重要关隘,巴塘民间还有很多关于“枯优腊”的传说,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它的故事。
“枯优腊”所在的山谷中有个村子叫纳西布,一个宁静的小村庄,静谧美丽。听瓜瓜老人讲,进村这条道路,以前也是通往“枯优腊”的路,只是原来的山间小道,变成了今天的通村公路。
村尽头那个陡峭的山坡就是“枯优腊”。“枯优腊”是藏语,“枯优”指杜鹃鸟,“腊”为坡之意。当年可能是听到谷中“布谷、布谷”的鸟叫声,就以鸟名来命名此坡。
听村里人讲,未到坡顶有块小草坪,因为路陡难行,人们走到那里都会停下来稍事休息,喝口小酒,因此得名“穷通德顶”。坡前的山谷中有一条小溪,流水潺潺。
到达坡顶前可见一块巨石,石头已从中间开裂成两半。从这里回望巴塘县城,可以看到县城的一角,据说当年离开家乡去西藏的人,走到此处会回首再看一下故乡,想想就要看不到故园了,有的人会当场失声痛哭。回乡的人到这里也因马上要见到亲人而激动不已,或因近乡情怯。
从巨石旁走过就可到坡顶,也是“劳栽”的所在位置,“劳栽”可译为鄂博,意为山顶插有旗杆的石堆。
藏族人到达山顶时,都会高喊“啦索啰!啦索啰!”表达越过山顶的喜悦之情,并会在鄂博上放两颗石子,祈祷平安。
巴塘有句谚语就出自这里,“我愿是杜鹃坡上的鄂博,来来往往的客商都要向它祈愿。”表达出行之人祈盼平安的强烈愿望。可惜的是,前几年修路时“劳栽”被毁。
朝前走,会看到金沙江与巴楚河在远处的山脚下交汇,后来沿河修建了318国道,从县城到交汇处有9公里,大家就称那里为“九公里”。
江对面便是西藏地界。左边这个山坡就是“角牛次顶”,依稀还能看到一条小路,当年就是通向牛古渡的路,县城至竹巴龙的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后,这条路也就少有人走了。
这里远离县城,又是进出巴塘的必经之地,无战事时,这里也没了驻军,就成了土匪打劫的理想之地。据说打劫对象多是单身和人少的客商,因此到西藏结伴而行或依附马帮同行是最好的选择。
而因被打劫创造出一句谚语,以前是闻所未闻的,我也是听到这个谚语,才关注到“枯优腊”的。相传有个人在家无事可做,就想到巴塘县城去逛一逛,母亲因为担心路上不安全劝他不要去,可他执意要去,结果一到“枯优腊”就被土匪打劫,此时的他,后悔自己不该想到巴塘去赶集,同时想起母亲的话,这句谚语就脱口而出:“东想西想到巴塘去赶集,到了杜鹃坡却想母亲。”
站在原来的鄂博所在地,像处在马鞍的鞍座上,两边的坡就像前鞍桥和后鞍桥,亦可称为南坡、北坡,两坡之上和西面的“角牛次顶”上,当年各有一座碉楼,当地人称为“玛宗”,即军事用碉楼,供驻守的官兵瞭望、休息和防守用。
《巴安县县志资料初集》上也有记载,说茶树山有险可守,我想指的就是这儿,三座碉楼形成犄角之势,封锁了金沙江一带进入巴塘县城的线路,可惜岁月流逝,三座碉楼早已没了踪迹。
而“枯优腊”正对着的小山坡上还有一个土碉,至今可以见到它的残垣,疑是保护水源的,或作为策应位的碉楼,不知山谷中的那条小溪,可还记得当年取水的士兵?
“枯优腊”作为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也曾为戍边要地,以及它带给人们的那浓浓乡愁,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讲讲它的故事。
再往前看,是苍茫的横断山脉,沙鲁里山和宁静山相对峙,两山夹一江,山一程,水一程,跋山涉水的艰辛,也只有这山水能见证。
牛古渡——“黑依曲卡”
巴塘人称金沙江和巴楚河交汇处为九公里,金沙江作为长江的上游,它是四川和西藏的天然界河。
沿金沙江向南行可到竹巴龙,中途有一个叫“勒哇”的村子,也叫水磨沟村,当年村前有个渡口叫牛古渡,它是川藏驿道上的一个驿站,属打尖、换马的尖站,而名称来历已无从考证。同时它也是一个渡口,过江便是西藏地界,最初的渡江工具是牛皮船或木筏,直到清末时才出现承载力更大的木船,新中国建立后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建成竹巴龙金沙江大桥,自此乘牛皮船过江成为历史。
渡口离水磨沟村还有一定距离,这里江面开阔,江水平缓,坡岸稳定,应该是选定这里为入藏渡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渡口上方有一栋两层高的房子,原是一座20根柱子的藏房,是渡口船工住的地方,当年的门是朝西开的,正对着渡口。如今的住户便是曾经的船工月登次仁的后人,同时代的船工还有甲阿称和益西次仁。听这家人讲,牛古渡藏语叫“黑依曲卡”,取自渡口上方的地名“黑依”。
听村中人讲,在河边的白塔南侧,原有一棵大核桃树,需几人合抱,粗大的根系裸露在地面,渡江的船只停泊时缆绳就拴在其根上。前些年白格堰塞湖下泄时,该树被洪水冲走。
再看对岸的山非常陡峭,人们形象地称它为“西松日直拉”,意为通往西松贡如长刀般的陡坡。要到山顶时,依稀能看到一座白塔,当年人们翻山时就要从旁经过。
听格松次仁老人讲,就因为路陡,有谚语这样说:“翻越西松贡如长刀般的陡坡时,即使是恩深似海的父母也难以顾及。”来形容难行。村中还有相对的一句:“翻越西松贡如长刀般的陡坡时,即使是背负父母翻山也难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形容世间之事没有比父母之恩更大的。
既然难行,为什么又会选择这里作为渡口呢?据《卫藏通志》记载:“巴塘至昌都,计有两道,其一为宁静大道,其一为贡觉小路,皆岳大将军西征时所开。小路较捷,而须野宿多日,不宜安设台站,故以宁静大道为官道,然须过乍丫,乍丫民风犷悍,多劫匪,故官商往来,由小道亦不少。所谓小道,系自巴塘至40里之牛古渡分路,渡金沙江,上山行,30里至西松工,为一小村……经江卡境,而至贡觉。”宁静和江卡指今芒康县,乍丫即察雅县。由此可知当年到西藏,从牛古渡过江的人员也是很多的。
这和格松次仁老人讲的相一致,他说到拉萨,有一条大路,也就是我们说的官道,走竹巴龙一线,经芒康、察雅一线到昌都。还有一条小路,就是从牛古渡过金沙江上山到西松贡村,从贡觉一线到昌都。
据此知道从牛古渡过江为捷径,捷径在藏语称“牛郎”,也叫“牛古”,因此推测,当时可能称此渡口为“牛古曲卡”,“曲卡”为水边,引申为渡口,后官方译为牛古渡,民间沿用此名,慢慢地“牛古曲卡”就无人提及了,不过这仅是个人猜测,不足为凭。
牛古渡作为入藏的渡口和驿站,也是十八军进军西藏时一个重要的渡江点,《巴塘县志》也有记载说:“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南线支队由茶树山、牛古渡、足的贡、竹巴龙胜利渡过金沙江。”这里的茶树山和足的贡两地值得商榷,因为茶树山村处在巴曲河东岸,需过河翻过象鼻山才能到金沙江边,茶树山在此是否是笔误?或是从茶树山坐船经巴曲河入江也未可知。而巴曲河和金沙江汇合的地方正是象鼻山鼻端的位置,如象鼻伸入江中喝水。听贡布老人讲,足的贡应该处在象鼻端金沙江西岸的村子,属于西藏地界,写从那里渡江也不知什么原因?还是因东岸没有地名,就借西岸之名?
十八军到巴塘后,巴塘人民积极支前,而渡江用的船只,本地的木匠参与了建造,县城亦有多名木匠到江边来支援建造,在这四个地方共造大船5艘、小船20艘、牛皮船50只,为顺利渡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听村中老人讲,大船可同时载二十到三十匹骡子,其运载能力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相当可观的。
同时这里也是当年平定叛乱的战略要地,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里都有一个排左右的解放军驻守,当地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属四团二营的。
随着竹巴龙金沙江大桥的建成,这里又恢复到最初的宁静。牛皮船也随着橡皮船的出现,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两岸高山依旧,江水奔流不息,牛古渡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竹巴龙——川藏咽喉
过牛古渡,继续沿金沙江南行,可到竹巴龙,它是四川進入西藏前最后一个驿站,也是这一线进入西藏的主要渡口。
竹巴龙为藏语音译,意为“船民居住的村庄”,据此可以推断,竹巴龙就是当年的驿道上因为渡江需要而形成的村落。
《巴塘县志》记载:“竹巴龙解放前系川藏咽喉,古为藏京古道要冲。”如今,它依旧是交通要道,是四川联系西藏的重要窗口门面,也是珍稀动物矮岩羊生活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村子下方的江边,就是当年的渡口所在地,当地人称“扎曲卡”。离岸边不远就是船工居住的房屋,均为一层,听住在江边的尼玛说,他小时还看到过,涨水时,水会漫过房基,从石头缝中流进屋里,却不会冲垮房屋,大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以前过江没有桥,人员和物资都是靠牛皮船运送过江,当地人还记得运送的物资有茶包、盐和红糖等,如今很难看到这种运输工具了。在巴塘县档案馆,我找到70年代由尼玛老师拍摄的一张照片,留下了船工用牛皮船送赤脚医生和一名学生渡江的影像。要感谢拍摄者,让我们今天能有幸一睹牛皮船的模样。
曾当过船工,现年85岁的贡布老人讲,这种牛皮船需要四张牛皮才能缝制出来,缝制用的线是牛尾巴上的长毛,骨架为当地一种称为“次日”的硬杂木。缝好后在牛皮相连接处还要涂上松脂,防止漏水。老人还说划桨时要由前往后划出弧形,有一定的技巧,不然牛皮船就会在原地打转。一人过江时,还得在船尾放一块大石头,防止头重尾轻导致翻船。
而木筏是用几根或十几根直径在十八厘米左右的圆木拼接,再用绳索绑好就可用于渡江。但牛古渡和竹巴龙两个渡口主要以牛皮船作为渡江工具,木筏一般是远离渡口的村落在使用。
到了清朝末年,官府招来八名雅安的船工匠人到竹巴龙,这些工匠带来了制作木船的技术,在竹巴龙制作木船,并用木船摆渡,于是竹巴龙渡口,在牛皮船和木筏的基础上,有了稳定性更高、承载量更大的渡江工具。
这些船工后来都在这里安家,如今还有七名船工的后人生活在这里。村里人还记得称呼他们的子辈时,会在名前加个“甲”,如甲仁、甲白登、甲旺堆、甲朗吉、甲尼玛等。“甲”就是汉族之意,从中可以看出藏汉两个民族在竹巴龙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相互通婚融合的一个过程。
1964年竹巴龙金沙江大桥竣工,渡口停渡。1989年大桥因地震基脚下沉停止使用,在其南侧又修一大桥,2018年10月13日,白格堰塞湖下泄,洪峰过境,两桥被冲毁。
如今竹巴龙的江面上,气势恢宏的新桥横跨金沙江,交通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作为进入西藏的门户,竹巴龙依然是318线连通金沙江两岸的咽喉要塞之地。
川藏驿道上的驿站三坝、大溯塘、崩察木、小坝冲和牛古渡从无到有,又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它们所起的作用,却定格在史书间,让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但作为四川西大门的巴塘县城和为川藏咽喉的竹巴龙则延续着曾经的辉煌。
一百多年前,古人将“孔道大通”、“竺国通衢”写在巴塘县鹦哥嘴的石壁上时,希望实现交通的通畅。如今,不仅在道路上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省道459、国道215、国道318让我们无所不至;在交通工具上也早已远离了马背牛驮的时代,高原上很多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小车。再过十年,巴塘人在家门口上高速、坐高铁也将会变为现实。
驿站的消亡,道路的变迁,古今的对比,让我无限向往更加灿烂的明天。
编辑导语:这篇历史文化散文行文逻辑谨严,内容有史有实有据有境。文中所引用资料详尽而扎实,不同年代的地方志书史籍资料为依据,穿插着当地民间传说、谚语和当事人的讲述,杂以作者的实地考察感受和生活记忆,这些信息互为佐证,将巴塘古驿道的前世今生梳理得脉络分明,通过对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等元素的合理运用,还原出了古道立体鲜活的岁月足迹。
责任编辑:子嫣
汪涛,笔名孔打布吉,四川巴塘人,七零后。2011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西藏文学》《贡嘎山》《甘孜日报》和《巴塘文苑》等报刊杂志。从小喜欢历史文化,故倾向于故乡巴塘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书写,在相关题材征文比赛中屡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