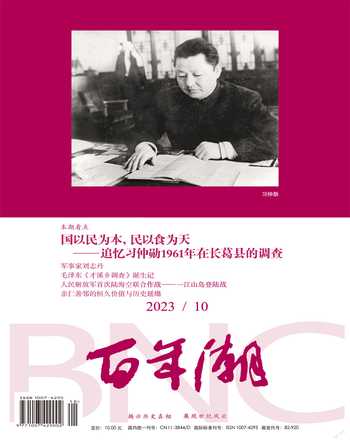亲仁善邻的恒久价值与历史延绵
2023-11-28书遁
书遁
编者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给予精辟阐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也是新征程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和必须深入研讨的重大课题。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且特意做了一些列举,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同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等。这实际上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炼的十大代表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名词高度一致,且指向性更为明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举出的中华文明十个关键理念即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均意涵深厚、流播悠远、影响巨大,可视为体现中华文明核心智慧的标识性概念,需要细加辨析。本杂志社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组合作,特邀十位专家,围绕十大理念逐一进行深入解读,以期说明其古典涵义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彰显恒久智慧和理论光辉。本期刊发的《“亲仁善邻”的恒久价值与历史延绵》是本系列文章收官之作。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句古训,闪耀着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处世之道与智慧光芒。在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悠久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可以说,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理念的承继与拓展。
一
“亲仁善邻”,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所著《左传·隐公六年》,文中写道:“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具体而言,这一段史实是记录郑庄公攻打陈国的文字中插叙的一段往事。在此次郑国攻陈之前,陈国与郑国产生过冲突,郑庄公主动请和,但陈桓公不同意。陈桓公的弟弟,同时也是陈国执政大臣的五父,有意促成和谈、消弭战祸,因此出言规劝。但陈桓公却很轻视郑国,认为不足为惧,拒绝与其修好。陈桓公对郑国持轻蔑态度也是有原因的—当时郑国与周天子的关系比较紧张,而陈桓公却很受周天子赏识。此外,从军事上讲,郑国只不过是一个“数百乘”之国,实力有限,陈桓公并不担心郑国会进行报复。但是自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之后,郑国接连发动战争,隐隐有称霸之势,这是陈桓公所未料到的。他的短视造成的后果就是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传文所记载的“郑伯侵陈,大获。”五父当年的劝谏虽然没有奏效,但他提出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句话却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深入人心的政治箴言。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和内部纷争不断,战乱频仍,这也就是孟子笔下所描述的“春秋无义战”的情形,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亲仁善邻”就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迂腐。即使如此,春秋时期仍有一些政治家坚持践行“亲仁善邻”的理念。
比如秦穆公在处理与晋国关系的过程中,就不念旧恶,解救晋国的危机。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冬,因为粮食歉收,晋惠公向秦国求购粮食。此时的秦晋关系非常微妙,两国国君虽有姻亲,但又互有矛盾。秦穆公曾辅助晋惠公夺得王位,但晋惠公却拒绝兑现之前许诺让给秦国的土地。在考虑是否援助晋国时,秦穆公接受了百里奚“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的建议,决定出于人道救济遇到天灾的邻国,挽救了晋国百姓的生命。
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子服景伯也坚持“亲仁善邻”的外交理念,坚决反对把持鲁国朝政的季康子攻打邻国邾国的主张,理由是“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在子服景伯看来,邾国是一个小国,他不愿意看到鲁国以大欺小,而是希望两国之间能够遵循“信”和“仁”的准则,和睦相处。攻打邾国,是无德之举,会给自身带来灾祸。
在《左傳》的叙事世界中,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事情层出不穷,但“礼”“德”“仁”“敬”等关乎秩序的修辞依然能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纵使过了2000多年,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人对建立理想道德秩序的渴望和追求。“亲仁善邻”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日,这句话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那就是以和平、平等的方式,发展国际关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睦邻友好的精神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互帮互助,以创造出更加丰硕的文明成果。
虽说“亲仁善邻”的明确主张问世于春秋时期,但倘若追根溯源,其萌芽可以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从尧舜以下,中国便形成了“先王之道”并一脉相承,其实质是“礼道”。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剪灭殷商、封邦建国,到了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制礼作乐,史称“周礼集夏商周三代礼乐之大成”,举凡政治、祭祀、战争、教育、饮食、婚俗等无不浸润礼乐规范,因此构成了独特的中华礼乐文明,称之为礼乐社会。
“亲仁善邻”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周礼精神的成果,可以归结为周礼在春秋时期的延续。“亲仁善邻”当然也是春秋时期邦国外交实践和思想的成果。当时政治失序但文化传统犹存,列国的邦交还笼罩在浓厚的礼仪氛围之中,邦交礼节基本上沿袭周礼,遵循着“贵贵”“尊尊”“亲亲”以及其他基本道德观念,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不能完全逾越。虽然霸主替代周天子成了维持秩序的盟主,但显而易见整个周礼体系的骨架并没有解体。列国在争霸斗争中仍然在寻求着合法性或者说最大认同,因此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列国在外交思维上依然标榜以德为本,反对不仁、不义、不信、不忠、弃亲等。“亲仁善邻”就是顺应时代变革而出现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道德原则。
二
综上,亲仁善邻,是中华民族重视和睦邻里关系、树立可信赖的外部形象、构建良好地缘关系的人际智慧与处世之道的重要体现。进而言之,理解“亲仁善邻”,需要从“亲仁”和“善邻”两个层次去认识。“亲仁”和“善邻”,都不是空洞的理念阐释或观念感受,而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一定要付诸真实的“学而思”实践。实质而言,“亲仁”是建立“善邻”关系的基础。“仁”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之一。“仁”是一个可以无限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对人的真挚感情和责任感,是可以从爱最亲近的人出发,真诚地去關怀、帮助、成就人、成就整体公共利益的“知仁”和“行仁”的统一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仁”或“仁德”是一切人伦关系的伦理之德的集中体现,是可以由“爱亲”之“仁”出发,成为“仁人”(即有仁德之人)的道德之本或基始。孔门弟子有子解释说:“君于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亲仁”有至少两层意涵,分别代表着“亲仁”的两种基本对象。“亲仁”的第一层意涵,是指亲近有仁德的人。《礼记·中庸》指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尽心下》也指出,“仁也者,人也。”“亲仁”之“仁”的重心落在了“人”之上。它既包含基于“泛爱众而亲仁”,将别人当作人;又包含基于“克己复礼”,把自己当作人。通过“泛爱众而亲仁”,超出一家一姓、一宗一族的伦理界限,将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给以同情与关心;通过“克己复礼”,出于人格的觉悟,发挥人的道德自觉,自我约束自己,是一种“由己”而非“由人”的“为仁”自觉行动。“亲仁”的第二层意涵,即亲近“仁德”这种德性。《易经》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亲近“仁德”,既可通过“里仁居”选择有仁德风尚的安居之所实现,更需要“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努力追求去达成“德日进,过日少”。在传统儒家看来,一个人如果立志于仁德,其本性有仁,就会有善念,就会向善、择善、行善、至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会真正地喜欢人、憎恨人,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且亲近“仁德”,将“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礼记·中庸》)。从“亲仁”的两层意涵来看,其本质上是希望由“亲仁”来“安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坚守仁德而不动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以动态的、不懈不止地亲近和走向“仁”,来提高与完善人,实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亲相爱,达到天下有道的目标。《左传·隐公六年》所记载的陈国公子五父劝诫陈国国君(陈桓公)同意郑国请求,两国交好,并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但陈桓公听不进去,结果导致国难,体现的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这一历史典故中,“亲仁”得以与“善邻”互文,进而揭示亲善友爱邻(国)人的重要意义。由“亲仁”而起,“仁”得以具体化、一体化地融入各种人伦关系之中,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宗族相助、家国一体,塑造中华民族温良敦厚、勤劳善良、反求诸己、注重内省、推己及人、成人之美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文化最独特的境界和魅力所在。
“善邻”从原则性和务实性相统一的角度体现“亲仁”理念的实践策略与方法智慧。“善邻”崇尚“仁”,倡导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立场和态度,是一场基于平等性基础之上的关于“责任”与“尊爱”的有机统一。《论语·季氏》中记载,季氏家臣冉有、子路二人去谒见孔子,告诉孔子说:“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听后,责问冉有为什么要攻打与鲁国共安危存亡的藩属。冉有却认为,颛臾城墙坚固并且离季孙分封地近,要提前将此地占领,以免留下祸害。孔子批评冉有:“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孔子看来,国家财富平均、境内和平团结,不需武力征伐小国就会招致归服。若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使其顺服。自古以来,中国人始终认为家族和国家的昌盛,从来不是通过对外战争抢夺攻伐而来,而是施以仁爱、道义于邻人和邦邻,讲信修睦、修文服远。隋唐时期,各国纷纷遣使来华,求学、经商、游历、进行宗教交流等。这一时期,正如李白诗中所展现的万国来朝盛况,“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善邻”的原则性和务实性,还体现在其并不是一味地迁就和忍让。西汉名将陈汤曾上书汉元帝:“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昭示着中华民族那种内嵌和融入骨子里的强大和自信。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中华民族虽崇尚正义,从不欺负、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和族群,但也不畏强暴,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行王道之必要、卫和平之需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古往今来,正是从“善邻”的导向出发,中国人始终主张和合与共、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坚持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国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三
就人类社会而言,情感互动是自然而必然的,情感认同是共同体的基石。中华民族的先贤从事物间的感应窥得社会和谐的天机,并加以推广运用,这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独特资源的体现。孔子弟子司马牛忧愁自己缺少兄弟,子夏劝慰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夏的话因为记录在《论语》中,影响极广。以仁为本,以情为基,情感相通,由近及远,当亲缘关系突破地缘关系,建立在情感相通基础上的亲情社会模式便可以延伸扩展到全天下,逐渐让陌生世界化为天下一家。这是儒家的情怀和理想,是中国人的美好信念,也是中华文明的卓越精神之一。可以说,亲仁善邻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与人为善,也使得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继承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精髓。5000多年来,中国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完成“凿空之旅”,开辟伟大的丝绸之路;还是郑和下西洋,打通海上贸易通道,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远播海外……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增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增强信任,减少疑虑。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主张争取和团结新兴的独立民族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制定并推行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积极努力争取与周边邻国建立相互信任的外交关系,形成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以打破美国编织的反华包围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实现更好的发展,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睦鄰政策,制定了“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对外战略总目标。中国的睦邻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强调主权平等,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以及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与周边国家合作与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来指导21世纪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工作,共筑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
同时,这一创新性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由此,“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的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站在聚焦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探索当代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倡导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更加重视。2013年10月,中国首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同时,他还提出“亲诚惠容”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赋予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全新内涵、丰富内容和时代意义。
放眼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在很多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典故,来表达中国的外交理念。2014年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论语》有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正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党所应有的气度、格局与风范。
古往今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合作才能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亲仁善邻”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亲仁善邻”流淌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内敛与厚重,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宽厚与包容,是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和兼收并蓄中所形成的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更是长治久安、繁盛昌隆的国之宝策。中华文明将“亲仁善邻”等思想文明作为价值共识和族类认同标志,以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中国智慧开创了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明建构传统,提供了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各国相互依存度持续增加,只有尊重、包容不同文明的存在,坚持互利合作,纳百家优长,集八方精义,才能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