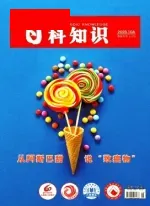夏威夷海岸:檀岛魅影
2023-11-25金文驰
金文驰
提到夏威夷,人们恐怕首先会想到椰影摇曳、水清沙幼的景象。其实这仅是夏威夷群岛海岸带万千面貌的一种,在漫长的海岸带上,精彩难以胜数:海水如喷泉般从地面的洞口直冲天际,火山岩在海蚀作用下形成了一座立于海上的天生桥,曾经烈焰熊熊的火山口如今似海边的一顶皇冠,20世纪初建造的防御工事则高踞于“皇冠”之上……就让我们前往夏威夷群岛中的毛伊和瓦胡这两座岛屿,领略一番海岸带的魅力吧!
怀阿纳帕纳帕:玲珑的“海岸盆景”
我们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乘机,直抵毛伊岛北岸的卡胡卢伊。毛伊岛在130万—80万年前形成,是夏威夷群岛中第二年轻的岛屿。岛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偃旗息鼓”的火山,不再喷发。西边的一座较为古老,在流水的长期侵蚀下,如今最高峰海拔仅有1764米,占地面积也小,人称西毛伊山;东部的哈雷阿卡拉海拔高达3055米。卡胡卢伊就坐落在两座火山交界的低地上,在暮色中望去,卡胡卢伊左右都是高山,气势雄浑。
我们的第一站是位于毛伊岛东北部的怀阿纳帕纳帕州立公园。夏威夷群岛所在地盛行东北气流,这些饱含水汽的暖湿气流为岛屿东北部带来了大量雨水。由于有哈雷阿卡拉火山的阻挡,毛伊岛东北部的降水量极大,数不胜数的溪流在山体上雕琢出了条条深陷的沟谷。虽然怀阿纳帕纳帕距卡胡卢伊仅80千米,沿途也不需翻越高山,但由于公路横跨众多沟谷,蜿蜒盘绕,即使一路不停地开车也需至少两个小时才能抵达。
从卡胡卢伊出发时还是阳光灿烂,进入哈雷阿卡拉的迎风坡后便阴云密布。沿路瀑布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高度超过20米的上怀卡尼瀑布。它从沟谷中分两段跌落,下段分为3股,水量从左至右递减。沟谷中温暖湿润,植被葳蕤,姜科的瓷玫瑰约有二层楼高,令人惊叹。不过瓷玫瑰并不是这里的“原住民”,而是外来物种。这时,空中落下了雨点,还是赶紧上路吧。

好在怀阿纳帕纳帕仍旧阳光灿烂。这里地处一个小海湾中,海风习习,虽然日头正高,但在树荫下静坐还是觉得太凉了些。循着阵阵涛声,我们向海边走去。小径明显下行,太平洋终于露出了真容,椰子等热带海滨的典型植物也闯入了眼帘。这一带为礁石海岸,基岩是哈雷阿卡拉火山曾经喷出的熔岩冷凝后形成的玄武岩,这种玄武岩含硅质较少,颜色黝黑。我们向一个伸入太平洋的小半岛行进,脚下的小径比海面高出了两三层楼的高度。在这里行走可要留点心,不仅仅是因为高度,而是在浪潮长年累月的冲蚀下,海平面附近的玄武岩被淘蚀出了许多空腔,在地理学中它们被称为海蚀洞。一些海蚀洞的顶部已塌陷,在小径旁留下了不少形状、大小都不规则的开口,从中传出沉闷的浪涛拍击声,别有洞天。
海蚀作用不仅塑造出了海蚀洞,还留下了十几根海蚀柱。顾名思义,海蚀柱主要为柱状,几乎全部是由海水沿岩石的两组节理(岩石的裂缝)冲蚀而成。它们有的出水仅一人多高,有的有3层楼高;形态嶙峋,没有定数,有的似一头巨象,有的如石猴观海……不少海蚀柱上还生有翠绿欲滴的天然植被,真是绝妙的“海上盆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半岛西侧回望海湾,蓝天、绿影、碧海、白涛、黑石……好一幅别具夏威夷特色的海岸画卷!

草海桐科的草海桐在这一带的礁石上颇为常见。这种灌木广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热带海岸,抗风、抗旱、耐盐碱,是热带海岸的先锋物种,并可在大多数植物望而却步的海岸礁石环境中成为优势物种。草海桐可高达4米,由于缺乏土壤,这一带的草海桐普遍不及腰高。它们的叶片稍呈肉质、倒卵形,终年开花,花朵洁白,花瓣有5枚,呈扇形排列,看起来似乎被人生生摘除了花朵的另一半。
在浪涛声中还夹杂着隐隐鸟鸣,一些灰黑色身影在海面上掠过,立于一根较大的海蚀柱上。沿小径走到一处海崖边,这里是距那根海蚀柱最近的地方,可以俯瞰一大群鸥科鸟类—玄燕鸥。这根海蚀柱不仅是一座孤岛,而且下部陡峭,即使有人乘船靠近也很难登岛,看来玄燕鸥选择在这里安家是很有道理的。三三两两的玄燕鸥在海蚀柱上栖息,它们体长约36厘米,翼展可超70厘米,不过由于距离较远,它们看起来体形显得不大。顾名思义,玄燕鸥浑身呈灰黑色,头顶为白色,这种体色和落满白色鸟粪的黝黑玄武岩背景几乎融为一体。玄燕鸥分布在全球熱带和亚热带海域,尤以太平洋海域为多。它们主要以鱼类和乌贼等海洋动物为食,和褐鹈鹕等扎入水中觅食的鸟类不同,玄燕鸥觅食时贴着海面飞行,用长喙快速衔起水中猎物。

将目光放得更远些,东北方向的海边出现了一座天生桥。桥体的长度远大于高度,显得颀长俊秀。桥的一端连着海岸,另一端继续在海面上延伸,真是“长虹卧波”的真实写照。天生桥也是海蚀作用的杰作:在海平面附近的岩石被淘蚀后,上方的岩石还未崩塌,便有了桥的形态,是为海蚀桥。不过假以时日,桥体一定会坍塌。
这一带的不少海蚀柱上还生有一种枝叶细小而下垂的植物,可惜距离太远看不清种类。它们在海风中徐徐飘动,无疑为“海上盆景”增添了一抹灵气。虽然这一带几乎为礁石海岸,但海湾西部有一片四五十米长的沙滩。和常见的浅色沙滩不同,这是一处黑沙滩,沙粒源于被海水磨蚀掉的玄武岩。由于地处海湾底部,拍击沙滩的海浪劲道颇大,吸引了不少游人戏水。

纳卡勒勒:奇石与喷泉洞
在毛伊岛西北部,有一处名为纳卡勒勒的海角。这里以表面呈蜂窝状的石块、一块带有心形孔洞的岩石和一个喷泉洞而闻名。虽然纳卡勒勒距离卡胡卢伊仅30千米出头,不过道路比前往怀阿纳帕纳帕州立公园的更崎岖,车程至少需1个小时。这一带的环境明显比去怀阿纳帕纳帕州立公园的路途干燥,且越靠西部,植被越稀疏。
在公路旁停好车,走到可以俯瞰纳卡勒勒的山崖旁,这里高出海平面至少四五十米。突然,海边的礁石上喷起一股水雾,宛如巨鲸换气,那便是喷泉洞。和怀阿纳帕纳帕州立公园相比,这里更具野性,没有专门的小径。我们依地势在岩石上选择路线,向低处进发。这里的环境颇为干旱,看不到一棵树木,仅有稀疏的草本植物,且越靠近海平面越荒芜。这一路上,我们最后看到的植物是番杏科的多肉植物—海马齿,它极耐干热和高盐环境。

快接近海平面了,这里寸草不生,色彩稍浅的地面上突兀地冒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深色岩石,其表面多为蜂窝状,密集恐惧症患者看了可能会非常不舒服。这一宛如外星般的地貌还有一个有趣的英文名—Acid War Zone,中文译为酸战区,不过酸并不是这一地貌的雕塑师,海沫和风才是。海沫中的各种盐类加速了岩石的风化进程,使岩石中溶解度较大的成分分解得更快。这样的差异风化在岩石表面形成了小坑,常年的海风则如刻刀般将坑洞凿大,而岩石中一些难溶的成分则保留较多,构成了似蜂窝、如脑纹的独特形态。在更临近太平洋的地方,风浪对火山岩的侵蚀作用更为显著。一薄壁状岩石的两侧在风浪的侵蚀下越靠越近,形成了一个爱心形状的穿孔,堪称一绝。
正当大家醉心于这一奇景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原来是海水挟带着空气从喷泉洞中冲天而起,有两三层楼高,随即坠落在礁石上,让不少赤色的螃蟹“惊慌失措”。现在不是高潮期,“喷泉”气势还不算最壮观。据说在潮位较高或风浪较大时,“喷泉”可达5层楼高,站在附近能明显感到大地震颤。这一喷泉洞也是海蚀作用的杰作:一个海蚀洞的洞体在浪潮的侵蚀下常年处于高压状态,终于有一天,一处较薄的洞顶崩塌了,形成了孔洞。如今这一近圆形、直径超过1米的孔洞便是“喷泉”的喷口。虽然喷泉洞景象壮观,但颇为危险,只宜远观,切不可靠近。
钻石头火山口:地质与军事遗产
乘机离开毛伊岛,仅过了半小时,夏威夷首府火奴鲁鲁(檀香山)所在的瓦胡岛便出现在机窗右侧。一座几乎浑圆的火山口矗立在一片摩天大楼和沙滩右侧,这便是著名的钻石头火山口。驻足于火奴鲁鲁人潮涌动的威基基海滩,你几乎不可能错过钻石头火山口的身影,它俨然成了火奴鲁鲁乃至夏威夷的地标之一。从这里看去,钻石头火山口的山顶并不是平的,右侧较高,极似金枪鱼的背鳍,因此它便有了“金枪鱼海角”这一形象的夏威夷语名称。据说19世纪时,英国水手见其山坡上有闪闪发亮的晶体,以为是钻石,其实这些晶体不过是碳酸钙,但“钻石”一名沿用至今。
钻石头火山口海拔232米,是一座凝灰岩火山锥,虽然历经侵蚀,它依旧是美国该类火山锥中出露和保存最完好的典范之一。早在1969年,钻石头火山口便被列为美国国家自然地标,这类自然地标在夏威夷州仅有7个。除突出的地质价值外,由于钻石头火山口如巨人般俯瞰火奴鲁鲁,实乃地理要冲,因此大量军事遗产也留存在这一火山口中,如今成为鲁格城堡历史区的一部分。

驱车穿过一条很窄的隧道,我们便来到了钻石头火山口中。站在平坦的火山口底部,发现火山口的宽度远大于高度,因而整个山体缺乏伟岸之感。钻石头火山口的形成颇有意思,不过我们得先从它所在的瓦胡岛说起。和毛伊岛相比,瓦胡岛的年纪大了许多,后者于400万—250万年前随两座火山的喷发开始成形。此后,火山活动暂停了约130万年。而在约30万年前的一天,火山再次苏醒。这一次的喷发发生在海底,炙热的熔岩形成了大量质地细腻的火山尘和火山灰。这些火山尘和火山灰被喷到空中后落回地表,壓实固结成凝灰岩。据信,这一喷发过程耗时仅数小时,便形成了占地约1.4平方千米的钻石头火山口。由于夏威夷盛行东北气流,大量火山尘和火山灰向西南方向的下风处飘去,这也是为何钻石头火山口的最高峰位于西南沿的缘故。
从火山口底部到最高峰通有一条长约1.3千米的小径,沿小径上行,海拔升高了约171米。由于这一火山口位于瓦胡岛东南部的背风坡,降水较少,属半干旱气候,加之土壤瘠薄,植被主要由草本植物和灌木构成,树荫难觅。据植物学家推测,这一火山口曾被热带干林(分布于热带较干旱地区的森林类型,林木通常较为稀疏)覆盖,这种森林的树木密度较小,树冠高度也低,由于树冠不连续,因此难有浓荫蔽日之感。遗憾的是,由于破坏易、再生难,在全球范围内,热带干林是一种颇为稀有的植被类型,仅在夏威夷群岛上的少数地方还有残留。钻石头火山口中的夏威夷本土植物仅有锦葵科的小叶黄花棯等少数种类,目之所及的绝大多数植物都是19世纪以来引入夏威夷的外来种。豆科的美洲牧豆树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之一,这一原产于南美洲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智利等地的小乔木不仅生长迅速,而且寿命较长。它们在这里生长得颇为惬意,不少枝头上开着一团团的小白花,长长的荚果颇为醒目。我们一路上还见到了主红雀和家麻雀等鸟类,它们也都是外来种。
1904年,整个钻石头火山口被美国联邦政府购下,用于军事目的。从1908年起,美军开始在火山口顶峰修筑包括炮台在内的军事设施。我们所走的这条小径同样建于1908年,是通往顶峰炮台的必经之路。越接近火山口边缘,地势越陡峭,“之”字形盘绕的小径前方出现了74级水泥台阶。上完台阶,紧接着是一段长约69米的隧道。刚出隧道,便是一段更为陡峭的台阶,这次共有99级。气喘吁吁地爬完,又是一条深入山体的隧道,隧道末端并没有钻出山体,而是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圆柱形竖井的底部。这里便是顶峰炮台内部,炮台隐藏在山体中,共有4层,在1910年落成时算得上一项工程奇迹。以顶峰炮台为主体的防御工事在当时的功用是守卫火奴鲁鲁,不过这一防御工事从未在战争中射出过一枚炮弹。
竖井中有一处螺旋金属梯,登上52级台阶后,我们手脚并用地从炮台第三层爬出了山体,眼前豁然开朗。向南望,山脚矗立着白墙红顶的钻石头灯塔,珊瑚礁如同固体护城河拱卫着钻石头火山口。向西望,山脊上的碉堡映入眼帘,远处则是高楼林立的火奴鲁鲁市区。
站在钻石头火山口之巅,战争的阴云早已被游人的欢声笑语所取代。在笔者看来,如今的钻石头火山口防御工事正以另一种方式默默地守卫着火奴鲁鲁。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