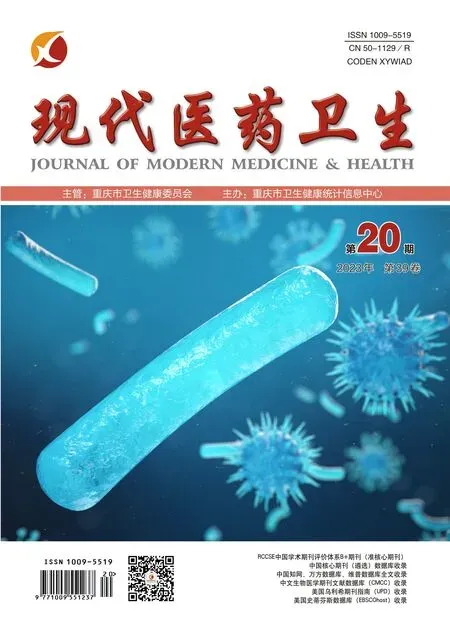肠道菌群及粪便代谢物与过敏性鼻炎的关系*
2023-11-23卢靖静综述董文婷纪鑫华审校霍金海
卢靖静 综述,董文婷,纪鑫华 审校,霍金海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
过敏性鼻炎(AR)又称为变应性鼻炎,是由变应原刺激引起的、免疫球蛋白E(IgE)介导的Ⅰ型超敏反应,AR的典型临床表现为鼻痒、打喷嚏、鼻漏和鼻塞,眼部症状也很常见[1],其作为过敏性炎症的一种,病情反复,发病率较高,各年龄段均有分布,是发达国家常见的慢性病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AR在低收入地区患病率逐年上升,现已逐渐成为全球性健康问题[2],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人AR发病率已达17%[3]。为缓解AR对患者工作和生活的影响,针对AR的治疗措施也在逐年更新,除避免接触变应原及一般药物治疗外,发展出了变应原特异性免疫疗法等[4]。对AR发病机制探究发现,AR的发生是T淋巴细胞分化从而导致辅助性T淋巴细胞1(Th1)/Th2、Th17/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比例失衡并释放特征性细胞因子所致[5-6],然而近年来有新的研究发现,肠和气道上皮细胞均来自相同的胚胎结构,其解剖结构很相似,且同属黏膜免疫系统,均能分泌包括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在内的黏膜蛋白,从而通过体液免疫共同在过敏性疾病中发挥作用[7],为AR发病机制、治疗方法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肠道菌群作为肠黏膜免疫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免疫系统疾病及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不言而喻,通过对其深入了解发现,肠道菌群及相关粪便代谢物失调可加速炎症因子释放,并导致肠道上皮黏膜屏障功能受损、免疫失调、内毒素及致病菌异位,从而加速AR的病程。现将近年来研究肠道菌群及粪便代谢物与AR的关系的文章综述如下,旨在为AR的研究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肠道菌群与AR的关系
肠道菌群是寄生在人体胃肠道的种类繁多的微生物,由此可见,主要包含四大类,分别为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包含了对益生菌(如双杆菌)、机会致病菌(如大肠杆菌)、有害菌(如产气荚膜杆菌)等[8]。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在保护肠道黏膜屏障、促进固有和获得性免疫的发育、免疫耐受的形成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来自肠道菌群的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及免疫模式识别受体[包括 Toll样受体家族(TLRs) ]之间的相互作用可通过调节免疫细胞的分化和合成细胞因子、防御素,以及免疫球蛋白等维持稳态和上皮屏障完整性,如脆弱拟杆菌可上调TLR2的表达从而诱导T淋巴细胞的分化和细胞因子的合成,TLR2和TLR4是维持上皮屏障完整性、保护黏膜免受急性肠损伤所必需的。同时,肠道屏障又通过TLRs调节为肠道菌群调节免疫提供了场所[9]。所以,TLRs被认为是肠道菌群、肠道屏障和机体免疫的交接点[10-11]。若肠道菌群组成发生改变就会打破耐受机制,TLRs与相关受体结合,启动相应信号传导,激活核因子κB,诱导过度的炎症,造成AR的发生。如ZHOU等[12]发现,与健康组比较,AR患者肠道菌群组成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存在显著差异。在门水平上,AR患者厚壁菌的丰度显著低于健康组;在属水平上,AR患者布劳特氏菌属、霍氏真杆菌组、罗姆布茨菌属、柯林斯菌属、多尔氏水平菌属、罕见小球菌属、Fuscatenibacter菌属的丰度也更低。VERHULST等[13]通过对过敏性哮喘的儿童肠道菌群分析发现,其肠道中艰难梭菌的丰度较低;由于过敏性哮喘的致病机制和治疗方案与AR相似,因此,肠道菌群对其产生的影响互相具有参考价值。
肠道菌群在黏膜免疫系统的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除上述路径外,肠道黏膜和肠道菌群之间的共生关系还具有屏障机制,可排除大多数细菌。有研究发现,AR患者上皮细胞细菌侵袭率高于非AR者,细菌侵入上皮细胞可破坏黏膜屏障功能,导致外源性病原体侵入;从功能方面讲,肠黏膜和鼻黏膜均属黏膜免疫系统,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共同具有免疫监视并唤起宿主免疫反应的功能[14-15]。因此,无论是内毒素还是外部环境中存在的致病菌均可通过侵袭失去屏障功能的黏膜免疫系统造成全身反应。
肠道菌群对AR的影响并不止于此,更多研究表明,生命早期健康的肠道菌群定植在建立过敏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机制上归因于先天免疫反应的差异,以及Treg数量和功能的增加[16-17]。如与剖宫产和配方奶粉喂养相比,婴儿接触由乳酸杆菌和链球菌组成的母体阴道和母乳可降低患过敏性疾病的风险;此外,生活在农业环境及有动物接触的儿童患过敏性疾病的风险也相对较低[18]。正常肠道菌群对免疫系统功能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肠道菌群失调对AR的发生、发展关系重大。因此,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恢复黏膜免疫等方式缓解AR症状,恢复患者正常生活,如口服益生菌或调节肠道菌群[19-20]、增强免疫的中药复方制剂等均能有效缓解AR的症状,也从侧面佐证了肠道菌群在AR病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粪便代谢物与AR的关系
2.1短链脂肪酸(SCFA) SCFA是通过肠道菌群发酵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产生的,拟杆菌、厚壁菌是参与未消化食物代谢的主要细菌群[21],也是SCFA生成的主要相关菌群。大量研究表明,SCFA不仅是肠上皮细胞能量来源,还能促进结肠环境的酸化,从而阻止病原菌的生长,并通过抑制组蛋白脱乙酰化增加转录因子叉头蛋白P3的表达、支持Treg的扩增并增加白细胞介素-10(IL-10)的产生等方式参与机体的免疫应答[22],是保证肠道健康的重要物质[23]。不同的肠道SCFA包括丁酸盐、醋酸盐等,在肠道中的功能及相关菌群各不相同,与AR的相关性各异:(1)丁酸盐能通过稳定特定转录因子、组装紧密连接蛋白和分泌黏蛋白保护肠腔厌氧,从而在维持肠道屏障功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粪杆菌、瘤胃菌科、玫瑰杆菌是已知的丁酸产生菌,CHIU等[24]通过对儿童鼻炎患者进行粪便代谢组学分析发现,粪便中丁酸盐水平与血清IgE水平呈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丁酸盐产量降低导致肠上皮屏障功能失调而加速了AR患者对过敏原的摄取及相关免疫反应,且丁酸盐对黏膜屏障功能的调节不止存在于肠道中,鼻黏膜屏障也受其调控[25]。(2)醋酸盐能协调肠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对T淋巴细胞进行复杂调节,从而影响下游的免疫反应,如醋酸盐浓度的改变能促进受到抗原刺激后CD8记忆T淋巴细胞释放γ干扰素[26];此外有研究证实了双杆菌(如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可产生醋酸盐和乳酸以降低肠道环境pH值,从而抑制有害菌和病原体的生长[27]。表明SCFA丰度降低对肠道环境和宿主健康是有害的,但不同的是,DE等[28]通过分析441名社区成年人粪便SCFA、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组成、肠道通透性发现,粪便中含有较高的SCFA反而会增加肠道通透性,且粪便中SCFA浓度与肠道菌群多样性呈负相关,推测可能是由于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相对丰度的差异所致肠道黏膜炎症降低了SCFA的吸收效率,增加了排泄率,但由于肠道菌群产物众多,且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因此,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探究。
2.2脂多糖(LPS) LPS是革兰阴性菌细胞膜中产生的一种有效的炎症分子,在人体肠道中大量存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肠上皮屏障作用,肠道内毒素不会对机体造成危害,但在病理情况下肠黏膜屏障被破坏,内毒素得以进入血液循环,其能激活肠上皮树突状细胞上的CD14跨膜受体TLR4,可将细胞外刺激信号传导至细胞内,进而激活核因子κB等从而诱导炎性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IL-6等)的产生,而这些炎症介质又会反过来激活机体内的炎症细胞通路,从而引发瀑布式的级联放大炎症反应,导致机体一系列的生理病理改变。肠道内高LPS水平也与动脉粥样硬化、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发生、发展高度相关,因此,粪便LPS已成为一种新的代谢失调标志物[29]。AR作为过敏性炎症疾病的一种,可直接由内毒素诱导发病[30-31]。对肠道细菌进行表征后发现,肠道内含硫细菌——脱硫弧菌被确定为重要的内毒素产生菌,大肠杆菌也与内毒素生成相关。SCFA和某些益生菌能共同作用减少LPS的产生并通过降低肠道通透性减少其入血,从而降低主动脉中TLR4、趋化因子受体7、趋化因子CC基序配体17、趋化因子配体21的表达,降低疾病发生率[32-33]。
2.3胆汁酸(BAs) BAs在肝脏中由胆固醇产生,在肠道中由肠道菌群代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BAs和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人体存在许多影响,一方面BAs不仅可通过直接(如破坏细菌膜)或间接(作为菌种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介体)的方式发挥抗菌剂作用,还可通过调节法尼酯X受体、胆汁酸受体5等信号间接影响肠道菌群组成[34-35];另一方面肠道菌群胆盐水解酶能将结合BAs水解为游离BAs,再由肠道菌群进一步修饰为次级BAs[36-37]。结合/游离、初级/次级BAs比例是表明BAs代谢程度的重要依据。目前,对BA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糖脂代谢异常疾病(如糖尿病、肥胖等)以及炎症性肠病等,与AR相关性研究较少见,但有研究发现,其与其他过敏性疾病具有相关性,如有研究发现,哮喘与牛磺胆酸水平升高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患有食物过敏且血清IgE水平高的儿童与健康组比较,胆酸和鹅去氧胆酸水平均升高[38]。由此推断,BAs代谢相关途径与AR存在一定的联系,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验证。
2.4氨基酸 肠道内的氨基酸是由食物中的蛋白质水解而来,经肠道菌群代谢后生成其他支链氨基酸、胺类、有机酸类等物质。有研究发现,AR患者的B淋巴细胞中谷氨酰胺转运体和中性氨基酸水平均较低,造成其功能障碍,无法产生IL-10,造成持续性的免疫激活,延长了AR病程[39]。ZHOU等[40]也发现,牛磺酸能促进IL-35的产生,从而促进CD4、Treg等的产生,使炎症反应正常化,减轻AR症状。还有许多其他证据也表明,氨基酸与AR关系密切,如有学者通过代谢组学研究发现,色氨酸、酪氨酸代谢途径均与过敏性疾病高度相关,与健康组比较,过敏性哮喘儿童体内色氨酸、酪氨酸水平均上调[41]。
2.5吲哚类 随着粪便分析技术的成熟,肠道中一些其他粪便代谢物功能被发掘,吲哚类就是其中之一。有研究发现,吲哚乳酸能促进Th17分化过程中IL-22的表达,IL-22能维持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从而抵御肠道黏膜处的病原微生物入侵;另一方面吲哚乳酸可作用于巨噬细胞表面的芳烃受体和羟基羧酸受体3,抑制巨噬细胞促炎性细胞因子——IL-12p70的表达,减少过度炎症反应[42]。而有学者对小鼠进行的研究也表明,丙酸吲哚在调节肠道屏障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3]。由此可见,吲哚类虽不与AR直接相关,但也可通过影响黏膜屏障、调节免疫细胞等方式间接参与AR的病程。
2.6其他 除粪便代谢物外,粪便中存在的其他代谢物,如脂质、酚类、氨氮等与AR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关系。WORGALL等[44]研究证明了鞘脂在气道疾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粪便中的氨氮浓度也与肠道pH值呈显著正相关,低pH值和氨氮浓度的肠道环境可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并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27]。但由于相关研究较少见,数据量小且具有特异性,在此不再赘述。
3 展 望
AR作为一种反复发作的过敏性炎症疾病,其发病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究;随着对肠道菌群及其相关粪便代谢物的深入研究,其在黏膜屏障的维持、早期免疫体系的建立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认识到,其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存在联系,这也为研究AR发病机制及治疗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但由于技术水平等的限制,现在还无法完全说明肠道菌群组成的改变是AR发病的原因还是造成的结果,只是大量数据的堆砌;另外,由于粪便内容物种类众多,产生途径各异,其与疾病和肠道菌群之间的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饮食、年龄等,关系复杂,难以真正厘清。因此,还需大量的实验探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各种检测技术的发展及多组学分析的综合运用,终有一天能探明AR与肠道菌群及其粪便代谢物之间的联系,为AR的治疗开辟新方式,彻底解决患者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