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别具一格的史学大家
2023-11-22欧文
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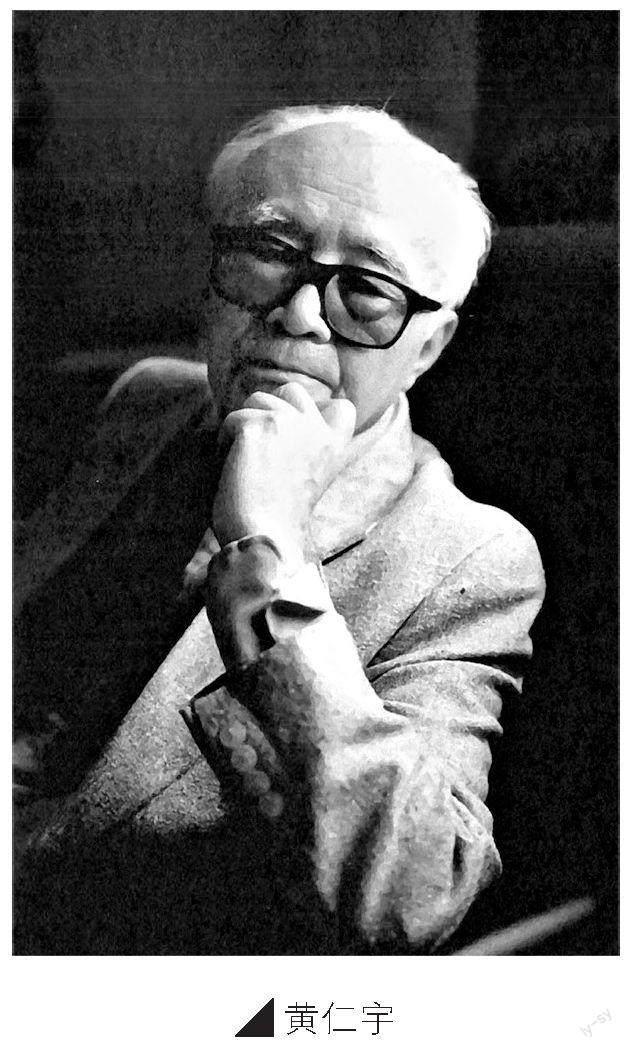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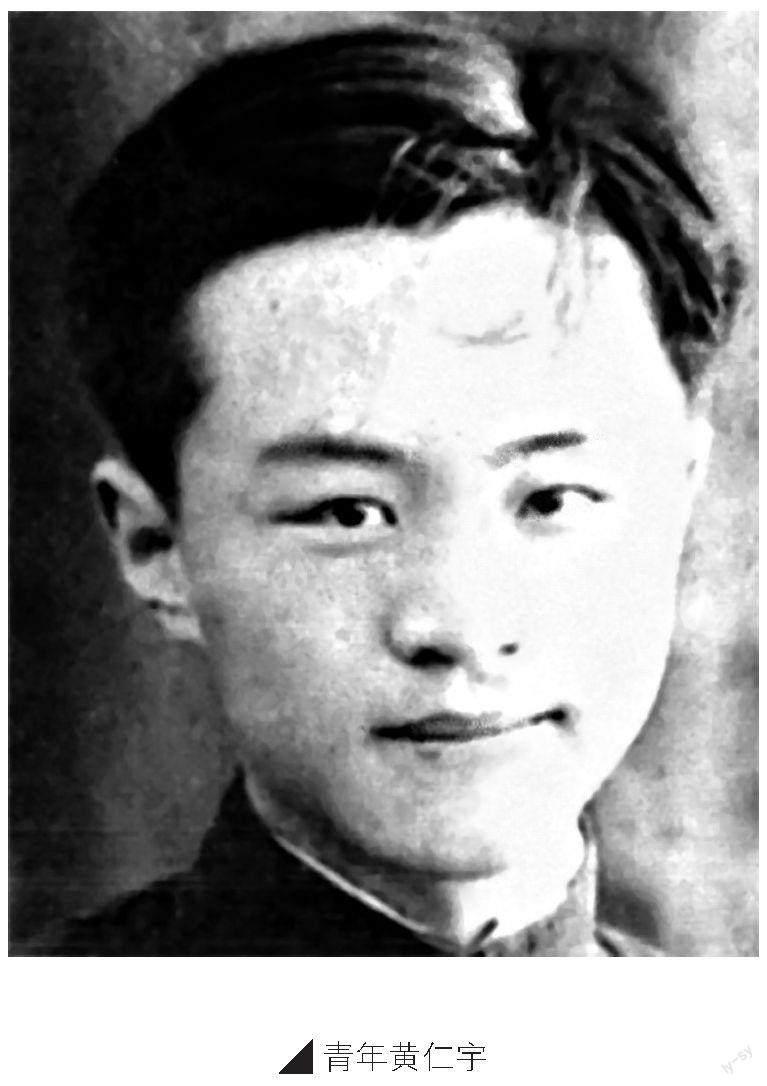

他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名著,以大历史观的倡导者,树立了史家品牌,为世人所欣赏。然而他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大家,他有着比他在书中所描述的历史故事还要传奇、精彩且曲折的人生经历。他曾弃学从军,曾在大学任教又被迫辞职,半路转向历史学研究,其治学态度曾被人批评……或许正是这样丰富和坎坷的经历,成就了他的别具一格。
有其父必有其子
1918 年6月,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一个军人家庭。父亲黄震白对他影响很大,黄仁宇曾说自己的历史观来自父亲的教导。黄震白自小家道中落,虽上过军校,成绩也优秀,但因求知欲及改变现实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直到年近三十,仍是“常在饥饿边缘徘徊的单身汉”。后来他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家中客厅墙上,曾经挂着一幅孙中山的题词,上书“博爱”两个大字,题赠“种苏同志”(“种苏”是黄震白的化名)。
参加革命后的状况让黄震白十分失望,他一气之下,辞职回到湖南,和黄仁宇的母亲成了婚,婚后生了三个孩子:黄仁宇与弟弟黄竞存、妹妹黄粹存。在湖南老家,黄震白寻觅不到适合的工作,只能在地方政府里谋个小职位,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和能力都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事业上的不如意,使得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长期处于困顿中。
从上中学开始,由于家庭困难,除了支付学费等一些必要开支外,父亲无法为黄仁宇提供更多的帮助,他因此很自卑。父亲为了生计在外奔波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操持家务。母亲是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传统女性,教育孩子只能遵循老一辈的家训——律子要严。碰巧,黄仁宇生性叛逆,不服管教,故而母子之间争执时有发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有时走在街上甚至很难避开行刑的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1930 年,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被敌人杀害,而杨开慧是黄仁宇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人而遭杀害。向钧被害前,黄震白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以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向钧当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给黄家留下了阴影,也深深震撼了黄仁宇的心。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父亲希望黄仁宇兄弟俩能好好学习,“专心学业,上大学,当工程师,或是靠着建设性的工作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
少年时代的黄仁宇一直对写作有着极大的热情,从十四五岁开始,他就积极向当地报社投稿,投稿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字,还包括自己手绘的插图。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了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文章旁边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后来,在他的著作中,黄仁宇也加入了许多自己画的白描、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可以说,萌发于少年时期的这种写作热忱,陪伴了他的一生。不管是军旅岁月,还是学术生涯;不管是攻读新闻,还是研究历史,他都喜欢用文图去表达自己,去重现历史。
至于父亲是如何影响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黄仁宇在其自传《黄河青山》中这样写道:“他(父亲)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为抗日毅然弃学从军
1936 年,自长沙一中毕业的黄仁宇,入读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平静的校园生活才过了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南开大学南迁。在继续求学和从军的选项中,黄仁宇选择了后者。尽管黄震白对两个儿子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和明确的规划,但在家国危难的时候,他还是决定尊重儿子们的意见。中日战争“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而且“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这是父亲临别时对黄仁宇说的话。
到了 1938 年夏天,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十六期)。在等待开学的半年里,黄仁宇在长沙暂时投身报界,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有剧作家田汉(社长)和后来成为共产党干部的廖沫沙(总编辑)。他还结识了《大公报》的范长江等人。
1939 年初开始,黄仁宇接受了近两年时间的军事训练。1940年底毕业后,他通过田汉的关系,与田汉之子田海男一起获得任命状,直接开赴前线。黄仁宇先后担任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他所在的连,兵员不及正常编制的一半,只有一名少尉和三十六名士兵,隶属国民党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临日军占领的越南。黄仁宇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其间还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
黄仁宇的滇南戍守生涯,因父亲病重去世而结束。1942年,他请假回家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后,没有返回第十四师,而是在重庆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在重庆工作的一年,看似安稳,黄仁宇却感到“无聊得要命”,“一心等着上战场”。
彼时,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印度岌岌可危。缅甸的沦陷对中国战场也产生了严重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驼峰航线”维持。中国方面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奔赴印度,从侧翼进攻缅甸,这支部队称为“新一军”,由英军提供物资后勤保障,美军则负责训练。中方统帅是郑洞国将军,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管辖。1943 年 2 月,黄仁宇被派到郑洞国麾下任参谋,军衔为上尉。此后一年半的当兵生涯,可谓黄仁宇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光。因为作战需要,他经常冒险出入无人地带。1944年5月,黄仁宇被藏在树丛中的日军狙击手射中了大腿,遂到后方调养。后来,他因此获得一枚海陆空军一等奖章。
而在战场外,黄仁宇把自己当作一名战地记者,尽自己所能将亲历的每一个历史场景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他随战事写的十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公报》上,读者甚众,影响广泛。其中,他关于密支那战役的报道长达一万两千字,曾连载四天。1945年3月,这批文稿由上海大东书局结集出版,这就是黃仁宇人生中的第一本著作《缅北之战》。
半路出家的史学大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郑洞国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黄仁宇随他回到上海,负责接收日本军队投降等相关事务。1945 年末在上海,黄仁宇遇到了自己的初恋——一个名叫安的女孩。这段恋情最后无疾而终,后来黄仁宇为安专门写了一本小说《长沙白茉莉》。在两人相处的日子里,黄仁宇曾告诉安,他想回到学校读书,但不想再读之前的电机专业。曾经亲身经历过战场的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则与走向。
黄仁宇虽然一心报国,但在人际复杂的军界始终难有发展。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起初,黄仁宇认为自己有做战地记者的经验,读新闻学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他打听到南开大学下一年将在天津复校,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就把自己登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做成剪报,附上在《抗战日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发表过的其他文稿一起寄到南开,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者至少下一年在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求学资格。然而南开方面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于是去南开求学的念头也就此打住。
1949 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彻底崩溃,黄仁宇没有随大部队去台湾,而是去日本横滨当了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的副官助手。
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后,1950年,因受到派系斗争的牵连,黄仁宇接到了退伍令,这意味着他的军旅生涯至此宣告结束。此时,他已经三十二岁。身处日本的黄仁宇,既无法返回中国大陆,也不愿南渡中国台湾。最终,他毅然决定赴美留学。
1952年9月,三十四岁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主修新闻学专业,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在班里,黄仁宇学习最刻苦,他抓住一切时间学习,两年内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但是,毕业对于黄仁宇而言就是失业,因为他还说不出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也很难在报社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写出符合要求的稿件,因此想要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工作非常困难。他也曾尝试向出版业发展,但一次次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被拒绝的尴尬。
黄仁宇在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就读期间,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然新闻界工作难觅,他干脆改行,研究自己曾經感兴趣的历史学。不过,这意味着一切要重新再来。历史研究本来就繁复枯燥,如果想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还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于是,黄仁宇开始攻读历史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明代历史。这一读就是十年。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大学的文科没有足够重视,政府的研究津贴很少用在文科方面。所以,大部分文科研究生要靠业余打工来维持生计,黄仁宇也是这样。来美国之前,他曾在日本攒了一笔钱,不过这笔钱很快就花光了。读博期间,黄仁宇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半工半读成了他的生活常态。他曾在餐厅当服务员,在夜总会当洗碗工,在仓库当收货员,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对于这段经历,黄仁宇感到既辛酸又喜悦。虽然生活不易,但体力劳动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还缓解了学习带来的孤寂。
1964年,四十六岁的黄仁宇终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四十六岁本该是学术生涯的黄金年龄,但对黄仁宇而言,却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好在黄仁宇在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就收到来自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话,聘任他为该校历史系的助理教授。
在南伊利诺伊大学,黄仁宇遇到了与他相伴一生的妻子格尔(Gayle)。经过一年多的接触,黄仁宇与格尔在 1966年 8 月结为终身伴侣,转年独子黄培乐出生。由于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待遇等问题,黄仁宇很快辞职了。
1967年,黄仁宇受聘于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中国历史。他在该校开设了“亚洲文明导读”这门课,由于每节课只有五十分钟,而要讲解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过于丰富,他不得不想法用最少的言语来传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要义。这番新的实践经验,为他的“大历史观”奠定了根基。
1970 年,黄仁宇得到一笔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拨给的研究经费,用于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于是他带着全家人迁居,开始了自己为期九个月的学术之旅。也正是在这次哈佛之行中,他结识了被称为“约翰王”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在费正清的指导下,黄仁宇完成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写作。
1972—1973 年,黄仁宇曾在英国剑桥与英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合作,并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材料,帮助其撰写其中的明朝部分。1979 年,黄仁宇到普林斯顿大学,受邀参加《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的撰写工作。由此,黄仁宇在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
另类名作《万历十五年》
说到黄仁宇学术生涯的顶峰,那当然非《万历十五年》莫属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诞生在黄仁宇人生内忧外患之际。《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几乎可以说是大陆史学领域最畅销的读物之一。
1976 年是黄仁宇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的第九年,对于五十八岁的他来说,急需出版一部著作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在此之前,他出版过的专著严格说来只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一本,而且销量很少。他寄予厚望的另一部文稿《中国并不神秘》,在接连遭到芮沃寿与费正清两位权威学者的否决后,再也没有得见天日。于是,黄仁宇向纽普兹告假,依照计划撰写《万历十五年》(原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
在写作《万历十五年》时,他已经决定另辟蹊径,从小处着笔,专门写“16 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他选中了1587 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书中,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右督御史海瑞,蓟镇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轮番登场,而所有人的努力均显得徒劳而悲壮——他们不能改变僵化低效的帝国体制,扭转大厦将倾的崩毁命运。该书融入了他的独特经历和深刻感受,最充分地展示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写作《万历十五年》非常辛苦,也非常快乐。明代官吏丝袍上的绣金线,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喇嘛寺上方盘旋的白鹤,庙里的钟声,司礼官低沉的唱名……他将一个年代的色声香味铺陈纸上,只为告诉他的读者和同行:“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
不过,《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却遇到了困难。虽然黄仁宇将写好的书稿分别寄给了曾经参加《剑桥中国史》写作的两位作者牟复礼和崔瑞德,得到了两位学者的大加赞许,但是书稿依然无法出版。因为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一旦决定出版,审稿人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而牟复礼和崔瑞德既然对稿子赞誉有加,无意间就排除了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
同时,《万历十五年》的稿子也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一点也很难得到学术界诸多审稿人的认可。商业性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应该交由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本书十分通俗,趣味性强,应该交由商业性的出版社出版。于是,等待黄仁宇的并不是“世界史学界的一场巨大震动”,而是美国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的无情退稿。
苦等数年,眼看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在美国出版遥遥无期,黄仁宇只得把书稿全部译成中文,将《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改名为《万历十五年》,于1979年委托友人将书稿带到中国,寻找出版机会。几经辗转,《万历十五年》简体中文版在 198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由黄仁宇的老友廖沫沙题笺。这本书一经问世,很快便销售一空,专家们也纷纷从内容、理论、写作方法等方面对该书进行探讨,并从此掀起了一波长久不息的明史研究热潮。
就在中文书稿来到中国这一年,《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屡屡碰壁之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1983年该书连续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提名。后来又以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刊行,并被美国一些高校选作教科书。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在《纽约客》发表书评,说“《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生前身后毁誉参半
遗憾的是,黄仁宇的职业生涯并不一帆风顺。由于经费的削减,纽普兹大学亚洲研究系的全职教员几乎减少了一半,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1979 年。就在《万历十五年》寻求出版的关键时刻,1979年3月,六十一岁的黄仁宇收到了纽普兹大学的解聘书:“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 8月31日中止。你的教职之所以中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解聘一事,给黄仁宇的身心和生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黄仁宇一生的难言之隐。这不仅沉重伤害了他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学术尊严,也使得黄仁宇的妻儿陷入生存危机。“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在黄仁宇回忆录里,这种难以释怀的委屈和悲愤常常出现。
从此,黄仁宇再也没有过其他固定的工作。在他人生的后二十年中,写作成了他获取收入的唯一来源。比如1989年后,黄仁宇在我国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开了一个小专栏,叫作《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后来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集结成书。此外的收入,主要是书籍出版的稿酬或版税。特别是1992年初,三联书店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在“海外学人丛书”中出版,由此开始了三联书店与黄仁宇的合作,相继推出他的一系列著作。
在20世紀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中国海峡两岸普通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历史学家。除《万历十五年》外,黄仁宇比较畅销的书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大历史不会萎缩》,以及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至1983年,完成之后并没有急于出版,而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意愿,在他逝世之后才和读者见面)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唯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
黄仁宇的一生坎坷多艰,生前身后毁誉参半。在民间,他拥有大量读者,被视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大师;但在他深耕多年的史学界,他更像一位“旁门左道”,不乏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人批评他的治学态度,把他视为介于学术与通俗历史之间的人物。
2000 年 1 月 8 日,黄仁宇离开纽约的寓所,坐着妻子格尔开的车子,到电影院看电影。路上,他还笑着对妻子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没想到一语成谶。刚到电影院,黄仁宇就说身体不舒服,在进门的厅堂上一坐下就晕倒了,等救护车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时,他已悄然离世。他曾对妻子说过:“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以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妻子所讲的话如出一辙,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传奇人生最好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