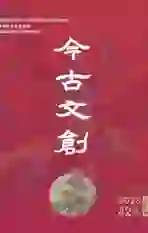论《边城》和《雪国》中的东方悲哀美
2023-11-20黄朝辉张兰
黄朝辉 张兰
【摘要】作为同一时代的两位东方文学巨匠,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在创作风格上具有相似性。两人的代表作《边城》和《雪国》都体现了以悲哀为美的艺术风格,具有东方文学中广泛存在的悲哀美。本文从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主题和表现手法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两部作品中如何拥有东方悲哀美,深入挖掘东方悲哀美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东方悲哀美;《边城》;《雪国》;沈从文;川端康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2-004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2.013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沈从文《边城》与川端康成《雪国》悲剧美比较研究”资助(项目编号:Jdx22064)。
作为同一时代的两位东方文学巨匠,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不仅在创作背景上存在相似性,在写作风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两人的代表作《边城》与《雪国》都呈现出一种东方悲哀美的风格,使读者在阅读后感到美的同时,又不禁萌生悲哀、忧愁的情感。作家通过营造悲凉的情境,将悲哀、忧愁的情感传递给读者,从而使读者获得一种纤细而又淡淡的悲哀美感。
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悲哀美在东方文学中经常出现。当我们研究《边城》与《雪国》中的东方悲哀美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两部作品中的东方悲哀美体现在哪?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要想研究这个核心问题,必须以具体的内容、情节以及作家的创作手法为基础,才能得出结论。本文将从小说中的人物、主题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去研究,以此了解东方悲哀美这种艺术风格是如何在文本中体现的。
一、底层女性形象
《边城》和《雪国》都以社会底层女性作为主人公,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展现了悲哀美的风格。作家通过人物自身的美与其悲惨命运形成对比,使读者产生怜悯、悲伤的情感体验。
《边城》和《雪国》的主人公翠翠和驹子都是悲哀美的范例,两人都呈现出一种美的特质。《边城》里,作者用“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 ①展现了她自然健康的容貌。自然風物的滋养,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翠翠的品质,使得翠翠在平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都流露出灵巧、自然、纯洁等特点。她像一只未经人事的小动物,天真可爱,无忧无虑。面对陌生人时,她会感到局促不安。一旦了解对方没有恶意,她便马上忘记刚刚的不安,又继续从容地玩耍。《雪国》里的驹子,岛村对于她的第一印象便是洁净,驹子玲珑的鼻梁和水蛭般的柔唇给他留下洁净而又漂亮的印象。驹子虽然作为艺妓,但她也没有因此就自卑自弃,反而努力生活。这也反衬出她“洁净”的高贵品质。她坚持写日记、保持阅读的习惯以及刻苦练习三弦琴等细节,正是最好的证明。两人漂亮的外貌和其高贵难得的美好品质,无不给人留下一种真实而又自然的美感。
与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这种真实又自然的美感相反的,是两人悲惨的命运和社会底层的地位。翠翠的父亲在她出生前自尽,母亲在翠翠出生后也殉情死了。翠翠由身为船夫的祖父抚养长大。尽管祖父十分疼爱翠翠,但是缺少父母的陪伴与教育,使得翠翠对于爱情总是懵懂害羞、缺乏主动,一次次回避大老和二老。而她的出身又使得她无法像团总的女儿一样,轻易地拿出一座碾坊作为嫁妆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最终,翠翠只能在回避中,茫然无措地接受自己的悲剧人生。与翠翠一样,驹子的命运也同样悲惨。驹子原本出生在雪国,后面不幸被卖到东京的酒馆当女侍。一位好心人帮她赎身,但一年半后这位恩人也去世了,驹子便回到雪国拜行男的母亲为师学习舞蹈。之后行男不幸染病,驹子只好卖身当艺妓为其赚医药费。驹子生活努力又怀有理想,她努力记笔记、看书和勤奋地学艺,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舞蹈师傅。然而出生底层、无所依靠的她难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的努力终究化作徒劳。
刘西渭说过:“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 ②灵动自然的翠翠和洁净可人的驹子,却拥有悲惨的命运和卑微的社会地位。巨大的反差使读者在阅读时,内在的共情本能被激起,不由得在心底萌生出一种悲哀之感。
二、主题的表现
《边城》里面的主题是人生的不凑巧。沈从文曾说过:“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 ③在《边城》里,沈从文通过对茶峒人民不同生活形式的描绘,反映出他对人性中真善美的追求。茶峒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虽不算富足却也能够自给自足,每个人都展现了乐天知命的积极态度:快乐地享受人生的美好,超脱地面对人生的不幸。《边城》中茶峒人民淳朴洒脱的生活,正是沈从文一直所追求的优美自然的理想人生。然而在茶峒桃花源般的理想外表之下,隐藏的是人生的不凑巧与命运的无常。沈从文以细腻而又抒情的笔触,一步步地向读者展现人生的不凑巧。首先是翠翠父母的爱情,翠翠母亲年轻时秘密地爱上一位驻守军人,两人的爱情在当时很难得到认可,于是两人相继殉情而死。翠翠父母的爱情,便是人生种种不凑巧一起酿成的悲剧。翠翠母亲死后,祖父独自抚养翠翠。当翠翠长大,祖父不得不考虑起翠翠的终身大事。女儿的死让他对于翠翠的婚姻非常谨慎,担心翠翠步入她母亲的后尘。他对大老二老所说的“车路”和“马路”,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然而祖父诸多的心事,顺顺家并不清楚,只当祖父说话弯弯绕绕,把大老的死简单地归结于祖父。大老的死也是不凑巧的,船夫靠水吃饭,本身就有一定危险性,并非祖父导致的。最后在命运的捉弄下,二老出走、祖父忧愁而死,翠翠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她的爱人。《边城》里的人物几乎都是充满爱和良善的好人,但是在人生的不凑巧之下,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雪国》里的主题是人生的徒劳。在川端康成的笔下,雪国美丽却又空灵虚幻,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虚无感。岛村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圆满又衣食无忧,然而这样的生活却没有让他感到满足。岛村常挂在嘴边的“徒劳”和他身上无由的哀愁,都反映了岛村内心的空虚。岛村热爱西方的舞蹈却从没有去看真人表演,只是去欣赏有关西方舞蹈的图片和书籍。岛村对于西方舞蹈的欣赏是劳而无功的,但他却还是沉迷其中,这反映了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徒劳。岛村身上的徒劳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而驹子身上的徒劳则体现在现实生活中。驹子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艺妓,她努力学习舞蹈与三弦琴、坚持看书和写日记,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改变现状。驹子虽然拥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但在当时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她的坚持和努力终究是徒劳的。驹子对岛村的爱,同样也是徒劳的。岛村对驹子的态度与其对待西洋舞蹈的态度相似,是一种具有幻想性的欣赏态度。但是他既然不爱驹子,却又不跟她说清,使得驹子总抱有虚无的幻想。这一切都反映了岛村的自私以及他对驹子的轻视。然而与岛村的态度相反,驹子对于他的爱恋则是坚定而热烈。驹子对岛村的爱,是她苦难生活的寄托。正因如此,即使驹子明白岛村不爱自己,她也很难放下这份爱,只能继续徒劳地爱着岛村。驹子对岛村爱是真挚的,但又充满着徒劳的色彩。正因如此,驹子越是爱着岛村,读者便越发为其感到悲哀。
翠翠和驹子的悲剧结局看似偶然,实际上体现了人生不凑巧和虚的本质。正因如此,读者在为兩人的不幸而感慨时却又无可奈何,心里不由得感到悲哀和忧愁。
三、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都擅长描写美丽的自然风景。在《边城》和《雪国》里,自然风景与全文悲哀忧愁的基调相融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首先,两位作家都有意将自然季节与人物命运建立联系,达到自然与情感的和谐统一。沈从文在《边城》里,没有刻意的交代情节发生的时间和缘由,而是以草蛇灰线式的描写巧妙地暗示读者。祖父的死亡是《边城》里非常重要的情节,祖父的死亡不仅是全书最大的戏剧冲突,同时也是翠翠命运的转折点。沈从文在描写祖父死亡的时候,巧妙地将其与季节建立联系,不知不觉地为人物的死亡营造悲哀的氛围。夏季湿热沉闷的特点,与祖父当时心中哀愁烦闷的心情相呼应。祖父担心翠翠的终身大事,但又无法面对二老父子。他心中的苦闷无人诉说,想要解决却又解决不了,于是心底的郁结越发严重。夏季的炎热干燥,象征着祖父心中的郁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炎热与祖父的郁结一同达到顶峰,终于在夏秋交换之际与大雨一同倾泻。《雪国》里,岛村来到雪国的季节分别是夏季、冬季和秋季。初见时,雪国结束了一场雪崩。雪地里长出的嫩叶,象征着驹子刚刚萌发的情感与羁绊。第二次与第三次的见面,驹子对岛村的爱恋不断加深。而岛村却相反,他对驹子的了解越深,心里对驹子的感情就越淡薄。这样的反差,使得驹子对岛村的爱更加悲哀和虚无。作家有意将后两次设置在冬季与秋季,一方面秋冬季降雪多,雪带给人的虚无感与两人间徒劳、虚无的爱情相契合。另一方面,秋冬季节万物凋零,暗示着驹子对岛村的爱是无望的,两人的关系终究要踏进寒冬。时令季节与人物命运巧妙的结合,使自然也渐渐沾染上人的悲哀与凄凉。
其次,《边城》和《雪国》里出现的自然意象与人物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方古典文化中,人物的悲与哀往往不会明显地显现,而是借助自然意象抒发出来。在《边城》里,流星和黄昏景色本是美好的,作者却将其与死亡联系在一起。黄昏常常被人们用来指代人的暮年。在小说里,翠翠就是看到黄昏时河面上的薄雾,联想到祖父的死。天上的星星如此美好,却也不是永恒的,也会化作流星离去。翠翠在祖父的葬礼上看到了流星,正对应着祖父的死亡。这样巧妙的描写,使得死亡的悲痛被自然的美冲淡了几分,使读者得以从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下获得暂时的喘息,以此得到纯粹的悲哀美感。而在《雪国》里,反复出现的白雪象征着驹子悲惨的人生。雪是晶莹剔透、洁白美丽的事物,正如驹子洁净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但同时,雪也是稍纵即逝的事物,一不留神就会融化。驹子最后在初秋的雪夜里精神失控,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雪美丽而又短暂的特质,更加凸显出人生的虚无与徒劳。
两部作品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既描绘了优美绚烂的自然景物,又为作品奠定了悲哀的情感基调,使自然美和悲哀美的融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四、东方悲哀美
《边城》与《雪国》从人物、主题和表现手法三个不同侧面,体现了东方悲哀美。两部作品所带给读者的纤细、淡淡的悲哀美感,是东方悲哀美的核心。
朱光潜说:“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 ④美生于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又起于形象的直觉。形象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又必须借由主体去欣赏,无我便无法见出形象;直觉作为主观感受,又无法完全脱离客观存在,无物则直觉无从活动。“以物的方面来说明美时,产生美的,是在最广义上说的形,它是处于物一方的条件;从思的方面来说明美时,产生美的,是思的主体——心。” ⑤东方悲哀美的形成既依赖物又依赖心,二者缺一不可。两部作品虽然都是凭借客体的“悲”激起审美者的美感经验,但客体悲的色彩也是主体所赋予的。沈从文曾说“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⑥川端康成也认为“日语‘悲哀’这词同美是相通的”。⑦两位作家相似的审美观念,使得他们在文本中有意地追求悲哀。他们将文中悲哀的基调和人的同情心相融合,赋予了作品哀伤、忧愁的悲哀美感。同时,两位作家又恰当地把握心与物之间的距离,使得客体的悲与主体的情融合地恰到好处,给读者带来纤细又余韵难消的东方悲哀美。《边城》与《雪国》中所体现的心物相融的东方悲哀美,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心物合一的理论不谋而合。由此可以看出,东方古典文学传统对东方悲哀美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而作家个人的创新又不断丰富东方悲哀美的内涵。
因为民族文化、社会背景和作品体裁等方面的差异,所以东方悲哀美在作品中的表现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固有模式。然而由于人类的共情本能,使得作家在面临人生的悲哀与不幸时所流露出的情感也总是相似的。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展现出来的悲哀美感,并不逊色于中国的《红楼梦》。沈从文笔下所流露出对底层人民的悲哀与同情,读者也能在泰戈尔的作品中发现。
通过对《边城》和《雪国》两部作品的人物、主题和表现手法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我们弄清了东方悲哀美是如何在两部文学作品在体现的。客体的悲和主体的同情是悲哀美感产生的重要源泉,也是东方悲哀美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民族文化底蕴、作家审美追求和作品表现形式的差异,导致东方悲哀美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并不总是相同的。然而差异并不一定代表对立,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固有的元素,欣赏不同作品间相通的东方悲哀美。
注释:
①沈从文:《边城》,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②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见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資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③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④朱光潜:《谈美》,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⑤(日)今道友信著、蒋寅等译:《东方的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4页。
⑥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⑦(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川端康成谈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8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2](日)川端康成.雪国[M].叶渭渠,唐月梅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何乃英.悲哀美的颂歌——评川端康成小说的艺术风格特色[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39-45,111-112.
[4]陈柯廷.浅析中日文学作品中的悲剧色彩——以《边城》和《伊豆的舞女》为例[J].牡丹,2019,(33):133-135.
[5]王平.悲美爱情的守望者—— 《边城》与《雪国》女性形象比较[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8):65-67.
[6]翟晓甜,齐雪艳.自由地吟唱悲美人生—— 《边城》与《雪国》比较研究[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0,18(03):
36-39.
[7]杨玉珍.《边城》:东方神韵[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54-57+66.
[8]王珺.从《雪国》看川端康成美学中的“悲美”风格[J].文学教育(下),2020,(04):116-117.
作者简介:
黄朝辉,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张兰,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