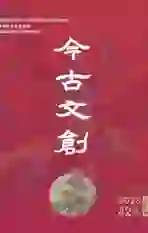论曹禺戏剧《原野》的意象类型
2023-11-20宋苏云
宋苏云
【摘要】曹禺戏剧《原野》通过选取繁复奇异的意象和采用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或传达对原始生命活力的呼唤,或展现两种文明之间的博弈,或表达对人类复归精神家园的忠告等文本内涵。本文旨在选择三类意象进行分析,以揭示曹禺戏剧《原野》深刻的主题意蕴。《原野》中的三类意象分别是:闭锁式意象、理想式意象、张扬式意象。闭锁式意象包括:黑林子、铁镣、老屋和红灯;理想式意象包括:铁路、金子铺满的地方;张扬式意象包括:原野、森林、红花。
【关键词】《原野》;意象;主题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2-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2.004
在《原野》中曹禺流露出对人类生命存在的关怀意识,表现出对蓬勃生命力的热切呼唤,对人类复归本我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这些文本内涵的传达正是通过意象来实现的,所以深入探析《原野》中的意象,不仅对于认识和理解戏剧《原野》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读者深刻体会曹禺戏剧中深沉的批判意识和敦厚的人文关怀。本文大致将《原野》中的意象分为三类,即张扬式意象、理想式意象和闭锁式意象。“这三类意象两两之间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张扬式意象与闭锁式意象的对立关系反映了封建势力对原始生命力的压迫,张扬式意象与理想式意象的对立关系反映了现代文明对原始生命力的摧残,闭锁式意象与理想式意象的对立反映了现代文明对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摧枯拉朽的撼动力” ①。
一、张扬式意象
张扬式意象在《原野》中象征着人类的原始欲望和人类蓬勃的生命力以及人类的童年时期。这类意象包括:原野、森林、红花。
(一)原野
在《原野》的序幕中便出现了原野这一意象,原野既是仇虎越狱之后的藏身之处,也是他释放在狱中被压抑已久的欲望的场所。读者可以想象到在经历过八年的牢狱束缚之后,仇虎在原野上自由自在奔跑的场景,这种奔跑是对人的原始欲望的释放,也是对封建势力的反抗。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仇虎在原野中发现了多年未见的花金子,仇虎多年的相思之苦及情欲之苦终于得以排解。原野中的一切都是“野”的,“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 ②,原野里没有人类力量的干预和束缚,使得各种生命都能够自由自在地生長。在苍茫的原野上穿着破旧的仇虎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同时“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红,像噩梦,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 ③,世界仿佛回到了开天辟地时的原始模样,仇虎也仿佛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时期。从戏剧舞台的艺术效果来看,整个舞台呈现出黑与红的混沌之色,给观众一种严肃、险恶与幽郁的观感,并且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是十分“张扬”的,非常符合“原野”这个意象的特征及内涵。
(二)森林
森林主要出现在序幕和第三幕,在第三幕中它出现在仇虎和金子一起逃出焦家之后,逃出焦家就意味着他们终于摆脱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他们逃进了森林里,森林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使得森林呈现出恐怖和严肃的面貌,他们走了几十公里,一路上他们又渴又累,恐惧占据了他们的内心,但即便这样花金子还是不后悔跟随仇虎逃出焦家,她说她一辈子只有跟着仇虎才真像活了十天,由此可见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纲常对于金子的欲望和精神的压抑,而森林这个神秘漆黑的场所恰好可以使得金子恢复日渐消亡的原始生命力,并且森林本身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性欲的象征,因为“森林是由树组成的,就树这个个体而言,树可以结果,孕育生命是女性生殖的象征,树的根延伸到大地,作为大地之根,它又与男性的阴茎相互指涉,象征着男性的生育” ④。仇虎在森林里出现了各种幻觉和恐怖的体验,并且最终他选择了自杀,没能够和花金子一起逃到那个“黄金子铺的地方”,也就是说仇虎最终没能够实现原始欲望的满足,因此曹禺试图利用森林意象向读者传达出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以及人类的原始生命欲求永远也无法被满足的哲性体悟。在原始社会,森林给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埋伏着各种危机,因为人类必然要面临残酷的“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这些“合理”的“挑战”培养了人类自身的生命力,但是反观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压力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命力逐渐萎缩,因此曹禺试图利用森林意象唤醒人类委顿的生命力。
(三)红花
红色是一种热烈的颜色,而花自古以来就是男子向女子求爱的工具,因此当仇虎把红花送给花金子的时候,就象征着仇虎对于花金子有着强烈的爱和性欲。红花也象征着仇虎与金子之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为“男性对女性近似心形的臀部进行生殖崇拜,使得心带有强烈的情欲色彩,又因红色是心的颜色,红色自然也点染上情欲的意味。仇虎送给金子一朵红花,那种抑制不住的情欲已经喷薄而出,这对金子是赤裸裸的诱惑” ⑤。在剧作中花金子让仇虎把这朵红花捡起来戴到自己的头上,表明花金子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仇虎的示爱。焦氏用手摸到花金子头上戴的红花之后,就让花金子把它取下来,虽然花金子并没有取下来,而是找了一个替代物放在焦氏的脚边,焦氏用脚使劲地踩踏这朵“红花”,焦氏的这一举动象征着对花金子和仇虎之间强烈的情欲的束缚和摧毁,而花金子没取“红花”的行为则意味着对于封建伦理纲常的反抗。而花金子头上戴的红花和她身上穿的衣服是同一种颜色,“红色”是一种和花金子的精神气质十分符合的颜色,或者说“红色”是一种符合花金子蓬勃生命力和旺盛欲望的颜色,所以曹禺运用“红花”这一意象不仅对于塑造花金子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戏剧主题的深化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闭锁式意象
闭锁式意象在原野中象征着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以及封建势力的压迫,这类意象包括:黑林子、铁镣、老屋和红灯。
(一)黑林子
仇虎和花金子逃出焦家之后便逃进了黑林子,一路上焦母叫魂的鼓声使他们心惊胆战,仇虎不时地陷入幻觉和内心的纠结之中,在经过几十公里的跋涉之后,他们终于挣扎着快要走出黑林子,但是侦察队也快追上他们了,仇虎最终选择了自杀,没能和花金子一起逃往那金子铺满的地方,也就是说仇虎最终没能实现理想,仇虎没能实现理想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因为他被“父债子还”的封建传统观念束缚,二是封建势力太过强大。仇虎的仇人焦闫王已经去世,但是仇虎还是要报这“一家两代”之仇,他杀死了无辜的焦大星和小黑子,使得他陷入内心的愧疚之中,这可能是他选择自杀的原因,也可能是造成他理想破灭的原因。另一方面焦母、侦察队等封建势力的穷追不舍使得他最终没能逃出黑林子,黑林子里面有焦母和侦察队,所以说黑林子象征着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黑林子的“黑”以及“广阔”给他们的逃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使得他们在黑林子里迷了路,一路上他们又累又渴,他们被封建势力的大网笼罩着、束缚着,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封建势力的恐惧和对理想的向往,曹禺对于这些细节的书写显示出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封建伦理纲常的巨大惯性。
(二)铁镣
铁镣这个意象主要出现在序幕和第三幕,在序幕中仇虎戴着铁镣的原因是他刚从牢狱中逃出来,读者可以追溯仇虎入狱的原因,即是封建地主焦阎王的迫害,那么铁镣自然就是封建势力的象征,仇虎越狱和敲开铁镣的行为即是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在第三幕的结尾,仇虎对花金子说他又要戴上铁镣了,因为仇虎被捕后的命运便是再次戴上铁镣,再次成为封建势力的俘虏,于是仇虎选择了自杀,他在倒下之前将铁镣掷到了铁轨上,也就是说仇虎宁愿自杀也不愿向封建势力投降。并且“铁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种刑具,其“铁”的材质使得罪犯们难以轻松挣脱,那么剧作中曹禺运用“铁镣”这个意象就意在说明封建势力的强大,仇虎等反抗封建文化的人很难摆脱其束缚,仇虎确实也是穷其一生也没有逃脱封建文化的牢笼,仇虎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原始欲望,但在强大的封建文化面前他也无可奈何,那么读者也可以进一步明确实质上这幅铁镣就是封建文化对仇虎原始生命力的压制,并且这种压制是十分残酷的。《原野》的悲剧性就在于此,它既是对于坚固的封建文化的抨击,又是对于人类原始生命活力逐渐衰颓的叹息。从铁镣的外形特点来看,它是一种闭环形的结构,这就意味着封建文化具有一种自闭性,这种自闭的封建文化是不允许有仇虎和花金子这样的异类存在的,像仇虎和花金子这样的异类要么屈服于封建文化,要么被封建文化排斥在外,成为封建文化的牺牲品。
(三)老屋
老屋主要出现在第一幕和第二幕,老屋在《原野》中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压抑着生活在其屋檐下的三个人:焦母、焦大星和花金子。焦母在丧偶之后,她把焦阎王的遗像挂在墙上,使得焦家的一切都在焦阎王的注视之下,当她和仇虎见面时,她让仇虎看看墙上挂的是谁,仇虎回答说是“干爹”,她紧接着问仇虎“你干爹怎么看你”,可见她的一切行为都想要符合焦阎王在世时的规范,因为她认为焦阎王还一直在看著她们,可见焦母是一个深受“夫权”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可悲的是她并没有意识到封建文化的愚昧,她又把这种封建伦理道德强加到自己的儿子焦大星和儿媳花金子身上,比如剧中她将鞭子递给焦大星,并让花金子跪下接受焦大星的鞭打,她对焦大星和花金子的婚姻指手画脚,她固执地认为是花金子霸占了她的儿子,因此焦大星始终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中,这使他变成了一个具有“懦弱”“没主见”性格特征的人,焦大星的这种性格最终也酿成了其婚姻的悲剧和生命的悲剧。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花金子“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内蓄满着无穷的原始本能和无尽的燃烧欲望。然而,花金子的命运却同焦氏一样,被残酷的困守在黑暗破败的“老屋”里,青春、爱情和生命在毫无意义的仇恨中虚掷浪费” ⑥,虽然她和仇虎在短暂的十天里尽情地宣泄着原始欲望,并一起谋划过逃往那“金子铺满的地方”,但最终她还是没有逃离“老屋”。
(四)红灯
红灯在《原野》中主要出现在第三幕,仇虎和花金子一起逃进黑林子之后发现一直有“红灯”在跟着她们,经过仇虎和花金子的推断之后,他们认为这盏红灯就是焦母,因为焦母说过孩子救不活的话,仇虎和花金子到哪,她就到哪,那么无疑红灯就是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的象征。在仇虎和花金子逃跑的过程中,这盏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这则象征了封建文化无处不在的、无时不有的危害性。“人死不能复活”是科学常识,但是身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焦母却认为只要把小黑子的魂招回来就可以使小黑子复活,而她认为仇虎就是杀死小黑子的凶手并且认为小黑子的魂一定在仇虎那里,因此焦母便一直跟随着仇虎和花金子,受封建文化浸染和侵蚀的焦母就这样提着“红灯”迷失在虚无的精神家园中。同时“红”也是血液的颜色,因此可以说“红灯”预示出戏剧结尾的械斗、暴动与死亡。红灯在阴暗的舞台背景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偌大的黑林子里只有一盏红灯不禁让人战栗,曹禺通过“红灯”这一意象将封建文化的可怖面目展现出来。
三、理想类意象
理想类意象在《原野》中象征着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目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类已经基本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境,科技的发展也使得人类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可以说现代工业文明是人类理想中的伊甸园。另一方面,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代价是需要底层劳动人民付出血和泪,现代文明中的竞争和掠夺使得人类的精神世界逐渐萎缩并使得人类逐渐成为麻木的“行尸走肉”。这种现代文明的悖论在《原野》中便是通过理想类意象表现出来的,这是《原野》的深沉之处,也是曹禺对人类生命存在的思考与关怀。
(一)铁路
从序幕中读者便得知“铁轨”一直延伸到了“原野”中,“原野”是人类原始欲望的象征,那么“铁轨”对“原野”的入侵便是现代文明对人类精神世界及生命活力的压抑,“铁轨铸得像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霭里闪着亮,一声不响,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 ⑦,仇虎和花金子在对“铁路”所承载的远方的想象中获得快乐和希望,同时对于当下生存困境的不满使得他们陷入痛苦的泥沼中。“铁路”所象征的现代文明,一方面因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而使人类获得快乐和希望,另一方面也使人类因精神大厦受到摧毁而产生痛苦。“铁路”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相比于旧社会的马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而言要快速很多,所以“铁路”可以说是“速度”的象征,也就是说面对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表现出对物质的极大渴望,或者说人类过多地关注物质世界而忽略了对精神世界的滋养。仇虎和花金子在黑林子里一直寻找的便是铁路,仿佛铁路就是他俩的救世主,封建文化的压抑和束缚使得仇虎和花金子对铁路、对理想中的远方有着无限的憧憬,她们渴望去那个人类精神完全自由的远方。在第三幕的结尾,仇虎一转身,用力地把铁镣掷到了铁轨上,这意味着封建文明必将被现代工业文明彻底取代,这不仅是曹禺对于历史发展的预判,还是仇虎对封建文化的挑衅和宣战,但现代社会只能是仇虎头脑中一个美好的幻想,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心中理想的远方。
(二)金子铺满的地方
在序幕中仇虎对花金子说他是从“金子铺满的地方”来的,“那边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睁眼坐着,路会往后飞,那地方天天过年,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 ⑧,可见“金子铺满的地方”俨然是一个天堂,人类的原始欲望在那里得到满足,人类的精神在那里自由生长。花金子回答仇虎说她早就知道这个地方了,可见以仇虎、花金子为代表的旧社会中的许多人都幻想过这个理想的远方,在仇虎和花金子的对话中读者可以得知这个理想的远方更像是人类的童年时期。
在第二幕中仇虎和花金子对于“金子铺满的地方”的极度向往使得他们勇敢地逃出“老屋”,虽然他们最终没能逃到“金子铺满的地方”,但他们为之做出的努力令人动容。在第三幕中仇虎对金子说“在那块地方整年整月地日里夜里受罪,挨鞭子。”仇虎实则揭示出了“金子铺满的地方”的本质——现代工业文明的化身,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血腥和掠夺、带来了生命力的委顿和精神的萎缩。
在第三幕的结尾处仇虎对花金子说“现在那黄金铺成的地方只有你一个配去”,究其原因大概是仇虎没能摆脱杀死焦大星和小黑子之后的愧疚和不安,这种负罪感使得他不能摆脱心理上的阴影,不能逃出封建文化的藩篱,也就是说他做不到成为一个精神完全自由的人,而花金子和他不一样,花金子从来没有后悔过和仇虎一起杀人、一起逃出“老屋”,也就是说花金子完完全全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她反抗封建文明的决心要比仇虎更坚定,所以仇虎认为只有花金子一个人配去“金子铺满的地方”。
纵观整部戏剧,曹禺运用这三组互相对立的意象群,不仅深化了《原野》的主题内涵,而且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思考空间。从这部戏剧中,不仅可以看到封建社会中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探析出封建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体制下构建的“超我”对“本我”的压抑和束缚,从而最终可以发现并理解曹禺的创作意图,即呼吁人类回归精神家园,并积极张扬原始生命活力,这是曹禺为“治愈”现代社会而做出的努力,也是曹禺戏剧传达出的人文关怀和普世价值。
注释:
①④⑤朱孜莘:《曹禺〈原野〉意象简析》,《文学教育》(下)2017年第5期,第24-25页。
②③⑦⑧曹禺:《原野》,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
⑥张清祥:《曹禺〈原野〉的意象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03页-106页。
参考文献:
[1]曹禺.原野[M].北京: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
[2]张清祥.曹禺《原野》的意象分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6):103-106.
[3]朱孜莘.曹禺《原野》意象简析[J].文学教育(下),
2017,(05):24-25.
[4]卫亭绒,张天曦.曹禺《原野》中的身体叙事[J].南大戏剧论丛,2020,(01):74-83.
[5]張清祥.精神家园的渴望与失落——曹禺《原野》森林和老屋意象解读[J].名作欣赏,2003,(06):66-70.
[6]古超强.《原野》主题意蕴研究述评[J].戏剧文学,
2013,(03):79-84.
[7]向宝云.曹禺悲剧美学思想研究[D].四川大学,2004.
[8]张思雨.曹禺《原野》中的焦母人物形象描绘[J].文学教育(上),2022,(04):22-24.
[9]李玥慧.曹禺《原野》中存在的对立元素[J].戏剧之家,2019,(06):24.
[10]张婧冉.《原野》的经典化与社会的文学观念变迁[D].武汉大学,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