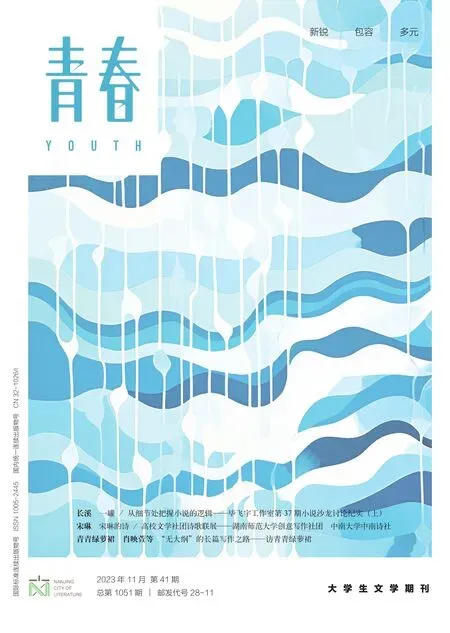画 师
2023-11-18南京大学缪政儒
南京大学 缪政儒
从前,在人们的雅兴尚未被金钱和浮躁之心腐蚀前,民间习画之风大为流行。当时有两个人,其一是阿泽,另一个唤作阿文,二人同在画师门下做学徒。和他们共同拜师的有许多人,只不过他们二人天资聪颖,才华最为出众,其他人在他们面前好像星群在满月下失了光。当时的规矩是这样的:画师持有类似商标的牌匾和印章,一代代传下去。一方面用于拓印在画作上防伪,另一方面作为流派的标志和门面,一提起来江湖上无人不晓。画师的高徒可以出去自立门派,也可以等师父封笔退休后得其衣钵。一般而言,牌匾将传于画师最得意的门生。由于大部分学徒只想谋得求生的手艺,出去自谋生路的很多。但也有不服气的,或是对所谓画技有追求的,同门之间为牌匾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的事情屡见不鲜。
后来有人传说,其实阿文的画技并不在阿泽之下,不过他太重名利,为其所累,以至于最终影响了画作的格调。这种说法现在仍是没有根据。可以确定的是,在大部分画师和天下人眼里,阿泽的画技远胜阿文。不仅如此,阿泽胸中的沟壑,对绘画根源的理解,更是远胜同时代的众多名家。比如说,二人初在师父那儿习画,都是童子,正是最贪玩的年纪。阿泽除了习画之外,整日只知在地上涂抹泥巴,抬眼看蝴蝶和落在墙上的树影。阿文不一样,能压抑天性,潜心念诵课堂上的口诀,课后一笔一画地仔细描摹,参照师父的画作加以修改,渐渐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所有人里,属他的画最似师父,这点就连阿泽也比不上。但每次习作,均是阿泽拔得头筹,阿文屈居第二。原因是,阿泽总能以妙笔天成,仿佛学习了课外书一样,在师父教授的内容上有所创新,大多是很微妙的细节。例如给近处的植株和人脸添上一笔,给远处的青山改变动势,画作就像变了质一般,和原来截然不同,有了生气。多次有同门的师兄弟向阿泽讨教个中秘诀,答案都是“这里一下,那里一下”,让人无法领悟。大概这就是无法模仿教授,只能个人领悟的天赋吧。随着他们年岁渐长,阿泽在绘画外照样每日饮酒玩乐,阿文照样在课后下苦功作画,可二人间的距离慢慢拉开了,只是他们都远超同侪。阿泽得到的典型评语是“如果没有阿泽的画,想不出有人能画得比阿文还好”。一般人听来是赞誉的话,当事人如何想就未可知了。于是,阿文一天天憎恶起阿泽来。开始是潜意识里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慢慢变成在众人面前揭露阿泽的怪癖,例如睡觉磨牙、爱咬指甲之类的,有意识地从人格上嘲笑攻击。最后竟然在交画前藏匿阿泽的画具,或是在画师面前大加贬损。据说阿泽天生性格温和,又对虚名浮利不看重,志在逸乐,就这样骄纵了阿文的气焰,以至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当时民间盛行江山画,达官贵人也争相收藏攀比。因而在一段时间内,画江山图成为衡量画师水平的标准之一。而二人所拜的师父尤善此道。一日,画师将二人招来,说是某某高官急求一幅江山图献于圣上,如果满意可能大获赏识,说不定从此步上仕途。他命二人速速作一幅样品,择优再细细创作。阿泽正在外面喝酒,大醉归来。左寻右寻找不到称心的画具,心想准是给人藏起来了。官员那边催得又急,阿泽也不恼,随手拾起地上的树枝,跌跌撞撞地走向画院后边的竹林,寻了一块空地,不知道怎么想的,竟以沙土为纸,以残枝为笔,趁着酒势哗啦哗啦,像是项庄舞剑般极为潇洒地挥动手臂。彼时强风阵阵,竹林端部的枝叶连同周围树群相互摩挲,一瞬听来恍如江边涛声。阿泽手持枯枝在风中起舞,好似散发的海夜叉擎着枪戟指挥浪涛起伏。师父知道他把画作在沙地里,扯着他脏兮兮的散发把他痛骂了一顿,然而等到和众人围观着看后,却不作声了。那个官员来看了,宽限日期选定阿泽另作。没人关注另一幅画得如何。可以料想,阿文在这之后大受刺激。不过,真正使阿文涌起杀心的还是决定牌匾归属的最终考核。考核内容是汇集全院结业的学徒,选定固定视角的景物作画,由师父本人遴选一位胜出者。这次要求绘制某处的江山风物。阿文心想,自己的画技并不比阿泽差,二人的画总体极为相似,只是师父有所偏好,偏爱阿泽罢了。无论怎样比较结果都不会变。于是阿文偷偷花重金贿赂了画院的僮仆,让他当天把阿泽灌醉了,将画卷偷出来,和自己的交换,并盖上印戳呈上。如果仍是阿泽胜出,就足以证明画师的倾向。不料却是阿文夺魁。画师悄悄将二人唤来,极其严厉地把阿泽训斥了一顿。说是没有半点心思,整天只知道醉酒度日,虽然有点天分,但是古往今来的天才有许多荒废才干潦倒去世的,像这样以后如何在江湖立足等。接着,轻描淡写地对阿文说,虽然你们二人从小一起习画,画风相似,但是画品和整幅画的取势在真正内行的人看来却大不相同。阿泽的画潇洒飘逸,你的清雅俊秀,一看便知。总是一味想成为别人,最后连自己的步调也会忘记。如此如此将二人打发走了,并没有揭露阿文的心思。
牌匾最终传给了第三者。事后有人传言,牌匾原是要传于阿泽的,只是他喜欢自由无拘的日子,一口回绝了。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两人离开画师后出去自立门户。阿泽天性自由惯了,没有师父的管束,好像鱼入大海,赚的钱马上拿去听曲喝酒了,虽然名声在外,前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但没有积攒什么产业。阿文仍是一样,兢兢业业地替人作画,声誉日隆。不仅是民间,逐渐连皇宫也对他有所耳闻。当时阿文尤其擅长花鸟画,画人像也是一绝,只是从不画江山图。阿文天生长得卑琐矮小,颇有尖嘴猴腮之相,在外貌方面常感不如人。等到出人头地,身着华衣美服,走在街上也有人作揖点头后,才抬头挺胸,算是出了气。阿泽却长得高大俊朗,谈吐儒雅,连说粗话也能引人发笑。与众学徒聚在画寮中作画时,时常有三五成群的女子觍着脸,互相拥挤着翻越外墙窥视,一看到阿泽出入就高声尖叫,多到需要驱赶的地步。阿文尤为不悦。为了在这方面胜过他,阿文早早地找了个寻常女子做妻,意为我有伴侣了你还是单身。只是出名后,阿文却想,我现在是何等人物,连京城的高官都认识我,家中的黄脸婆又算什么呢?
一天,阿文在街上游荡。靠近运河两侧的排屋上端,有向河面突出的凉廊。夏夜,常有佳人雅士凭栏作诗。阿文听见清脆的娇声,循声望去,见有几个富家闺秀嬉戏打闹。她们身着各色薄纱,恍若天人。中间那个最是美艳,打听身世,才知道是本地最大茶商的女儿,还没出嫁。因为再也没有生育能力,富商对独女特别宠爱,一直由着她对男人挑挑拣拣的性子,没有逼她尽早成婚。阿文一听,立马回家休妻,凭记忆绘了一幅美人图,把画和礼物托人赠予富商,希望能娶到他女儿。富商爱画如痴,家中有一个藏满历代名画的密室,因而格外欣赏画才。加上女儿早到了出嫁的年龄,便动了许配的心思。与家人商榷时,身边的管家却说:“阿文虽然是当今画师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如果单单比画招亲,同门阿泽更胜他一筹,何况还有江湖上各种奇人异士。把女儿许给他未免师出无名,不如公开举办画赛,就画江山图,再把阿泽叫了来,既可汇聚各路豪杰争个高下,又给您长脸。”富商大为赞同,当下写信力邀画坛中有名望的人物出席做评委,并广贴告示,特意知会了几个较大的门派和画师。阿文听后脸色煞白,几夜睡不好觉。先前,富商派人告诉阿文,提早将所命的画题告诉他,意为特别照顾,有意将女儿嫁给他。画题虽是创作一幅江山图,画幅不限,却唯独不能作在纸上。这缘于富商对绘画的理解超出传统,将画境延伸到纸面之外,风鸟虫鱼,山川河水,皆可为画。

东良《小狗花车》
阿文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某日清晨忽得灵感,即刻去市场上定制了一支巨笔。笔身一人多高,粗达猛士的臂膀,笔毛用禽兽的毛连缀而成。阿文寻得附近郊野小有名气的崖壁,用绳索捆在腰上,悬吊下去,挂在半空,用沾了白浆的巨笔在漆黑的石壁上作画。阵仗甚大,白色的墨点雨水般纷扬洒向底部的溪流,把水染浊成了乳白,四周有众多围观的乡民拍手起哄。崖壁表面有嶙峋乱石突出,甚为崎岖,本来就是充作山川的天然素材,只需寥寥数笔勾勒轮廓;江水则取平坦之处顺势涂抹。阿文站在对岸远观成果,听着旁人的奉承,心里深为得意,心想美人是否到手无关紧要,阿泽大概不能胜出,无力回天了。
富商在广发告示后,曾邀请诸多名家出席酒宴,阿泽位列其中。由于人数众多,拼凑的酒桌太长,从大厅的一侧延伸到另一端。富商一面想炫耀女儿的姿色,一面想以此为饵刺激众画师尽力,于是叫女儿出来献舞。富商的女儿名为阿平。阿平被骄纵惯了,极为讨厌这种场合。本想发脾气躲避,但当她透过酒席两侧的垂幕偷偷向内观察时,看到在座的阿泽一副超然物外的悠闲神态,只顾独自吃喝,便一下被他潇洒的气质吸引。又因为阿泽相貌出众,就借婢女打听他的名字,芳心暗许。于是阿平穿了通红的纱衣,用薄纱蒙了俏脸,颇为放肆地跳上餐桌。宾客们先是一怔,随即起哄鼓掌。阿平赤裸着有肉感的脚丫,脚趾微微泛红。接着她交叉舞步,一前一后,扭转身姿,随着音乐一步一步向阿泽的方向跳去。等到近了,她迎着阿泽的醉脸转头,使了个媚眼,屈身将长袖拍拂在阿泽脸上,从左耳到右耳。阿平问他:“我跳的舞如何?”阿泽笑了笑说:“跳得挺好的,只是不如我认识的一个人,她在酒楼做舞女。”话音刚落,阿平立刻变了脸色,跳下桌跑走了。在场的阿文以为女人对阿泽心生厌恶,就更加得意了。阿平闭门不出,过了多日,渐渐息怒了。她听说阿泽迟迟没有作画,整日耽溺酒肉,心中很是焦急。想着以他的才干定能夺魁,又因为参赛的画手全都交付作品,只剩下阿泽一人,就心忧如焚。阿平派家仆前去催逼,而请来的评委和众画师此时都在富商别院的花厅中宴饮。阿泽被人找到时,正瘫睡在酒楼的一个角落里,身上酒气熏天。他眯缝着眼,似笑非笑地对前来催促的人说:“哈哈哈,不用着急,我早就准备好啦。”说罢,拉着他相好的舞女就往茶商家里去。仆人们看他是贵客拗不过,只好放他进去。等到阿泽一瘸一拐地来到厅里,众人本来在说笑,看到他一下满座寂然。阿泽扯着舞女的手,那女人忸怩地藏在他身后,用宽大的袖子遮脸。看到这儿,连平日以宽厚出名的富商也蹙着眉,变了脸色。许多人议论纷纷,说他白日纵酒,又拉着不三不四的女人登堂,很不成体统。风闻平小姐还心许这等货色,怕不是迷了心窍,纵使再有才华,也不合适。阿泽也不恼,抚摸着肚子,朝空中打了一个震耳的酒嗝,清了清嗓子。众人安静下来。阿泽说:“我已经完成独一份的江山图了,从前没有出现过,今后也没有,是我的独创,今天给各位前辈开开眼。”他一把将舞女推到大家面前,女人捂脸的手滑落下来,露出极其貌美、举世无双的脸庞。众人为之一愣。藏在帷幕后面偷看,怒视这一幕的阿平瞬间也慌了神,倒吸一口气。阿泽接着说:“诸位都是各地的达官显贵,家中的妻妾僮仆,貌美的不计其数,但今日你们看看,有谁像这女人?她虽然出身卑贱,是我发现了她的美,把她发掘出来。你们虽说身居高位,但容我说一句僭越的话,就是当今帝王家中,也没有这等女子。我从执笔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美,没有比这肌肤更适合画江山图的了。这便是我为这次画赛所解的画题。我毕生一直在苦苦寻觅美的素材,不料却让我找到了美神本身。静观这幅画是不够的,现在,请诸位一起欣赏这一生仅一次的舞蹈吧!”
说罢,阿泽抢过仆从的笛子,为舞蹈配乐。天色渐晚,室内昏暗下来,左右宾客桌前燃了一排灯。幽暗中,女人伏于地上,随着乐律起伏,她像水蛇一样扭动身躯,屈身立起。跳动的烛光映照女人闪烁的脸庞,她明暗不定的肌体仿佛被室内的昏暗吞没。女人的头深深地埋入臂弯,缩成一团。一霎间,像是阴风穿堂,所有蜡烛瞬间灭尽。宾客们慌乱起来,有盆器侧翻的脆响。这恐惧随黑暗越来越大,甚至能听到某人喉咙压抑的嘶吼。女人猛地将头抬起,光亮一下回来了,蜡烛奇迹般地重新燃起。众人看来,仿佛在谷中起了飓风,吹得两岸树群大摆,江涛亦剧烈流动,汇于漆黑的旋涡。渐渐地,在山的彼端,有一轮硕大的月亮缓缓升起,却散发着太阳的光芒,占据半个江面。众宾客眯着眼,沉浸在驱散荫翳的温煦里……不知过了多久,有紧促的笛声将人唤起,抬眼一看,这哪是月亮啊,分明是那舞女的头!女人紧闭着眼,背后散发出神圣的金光,好像照亮了整个宴厅。众宾表情木然,一个个竟纷纷向舞女屈身下拜,只有阿泽仍在一旁吹笛。关于舞女所跳的舞,后来历史上有几种说法。有说是西域的艳舞,阿泽借此讨巧而已,实则格调不高,舞女也不过是寻常艺女罢了;有说是来自东洋的祭舞,专在神祇面前跳,配合秘乐有魅惑的效果,所以激得评委产生幻觉,向臆想中头顶圣光的女神下拜,全体陷入癔症。真实情况已不可考,总之,阿泽照常得了头筹,而阿文早在半途离席。第二天,有人在街角看到折为两半的巨笔。阿平本来满心欢喜,阿泽却托人说:“平小姐美貌过人,家世又远超常人,我们并不相配。”其实只是他爱好自由,给出去厮混找的托词罢了。三番五次,连阿平的面都不见。阿平平日多受宠爱,心气极高,青年人的情欲又如风不定。被父亲和阿泽像玩具般摆弄,静心想想,竟由爱生出极端的恨意。
画赛之后又过了几年,天下大旱,饿殍遍地。当朝的皇帝睡不安稳,唯恐乱民生事,自己的江山不保。这皇帝是他先祖众多子孙里最坏的一个。他曾经单纯为取乐,命众臣排成一列,跪在地上作为人桥,自己从他们的头颅和脊背上踏过,边走边笑,从内廷一直走到外朝,从谁那儿滑落,谁的头就要被砍下。皇帝非到万不得已,不想大开粮仓赈灾,恐怕他们轻易得到满足,滋生好逸恶劳、依赖朝廷接济的心态,便问他的臣仆,有什么逆转大旱的方法。臣仆们回答说:“王上,恕臣愚昧,风雨雷电俱是神意,不好忤逆。若王下定决心,不妨请术士和观兆占卜的前来,在神面前献祭,或许有消灾的余地。”于是皇帝召集国中的术士。第一个术士筑坛做法,报告说因王平素横征暴敛,神明降灾,还望王罪己放粮,旱灾必停。皇帝命人砍下他的头颅。第二个术士上前来,报告说我作法跳舞,神启示我王有缺欠,希望王如何如何。皇帝也砍了他的头。第三个也是如此。皇帝震怒,转头问:“难道天下没有真正的聪明人吗?没人能消解此灾吗?”侍立两旁臣仆的腿都软了。这时,术士中有个狡猾人来见皇帝说:“天道不仁,贪爱王的江山和谷物,所以暂时取去享用。王如果想索回,只需寻来全国的画师,越善于此道越好,将王的江山转画在纸上作为替身,于坛上经火焚烧献给神明,旱灾就必停息了。”皇帝大喜,重重地赏赐术士,并命人在宫外堆了一座金山,凡来献画的可以在其中取与自己头颅等重的财物;若有匪类假作画师献画,或是献画后旱灾并没有减弱,那献画之人就得留下头颅。一连多日,不管乐不乐意,有许多画师前来献画。祀坛黑气上腾,从远处都能望见。但灾殃仍不见止息。那术士唯恐性命不保,便先行一步,去找皇帝陈明:“王的江山辽阔稳固,无边无际,岂是此等凡胎俗手所能描绘的?自然骗不过神明。不如王出一道画题,宣通国最能绘江山图的人,让他作一幅画,必须囊括国的全境。”皇帝深以为然。有臣宰进言:“臣知一人,平素行事怪异,但独有绘画的才气,画山川草木尤为一绝。又有一人素来做他对头的,画技不相上下。王可召二人进宫,为王绘制江山图,又能争斗为王取乐。”皇帝听了说:“速速把二人叫来。”皇帝看他们情态各异,一人样貌俊朗,洒脱异常,在自己面前都毫无拘泥之色,只是形容邋遢;另一人矮小拘谨,但贼眼飞转,目露野心,也是人杰。皇帝见这样的搭配,一时乐极,遂忘初衷,心想捉弄他们一下。于是从宝座上一跃而下,挺着大肚子,背着手在殿里踱步,从这头到那头。皇帝开口说:“看到二位当世卧龙凤雏,甚是欣喜。又知寻常题目难不住二位。故这次的考题是如此,朕缓慢从殿翅走到殿尾的时间,你们二人要比赛作画,必须将朕的所有江山边域绘入其中,这是要点。没画全或者没画完都算作落败。赢的那个人嘛,朕封他做管理全国画师的长官,并且满足他一个愿望;至于输的惩罚…… ”
“恕草民多嘴,”阿文躬身上前说,“草民向来与这人不睦,自认有不输此人的才华,只是机缘巧合,因天道不公每次略逊于他。求王为我伸张正义,这次正是大好时机。依我愚见,王的惩罚应当是这样:输了画赛的人,当立即处死,并将技不如人的事实用快马昭告天下。”阿文为了进宫得名取财,早在家中练习画了江山图数月,以为准备充足,而阿泽终日潦倒,直到酒钱花完了才动笔。阿文打听了之后心想,如果此次仍负于他,不如一死了之,免得终生陷于为其所败的阴影里。于是变了神色,视死如归。二人坐在殿中,在抬来的鎏金楠木桌上作画,纸面不过画桌大小,怎样也无法囊括国境。这是最需要动脑的地方,如何将山河以抽象的方式表达。皇帝开始行走,刻意用力跺脚发出回音,给画师们增加压力。皇帝远观阿文满脸的汗珠,像天真的孩童般咧开了嘴。而阿泽呢,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态度,以手支额,嘴里衔着画笔,纸上一笔未动。皇帝不禁心生疑窦。过了一会儿,皇帝在墙边拍手喝止。待把画纸卷来一看,阿文绘了只雄鹰,开展翅膀,在九天翱翔。能看出鹰眼中略显出的江山景色。阿文解释说:“王的全境甚为庞大,时间又短,仆人的拙笔不能一一绘尽,唯有鹰隼鸟类才能将之尽收眼底。”皇帝唔了一声,看向阿泽空白的纸面。阿泽扑通跪在地上说:“愿王万岁!王的国度无边无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没有一支笔能将这景色绘尽,就是神笔也不行。而且草民知道天神立王治理全境,是借王手辖管天下万民。所以旱灾必速速离王而去,不必惧怕。至于我这幅画,王可知山河图的要义是什么吗?并非在于山川本身,而在于空白,即尚未被画的部分。因为无又蕴含有,包含无穷尽的变化,直达人想象的终极,这就是画机,即画的生机,只要有一线画机,图面就不至于死地。草民表达的意思乃是如此:王上的国无穷无极,且于至无处还能生出有来。无论灾变到何等地步,王的国永无绝路。”皇帝听了,连连点头,或有所感,转头对阿文说:“已经分出胜负来了,朕要昭告天下,你的画远不如他。你想置比你更好的人于死地,朕算是知道你居心不良了。无论是作画还是言语上的解释,都远不如他,你自取苦果吧!”皇帝一转身,就有人用黑袋套了阿文的头。阿文伏地爬行,抓着皇帝衣服的下摆求饶。皇帝大怒,一脚踢中他的脸。从那日起,阿文的左眼就瞎了。
皇帝转身问阿泽:“你的画我很喜欢,你要什么,全都可以给你。”阿泽用力叩头说:“今日是为王的江山求画,不可见血,阿文虽坏,终是与我同道同门。还望王饶他一命。另外,草民还有谏言。王的国无穷尽,但国中的民有限,王的良田无人耕种,就没有足数的粮上缴了。求王顾惜这如尘土般的百姓,如果要让他们子子孙孙为王纳贡,还望王能大开粮仓,存留他们的小命。如果王动怒,草民就是死也不辞。”说罢,仍是叩头。皇帝心感不悦,但不好当着群臣的面食言,于是不情愿地开仓放粮,阿泽辞官仍归原处,阿文得以保全性命。其实以上全都是民间没有根据的谣言野史。平日里放浪形骸,目中无人的狂客,又怎会摇身一变,一下变成为国为民的侠者呢?不过是寄托穷苦百姓的良好期许罢了,幻想有一位从天而降的神人能改变一切,拯救自己。最后朝廷大开粮仓估计也是臣宰进言和饥民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再说为国难求画,无论怎么昏聩的皇帝也会暂收玩心,以画的质量和完成度为首,不会想出限时作画之类的儿戏吧。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二人确确实实被召进宫作画了,画也在坛上烧了,旱灾因为时候差不多到了便停了,根本没法说是谁的画起了作用,也压根没什么生死之赛。倒是阿泽本人大概求了些财物和御令,回酒楼把舞女赎了出来,两个人一起快活去了。
关于这个有些滑稽的故事还有一个同样荒诞的结尾。传说阿泽和舞女私奔后,阿平变了性情,誓要寻机杀阿泽。阿文悄悄上门谋划说:“平小姐你这么好的姑娘,为那等小人所误,我深感惋惜。正巧我与他有仇,要不我们联手,你派家丁强买他和那舞女的房屋,不然就派人闹事强拆,在厅堂后埋伏打手和证人,等他前来理论时作伪证说他非礼平小姐,当场给他拿住,用乱棍打死。这样,事后不好查明具体是谁的罪,大不了嫁祸几个小厮赔点钱了事,我们也有回旋的余地,确保我俩平安无失。”阿平吩咐下人照阿文说的做。阿泽没有积攒钱财的习惯,也没有攀附权贵,不知道怎样处理这类事。他安慰舞女说:“都是认识的朋友,没准还是因为从前的私事生气。我们上门好言劝慰,让她心软让步。”于是同舞女,当时已经是他的妻子,一道登门拜访。阿泽甚至随身带了画具,心想若是不成,作几幅画献给茶商,阿平总要依她老爹的意思。二人踏入堂坎,阿平神气地端坐在屏风前等候,后面藏了阿文和若干家丁。阿平一见阿泽,就心软了,眼睛里噙着泪。但一看到他身后的女子,便紧咬下唇,狠心发话:“好,你想要我放你一马,那很容易。看你带了画具,正好为我作画,像从前为那个女人作画一样,我倒要看看是谁的更好。”阿文摩挲着汗涔涔的掌心,心想平小姐怎么不按说好的来呢?暂时忍耐没有发作。阿泽听了,沉思半晌,松开与妻子十指相扣的手,上前拾起阿平脱落的衣服,一件一件披在她身上,又饱含怜爱地轻抚她的发梢。阿平全程一动不动,任凭他摆弄。她脸上的几行清泪蜿蜒着爬到下颌。阿泽说:“从前三番五次拒绝你的好意是我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并不相配。你一生被人随意左右,受奸人蛊惑,现在又想要同人争个高下。我算是知道了,你生来聪明,想要做谁都很容易,但唯独不会做自己。一味将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刻意模仿,到头来在镜中一照,只会连自己本来的模样都忘记了。”阿平大受感动,正想认罪揭露阴谋时,阿文大喝一声,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手里持着明晃晃的尖刀。阿泽躲闪不及,中了一刀,刀刃从腹部进。阿泽在惊呼声中倒在地上,捂着伤口,血水不断地涌出来。阿文操刀,正要捅第二下,不料阿泽突然哈哈仰天大笑,鲜红的唇齿间泛着血沫。他蹙眉低头,怒视阿文,吼道:“你万不可杀我!我活着你或有一天能超过我,我死了你就永远无法胜过我,终生活在被我击败的屈辱里。”阿文大吃一惊,手里的刀慢了半寸,给了舞女护在阿泽身上的机会。女人一边抚摸爱人颤抖的脸,一边转头诅咒阿文。阿文狠下心说:“不管怎样,我恨你至极。今日已没有退路,我定要杀你,你们两个苦命鸳鸯就共赴黄泉路吧。”说着把第二刀扎入舞女的身体。阿泽盯着身上不断喷涌的血流,知道无力回天。他望着同覆血泊,倒在怀里爱人的朦胧双眼,轻声对她说:“我现在更确信了,你就是我的美神啊。要是我们还能在一起跳舞该多好呀。”阿泽放声大哭,紧紧地吻着她,她也用手轻抚他的头。阿平望着倒在血泊中的二人,苦涩地想,这真是上天对自己最重的刑罚了吧,我只能亲眼目送他们步入深渊,就连和阿泽一起死,也被舞女抢了先。阿平最后终生未嫁,据传她房内从地板到天花板挂满了从各地搜罗来的阿泽的画,就连他学生时期的习作也不放过。
不过呢,关于这个版本,也有传言说有当时亲历事件的家丁作证,说其实二人没受多大的伤损,阿文一蹿出来就被授意扑倒,被摆了一道,平小姐是借机为阿泽讨回公道而已。传成这样实在是太荒谬、太罔顾事实了。只是闲着没事干的酸腐文人的无聊幻想,把故事加工得更容易卖钱罢了。而阿泽经过此事重振了精神,彻底一转心性,安安稳稳卖画度日,和妻子过上了潇洒幸福的生活。至于故事之外的真相到底如何呢?现在看来反倒没人挂心,也再无从考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