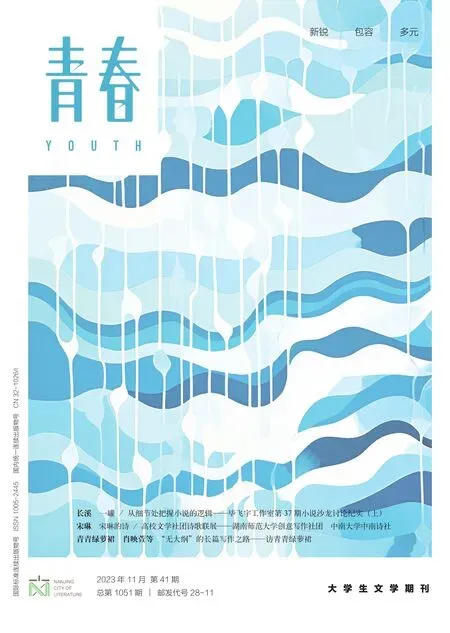抒情·废墟·怀旧
——理解孙频近作的三个关键词
2023-12-19山东大学纪水苗
山东大学 纪水苗
无论是以代际群体被概括,还是以创作关键词被总结,作家总是无法避免被标签化的命运。孙频亦是如此,她的创作被冠之以“80 后写作”“底层叙述”“女性写作”“苦难叙事”等标签。众多的标签说明孙频创作的多重面向,也说明孙频在有意识地进行叙事的实验和创作风格的转向。在孙频2022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孙频有意打破以往“生猛酷烈”的叙述惯性,代之以平和而忧伤、素朴而诗意的叙述笔调。从《我们骑鲸而去》到“山林三部曲”(《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再到《海边魔术师》《天空之城》《棣棠之约》,孙频持续书写着对自然的重返与复归,并不断扩展叙述的限域:将写作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山林湖海之中,而是让笔触伸向了更遥深的历史和文化之中。
一、诗性的叙事与抒情的面向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处理“情感”与“现实”、“抒情”与“叙事”、“内倾”与“外涉”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个人的情感世界获得广泛而普遍的经验,以及如何使历史与时代的记忆书写更具审美性,是中国小说在对传统叙事进行“创造性转换”而进入“现代”之后无可避免的问题。在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中,小说一直存在着抒情倾向,而这种内倾的抒情性在不同作家那里又有不同的风格体现。20 世纪20~40年代,鲁迅小说既抒“哀而不伤”之情,又有文化批判的反抒情倾向;郁达夫的感伤浪漫主义小说抒发强烈的主观情绪;萧红以纯粹而沧桑的笔调书写“小城春秋”的诗篇;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则执着于用“温暖与真挚的情感”塑造审美乌托邦。20 世纪50~7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激情高涨,当代文学中强烈的抒情性主要表现为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和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抒情散文。进入新时期之后,知青文学带有强烈的情感抒发和个人诉求,或书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或反思历史和人性:知青文学的不同面向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抒情性。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多位作家创作出诸多抒情意味浓郁的作品,如汪曾祺、王蒙、张洁、张承志、张炜、贾平凹、铁凝、王安忆等。岳雯在论述抒情话语在新世纪的“变声”时,将其概述为“温情主义”,并以“对朴素自然的亲近与诗意体验”“对人性理想的发现与珍视”“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与体恤”和“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岳雯:《温情主义的文学世界》,《文艺争鸣》2011 年第3 期)
来概括“温情主义”写作的特点。我想,孙频的小说对朴素日常的描述,对重情重义、不卑不亢的理想人格的描绘,对人间真切情义与和谐关系的讲述,对人面对无常命运时的韧性的表现都可以当作是此类“对生命抱有暖意关爱的写作”的例子。
《鲛在水中央》在第五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的提名奖颁奖词为:“孙频的写作从容大气,抒情气息浓郁,人物命运的浮沉、社会现实的变奏,都在诗性的叙述里得到丰富呈现。”由此可见,“抒情”和“诗性”是解读孙频小说的关键词。孙频小说抒情性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立足个体的感性生命,试图通过肆意勃发的情感、哲理丛生的思想、完满纯熟的技法以及绵密蕴藉的语言来探讨人的枷锁与自由、内心的痛苦与平和、存在的艰难与解放的可能。这是生命的荒芜与灵魂的丰饶、心灵的黯淡与生命的张扬交错而迸发的诗意;这是形体的孤独与思想的蓬勃、肉身的沉沦与精神的突围交织而迸发的诗意;这也是孙频试图在生命的废墟之上通过自然的召唤恢复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诗意瞬间。抒情性在孙频小说中,主要通过抒情式叙事、诗性意境、情义世界来建构。
其一,抒情式叙事。陈平原认为“诗骚”是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之一,而“‘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引‘诗骚’入小说,突出‘情调’与‘意境’,强调‘即兴’与‘抒情’,必然大大降低情节在小说布局中的作用和地位”(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孙频的小说常有很好的故事内核,其故事性和传奇性让读者乐此不疲,但孙频新近发表的小说不再刻意突出故事的传奇性和曲折性,而是着意表现人物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诉求。如在《海边魔术师》《棣棠之约》《天空之城》中,尽管孙频仍然设置了小说的悬念——刘小飞到底去了哪里?戴南行于何处漫游?杨声约为何失踪?——但是她不再着意于解密,而是重在展示人物心里的波澜。因而,孙频常在叙述中以饱含情感却不泛滥的笔调表现情节发展和人物的情绪起伏,如戴南行在参悟具象与实质之后,感悟到“春日的雨滴,夏日的蝉鸣,秋日的凉风,冬日的雪花,把这无法留住的一切做成标本,就是诗。每一株植物是诗,每一个星座是诗,跳动的烛光、炉子里的火苗、茶杯里的新茶都是诗,蜜蜂采的蜂蜜是金色的诗,夜是黑色的诗,友谊是血红色的诗,所有的这一切放在一起就是诗集”(孙频:《棣棠之约》,《钟山》2022年第4 期)。像这样具有哲思、抒情性与审美性的表述在孙频小说中俯拾皆是。
其二,诗性意境。文学是情感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那么小说则往往由情而景而意境。“小说中的‘意境’是一种‘场面’化的‘情旨’。把‘情’景化,把‘景’情化”(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意境即情景交融。“黑色的夜空倒扣在大地上,大地上没有一丝光亮,连河水都是黑色的,从我们脚下流过的时侯,带着一种可怖的幽冥之气。而古老的星座像神话一样悬挂在我们头顶,就连我们脚下的巨石也散发出某种精神场域,仿佛天地之间的一切都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孙频:《棣棠之约》,《钟山》2022 年第4 期)。赵志平和戴南行阔别重逢,饮酒畅谈,天地万物都被赋予了灵性,星空辽阔灿烂,宇宙永恒,而戴南行有志于做月光下的漫游客和大地的守夜人。正如朱光潜所说:“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著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这番情境既有“景”之诗意,又具“情”之诗性。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之中,戴南行领悟到个体之于时空正如一粟之于沧海,因而将对逝去时代的执念、自我的失落与痛楚化作于天地间漫游的自在。
其三,孙频小说的抒情性还表现为以情义之柔调和与现实的紧张感。在《棣棠之约》中,桑小军可以为戴南行的房子问题只身犯险,戴南行亦可以为桑小军自愿入狱,桑小军为戴南行的诗集梦想替他自费出版,而戴南行则为桑小军的文学理想选择永行路上。《海边魔术师》中海岛上形形色色的人,或是拒绝开发的土著居民,或是被迫逃离至此的外地人,但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温暖。《天空之城》中的刘静默默等待着失踪的杨声约,即使在杨声约残疾之后,刘静仍然对其不离不弃。孙频在小说中没有以叙述者的口吻对人物多加议论,也没有用绮丽冗长的语句反复渲染,只是以朴素的笔调讲述无常的历史中人与人之间永恒的温情,自然而然使作品流露出抒情意味。
尽管孙频小说有强烈的抒情倾向,但她没有刻意通过打破叙事的完整性和内在的逻辑性而使小说获得诗性品格,而是更为注重保持抒情与叙事、情感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从而使得小说在保持情感饱满、诗性浓郁的同时,亦对历史、时代、现实有所指涉。
二、历史的记忆与时代的痛感
孙频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既定秩序的边缘者,甚至是社会现实的溃败者,他们游离在主流社会和现代生活之外,在各自凋敝的漫漫人生路上踽踽独行。在近期小说中,孙频依然在书写失意者,书写着他们失意生活中的诗意瞬间。《海边魔术师》中的刘小飞,因偷窃入狱而被家庭和社会排斥在外;《棣棠之约》中的戴南行、桑小军、赵志平失落于20 世纪80 年代理想主义的溃败;《我们骑鲸而去》中的“我”、老周、王文兰无一不是过往生活中的失魂落魄者……孙频在一个个灰暗又明亮的故事之中,不仅洞察到人性的晦朔与明媚,还在人性的隐秘幽微处察觉到历史的脉动。在这些荒芜又丰饶的生命之中,她不再痴迷于对“沉重的肉身”的书写,而是向生活的更深更远处、向生命的更隐秘处、向历史的更幽微处,探寻人性的可能以及精神的出路。
孙频的小说几乎都关涉时代记忆、个人创痛以及对历史、人性、生命的反思,与此同时,她常在小说中设置“乌托邦”来探寻个人精神困境的出路。孙频显然是一位对生活、对历史、对时代有所思且有所得的作家,她不满足于仅仅描写个人的情感经历和经验世界,而是着意于“通过介入历史的方式——这个历史也显然不是她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试图构建出个人与历史、与时代、与世界之间的一种错综复杂的生命面相”(韩松刚:《孙频小说论》,《上海文化》2019 年第7 期)。《天空之城》中的刘静毅然决然地反抗自己“工厂子弟”的命运,不知疲倦地攻读学位并以此来寻求自我解放。杨声约由插队的北京知青与当地女子结合而生,但他的父亲后来抛妻弃子,母亲精神失常。杨声约从师大历史系毕业之后,返回老县城,徘徊于仰韶文化的废墟之上,乐此不疲地找寻昙鸾墓葬。刘静和杨声约显然都背负着时代给予个人的创伤和痛感,他们无法摆脱这些创伤,只能不断向历史的更深邃处,向文明的更遥深处漫溯,并从中汲取超越创伤的力量。《海边魔术师》中的刘小飞行窃成瘾,后因行窃失去了学业,也失去了家庭的庇护。此后,刘小飞辗转于县城的各个角落却总是无法找到心灵的归依,直至他决定以“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行走在大地上”。在行走的过程中,刘小飞认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并在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和神秘旖旎的自然风景中与过往的自我和解,找寻到精神的依归。《棣棠之约》中的戴南行、桑小军、赵志平在20 世纪80 年代为理想主义所鼓舞,却在“光辉岁月”流逝之后,惶惑于20 世纪90 年代的浪潮之中。他们曾在20 世纪80 年代热情地讨论诗歌,在月下酌酒,在大地漫游,然而,“20 世纪80 年代那种逢人谈论诗歌和文学的酒神精神正从山城上空悄然消退,所有人忽然集体转向,抛弃了不久前的价值观,转向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这个过程发生得如此之快之迅速,简直让人措手不及。人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怎么当官和挣钱,怎么炒股和下海”(孙频:《棣棠之约》,《钟山》2022 年第4 期)。20 世纪80 年代的理想主义在20 世纪90 年代全面溃败,与理想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陷入恐慌与焦虑的精神困境之中。赵志平决心随波逐流以缓解痛苦,桑小军以拒绝谈论诗歌的方式来反抗现实,而戴南行则选择以拒绝谈论世俗、沉迷象棋和《易经》的方式来卫护理想主义。然而,遗忘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现实视而不见,抵抗亦不意味着能与世界相安无事。他们在持续的痛苦中抗拒,又在不断的抗拒中痛苦。戴南行无疑是三人中痛苦最甚但也是真正从痛苦中解脱之人:他从早期具有表演性质的漫游走向于天地间“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真正的漫游,从狭窄、局促的个人世界走向辽阔、深邃的宇宙空间。
孙频的小说一直试图通过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遭际来使小说获得历史感和纵深感,试图通过多维度的情感面向来消化时代记忆、弥合历史创伤。如果说在《河流的十二个月》中,孙频尝试将文学作为王开利、李鸣玉、储东山、张谷来精神自救的出路,那么在新近发表的小说中,孙频则将精神解放和自我救赎的路径设置在更深邃的文明、更辽阔的天地之间。无论是头顶的月光和满天星斗对刘小飞内心创痛的抚慰,或是仰韶文化对杨声约和刘静空虚内心的盈满,或是漫游于天地对戴南行心境的平和,孙频都将精神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无有边际、无所制约的自然宇宙和文化文明之中。如果说《河流的十二个月》中王开利的死以及其他三人的无动于衷预告了寄情于文学的精神自救之路的无望,《我们骑鲸而去》中老周的失踪、“我”复归现代生活说明了一切逃离都是失效的,那么《棣棠之约》《海边魔术师》则以戴南行的精神自由、刘小飞的精神解放彰显着永恒的自然时空对人的渡化:“无论走到哪里,白天都能看到太阳,晚上,在我的头顶都有月光和满天星斗。一万年前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是我们内心真正的安慰”(孙频:《海边魔术师》,《收获》2022 年第1 期),“我坐在这河边,看着河水,看着黑夜,数着星星,发现万物静美,内心里温柔宁静,没有一丝恐惧,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得到和失去,现在任何人任何事都勉强不了我”(孙频:《棣棠之约》,《钟山》2022 年第4 期)。刘小飞和戴南行都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或是被迫之举,或是主动选择,但他们都在无有边际的自然时空中感受着有限生命的无限延展,领悟存在的真实与生命的真谛。自然对刘小飞来说,是众生平等无所差距的存在,是理解所有并宽宥所有的存在。因而,刘小飞在感悟自然的过程中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刘小飞的父亲也在寻找刘小飞的路途中谅解了他和自己。天地对戴南行来说,是诗的具体形态,是一部完满的诗集,是生命的栖息地,是灵魂的徜徉地。因而,戴南行在漫游天地的过程中领会了个体的有限和无限,参悟了生死的虚无与实际。诚如孙频自述,在辽阔的天地之中,“人会忽然被这来自宇宙间的巨大力量击中,仿佛是触摸到了一只巨兽的鼻息,苍茫辽阔而温柔,人会忽然觉得自己与脚下的那片落叶其实没有多少区别。如此一来,那些不甘、那些悲怆、那些屈辱,所有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感,竟都烟消云散了,心境里多了几分澄明与豁达,如月光皎皎,悬于心上”(孙频:《物对人的渡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1 年第5 期)。
三、记忆的废墟与怀旧的未来
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认为,“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之中。在这种伪装之下,历史呈现的与其说是永久生命进程的形式,毋宁说是不可抗拒的衰落的形式”( [德]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版)。也就是说,废墟不只是荒废的场域,而是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时代印记的载体。废墟是一种历史的空间,这些废墟并非只是象征过往的一曲挽歌,而是历史与现时的“静止的辩证”的形象;它们显示了历史与现时的共处状态以及未来潜能的多样性。废墟的寓言性即在于它所彰显的历史内容和未来指向,它蕴含着荒凉、颓唐的美感,同时也蕴涵着新生与未来。
在孙频的小说中,废墟之义并不只局限在具体事物的崩溃之上,还包含人物精神的荒芜。一方面,“废墟”指涉实体的溃败。在《天空之城》中,纺织厂是一个由五湖四海的异乡人组成的空间,它没有历史更没有文化积淀,犹如天外来物一般降落在千年古城里,其后,纺织厂因为商业开发而成为坍塌的废墟。由热闹拥杂的工厂变为坍圮的废墟,由人声鼎沸到人烟稀少,“纺织厂如经历战争一般彻底成为一片废墟”,“灯火寒凉,危楼幢幢,废墟的效果更加立体逼真,这让我们感觉自己已经不属于人类社会了”
(孙频:《天空之城》,《十月》2022 年第4 期)。与曾经繁荣的纺纱工厂相比,坍圮的废墟百废待兴,而原属于纺纱厂的工业荣誉则变得黯淡无光。在这个意义上,“废墟”指涉实体的衰败与没落。另一方面,“废墟”指认的是精神的荒芜与失落。在《海边魔术师》中,偷盗行窃成为刘小飞的精神暗疾,也成为刘小飞生命的枷锁。《棣棠之约》中随着20 世纪80 年代理想主义的消失,曾对文学抱有全部热情的赵志平、桑小军、戴南行陷入了人文精神失落的精神危机之中。在这个层面上,“废墟”指涉的是精神上的失落或心灵上的空虚。
在本雅明看来,废墟具有寓言性,这体现在不注重形象与感知整体性的表达,而是从整体的碎片和裂缝中发现其背后所指涉的意义,从而发现新生的力量。废墟“不是通过可见可触的建筑残骸来引发观者心灵或情感的激荡:在这里,凝结着历史记忆的不是荒废的建筑,而是一个特殊的可以感知的‘现场’”([美]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肖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天空之城》中所谓“天空之城”是指纺织工厂,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建立,又在商业开发浪潮中成为坍圮的废墟、再起的高楼。从纺织厂的新生——废墟——新生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的社会印记,也能看到企业改制、下岗潮的时代记忆。尽管孙频也对“天空之城”的消失感到惋惜,但她没有因而陷入哀伤与绝望之中,她借刘静之口表达自己对“废墟”的认知:“万事万物都各有使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是一种荣耀,这座纺织厂也不是没落了,它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到底还是荣耀的。”(孙频:《天空之城》,《十月》2022 年第4 期)也就是说,尽管纺织厂成为衰落的象征,尽管纺织厂的废墟上已经建起楼房和商业街,但其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历史语境之中,纺织厂也没有因为成为废墟而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相反,历史的故事都成了它的“前史”,并孕育了新生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孙频新近发表的小说流露出对理想主义、理想时代的重返意识以及对已逝去的文明文化的怀旧意味。如《海边魔术师》中刘小飞选择复归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给刘小飞带来了精神的解放;《天空之城》中刘静被偶然发现的仰韶文化废墟所震撼并沉迷于历史研究之中;《棣棠之约》中戴南行、桑小军、赵志平三人一直深切缅怀着热烈而激荡的20 世纪80年代,甚至于戴南行一直以自我实践着20世纪80 年代的酒神精神和理想主义。在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看来,“初看上去,怀旧是对某一个地方的怀想,但是实际上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怀旧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怀旧意欲抹掉历史,把历史变成私人的或者集体的神话,像访问空间那样访问时间,拒绝臣服于折磨着人类境遇的时间之不可逆转性”([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可见,怀旧所处理的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涉及的是历史的不可返回、现时的无可把握以及个体的有限性。
孙频作为一个对创作有清醒认知和对历史有相当思考的作家,她并没有让小说中的人物沉溺于怀旧的感伤中,没有让他们沉浸在虚幻的个人神话之中,没有让他们被情感所羁绊、被想象的浪漫所纠葛,而是让他们对“光辉岁月”的怀想成为对现实和未来的指引。因而,《棣棠之约》中曾痛苦于人文精神失落的戴南行领悟到20 世纪80 年代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存在于心灵的深处:“我原来以为20 世纪80 年代的酒神精神和理想主义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就彻底消失了,为此经常怀念那个时代,后来我想明白了,它们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由阳而阴了,只要时光不灭,人类一息尚存,它们就还会由阴而阳。”(孙频:《棣棠之约》,《钟山》2022 年第4 期)孙频对理想主义的“重返”以及对“重返”局限的思考可以看作是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所认为的“反思型怀旧”:“反思型的怀旧更多地涉及历史的与个人的时间、过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反思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静态。在这里,焦点不在于再现所感受到的绝对真理,而在于对历史和时间逝去的思考。”([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对于修复型怀旧而言,过去应该是被完整还原的,而不应该显露出衰败颓唐的迹象。反思型怀旧则更注重对集体记忆、历史逝去的思考。在孙频的小说中,反思型怀旧存在于对往日家园的幻想之中,与此同时,她又在废墟之上尝试通过日常琐事的历史来再现凝固的时代记忆、把握所处的时代。孙频不仅对历史记忆和时代痛感进行着反思,也对小说的思想进行着或深刻或革新的表达。
孙频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的作家,她以“抵抗遗忘”的方式切实而诚挚地书写着时代记忆和记忆中的痛感,同时,她又不断以纯熟的写作技法讲述着个体迥异的故事。无论是《海边魔术师》还是《天空之城》或是《棣棠之约》,尽管小说中的疼痛感仍然存在,但孙频都在有意打破以往“生猛酷烈”的叙事惯性,代之以更为从容、更为轻盈的叙事风格。孙频正通过新的故事和叙事风格,探索小说的文体结构,丰富小说的思想内涵,但究其根本,孙频一直在意的仍是人的生命与枷锁、艰难与自由,这是她对心灵荒寒但生命炙热之人的爱与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