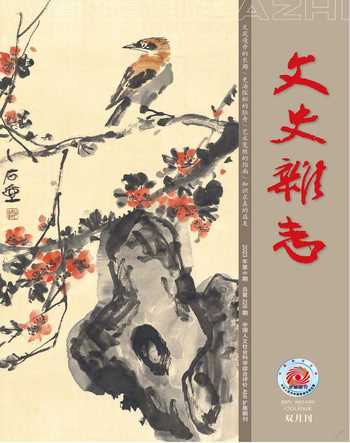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早期交往的档案印记
2023-11-17谢鸿波王楠李开
谢鸿波 王楠 李开


摘 要:成都市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表明,20世纪上半叶,成都与德国在外事、商业、旅游、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方面颇有交往。从结果看,早期的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的关系以德国来成都的单向交往为主,保持了“尊重与平等”的原则,具有“开始早,有广度,缺深度 ”的特点。
关键词:成都;德国;交往;历史档案
一、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打开。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烟台条约》(1876年)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85年)签订之后,重庆成为通商口岸,美、英、法、德、日等国相继派驻领事。由于成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各国通过各种机会向清政府施压(比如1895年发生的“成都教案”),要在成都设立领事。尽管清政府并未同意,但是,各国驻渝领事总是以各种借口经常到成都寓居,久而久之,就以“驻川总领事”自称。当时的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多听之任之,不予抵制,甚至以礼相待。直到上世纪40年代,也只有英国(1942年)和法国(1945年)的驻蓉领事才得到民国政府的正式承认。[1]
在这个大背景下,1904年,德国驻渝领事获准可以到成都寓居办公。不久,德国人弗里茨·魏司以“大德钦命驻川正领事”名义在成都设立“大德领事署”。如前所述,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德国驻成都领事馆;但它实际上开启了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的正式交往。成都市档案馆的清末和民国档案保存比较完整,其中有与德国有关的大量档案资料。通过梳理这些档案,可以勾勒出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关系的早期轮廓,从而为今天提供借鉴。
二、外事方面的交往
尽管德国与美、英、法等国一样很早在成都设立了“领事”,但是,纵观整个20世纪上半叶,相比于其他几个国家,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在外事交往上非常少,没有重大活动。双方不多的交往基本保持了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大体能够按照国际公约、中德协议,以及成都本地规定办事。比如档案显示,1913年德国领事魏司就德侨在过城门时被扣留马匹,遭“任意搜检”一案向成都军事巡警厅“函告请查”。函件以“敬启者”敬语开头,要求对德人“和平待遇”,“勿令侵害其自由”,要“符彼此优待之约”,最后以“此颂日祉,领事魏司谨启”结束。成都军事巡警厅很快处理完毕并回复称“来函敬悉”,告知“已饬各署所及各门”,要求“须和平待遇,不得稍涉造次”;最后“此复即颂公安”。[2]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我国与德国是非直接交战敌对国家,但是,当时的成都政府能遵照国民政府对德政策的要求,比较友好地处理与德国或德侨有关的事务,没有歧视。比如档案显示,1919年2月,作为敌国的西门子电机厂经理宝尔德需要遣送出境。此时宝尔德的妻子因小产患病不能成行。成都市政当局没有强制执行,而是先后派遣了中西医4人为其妻诊疗,详细记录病情,开具药方,并延长了宝尔德的离境时间,直到病情痊愈才遣送出境。[3]
三、商业方面的交往
成都与德国在商业上交往开始得比较早,但并不频繁,而且主要是单向的,即只是德国企业将商品销售到成都。在这些企业中,有两家德国企业最引人注目,它们是西门子和拜耳。这两家当今世界500强企业早在100多年前就来到成都。西门子公司为了发展在成都的业务,先后成立了成都西门子洋行和成都西门子电机厂。档案显示,1917年西门子与成都電话局、成都陆军电话局、成都商业场电灯公司分别签订了机器购买合同。[4]其中,与成都商业场电灯公司的合同金额达到40万两。成都启明电灯公司与西门子公司合作最密切,除了经常向西门子采购机器设备外,1937年还与当时的上海西门子公司就汽轮交流发电厂的建设规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5]20世纪初,拜耳的产品就进入了成都。1922年的一份档案显示,拜耳颜料厂的颜料已经在成都销售一段时间了,且有一定影响力,以至于有假冒产品出现。1925年拜耳颜料厂“因推广销场”需要,委托成都市盐市口街17号的华商锦丽公作为代理分销处销售其产品。除了西门子和拜耳,档案中还能看到:当时在成都销售产品的德国企业还有柏尔格曼、大而马纳、业嘉颜料、勃搿门等。成都的一些学校和地质研究所采购了产自德国的仪器设备。市面上还出现了德国钢丝布、德国药品、德国仪表等产品。此外,还出现了专门做成都与德国之间商贸的实体。在成都市档案馆所藏档案中,就有德商礼和洋行、德商泰来洋行、德商兴华公司等实体。他们主要从事将德国商品引入成都的业务。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实体从成都往德国销售产品的相关档案。
四、教育科学方面的交往
德国在成都设立“大德领事署”后,与成都在教育科学方面的交往也开始了。档案显示,1913年,德国在成都开办了第一个教育机构——德文专门学校,并附设中学校。其位于成都鼓楼北三街89号,直到1917年“一战”期间被迫停办。[6]这所学校是被官方承认的四川第一所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7]20世纪20年代,成都开始出现去德国留学的学生。喻正衡、黎纯一等人1923年留学德国的护照存根说明他们有过一段留学德国的经历。[8]从彭道尊和张国元1931年申请注册医师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毕业于德国佛朗府大学和魏滋堡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9]此外,一些德国的科研人员也来到成都来开展科研活动。比如档案显示,1927年,德国人傅德利在灌县采集了虫类标本10箱运回国,为“学校及博物院考究陈列”使用。[10]1938年,德国研究人种学和人身构造学的大学教授艾克富伯爵到成都进行“人体考察”,以“资学术之研求”。成都市政当局根据他的请求提供了三代居住在成都,且22岁以上的男女各100人供其进行“头、面、手部”的人体测量。[11]
五、游历方面的交往
自清末重庆开埠以后,就有外国人经由成都到四川游历的。据《成都外事志》记载,1904年德国驻渝领事获准可到成都居住商办公务后,有不少德国人来成都游历。在我们的档案中,自1913年开始,可以看到有德国人来成都游历。这些德国人有传教士、商人、工程师、企业经理、公务人员、考察家、以及无明确身份者。从这些游历档案中可以发现,有不少带有明确身份的德国人并非是单纯的旅游,而是有其他目的。比如1937年的一份档案显示,德国工程师斐士赉来成都游历,其目的是“考察厂址”。[12]1941年,德国大使馆参事携带华浮洋行和德商合步楼公司来蓉游历,其目的是考察商务。[13]
六、其他方面的交往
除上述情况外,成都与德国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一些德国人因为各种原因在成都加入了中国国籍。比如档案显示,德国人江希德因为是犹太人,“二战”期间来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其丈夫江声涛是中國人,江希德本人于1944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国籍。[14]德国有关方面在军事上与成都也有一定的交集。1935年的一份档案显示,德国人波勒受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从本年起在成都凤凰山教授军事课程。[15]在医疗方面,除了一些在成都的德国教士从事医疗工作外,1936年,德国还派出了一支医疗队到成都进行考察。另外,20世纪上半叶,德国民间与成都民众或社团也出现了一些交往。档案显示,1917年,成都人沈雨伯等人与德国人瓦格尔等人曾短暂组织过一个民间组织,开展“游艺”活动。1937年,根据德国远东协会来函请求,成都市同业商会为其提供了成都市“劳动服务”。
七、结语
综上,根据成都市档案馆现有馆藏档案显示,自1904年始,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在经济、外事、教育科技、旅游、医疗、民间往来等领域有比较全面的交往,形成了早期的档案印记。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的早期交往具有“开始早,有广度,缺深度”的特点。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基本保持了“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此外,在双方的互动中,成都是比较被动的,以德国到成都来开展各种活动为主;而成都除了有些去德国留学的人员外,几乎没有主动到德国去开展其他活动的。
今天,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的交往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双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深入和广泛。正如德国前驻成都总领事任汉平所说:“现在,德国不管是政治界还是经济界都意识到,这里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大门。而在两国合作当中,成都乃至四川地区积极、健康的表现,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晴雨表。”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成都与德国有关方面早期良好的交往传统会在新时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彼此之间会有更美好的合作未来。
注释:
[1]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成都市志(修订本)》第30册,方志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4页。
[2]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127-00-159-6。
[3]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93-06-2519-11。
[4]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127-00-165-8。
[5]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111-00-243-2。
[6]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93-06-2518-9。
[7]塔玛拉·魏司:《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8]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127-00-101-17。
[9]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38-19-38-22。
[10]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127-00-53-5。
[11]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93-02-5840-2。
[12]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93-02-6495-7。
[13]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038-02-1406-24。
[14]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38-02-1393-19。
[15]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093-04-13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