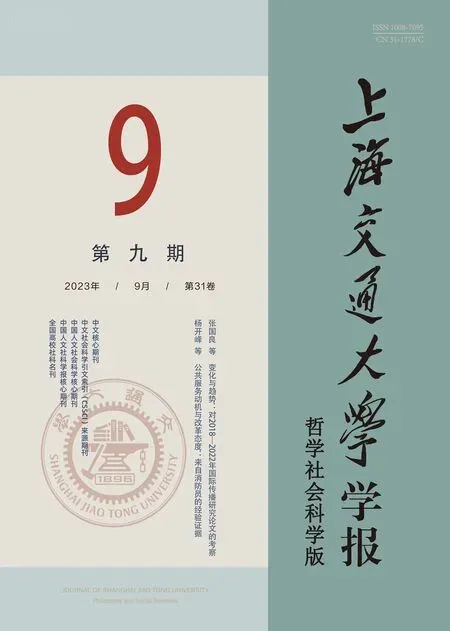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2023-11-14陈良雨
陈良雨 沈 华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
一、 问 题 提 出
高校乃是承担科技强国重任的核心主体之一,其科研创新绩效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强弱。近些年,对于高校科研创新发展而言,涉及的热门问题之一就是原始创新能力问题。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将“学术探索与服务国家需求紧密融合,着力提高关键领域原始创新”(1)《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8年8月8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55477.htm,2022年11月11日。,即高校的学术研究需要与国家发展需求相联系,并强化关键领域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同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其中也强调,要实现创新引领,则需要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突出的位置(2)《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的通知》,2018年7月19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moe_784/201808/t20180801_344021.html,2022年12月10日。。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在创新发展上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视,国家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提升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原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高等教育领域内原创成果不足,还需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进行重大突破。原始创新能力突出“原创性”“突破性”,但当前中国在国际科技领域中面临“卡脖子”技术难题,这直接体现在原创性成果的缺乏,并折射出基础研究上还存在薄弱环节。而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重要主力军之一,关系到创新人才的培养,更是需要承担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重任。因此,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进行研究的现实价值也凸显出来。
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们已经关注学科建设与高校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在学科组织模式层面,有研究指出,政府支持与学科群协同模式,有利于在实践中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3)吴伟、孟申思、余晓等: 《政府支持与学科群战略协同如何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基于两所地方高校的案例分析》,《高教探索》2020年第10期,第23—27页。;跨学科组织与创新知识生产紧密联系,且跨学科组织融合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知识创造价值的理性诉求(4)陈亮、徐林: 《跨学科组织融合: 知识创造价值的理性诉求》,《现代大学教育》2022年第38卷第4期,第72—82、112页。。又如在更进一步的学科交叉层面,有学者认为,学科交叉融合是开拓前沿领域、创造新知识、发现新理论的重要助推剂(5)张新培: 《学科交叉场域的功能失灵及其治理路向》,《高校教育管理》2022年第16卷第1期,第61—71页。;学科交叉也是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6)姚乐野: 《以学科交叉融合赋能本科创新人才培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4—19页。;多学科交叉还是协同创新网络的重要表现(7)房银海、谭清美: 《协同创新网络研究回顾与展望——以复杂网络为主的多学科交叉视角》,《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年第42卷第8期,第17—40页。。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学科组织模式有利于高校的创新活动,尤其是在微观领域如学科群或学科交叉这种模式,更有利于知识和理论的创新。从上述研究可见,对于高校创新活动,学者们已在学科建设上做出有益探索。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在于,除了学科建设对高校创新实践的一般意义之外,是否还存在具体的学科建设领域支撑高校创新实践?如果有,其驱动的机理是什么?又应当通过怎样的机制建设来拉动高校的创新实践?为此,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本文以学科组织建设为观测点,通过探究学科组织中的学科群落生态模式,来明确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期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发现提供思考方向。
二、 概 念 界 定
(一) 学科群落生态
学科群落生态是从群落生态视角来理解学科间交互关系的概念,是借鉴生物学中物种的群落关系来考查教育学中学科的群落关系。从理论适用性来看,群落生态理论在研究问题性质上与学科建设具有相似性,其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内部要素的互动性上可以对学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整个学科系统建设提供观测点(8)陈良雨、汤志伟: 《群落生态视角下一流学科组织模式研究》,《高校教育管理》2020年第14卷第1期,第8—15页。。在群落生态理论中,群落生态是不同物种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构成的组合结构单元(9)尹钧主编: 《农业生态基础》,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群落生态描绘出不同物种之间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强调物种与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动态适应性,并突出该环境中的群落特征及作用。其“物种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环境适应特征”“组合结构单元”等,与高等教育场域中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学科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学科组织模式等具有较强的契合性。研究问题性质的相似性,为物种的群落生态与学科的群落生态的类比研究提供了参考。在群落生态视角下,学科群落生态就是由若干同类或非同类的学科通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特定组合结构单元的关系总和。根据该概念界定,学科群落生态指向不同学科之间动态调适而形成的群落环境,相较于单纯的学科群而言,学科群落生态除了具备与学科群一样的学科单元组合形态这一静态概念外,还更加突出不同学科单元之间的互动适应这一动态行为。
学科群落生态一方面表现出生物种群间的生态性,另一方面又结合了学科知识的自有特征,其特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群落功能的协同性。在群落生态环境中,不同的生物种群之间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虽然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结构,但整体上表现出集合体的形态(10)陈阜、隋鹏主编: 《农业生态学》,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页。。群落生态环境下的生物种群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作用基础之上形成集合力量来维系生态的平衡关系,从而在群落功能上呈现协同特征。由此,学科群落生态中的若干同类或不同类的学科也不是一座座“孤岛”,同样也是依靠各类学科协同发展来维系整个学科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并以其“协同性”来突出学科间在功能发挥上的整合力量。其次,群落关系的交融性。群落生态环境中物种间存在相互作用的现象,其中就包括互利共生,并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11)罗宾·康迪斯·克雷格等主编: 《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张天光译,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即种群之间除了存在竞争关系之外,还存在相互依存关系,这使得双方都能够在生存中持续获益。那么,在学科群落生态中,不同的学科之间在相互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存在共生关系来增进学科间的互利共存,其对应现实中学科交互关系上就是“交叉融合”,这是学科间共生关系的写照。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进一步诠释了学科群落生态环境的交互性,也正是交叉融合的存在才使得整个学科群落生态的多样性得以持续。最后,运动状态上的重组性。群落生态环境指向一定时间和地域内不同种群的组成结构,这种构成关系并非杂乱无章的状态,而是协调有序与有机的组合(12)梁士楚、李铭红主编: 《生态学》,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7页。。这种特定的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也在于不同生物种群在运动状态上的有机、协调组合。那么,在群落生态视角下,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系同样也不是杂乱无章、随意结合,而是由具有知识互补性的学科基于各自的发展需求而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的协调组合。因此,在学科群落生态中,学科知识的运动状态也可以呈现“协调重组”,这种“知识重组”的过程也使得不同学科在动态交互过程中开辟新的学科知识领域。
(二) 高校原始创新能力
关于原始创新,有的学者认为“它体现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或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突破性技术”(13)邢纪红、龚惠群: 《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南京高校的实证研究》,《江苏高教》2017年第3期,第44—47页。。该界定将原始创新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在该领域能够创造或开发前所未有的发明或技术的能力,突出该项技术或发明在发展史上的“前所未有”;二是从现实价值上突出该项技术或发明的“重大意义”与“突破性”。有的学者认为,原始创新必须是首次的发现与成果,是针对自然、社会规律、事物机理、新型科研成果等方面的首次发现,并对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起决定作用(14)王云飞: 《基础前沿科学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机制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8年第36卷第5期,第1—4页。。该界定不仅肯定了原始创新在研究成果或发明上的“初创性”,还着重指向一个原始创新的重点领域——基础研究领域,突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紧密联系。有的学者认为,原始创新在指向研究的科学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具备颠覆性,即不仅在科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可信度,还会产生新颖性并令人惊叹(15)Thomas Heinze, “Creative Accomplishments in Science: Definition,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Examples from Science History,and Bibliometric Findings,” Scientometrics, vol.95, no.3 (June 2013), pp.927-940.。在该界定下,原始创新表现为兼具重要科学研究价值与颠覆性认知的活动,突出对前人研究成果、研究观点的“创造性”颠覆。还有的学者认为原始创新就是第一次获得问题解决的方案,且在此之前没有相似的案例可供参考(16)Richard Adams,Perceptions of Innovations: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Innovation Classification, PhD Thesis, United Kingdom: Canfield University, 2003.。那么,在该界定下,能够创造性提出前所未有的方案都可以视为一种原始创新活动。根据国内外相关学者对原始创新的理解,原始创新的特质聚焦于“前所未有”“突破性”“颠覆性”“基础研究”等关键词上。原始创新可以理解为在对规律认识、机理发现、研究探索中创造前所未有的、具有突破性、颠覆性的重大发明或发现的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原始创新能力则可以理解为在对规律认识、机理发现、研究探索中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具有突破性、颠覆性的重大发明或发现的能力。
其中,原始创新实践在主体上具有多元性,即企业和高校都是推动原始创新的重要主体,但两者在原始创新上又存在本质区别。企业的原始创新更加关注市场导向,突出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而高校原始创新则更加立足于基础学科探究,注重利用知识资源和学科优势等来实现原创突破。因此,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可以理解为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创造前所未有的、具有突破性、颠覆性的重大发明或发现的能力。首先,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表现领域为基础研究。即通过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基础学科领域的原理、机理以及相关规律的探寻与创新发现,高校在上游学科领域获得突破,为应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原理或理论支撑。基础学科的发展状况可以成为衡量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只有基础学科得到充分发展和挖掘,其他相关应用学科才能获得“源头活水”。其次,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突出“前所未有”。高校在科研领域创造“前所未有”的发明,就是该领域发展史上“从0到1”的超越。这体现出对以往技术“历史空白”的填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科研创新自主性的增强。于是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就可以从其科研创造发明是否实现了“从0到1”的根本性转型来考察。再次,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表现在技术的创新突破上。即通过新技术、新发明的创新突破,高校能够有效应对“卡脖子”问题,并扭转技术上始终受制于人的局面。尤其在关键领域,高校是否处于技术引领地位,抑或能否实现自主创新并突破技术瓶颈,这也是衡量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最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还表现为颠覆性思想或观点的产生。高校原始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颠覆性创新”,即其思想或观点能够超出一般性思维、打破常规,并对以往流行观念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在变革中产生新的思想或观点。因而,是否产生颠覆性思想或观点,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评价标准之一。
三、 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
学科群落生态作为学科与学科之间、学科与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对跨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无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其又是如何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产生关联的呢?即学科群落生态如何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呢?这就涉及二者间的驱动机理问题。其中,学科群落生态在协同性、交融性与重组性等方面体现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需求,尤其对高校“从0到1”创新发现、重大技术突破以及颠覆性创新观点驱动上的需求更为明显,从而构成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
第一,高校“从0到1”创新发现的重要助推力是学科之间的协同性,而协同性是学科群落生态的基本功能。协同性表现为各子系统或子要素之间相互合作、协调或同步的联合功效及集体行为,最终将多方力量汇聚成总力量,这种总力量远远超越各自单个的能量,并产生1+1>2的效果(17)项杨雪: 《基于系统演化科学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研究》,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学科之间的协同性以不同学科知识的互补与整合为特征,并通过学科间多元化知识的整合利用与相互补充,形成多元知识的联合功效,从而产生超越学科知识的整合性效果。对于高校在科研创新活动中实现“从0到1”创新发现而言,学科之间的协同性有利于为原创成果的产生提供多学科协同创新的知识基础。这种多学科联合攻关基础上的知识对流、模式组合与方法移植,是单一学科难以匹敌的(18)武建鑫: 《世界一流学科的政策指向、核心特质与建设方式》,《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2期,第27—33页。,并推动高校实现创新知识生产。相较于单一学科知识,多学科知识的协同关系能够实现“复合型”知识生产,从而开辟知识、技能从无到有的新路径。因此,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学科之间具有协同性。而学科间的协同性又是学科群落生态的重要特质之一,体现为多元学科知识的集合与协调。一个学科群落生态,就是若干学科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协调等集体行为来汇聚成总的“学科合力”环境。其学科集体的组织形态、知识合力的整体功效等学科协同性,就是学科群落生态的重要特质的表现。因此,学科群落生态中协同性这一重要特质,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源头活水”。反观实践经验,当高校面临纯粹单一学科知识难以应对的前沿性技术与问题时,通过多元学科知识的“复合性能量”来营造的学科群落生态,成为推动原始创新技术产生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例如,由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领衔的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实验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该研究就是我国高校原始创新实践探索的重要表现。该团队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证明了“量子反常霍尔态”这种全新物质;该实验与材料应用紧密联系,其所涉及的材料具有拓扑特性、长程铁磁序以及绝缘态等特殊性,并对低能耗晶体管、电子学器件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大推动作用(19)《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推动信息技术新发展》,2022年11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22-11/17/c_1310677362.htm,2022年12月19日。。“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作为科学研究中的首次发现,体现了高校原始创新从0到1的转变。而这一原创发现不仅仅依靠物理学科,还涉及材料科学、化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支撑作用,从而实现多学科知识的“协同创新”功能。又以香港理工大学超分辨率成像的研究为例,其推进最前沿的随机光学重建显微镜(Stochastic Opt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技术,就要求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与工程学等学科的协同进行(20)刘海兰: 《香港一流大学学科群网络化组织形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1年第3期,第78—90页。。在这一过程中,随机光学重建显微镜技术的创新发明并非由某一单一学科知识来完成,而是集结了至少三大基础学科才能推进该项创新研究,这三大基础学科知识的协调整合就构成一个学科群落生态。再如在实验中发现的量子密钥分发,其旨在抵御针对探测系统的攻击,被美国物理学会《物理》杂志评选为2013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一项重大进展之一,而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相关学科诸如电子学、核磁共振与量子博弈等学科的协作与互补(21)陈劲、汪欢吉: 《国内高校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 多案例研究》,《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33卷第4期,第490—497页。。电子学、核磁共振与量子博弈等学科知识的整合,同样是学科群落生态协同效应的表现。从相关案例可以看出,高校的重大技术突破与学科知识的协同推进具有紧密关系。值得反思的地方在于,当前我国学科建设中仍然存在对学科间协同效应认识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学科过度细化、过于“本位化”,更容易形成学科壁垒,从而制约学科协同效应的发挥。综上所述,学科协同性构成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机理。
第二,高校重大技术突破的重要支撑是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而学科间的交融性是学科群落生态的关系样态。“学科交叉产生的新知识领域已成为科学研究最具活力的领域和创新成果的重要来源”(22)袁广林: 《学科交叉、研究领域与原始创新——世界一流学科生成机理与建设路径分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第1期,第13—20页。,使得学科交叉融合在重大创新发明发现上呈现出催化剂的功效。重大技术突破本身就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观测点,而学科交叉融合能够进一步推动重大技术突破的产生,这实质上就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表现。在此逻辑之下,学科交叉融合也就成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条件。而学科间的交融性则是学科群落生态的重要特质,体现为不同学科通过知识的交叉融合实现互利共生。在学科群落生态关系中,除了最基本的学科多样性存在外,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动态交互性,并在互动调适中共生,其中的典型特征就表现在学科交叉融合上。因此,学科群落生态中的交叉融合特质,也是高校创新发明的重要支撑所在,从而形成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从世界一流大学原始创新的实践状况来看,通过营造学科群落生态环境,利用其学科交叉融合特质来跨越不同学科间的边界,并将异质性的学科知识技能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生成新发明这一创新过程,就是对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机理的诠释。
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其建立了超过70个学科交叉研究组织,以跨学科的研究计划、课题组、实验室等为基础推动学科交叉研究,其中跨学科实验室14个,包含美国高校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林肯实验室,该实验室乃是跨学科实验室的代表,其前身在二战中雷达研制上发挥重要功能。与麻省理工学院相比,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以生物学为基础,融合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计划,其中X就是指工程、化学、人文、伦理等领域与生物学的交叉。自从该计划实施以来,该校的生物科学就取得突破性成就,其中包括基因测序技术的开发,该技术乃是基因组学的奠基石(23)董樊丽、聂文洁、张兵: 《美国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借鉴及启示——以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为例》,《科学管理研究》2020年第38卷第5期,第161—167页。。从以上案例可见,无论是麻省理工学院组建学科交叉研究组织,还是斯坦福大学实施多学科融合研究计划,皆体现出营造学科群落生态的行动,即通过构建多学科参与的组织模式形成学科群落生态,并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跨学科实验室通过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催生了雷达技术的发明,这无疑确立了该校在雷达、导航、信息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斯坦福大学将生物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研发的基因测序技术,也使得该校在生物学交叉领域显示出竞争优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缺乏学科群落生态环境的营造,是否会导致新技术发明受阻呢?以北京大学环境生物地球化学领域的原始创新实践为例,其陆地碳循环、区域多介质模型及内分泌干扰物质研究等获得领域内的重大突破,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研究被《科学》杂志评为2001年十大科技突破之一,而重大技术突破背后离不开环境地理、环境生物、环境地球化学等学科交叉的作用(24)冷疏影、宋长青: 《重大突破背后的“学科交叉”》,2004年4月2日,https://www.gmw.cn/01gmrb/2004-04/02/content_9645.htm,2023年3月9日。。这一国内高校原始创新实践中的重大技术突破,就是建立在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基础之上,从而创生新的研究生长点。由此观之,世界一流大学中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群落生态,对高校重大技术突破具有驱动力。同时,值得反思的地方也在于,当前我国高校原始创新能力问题是否体现在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不足上,高校是否着力推进跨学科组织建设?学科群落生态环境建设,为学科交叉融合奠定基础,也正是这种学科间知识的交融、渗透与吸收,进一步推动高校重大技术的突破,从而提升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
第三,高校颠覆性创新观点的孕育条件是学科知识重组,而学科知识重组是学科群落生态的运动状态。学科知识重组即重新组合现有知识元素,以此作为新知识创造的物质基础(25)陈立勇、张洁琼、曾德明等: 《知识重组、协作研发深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制定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2019年第16卷第4期,第531—540页。,它对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在对颠覆性创新观点的孕育价值上。科学发现过程是把结晶的知识单元抽离出来,然后再进行重新结晶。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组中形成全新的知识系统与知识单元(26)赵红洲、蒋国华: 《知识单元与指数规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4年第9期,第39—41页。。原有的知识单元在特定的结构下形成特定的知识系统,而对原有知识单元进行重新组合之后,新结构下的知识单元也会存在产生全新知识系统的可能,这也是知识重组对产生颠覆性创新观点的重要贡献。在这一逻辑下,学科知识重组是将学科知识单元进行重新组合匹配,其作为知识单元管理的一部分,也能够通过重新组合匹配后的新生成的学科知识来实现异于常规的创新突破。而在学科群落生态中,学科知识重组体现为学科群落生态内部知识单元的一种运动状态,反映出学科群落生态中知识单元组合的有序性、协调性,而非随机组合抑或杂糅状态,从而发挥知识单元重组的特定功能。因此,学科群落生态在学科知识重组层面,也能够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创造条件。
一些成功的原始创新活动案例,也不乏学科知识单元匹配的痕迹,这也显示出学科知识重组的创新实践价值。以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为例,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和美国生化学家沃森合作,促成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在其探究过程中,因受到前人研究的影响,工作一度停滞不前,最后他们毅然对蛋白质结构权威鲍林的观点进行否定,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取得了震惊世界的发现(27)沙森: 《打开生命奥秘之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2015年1月23日,https://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5/1/296517.shtm,2022年8月14日。。物理学的X光结构分析方法和化学的分子结合键知识(28)袁广林: 《学科交叉、研究领域与原始创新——世界一流学科生成机理与建设路径分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第1期,第13—20页。,在该项成就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该案例中,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敢于挑战、否定先前流行的科学观念以及权威观念,这就是“颠覆性”创新观点的体现。而不同基础学科领域的知识组合,乃是产生具有震撼力的原创研究成果的前提,是颠覆性创新成果的知识支柱。因而,学科单元就像一个大拼盘,若改变以往的知识拼接模式并进行重新组合,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饶有趣味的拼图。这对于高校原始创新实践的启示在于,颠覆性创新成果可以建立在不同学科知识单元的重组基础上,这就指向高校在学科布局方面的生态性。而我国高校在学科布局上是否存在支持知识重组的环境,学科知识的分布是否合理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正如DNA双螺旋结构发现案例中,不同的基础学科知识单元如化学知识、物理学知识按照特定规律重组,从而产生了新的知识系统。作为学科群落生态运动状态的学科知识单元重组虽然是高校颠覆性创新成果的重要孕育条件,而这也为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可能。
四、 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实现机制
学科群落生态中的学科协同效应、学科交叉融合以及学科知识重组作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性元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驱动高校原始创新思想的萌芽以及原始创新知识技能的生成。因而,学科群落生态在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上具有拉动作用。那么,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实现学科群落生态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上的这种积极效应呢?这就涉及重要的实践路径问题。从学科视角来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则需要突出学科群落生态的机制建设,其中强化生态网络建设、跨学科组织建设和学科梯度结构布局可以成为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实现机制。
第一,强化生态网络建设,为学科群落生态的协同效应持续提供保障。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之一就是学科知识的协同,因而重视学科知识的协同效应,就成为学科群落生态发挥作用的焦点。虽然学科群落生态内含学科知识协同性,但在如何进一步增强这种协同效应上,还需要相应的机制建设。其中,可以尝试通过“生态网络”建设,来为学科群落生态中学科协同效应持续提供保障。生态网络作为一种生态系统中的网络结构关系,体现为物质、能量、信息的交互(29)龙瀛、顾朝林: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6页。。其对学科群落生态中学科知识协同效应的强化功能在于: 当生态网络与学科知识及学科关系结合起来,就有利于建立起学科间的资源、信息等交互的网络关系,这对学科知识的整合、互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建立特定领域生态网络的联盟机制,如在高校原始创新实践最薄弱的基础学科领域,建立“基础学科生态网络”,形成基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的网络联盟,来共同应对基础学科领域的原始创新难题,如原始创新难题中的“超导”研究,已经不可能由单一的物理学知识来破解,而是需要多类基础学科知识协同应对。另一方面,建立相关领域生态网络的联通机制,通过桥梁作用来促进学科知识与信息的交互,为学科知识的整合提供可连接的纽带关系。这就要进一步消除当前学科壁垒或碎片化现象,为学科间的常态化、持续性合作创造条件。可见,以生态网络建设为基础,通过网络关系构建来激发学科间的协同效应,促进相关学科间资源要素的整合与合作,是高校破解原始创新难题的重要路径之一。
第二,突出跨学科组织建设,为学科群落生态的交叉融合提供着力点。由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学科,与加快建设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并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紧密相关(30)张丹、姚婷洁: 《法国交叉学科研究机构评估的制度变迁与指标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1卷第5期,第100—118页。。因此,从应对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角度来看,高校的学科群落生态建设就需要着眼于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而要实质性推进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跨学科组织建设可以成为重要的拉动机制。其一,突出跨学科组织的制度建设。高校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尤其是制定实施相应的激励政策,来推动相关学科针对前沿问题或原始创新难题来建立跨学科组织。这不仅有利于从制度层面对传统学科壁垒的组织模式进行突破,应对过于拘泥于“学科本位”而不认同跨学科行为与现象的问题,还使跨学科组织在学科建设层面具有“合法性基础”,从而让跨学科组织在高校中作为一种常态性组织形式而存在。其二,突出跨学科组织的模式建设。建立具有灵活性、多样性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如以某一学科为主体其他多元学科共同参与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院等,以这种灵活多样的跨学科组织模式来加强多学科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知识交叉融合。除此之外,还需要配套相应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诸如跨学科研究人员的培训与交流,以及跨学科人才的创新培养等。在跨学科组织建设过程中,多元的学科知识与研究人员在交流互动中相互吸收与融合,这不仅有利于拓展新的学科知识边界,还是发现原创问题、开展原创研究的关键。
第三,推动学科梯度结构布局,为学科群落生态的知识重组提供驱动力。学科知识重组是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又一机理,因而要实现学科群落生态这一功效,就需要聚焦于如何推动学科知识重组。其中,学科梯度结构与学科知识重组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尝试学科梯度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学科知识重组,以实现学科知识重组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上的实践价值。学科梯度结构意味着高梯度与相对低梯度的学科并存,高梯度学科相较于低梯度学科往往具有知识、技能、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因而高梯度学科主要表现为优势学科、强势学科抑或特色学科,而低梯度学科则表现为在优势或特色等方面不太明显的学科,两者之间存在对流关系(31)陈良雨、汤志伟: 《梯度转移视角下高校学科生态治理研究》,《江苏高教》2021年第3期,第42—48页。。这种对流关系使得高梯度学科与低梯度学科之间存在知识交互的可能,从而进一步推动知识重组。正如相关研究显示的那样,创新主体之间存在的知识势差越高,那么高势差的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越强,更有利于知识的吸收与获得(32)米捷、郭彬、陈怀超等: 《创新生态系统内的知识势差与知识流动机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2卷第6期,第78—87页。。一方面,重视优势学科的培育,为低梯度学科的知识重组提供条件。尤其是优势的基础学科,更能够为相对低梯度学科提供知识重组的条件。另一方面,从低梯度学科挖掘创新知识生长点。低梯度学科可以利用并重组高梯度学科的知识,在弥补自身不足的同时,挖掘学科边缘的新生长点,从而强化学科知识在高梯度学科与低梯度学科之间的合理流动,并通过新的学科知识组合来促进高校的原创性实践。由此可见,在学科群落生态中,具有梯度结构的学科布局,有利于不同梯度学科间的知识重组,这也是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结 语
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从基础研究本身来观测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问题,鲜有从学科视角来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进行系统研究。尽管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不同的侧面,但学科群落生态也显示出一定的驱动力。在学科群落生态环境中,学科群落生态在协同性、交融性与重组性等方面体现的特质有助于推动高校技术突破、创新发明以及创新发现,因而成为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在此逻辑下,从协同性、交融性与重组性等层面来建设学科群落生态,也就成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实践路径之一。然而,学科的协同性、交融性与重组性更加侧重于学科群落生态的内部观测,即从学科群落生态内部系统的建设来探讨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提升问题,那学科群落生态的外部环境建设是否也是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路径呢?学科群落与其他网络主体如政府、社会组织、智库等的网络关系是否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线索呢?与此同时,在建设学科群落生态上,怎样的评价标准才更有利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呢?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整体性、系统性地对学科群落生态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这一研究主题进行进一步思考,也是未来超越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角度来探索高校原始创新能力问题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