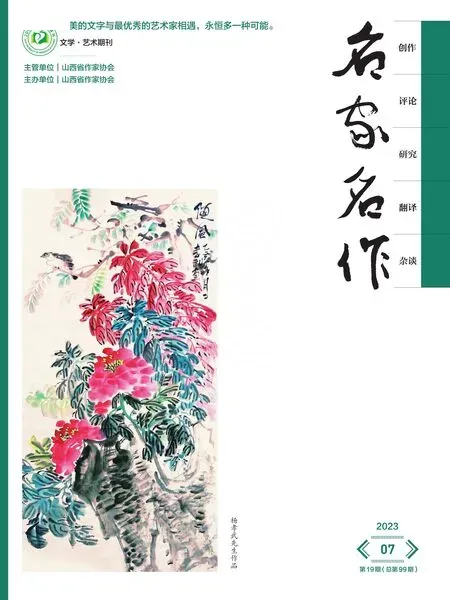AR 模式下诗歌翻译的情感审美及再现研究
——以《红豆曲》为例
2023-11-13秦龙蛟
秦龙蛟
情感是人类认识和体验世界不可或缺的途径,是存在于人脑的一种生物基因。审美的本质就是情感体验,情感不仅是一种审美需求,更是翻译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同时,情感作为诗歌的本质属性,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将基于AR 模式对译者审美能力的调查,对诗歌情感的特征、功能以及翻译审美再现模式进行探索研究。
一、基于AR 模式的译者审美能力调查
(一)AR 简述
AR 是Action Research 的简称, 由Kurt Lewin 于1946 年正式定名,主要指通过计划、实施、观察与反思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具有现实性、参与性和反思性等特征[1]169。具体而言,AR 强调主体以实际行动参与集计划、步骤与反思为一体的研究,以解决自身问题、改善现状为目标,其过程表现为动态性和非规约性,以What-Why-How 为其常规操作模式,即探查具体问题、分析问题成因、寻找解决方案。自20 世纪80 年代传入中国以来,AR 主要被应用于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方面的教学研究,但受其应用属性影响,该模式为发现和研究翻译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探索译者培养机制、提升译者审美及再现能力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二)调查方式及译者审美能力现状
为了解当下译者的审美水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其在翻译审美上的主要诉求,笔者将其分成若干小组进行诗歌翻译练习,要求以小组为单位探讨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关成因和具体解决方案,并以PPT 呈现的方式与其他小组分享本组的最终译文和翻译体会。除此之外,笔者通过私信或访谈的形式随机了解个体的疑问与心得,将其与各个小组的汇报情况进行整合,然后适时调整翻译方法并在随后的实践中进行验证,以此来了解相关方法的有效性、可行度以及译者翻译审美及再现能力的改善情况。
通过调查,笔者初步发现译者的翻译审美及再现能力存在理解失真、表达不畅、校对不力、审美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模式包括四点:第一,基于朗诵的审美路径,即通过诵读的方式理解原文,整体把握原文大意,体会其节奏、韵律、情感等蕴含意义;第二,基于探意、凝神、正言、润色的翻译步骤,即在朗诵原文的基础上识别原文主旨大意,把握其内在精神,以目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之后再进行文辞上的修正与润色;第三,基于真、善、美的翻译原则,即在总体翻译原则上要力求原文义旨转换之真实、译文语言表达之完善以及翻译效果之优美;第四,基于形式与非形式系统的情感焦点,即在语言形式之外,要尤其注重以情感为主的蕴含意义。为此,本文将着力探讨诗歌翻译中情感审美及再现问题的解决模式。
二、诗歌翻译中的情感研究
诗歌作为历史久远、影响广泛的一种文学体裁,是语言运用原始朴素性和现代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然而,在诗歌的所有特征中,情感是其最为明显、最为强烈和最为稳定的一个特征。本部分将就诗歌与情感的关系以及情感的翻译问题进行研究。
(一)诗歌与情感
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指出“言寡情而鲜爱”,认为缺乏强烈情感的诗歌无法获得读者喜爱;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情感是诗歌的根本;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视情感为诗歌境界的决定因素。在现当代诗歌文学理论中,朱光潜[2]6视诗歌为情感的最佳表达方式,而成仿吾和郁达夫等学者则认为情感是诗歌的生命和实质。
而在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Socrates 认为好的诗歌要以真挚的情感投入作为基础;Aristotle 认为,诗歌是基于情感体验的创作,可以激发并给人带来审美愉悦;Horace 阐述了诗歌说教与娱乐的主旨功用,从侧面证实了情感在诗歌中的价值[3]10-30。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流派中,以诗歌见长的浪漫主义认为情感表达是诗歌创作的初衷和目的,可以激发人的心弦并引起共鸣。
由此观之,情感作为诗歌的本质属性未曾受到历史时序、地域空间、文化异质等客观外在因素的影响,是中、西方诗歌文学创作与接受的主要内容和驱动因素。同时,从翻译审美再现及接受的角度而言,情感是中、西方诗歌译/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区域,是诗歌认知理解与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
(二)情感翻译研究综述
许渊冲[4]84-100认为,诗歌翻译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读者乐之,实现情感上的愉悦,提出了等化、深化、浅化等审美再现策略,倡导文化寓意、语言文字、审美效果等多层面的优化。刘宓庆[5]110-140指出,审美主体对客体内在情感的感知、理解与把握存在明显的间接性,需要主体借助审美想象与移情等手段来进行捕捉和再现。Newmark[6]14-15主张从韵律、修辞、文化等多个角度对情感的理解和审美再现进行把握。
但是,通过想象与移情捕获诗歌内蕴情感离不开有效的意象营造,而诗歌意象往往是特定文化审美取向在审美主体内心世界的选择性映射,诗歌翻译若想取得近似于原文的审美效果须重视意象营造的文化适应性。同时,诗歌抒情目的与效果的达成有赖于语言的合理塑造及传递,这就需要从韵律、修辞等语言层面对译文进行优化。因此,诗歌翻译的情感审美及再现可以通过意象营造、文化适应和语言优化的综合运用予以展开。
三、诗歌翻译中情感的审美再现模式
基于上文对诗歌情感及其翻译的研究,本部分将以《红豆曲》及其翻译为例,对诗歌翻译中的情感审美再现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一)意象营造
意象是一种基于物象、形而上的精神产品,可以促进意义的表达和情感的传递。在《周易·系辞》中,孔子曾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问题解决范式,并对立象途径和功能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表明意象营造是审美叙事的重要路径。
《红豆曲》原文营造出了动觉、意觉、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维并置的意象集群,赋予了该诗独特的具象美和虚象美。原文借助视觉所营造的具体意象和借助意觉所营造的虚拟意象,在杨宪益和霍克斯(Hawkes)等主流译文中[7]167-169都有所呈现,但受诗学、意识形态、主体能动性、主体间性等因素的影响,其呈现方式不一而同。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杨、霍的意象营造方式主要表现为再现、重构、新造、省略。在具象的审美再现中,杨宪益的译文以再现为主,如将“春柳”译为willows;而霍克斯的译文则以新造为主,如“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的魔镜意象。在虚象的审美再现中,杨宪益以重构为主,如将“相思血泪”重构为drops of blood 和tears of longing 这一视觉和意觉相结合的复合意象;而霍克斯则全部采用了重构方式,如将“玉粒金莼”重构为food and drink 等意觉意象。
总之,杨宪益的意象营造方式以再现和重构为主,而霍克斯则以重构和新造为主。从两个译本在国内外读者群体及学界的不同反响可以得知,在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翻译前提下,再现是一种合理的意象营造方式,而在考虑读者的审美期待、审美接受与反应以及诗学等因素的情况下,重构和新造则更为可行。
(二)文化适应
文化是特定思想、物质和行为的多元集合,反映或代表了特定审美理念和审美取向。集体审美意识、习惯及实践的传承、变革和创新构成了文化发展与演变的主要模式,审美始终都是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所在。因此,为观照目标读者的审美期待及其与作者的情感同向,文化适应在翻译实践中更多的体现为审美适应,要求译文与目标受众所属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诗学理念及社会规约等价值标准相契合,使译文在文化异质性审视下以恰当方式确保非通约性信息的有效传播。
《红豆曲》使用了中国诗学审美叙事所独有的系列文化词汇,且皆与爱情、相思、盼念有关。通过分析杨、霍两个译本可以得知,两者都用到了简化性缩略,即原文本意义与目标文本意义基本对等,但后者是对前者进行浅化或省略的结果。不同的是,霍译本采用了适应性改写,即在观照目标受众审美期待、诗学规约和文化从属的前提下,译者对原文意义进行了重构性或创造性的改写,致使目标文本意义与原文意义明显不同却又更容易为目标受众所接受。
具体而言,杨氏对文化蕴意的处理以简化性缩略为主,如在目标文本中直接省略“红豆”,并将“画楼”浅化为painted pavilion。霍氏则主要采用了适应性改写,如将“红豆”译为little red love-beans,在保留其文化异质性和非通约性的同时,又使其意义和形象可以为目标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此外,如果说上述案例只是在措辞上的文化适应,那霍氏对于“菱花镜”的处理则是在风格、内涵、联想和移情等蕴意上多方位的文化适应,“Mirror,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在目标读者对“菱花镜”的认知理解上添加了神秘性、方位性、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留白。
总体而言,杨、霍两位译者在文化信息的呈现方式上各有特色,但就译文的审美接受与传播而言,霍氏的适应性改写更为值得参考和借鉴。
(三)语言优化
语言是情感与意义的外在形式,而情感与意义则是语言的内在构成。在语言表达中往往会出现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语言形式重要性的贬低。相反,美学注重形式的提炼,语言之美通常体现为确切和稳定的客观形式。翻译美学强调主体从审美视角对客体的翻译再现进行语言优化,在保证基本语法、句法和逻辑正确性的基础上从修辞、韵律、节奏等层面力求译文的进一步完善。
曹雪芹在创作《红豆曲》的过程中从整体上对该诗进行了艺术把握。就修辞而言,原诗用到了对偶、排比、夸张和用典等多种修辞手法,强化了情感的灵动性和触动性;在韵律层面,原诗以尾韵“ou”为基准,在保证诗歌音乐性的同时也彰显了主题情思的绵长,而临近收尾处适时的变韵“a”和“in”则在起承转合中强化了情感的强度和韧性;在节奏层面,原诗以一行三顿的模式为主,在情感转折的节点上又辅之以一行一顿或两顿,形成了轻缓往复的情感脉动。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杨、霍两个译本在语言优化上各有特色。首先,在修辞应用上,两位译者都借此来保证译文结构形态的简练精当和意义传达的灵活律动,但杨译本以明喻、倒装和排比为主,而霍译本则更加多元化,涉及悬垂、错格、排比、联珠和松散句,后者的语言张力更强,而且在结构形态上与原文存在着一定的共鸣。其次,在韵律安排上,两位译者都借鉴了十四行诗的格式,押尾韵且以双行体收尾,但杨译本采用的是隔行押韵模式,整体韵脚为abcb/bded/ff,而霍译本主要是两行转韵模式,整体韵脚为aabb/ccddd/e/ff,后者的音乐感性更为明显。最后,在节奏的把握与设计上,两位译者都充分发挥了音步的优势,但杨译本采用了五音步为主、六音步和七音步为辅的模式,而霍译本则采用了六音步为主、多音步为辅的模式,更容易将读者带入共情语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语言优化过程中,韵律的作用最具感性,而两行转韵的韵脚模式由于其集中性、突显性和规律性等特征,在审美乐感上要比略显流散和随意的隔行押韵模式更为强烈。同时,节奏是诗歌韵律之美的重要支撑,可以有效激发读者的情感体验。此外,修辞手法的灵活应用可以促进语言结构形态的提炼和优化,提升读者的诗性体验与畅想。
四、结语
本文基于AR 模式下译者审美及再现能力的调查结果,对诗歌翻译中的情感焦点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分析和研究了情感与诗歌的关系以及相关学者对于情感翻译问题的论述之后,初步提出了意象营造、文化适应和语言优化的情感审美及再现路径,并以“红豆曲”及其翻译为例,对该模式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描述分析。情感作为诗歌翻译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对译者审美及再现能力的重要考量模块,此次研究及相关成果对今后译者审美及再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