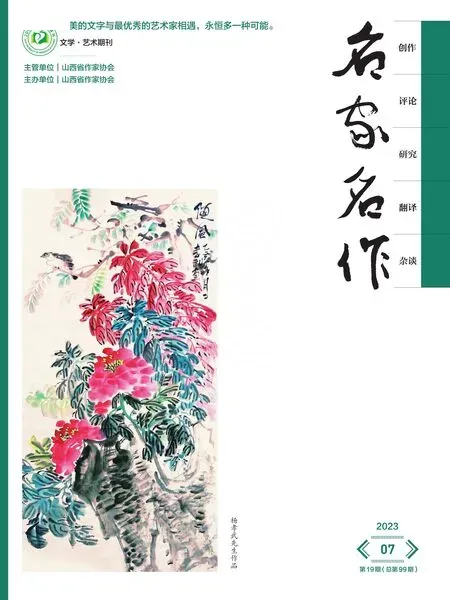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梁上君子》的跨语际实践与戏剧中国化
2023-11-13毕贤慈
毕贤慈
外国戏剧的改编是抗战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是贯穿于我国现代话剧发展史始终并大有可观的创作现象,改编剧作更是在中国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上海1937—1945 年先后上演及发表的改编剧本多达40余部。改编热潮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还体现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其中就涉及英国、法国、美国、匈牙利、苏联、意大利等众多国家的剧作改编。[1]剧作家们“抓住中国的一切,完美无间地放进一个舶来的造型的形体”[2],在凸显现实意蕴的同时,也推动着外国戏剧中国化的改编进程。也正是在此视域下,匈牙利作家费伦茨·莫尔纳的《律师》(A Doktor Ur)进入了黄佐临的文学视野,经由其中国化改编、出版并上演的《梁上君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剧目,其盛况可谓空前。[3]本文以《梁上君子》这一具体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在其中国化改编具体而系统的探析中,试图透视1937—1945 年上海外国戏剧中国化改编的整体概貌与文学史意义。
一、黄佐临与《梁上君子》的改编及影响
中国现代话剧作为舶来品从无到有始终关涉“改编”,在1937—1945 年间,滞留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将改编视为翻译和创作之间的津梁,借由改编之名避人耳目以通过审查,表达自己的文学诉求与抗战愿望,这也成为戏剧生存的一条可行之路。1944 年12 月世界书局出版发行的《梁上君子》便是黄佐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译介选择。
黄佐临,原名黄作霖,广东番禺人,1906 年出生于天津,是中国现当代史上颇负盛名的戏剧、导演艺术家。1925 年至1935 年间,先后赴英留学,并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佐临义无反顾地返回祖国,先后在天津、重庆与上海三地开展戏剧事业,为中国现代戏剧在抗战时期的再度兴盛撒播希望的火种。黄佐临热衷于外国戏剧的中国化改编,《梁上君子》便是其中国化改编成功的最好例证。该剧自1944 年12 月世界书局发行初版,另有1947 年4 月再版和1948 年4 月三版[3],主要讲述了大律师夏屏康与小偷包三狼狈为奸的故事。其中穿插了夏屏康之妻爱梅与屠副巡长的交易、爱梅之妹爱兰与夏屏康秘书白梦兰的交际,以及夏屏康与其同学、老师聚会的误会等等,极具戏剧性与讽刺意味。
立足于创作层面本身,黄佐临充分切实地保持和发扬了莫尔纳原作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植根于中国的社会情状,精细地刻画了每一个人物的心理与形象。剧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律师靠着一位“梁上君子”的罪行与“生意”敛取钱财,律师为罪犯获得一次次“免死金牌”的同时,罪犯也将“重生”的价值回报给他。其表面在写律师夏屏康与小偷包三、爱梅与屠副巡长见不得人的利益勾当,实则是在暗讽日本帝国主义与汪伪政府之间同恶相济,对上海展开的政治奴役和文化殖民。包三冒名顶替夏屏康去国际饭店参加同学聚会,高谈阔论的同时盗取了学生和老师价值连城的物品。其他寄生于夏屏康家中的爱兰、马露西与白梦兰等都是抗战时期上海都市中上层阶级千姿百态的生活缩影。
《梁上君子》自1943 年首演以来,便轰动了整个上海,开了一年来话剧界前所未有的盛况。此剧在巴黎大戏院演出期间,其所在的霞飞路电车站被称为“梁上君子”站,车到站之后,售票员竟然幽默地让“梁上君子们统统下车”,甚而“戏迷坐了三轮车来看戏,三轮工人放下车,也进来坐在‘苦干座’看戏”。[4]《梁上君子》在各地剧场争相上演,层出不穷,甚至在1946 年6 月苦干剧团宣告解散后,剧演的余音也仍在延续。
《梁上君子》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关注与喜爱,更是激起了学界各方的回响,争相论道其中意涵。大众传播媒介关于《梁上君子》的评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批评家一是从《梁上君子》的内容本身出发,表达个人见解与立场,包括剧本、上演情况、剧中人物、演员与场景等。其中,关于“梁上君子”包三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居多,多持赞扬态度,认为他是反映真实社会的一面镜子。二是把落脚点置于《梁上君子》的形式上,即其作为闹剧,向大众呈现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意义,同时肯定了黄佐临外国戏剧中国化改编的成功性。
二、《梁上君子》的跨语际实践及其在地性
抗战时期的上海,民族危机已然成为大众的普遍感受。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戏剧不仅是人民消遣娱乐与发泄情绪的有效渠道,更成为剧作家戟刺社会的投枪。费伦茨·莫尔纳的《律师》因其具有进步意义且避开了直接描写启蒙与革命、民族与国家等宏大主题,成为黄佐临戏剧改编的不二之选,并在上海的戏剧界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梁上君子》的翻译与改编作为一种跨文化行为,获得欢迎与成功的背后,译者在跨语际实践进程中做了怎样的努力?又是如何使其具有了适应中国剧场的特质呢?
在《梁上君子》的改编过程中,黄佐临无意识地参与着“跨语际实践”的生成,即在“忠实”原著的部分,作品文本本身与译文存在着不同的语言之间的通约能力、不同词语与意义之间的虚拟等值关系的展示。[5]黄佐临跨越历史、文化与语言之墙,在创造性阐释中实现了一种语言模式向另一种语言模式的转型与再造。其将题目《律师》改译为《梁上君子》首先便做到了这一点。“梁上君子”作为窃贼的代称,在汉语的文化语境中含有“侠盗”的深意,相较于“律师”,更能直接、深刻地触碰受众的内心。黄佐临更是充分发挥翻译接受方的主体作用,进行着语言层面民族化与中国化的“发明创造”:一方面是本土方言、俚语等口语的趣味表达。戏剧表演是一种社会化活动,其面对的是不同文化程度的观众群体,通俗易懂的个性化、口语化语言便成为改编的最佳方式。《梁上君子》运用大量语气词和感叹词,如“嚯”“啛”“喽”“嗳”“哎呀呀”“喏”“嗐”“啧啧”“唬”“唔”等,在表达人物情绪上更直接、更生动。“甭说”“久仰久仰,久违久违”“磨咕”“老油子”“拆白党”“打哈哈儿”等方言、俚语的使用,更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化与生活化,在妙趣横生的俏皮与幽默中,推动戏剧的进一步传播与接受。另一方面是典故修辞里渗透的中国蕴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剧作家将民间审美与传统文化浇筑于外国戏剧中,使得改编剧焕发出新的现实力量。在《梁上君子》的中国化改编中,黄佐临引用较多的成语、谚语、诗句与俗语,如“君子隐恶而扬善”“恨不相逢未嫁时”“打是痛,骂是爱”“摄成双璧影,缔结百年欢”“口若悬河”等,均体现出中国语言的意犹未尽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语言之外,黄佐临根植于民族传统的中国气质与形象,强调地方特性,在改编剧作与特定空间场域的连结中,为“梁上君子”赋予特殊的时代意义。《梁上君子》模糊了原作《律师》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地点、场景、社会背景与人物身份等进行了本土化改编与重塑,更具民族特色与中国气质。全剧不再以“律师”为中心进行演绎,而是围绕“梁上君子”之意的“偷”字展开叙述[6]。其表面上写梁上君子实名的偷盗,实则指向各阶级不受法律约束的暗偷,黄佐临将“梁上君子”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影射着彼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的畸形与黑暗,以共同的家国记忆唤醒观众对混乱现实的觉察。
值得一提的是,《梁上君子》以闹剧的身份进入中国剧场,黄佐临对其中的西方式幽默进行在地化与本土化的改造,使其转变为更适合中国剧场的讥讽。“空前闹剧”“笑!笑!笑!”“狂笑102 次,大笑603 次,微笑161 次”等广告词尽显剧作之趣,以至汉奸(包括日军)也以为《梁上君子》是个娱乐戏,抢着买票来看戏[7],其闹剧效果不言自明。笑声与泪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体两面,“喜”同“悲”一样成为丰富且复杂的存在,《梁上君子》之类闹剧的“笑”便也成为“涕泪交零”的文学主流之外的另一种文学想象方式[8],成了传统中国文化个性的再现。
三、外国戏剧改编与《梁上君子》的中国化
除《梁上君子》外,李健吾的《王德明》(改编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与《金小玉》(改编自萨尔度的《托斯卡》)、魏于潜的《甜姐儿》(改编自保罗的《买糖小女》)、顾忠彝的《三千金》(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均是同时代其他剧作家致力于外国戏剧中国化改编的创作,对于中国戏剧民族化进程中的探索实绩不容忽视。
《梁上君子》名不见经传,却衍生出很强的“中国化”潜力,表现有三:首先,在政治、文化高压下,知识分子纷纷内迁,原创剧作极为贫乏。戏剧改编用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着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意识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其不仅满足了“剧本荒”的社会要求,而且剧作家将深刻的民族现实蕴含其中,极具典型意义。其次,抗战时期上海戏剧职业化、商业化,戏剧团体层出不穷,无论是剧作选择还是舞台效果都呈现出新的发展活力。最后,在“民族形式”讨论的艺术空间下,《梁上君子》的改编于民族化与中国化方面更加注重“深入今日中国的民族现实”[9]。黄佐临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实践,并在国际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去芜存菁中实现“朴素的,自然的,明确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带泥土信息的”[10]戏剧追求。《王德明》《金小玉》《甜姐儿》等其他外国戏剧的改编概莫如是,其中国化在深刻的现实意蕴与民族性旨归中得以进一步向纵深开掘。
在布满创伤的历史时空中,外国戏剧中国化改编的大放异彩,既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也存在时代的局限与困境。正如上文所言,抗战时期上海戏剧文学相对沉寂与贫弱,中国化改编剧无疑是极为可贵的存在,其意义具体体现为文学荒地的开拓。《梁上君子》填满笑腹纷纭全沪,在“偷”的贯穿之力中形象地刻画出中国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在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的感召下给予时代隐晦而严肃的吁求;《王德明》将故事背景放置于五代初期,并增加了《赵氏孤儿》的情节,在保持着《麦克白》激动人心力量的同时,也在内容到形式的呈现中尽显中国特质;《三千金》在嫁接旧剧《王宝钏》内容的同时,更是将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与伦理转化为中国式大家庭的伦理悲剧,其中国化改编称得上彻底二字。这些改编戏剧均在上海如火如荼地演出,并成为时代艺术的精华,在现实体察与艺术建构两方面进行中国化与民族化的多元探索,历久而弥新。
抗战时期的上海现代戏剧已进入职业化、商业化演出的新阶段,在严苛的政治干预与审查制度下,外国戏剧的中国化改编在飘摇的岁月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相对逼仄的生存空间,呈现出市场效益妥协下文学精神的失落。纵观《梁上君子》《甜姐儿》等闹剧,虽取得令人瞩目的票房收益,并在幽默的微笑中兼容着严肃的社会批评,但无论在改编创作、舞台呈现上,还是在广告宣传上,仍然无法摆脱“嬉笑玩闹”的把戏与低趣。
抗战时期上海外国戏剧的中国化改编,作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战争泥沼下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民族文学的命脉延续。本文通过梳理与考察此时期外国戏剧中国化改编的真实情境。一方面是聚焦文艺本身,具体分析以《梁上君子》为代表的外国戏剧的改编,肯定其中国化过程中的跨语际实践及其在地性。同时,其他剧作家也同黄佐临一致走向了外国戏剧中国化的改编之路,其中渗透的文化内蕴不仅具有璀璨与落俗的两极价值,而且对于重塑中国文化的自我形象有着跨文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抚今追昔,在全球化背景多元文明互鉴、中外戏剧交流日益活跃的背景下,进一步剖析外国戏剧中国化改编在我国戏剧发展史的独特内涵,为当下及未来的戏剧创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