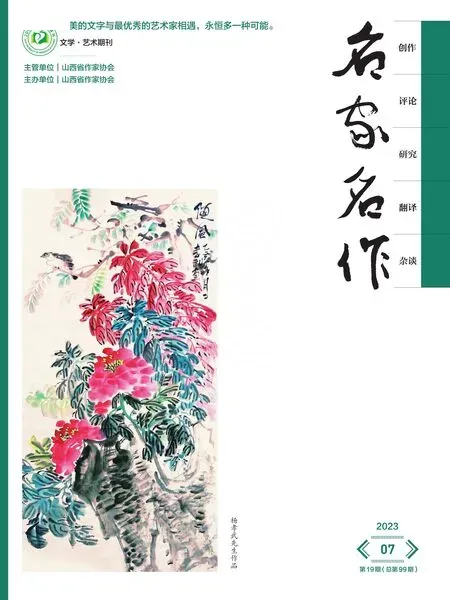王元化先生治学及训诂学思想初探
——纪念王元化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2023-11-13易佳妮
易佳妮
王元化先生是中国当代一位极具思想穿透力的著名学者。他治学的领域相当广泛,自从《文心雕龙创作论》使他名声大噪后,他的学术视野就越来越开阔,从中国古代文论到西方古代、现代文论;从文艺学到美学、哲学;从古代思想史到现代思想史,他的学术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既得益于中国广袤、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又得益于接受西方哲人的抽象思辨能力。在他的著作中,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考证、训诂等传统学术手段的纯熟运用,也可感受到西方学人的玄思论辩,从义理角度辨析入微的精细分析。从文本解读到阐发新义,从语言文字的训释解说到自抒胸臆,均表达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许多中外学者提出建立中国阐释学的想法,如汤一介、成中英等人,无不需要借助中国传统训诂学、经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治学思想
(一)坚守传统学术的纯洁性,秉承“无证不信”原则
王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多次提出“无证不信”这一原则,并在训诂实践中始终贯彻这一原则。王先生曾说:“《经韵楼娱亲雅言》引戴震一句名言:‘知十而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可见戴震是最讲求真实性的。在注籍诠释方面,他严守‘传其信不传其疑’的原则。后人说他倘没有确凿的证据,‘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王先生是服膺信从这一观点的。王先生将胡适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做比较时说:“日记中说(指胡适的日记),汤对胡自认胆小,说只能做小心的求证,不能做大胆的假设。胡适说这是‘谦词’。依我看,这未必是谦词,而是老实话。这表明两人在治学方法上存在分歧。胡适先生在日记中也承认‘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凡读过汤著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这也说明两人治学方法之间的短长所在。”显然,王先生是赞同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方法的,并以此来评判二人学术的高下。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主张按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以西方哲学的体例和模式,来构思和建立中国哲学史体系。以至于先入为主,没有从古人的著述中寻绎出固有的学理和思路,忽略以至抹杀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对于解读和阐发的区别,王先生也做出了较为清楚的区分。应该说,在评说前人的学说时,“应依原本,揭其底蕴”是基本的前期工作,是“做出价值判断”的准备工作。没有前期的工作,后期的工作就是可疑的,甚至会歪曲古人。
王先生并非不知道以往传统的考据有弊病,今人应当在古人的考据训诂方面有所前进,但是传统训诂学“无证不信”的基本原则却是不可动摇的。
(二)反对墨守先人旧说,坚持“推陈出新”理念
王先生并非墨守旧学,只知守成、不知创新的迂腐学者。他多年沉潜于中国古代文化研读中,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对于古代文化的利弊得失也多有独到的体会,他在评论玄学家荀粲、王弼的学说时说:
荀王二人,无非是说,不可拘泥于文字的表面,而应探求其内在意蕴,以达到寻言的观象,寻象以观意。这对于纠正汉儒拘守于文字训诂及其末流的咬文嚼字之弊,可以说是一大解放。
王先生反对以圣人为是非,尊崇权威,迷信典籍,以至于迷失自我,禁锢自由思想的做法和风气,所以对于魏晋玄学摆脱汉代“独尊儒术”的做法三致意焉,认为这是冲破旧思想罗网的行为。
王先生非常注重玄学冲破儒家思想罗网的历史作用,鉴于他一贯的民族和自由的信念,他赞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的一段话:“秦代的焚《诗》《书》,废古语,和汉代的注《诗》《书》,尊经师,其形式虽相反,而其实质则相一致,都是把活的自由思想斩绝。”
王先生既坚守传统学术的纯洁性和学理规范,又反对墨守先人的旧说,也能够推陈出新,他认为自由的思想理念、蓬勃的思想活力才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他对玄学的重视,就在于他认为玄学冲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使中国的思想史发生了一大转折。
二、王元化先生的训诂学思想
(一)总结传统训诂学利弊,推崇“史”的大背景观念
王先生特别注意晚清时期乾嘉学派末流的弊病所在,他说:“乾嘉学术极盛之后,首先蔑贬汉学者,人多举方东树《汉学商兑》……然而远在他之前,章实斋撰《文史通义》即已论及汉学流弊。”王先生意识到乾嘉学派末流的影响。所以对于批评这种弊病的学者也相当重视。王先生把训诂学的兴衰利弊放在学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批判,其视野自然就不局限于训诂学本身。王先生主张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研究训诂学,特别是训诂学在晚清以至近代的发展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王先生也注意到了现今学人趋新而不务实的学风问题。他说:“近有一想法,学人多钻研海外诠释学……在此基础上,或得在古史辨学派后开创一新方法、新境界。”王先生既期待着训诂学的更新与发展,也期待着通过对乾嘉学派学术思想的总结,带动或推动其他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在他的大量著述中,常常提出自己的训诂学思想。
(二)倡导实事求是精神,区分释读和阐发
王先生主张把对别人著作的释读和阐发区别开来,它们不应当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我们对别人著作的释读,尤其要具有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王先生要分清释读和阐发的区别,就是为了避免曲解原文、望文生义的弊病。辩证地说,阐发是对已经梳理清楚之后,在确信是原作者的意思之后完成的,同时在经过批判之后才能真正地释读原文。
(三)尊重客观规律,反对以逻辑臆断替代历史事实
王先生坚决反对以逻辑发展来代替历史发展本身的说法和做法,即尊重客观事实本身,就必然要否定以逻辑推理来代替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他说:“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所谓“义理置于训诂之上”即是无视或漠视客观事物本身,以主观想法推出“应当”出现的事物事实,这就有悖于研究的初衷了。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是后人在研究过程中从历史事实本身总结出来的。研究者不能先用某些规律推导出历史事实,客观事实可能是错综复杂的,人们总结的规律是齐整严格的,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就要求研究者首先放弃“规律”,潜下心来研究历史事实,规律应产生于研究之后。
近些年,一些文化史研究者不遵守训诂学的基本规则,不是从材料中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而是先主观定一个框架,再加上所谓“考证”,往往谬误百出,令人瞠目不解,特别是在乱用“声训”这种方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利用“声训”作为训诂手段,本来是由于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等人提出了“训诂音声相为表里”的说法,现今有的学者缺乏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常识,离开确凿的文献的佐证,仅仅据声音妄加臆测,势必多有谬误。王先生的说法是有针对性的,他对于不尊重历史事实、用主观意愿代替客观事实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
三、王元化先生训诂研究及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一)横纵结合比较分析,体会真实意蕴
释读古书和阐发新义应当分开,这是王先生反复强调的观点。怎样才能正确地释读古书呢?王先生要求人们在释读古书时,要能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要点面结合。他说:“我们很少去把握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从各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各部分,进行见树又见林与见林又见树的科学剖析……”这是一种横向的分析研究,还要将研究的对象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他在评论王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时说:“对于这本看来零碎散漫实际却寄意遥深而不容易看懂的著作,我觉得纵使只写短短几句话,也需要多读几遍,才能够领悟作者在横逆中用自己的心血所写下的文字。”理解原著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体会过程。王先生的解读方法是历史的纵向比较,整体部分的横向分析,还要多次体会理解,才有可能不歪曲原著,理解作者所表达的真实意蕴。
(二)“善入”又“善出”,进入“化”的境界
王先生提出了“善入”“善出”的学说,很有指导意义。这不仅限于训诂学,而且反映了王先生一贯的治学思想,也可看作王先生的诠释学思想。龚自珍在《尊史篇》中提出了“入”和“出”两个概念,王先生作了阐发,他说:“不以物为主,就入不深;不以心为主,就出不来。不仅要能入能出,还要善于入善于出,这就是实现心物交融原则。”“善入”就要能够体会作者各方面的状况,从它自身去理解他。“只有处于作者那样的特定环境和特定境遇,并具有作者那种特定的个性、气质、禀赋、思想和经历的人,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善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也可以是一种投入的热情。“感情是激发创造的动力,也往往成为导向理解的媒介。”在“入”之前,人们并非纯粹消极地接触研究对象,而是主动地参与注解与创造。王先生肯定了研究者的积极主动性,认为研究者本身也是创造者,接近研究对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他说:“善入善出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不可分离。入时亦出,出时亦入。刹那刹那,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着。”王先生批评只能“入”不能“出”的做法,要把“出”的思想融入“入”的过程。他说:“前人注疏(汉人尤甚),以找出出处辄止……而不能因袭旧惯。”这种“入”就是一种创造性地接近研究对象的过程。他特别赞赏勇于创新“善入”“善出”的学者,反对株守前人故训、因循守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他说:“戴震是经学家,但他破除了经生注经的传统,在注释经义时把自己独到的哲学思想阐发出来。这是令人敬佩的。过去经生注经讲究师传和家法,所谓师之所授,一字不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这就把自己的独立思考,有创见的东西,在知识的长河中增加新的颗粒的努力都给压制下去了,我们不能轻视经生注经的传统,它给我们带来教条主义,危害很大。”
人类思想文化的进步总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所谓继承不仅仅是一种字句的沿袭,所谓创新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王先生所推崇的“化”的境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四、结语
王元化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王先生训诂思想及治学方法和态度做出初步探索。本文从王先生大量的著作中紬绎出他关于治学方面的论述并加之笔者本人的体会与理解。我们感到在西学涌入、学人浮躁的今天,更需要重视传统学问与现代西学接轨融合问题,这也是写作本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