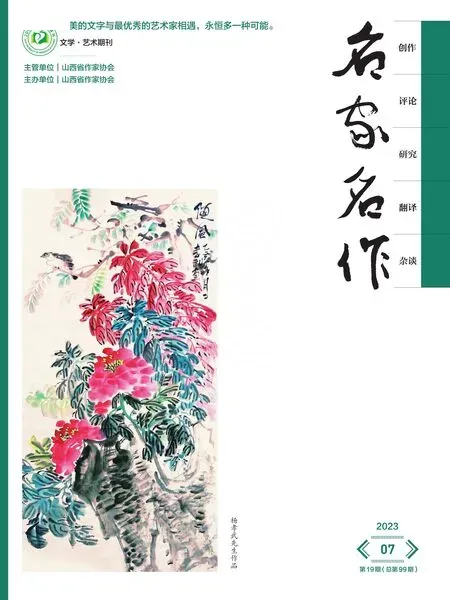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等待”与“追寻”
——宋代“闺思”小令的经典意象探析
2023-11-13霍明宇
霍明宇
宋代令词的“闺思”之作中有一种常见的抒情意象,即对远去未归恋人的“等待”,等待着回归和重逢,等待着殷殷召唤有所回应。伴随等待发生的是时空的流转、心境的起伏、热望与失望的交替。处在“等待”中的抒情主体,既具象为经典的思妇形象,又被抽象为人类共通的情感符号,表达着热烈的渴望和恒久的连接。
一、抒情主体的“等待者”意象
令词中抒情主体的“等待”意象被反复言说,是等待与爱人久别重逢后的一次胜会,是重温曾经的佳期似梦。如“香闺内、空自想佳期。独步花阴情绪乱,谩将珠泪两行垂。胜会在何时。”(张先《望江南·闺情》)“初将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晏几道《虞美人》)词中人闺阁独处,漫步花阴之时不觉想起爱人的陪伴,然而相会之日遥不可期,让人珠泪涕零。月圆人静的时候,最容易撩拨对远人的怀念,暂且以想象宽慰自己,说道月圆的时候人也会团圆。但明月真是不谙人间离恨之苦,每每月圆却并不能带来相恋之人的归期。如此一来,“胜会在何时”的追问其实并没有答案。“初将明月比佳期”的宽慰,也从未真正实现。如果不能等来远人的回归,那么有一封信笺,递送一份平安和思念,这样的期待似乎并不是奢望,但往往久久等待后并无任何消息,只见帘幕低垂,无人叩问。“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晏殊《浣溪沙》)抒情主人公在昏暗的烛光下醒来,想起刚刚梦中的相遇,更觉眼下的孤独。等待远方的信笺递送衷情,但尽管如此,又忍不住想象,如果能够再次相遇,一定把今天的相思之苦、眼中的清泪迥迥诉说给情郎,让他怜爱和珍惜。“闺思”词中的这类“等待”往往没有结果,而抒情主体却因为等待而变得憔悴忧伤。“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晏殊《浣溪沙》) 词中的这位女子有着天仙一样的姣好容貌,却终日愁眉不展,无心装扮。天气渐凉,甚至连衣衫单薄都没有察觉,更无心增补,什么样的心事让她如此无精打采呢?原来是因为放不下与恋人一起经历过的往日的欢娱和恩爱,如今恋人不在眼前,当下的一切都感到了无生趣。
“闺思”小令中,女子的爱情一往情深。“罗衣著破前香在,旧意谁教改。一春离恨懒调弦,犹有两行闲泪,宝筝前。”(晏几道《虞美人》)罗衣即使穿旧破损了,仍然留得恋人的体香,因此弥足珍贵。人的情谊铭心刻骨,怎么可能随意改变呢?而因为这份爱情的执守,女子又要忍受多少等待的孤独和期待的落空,每到伤春时节,更勾起离别之恨,此时空对琴筝,心中无数美好的曲目都无心抚按,等到夜晚只能独自暗落珠泪。“等待”令人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厌厌病,此夕最难持。一点芳心无托处,荼蘼架上月迟迟。惆怅有谁知。”(张先《望江南·闺情》)荼蘼据说是春天最后开的花朵,因此一旦荼蘼花开尽,就意味着春天即将消逝。南宋王淇的《春暮游小园》中云:“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在古典文化中,荼蘼花象征着即将与春天一样美好的人和事告别,那荼蘼架上的明月升起又落下,也代表着昼夜时光的交替流转。伤春惜别,而今夜的月色迟迟不能褪去,似乎使夜晚更加漫长,这增加了女子的惆怅,因为夜晚的怀思更甚于白日,夜深人静之时,芳心无处倾诉、无人知晓,直教人相思成疾,昏昏恹恹。
“等待”让人陷入一种时间之流中,随着等待的进行,时光也在不停地流逝,物事与人情都处在变化之中。而被赋予“等待”意义的抒情主体,更在时空的流转中保持了一份执守。在“等待”中,女子对男子的衷情和痴情往往带有一种审美的特质,女子等待的姿态被具象为一个凝固的“望”。“望”虽然分隔两地但依然期待着连接,它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却并不被时空所改变,因此喻示了一种稳定的、恒常的存在。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人们会赋予一些自然物体以人的情感和文化意义,从而表达人类的某种情感和愿望。例如在很多古迹中出现的“望夫石”,就隐喻了人们对于稳定、恒常之感的一种追求。即使游子辞乡万里,离去经年,历经种种世态炎凉,总有一个熟悉温暖的所在,等待着他的回归和重逢。唐代刘禹锡作《望夫石》诗云:“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诗人途经安徽当涂,有感于当地一座望夫石,取古代民间传说中思妇等待外出未归的丈夫,最终化为磐石的故事,檃括成诗,赞颂女子千载不变的爱情,也暗示了自己的思归之情。北宋薛燧《南乡子》词云:“逐日望归舟,暖藕全宽玉臂韝。待得君来春去也,休休。未老鸳鸯早白头。”用一整天的时光,从晨昏到日暮,守望恋人的归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等待,即使有一天爱人归来,恐怕已经荒老了岁月。思君令人老,有情之人也因思念而生起了华发。一句“休休”表达了近乎绝望的心情。虽然可以想象到如此绝望的结果,心中的期盼和等待却并不能停止,否则又何必担忧“未老鸳鸯早白头”呢?即使等到天荒人老仍然不能相聚,相恋的人依然是各处一方的鸳鸯眷侣。“留恨城隅,关情纸尾。阑干长对西曛倚。鸳鸯俱是白头时,江南渭北三千里。”(贺铸《惜余春》)空间的流动,时间的推移,乃至心中的质疑,都不曾撼动那份“等待”的执守。
“望”是一种等待,也是一种召唤。当这种等待和召唤无法得到现实的回应时,便将这种“望”的姿态抽象和升华为一种审美的存在,把悲伤绝望的等待想象为一个凄美的女子形象,从而用一种美感体验扩大了原初情感的维度,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赋予忧伤绝望的离别之苦以更多元的审美意义,也在人类共同的悲哀体验中消解了个人的遭际和不幸。北宋张先《浣溪沙》词云:“楼倚春江百尺高,烟中还未见归桡。几时期信似江潮。 花片片飞风弄蝶,柳阴阴下水平桥。日长才过又今宵。”倚楼凝望,是“闺思”诗词中抒情主人公的经典形象。从唐代王昌龄《闺怨》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到唐末温庭筠的《梦江南》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诗词中的女子登上江楼,随着视野的开阔,心中的思念也油然升起。张先这首小词中,抒情主人公与所爱之人有期信在先,因此她的等待似乎应该指向一个能够实现的未来。她在一片江水的雾气中辨识那熟悉的归舟,但是一整天的等待却令她空手而归。“烟中还未见归桡”,一个“还未”道出她无数次的眺望和无数次的失望,以至于不禁嗔怪,“几时期信似江潮”,江潮涨落总是遵循自然规律、不会误时的,她多么期望恋人之间的爱情也能这样稳定、牢固。但实际上,爱情如此捉摸不定,信约在前,却负约在后,令人空自等待,空自惆怅。“花片片飞风弄蝶,柳阴阴下水平桥”,花与柳是春日的典型景象,落红漫天预示着春日将阑,女子伤春,是伤感生命的青春流逝,也在伤感美好的青春因为缺少爱人的陪伴而变成一场孤寂的虚度。女子由兴奋而焦急的期待,到期待落空后的失落,心情好像风中的落红,被造化捉弄。傍晚时分,江水上涨,垂柳丝丝已经拂动水面,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行将结束。在江楼眺望了一天的女子,也要带着失望离开,白日漫长的期待已经令人疲惫,而接下来则更要面对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女子由期信将到的兴奋到遭遇背信负约的失望,由于内心的这份等待,使自己陷入心绪的起伏躁动。抛开词作表面的爱情主题,这样的情感体验恐怕为很多人所熟悉。生命中的一次次等待,都是游走在期望与绝望之间。
二、想象中的“追寻”意象
相思令人老,“闺思”小令中抒情主体的心情因为无望的等待而变得暗沉低落。但有时他们又不甘于在时光的交替流转中默默等待,而是跟随强烈的内心情感,做出执着的“追寻”。“追寻”似乎是对被动等待的抵消,但这种追寻又是幻想中的、非现实的、是无处安放的等待情绪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北宋周邦彦《醉桃源》一词云:“冬衣初染远山青。双丝云雁绫。夜寒袖湿欲成冰。都缘珠泪零。情黯黯,闷腾腾。身如秋后蝇。若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在一个冬日的夜晚,远方的爱人未归,女子忧思难耐,珠泪涕泗飘零,打湿了衫袖,使衫袖在寒冬时节凝结成冰。秋后万物肃杀萧瑟,蚊蝇这样小小的生灵们也进入了生命的尾声。而抒情主体的内心正如这秋后的蚊蝇一样,消沉、落寞而忧伤。用秋后蝇来比喻相思中的女子,将女子哀怨而卑微的形象呈现出来。最后一句“若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则将思念化为想象中的行动,只要能追寻所爱之人,跟着他的马儿游走四方,女子甘愿做一只小小的卑微的蚊蝇,不辞万里跟随情郎的踪迹。一个“若教”点出女子殷切的期盼,而这份期盼又能实现几何,也只是女子难耐相思而产生的幻想。
有时,追寻的情节体现为一种视野的跟踪,宋代蔡伸《洞仙歌》词云:“楼外江山展翠屏,沈沈虹影畔,彩舟横。一尊别酒为君倾,留不住,风色太无情。 斜日半山明,画栏重倚处,独销凝。片帆回首在青冥,人不见,千里暮云平。”小词呈现了一次离别的场景,江畔楼前,恋人的舟船已经备好,别酒频倾,道不尽不舍之情。离别,应是人生中最痛苦难耐的事情,而词中的女子正被这份离别之苦淹没。她登楼远眺,在视野里搜寻那载着恋人的扁舟,却只见片帆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茫茫云水之间。小词上片道出“留不住”的无奈,下片则追写分离之后在视野中的继续跟踪,足以感受到抒情主人公对爱情的不舍和执着。
当视野难以企及的时候,追寻又往往成为一种思绪的追踪。如柳永的《甘草子》词云:“秋暮,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雨过月华生,冷彻鸳鸯浦。 池上凭阑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词的背景色调十分清冷,在一个暮秋的夜晚,雨滴声声敲打着枯荷败叶,似乎叩响了主人公内心的愁绪。雨过天晴后独自凭阑,只见孤月高悬,冰冷的月华撒向池浦,让人不胜凄寒之感。单栖难耐,如何抚慰?“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姑且把鹦鹉当成自己的陪伴,教它“念”粉郎言语,听着鹦鹉学舌,好像粉郎就在眼前。那些恋人之间曾经的互诉衷肠如今仍然如在耳畔,虽然不能相见,但依靠着对过去的追忆,仿佛寻到了曾经的粉郎,将相恋的两人在此刻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时,追寻是将爱的信物寄送。宋代王灼《长相思》词中的抒情主体就是借遥寄信物来表达对爱的追寻:“来匆匆,去匆匆。短梦无凭春又空,难随郎马踪。 山重重,水重重。飞絮流云西复东,音书何处通?”匆匆相见又别离,来不及深表爱慕,已然远隔万水千山,回忆中恍如春梦,连去时踪迹都难以寻觅。这让抒情主体情何以堪!离别后的日子填满了思念,而所爱之人的行踪就像柳絮纷纷、流云片片,总在飘忽流动中,没有安定感。远人既不能相见,那么就借一封书信传达相思、互通音讯吧!然而,连对方身在何处都不能确定,这封书信又寄向何处呢?在以上这些“闺思”小令中,抒情主人公的“追寻”并不能换来现实中的重逢,她们更多的是用想象中的团圆慰藉当下的孤单,而在这辗转反侧的想象中却让人体味到一份追寻的执着。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重逢遥遥无期,想象中的相遇亦被层层阻隔,抒情主体对所思之人热烈的渴望似乎终究会落入无奈的失望。抒情主体希望通过想象中的上下求索和苦苦追寻抵消作为现实中的“等待者”身份,但回到现实仍然要面对期待的落空。这份有所期待又无所回应,却依然期待的情绪体验,超越了文本表面女性和爱情的主题,而象征着人类普世生命中对内心深处渴望的执着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