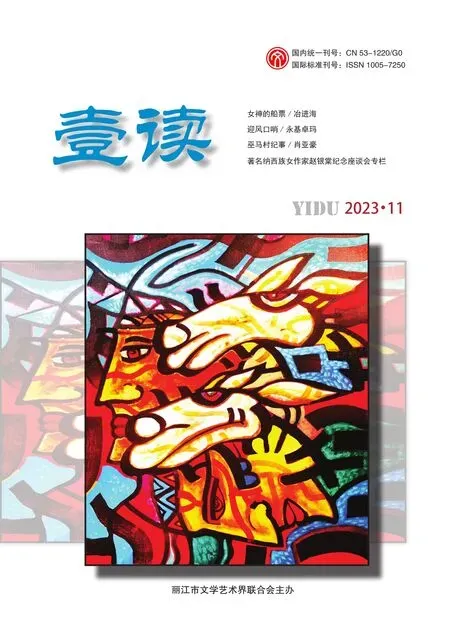巫马村纪事
2023-11-09肖亚豪
◆肖亚豪
一 傻子拉暖
我从县城回巫马村。刚进村子,就看见拉暖立在沙玛拉体家院坝的正中央,转动着脑袋,嘴里不停地哼着各种不成曲调的流行歌曲,手中握着一瓶绿色的雪碧瓶子。正午的日光透过他背后的竹篓子往地上投下几缕斑驳的碎影。有人从沙玛拉体家屋后的泥巴路上经过,停下来打量他的举动。拉暖发觉有人来了,紧忙解释说沙玛家是他的亲戚,他不会偷东西的。阿余务达抽出一根红河牌香烟递给他,为他点上火。拉暖将烟叼在嘴里,昂起了头颅,仿佛一只骄傲的大公鸡。“走吧,你亲戚家去隔壁村子吊丧了,没人。”阿余务达说。拉暖将竹篓卸下,拿出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太阳底下闪了闪。接着去牛栏旁站住,抬起左脚蹬在一根横木上,甩开膀子猛砍一棵白杨树垂下的枯枝。枯叶哗啦啦落下来,再砍一下,枯枝落了下来。他将树枝砍成若干小段,投进竹篓里。接着背上竹篓离开了院子。在爬上屋后的陡坡时,他回过头来嘱咐阿余务达,要他跟沙玛亲戚家说一声。他老娘没柴烧了,眼看要冬天了,电费又贵,烧不起电炉,只能来砍点树枝回去给老娘生火取暖。反正大家都是亲戚,想必都不会计较的。远处传来炮仗声,他冲路边围观的村民吹口哨,往远处传出炮仗声的地方努嘴,“去吃肉了。”说罢,哈喇子流了出来。“谁跟他是亲戚,这哑巴,尽瞎扯。”沙玛拉体后来说。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都没有去吊丧,只有阿嘎顺路去挂了点礼钱。傍晚,她来我家借农具,和我的母亲立在大门口闲聊起来。聊着聊着便放下农具进了屋。正值隆冬时节,寒风凛冽,天又阴沉沉的,看来要下雪了。母亲生了火,和阿嘎围在火塘边闲聊开来。我去户外拉风景屎,差点被人撞见。这么多年了,村里少有修厕所的人家。我们从小就躲在深沟、林子和田埂解决大小便问题。这种与人相撞的场景也并非第一次。无非是提起裤子若无其事地躲开。我进屋才发现她们在聊村里的五保户拉暖。火塘里,榕柴烧得正旺。间或发出哔剥的声音。阿嘎说拉暖又去要肉吃了。他一来,主人家先顾不上办丧等事宜,单独给置办了一桌酒席。他也不客气,低起头吃了起来。酒足饭饱之后,点上根香烟,边吸边把剩下的食物统统倒进备好的塑料袋中。接着走到男主人跟前要坨坨羊肉,说他老娘很久没吃过羊肉了,想带些回去让她尝尝。主人见状,二话没说就给他装了半袋羊肉。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他如今在巫马村里活成菩萨了哩。”阿嘎说。
我在外面待久了,对于村里的事情逐渐生疏。关于他们的生存状况的细微变化我更是一无所知。以为巫马村永远都是那副模样。无非是死去了一些人又添加了一些人。无非是屋舍和交通的变化,至于村民的精神面貌永远一成不变。拉暖就更不用提了,闭上眼睛一想就知道他还是老样子,不曾料到他也有咸鱼翻身的一天。过去,他整天脏兮兮地在村口拾荒度日。大人小孩都可以拿他取乐。叫他唱什么歌他就流着哈喇子咿咿呀呀地唱几句。“看不出来,拉暖还是个大歌星呢。”大家说。拉暖就嘿嘿嘿傻笑不停。村里有红白喜丧时也不愿他参加。有时他才进大门口就给他点吃食或塞给他一根香烟就轰走了。大堂兄结婚那年,我十岁出头,婚礼当天,我和一众堂兄弟接到的任务就是在房前屋后巡逻,碰到拉暖就给几颗糖和花生米就让他离开。拉暖的鼻子比狗还灵呢,哪儿有肉吃他准能出现在哪里。而那时肉食是极稀罕的东西,不会随便让无关人员吃的。那天,大概中午时分,他哼哼唧唧地出现在屋后的空地上。在一堆苦荠桔梗堆旁,我们将他围住,先往他的口袋里塞了一把花生米,然后比划着手叫他回家。三堂兄胆子大,也最调皮,他折了一根松枝抽拉暖的屁股,他才悻悻地离开了。
阿嘎告诉我,拉暖并非天生如此。他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是他的母亲拉扯他们兄弟俩长大的。他小时候很聪明,眼珠子亮亮的,像灯泡似的,目光灼人。“判断小孩聪不聪明,就看眼睛。”阿嘎说。有一年,拉暖的母亲在户外干农活,由于怕孩子吃土,将他放在离地很高的大石头上。拉暖不慎摔了下来,头先着地,去医院治了好久,但小孩不再像以前那样机灵了。祸不单行,有一次被年猪绊倒,被猪拖行了几十米。自此以后彻底傻掉了。他认知能力差,几乎不认识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兄弟。独独记住了他老娘。每天去拾荒,卖了钱就给老娘买面包、饼干和泡面。这几年,巫马村里有年轻人去外面打工,学会不少新潮的玩意儿。抖音和快手很快在村里流行开来。年轻人脑子活泛,知道什么样的视频赚钱。有人很快瞄上了拉暖。利用他制作短视频,发布到快手上,收益很可观。拉暖得了分成,也不再拾荒了。视频发出去,有给钱的,有寄吃食的。“噢哟,拉暖的老娘现在可是享福了,想吃啥吃啥,我们听都没听过的东西,拉暖都弄回家给她吃了。”阿嘎说。拉暖有了收入,到处蹭肉的习惯却没改掉。而人们也开始不再阻拦他了。如今,天天有肉吃,办红白事时,吃都吃不完,也不多拉暖一个。阿嘎告诉我,刚开始时,还有人拦拉暖,也不给拉暖肉吃。但这几户人家后来都有了灾殃,有人被狗咬掉耳朵,有人办了喜事后不能生育,更有人淹死在池子里。慢慢地,没有人敢再怠慢拉暖了。只要他一到场,立马引为上宾,要什么给什么。他总是自备几个塑料袋,将食物分门别类地装好带回家。有时还张口要东西,说是他老娘想吃,主人照例是爽快拿给他。“世道真是变了,拉暖轻轻松松就变阔气了,而我们这些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地里刨食,生活却总是那个鬼样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阿嘎说。
夜已深,我突然觉得背后冷飕飕的。发现屋外朔风呼啸着穿过木屋的缝隙直往屋里灌。火塘里的榕柴即将燃尽。阿嘎起身与我们道别。我打开房门,发现地上亮堂堂的,借着屋里的灯光,我看见雪花在不断坠落。“下雪了。”阿嘎说。她转身走进漫天风雪里,很快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
二 梅花人浪布
一些人能算出别人的生死,却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在巫马村,由于腿有残疾,浪布像一块发霉的抹布,几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随手扔在土坯房的一个角落,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起初,没人注意这个毫不起眼的人。有一年冬天,有人看见他拄着竹杖出了村口,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去户外某个犄角旮旯里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也有人说他死在了邻村阿洛寡妇的肚皮上,被人剁碎当猪食喂了猪。过了一个月,村长慌了,以村民离奇失踪为由拨打了110,警察来了几次,折腾了好一阵子也不见踪影,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村长阿西边布有一句经典口头禅叫“离了谁,地球照样转”。这是他去乡里开会时从老乡长嘴里学来的。他自己可不知道地球会转动。老乡长一动肝火就说,爱干不干,离了谁,地球照样转。浪布失踪真是应了这句话了。没有了浪布,巫马村照样是巫马村,它永远如一小块牛粪粑粑一样贴在大地褶皱处。所有人都是寄宿于牛粪中的蝼蚁罢了,更何况浪布这样像抹布一样可随手一扔的不起眼的家伙呢。记忆中,那一年,好像整个冬天都在没完没了地下雪。万物隐没于皑皑白雪中,所有生灵都遁了形。大家抱了羊毛披毡,和衣蜷缩在自家的火塘边,像一只只懒洋洋的猫。只有此时,人们才会围着火塘偶尔提起浪布。我的二婶是村里有名的“万事通”,村里没有什么事是她不知道的,但关于浪布,每次问她时她总是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她也搞不清楚浪布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村里的,他应该是从外地迁来的吧。但细细一想,又觉得浪布是巫马村的土地里长出来的人。仿佛一棵树,在巫马村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知不觉已长成大树,成为村庄的一部分。他先天残疾,一只脚脚掌蜷曲成球形,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的坑,像一团发酵后蓬松的面团。他在巫马村里并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角色。由于他身有残疾,为了体面,所有的红白喜丧都不让他参加。他常常躺在屋后的一堆松毛上,嘴里叼一根枯草,望着远处的天空出神。可以肯定的是,浪布是个很聪明的人,干什么会什么,学什么像什么,偶尔出现在公共场合里,一开口就知道他见识非凡。有人企图和他争论,他一言不发,等对方辩解了一大堆,他才抓住对方的逻辑漏洞,言简意赅地反驳一句,即刻就能将对方噎得哑口无言。
雪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下。有一天傍晚,天边的浓云被撕开一条口子,残阳露了露脸又躲进乌云里。只有几缕霞光于滚滚乌云中洇开来,在天边留下一抹淡红的金边。巫马村沸腾起来,村民们纷纷涌到户外的雪地上,望着空中叫唤。只见村庄的上空,在团团飞舞的雪花中,一只巨大的公鸡在空中展翅飞翔。它悄无声息地绕着村庄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在朦胧的云气中,它撑开巨大的翅膀,仿佛滚滚的乌云一般覆盖了整个村庄。一种刺眼的光芒将天空映射得一片火红。那光芒来自公鸡血红的羽毛。村长阿西边布大喊一声,叫大家看公鸡的背上。仔细一看,可以发现上面坐着一个人,他骑在鸡脖子上,脚耷拉在鸡脖两侧。一会儿,公鸡像一片巨大的红色的雪花悄然飘落在远处的光加阿别山上。乌泱泱的人群涌向山巅,那只大红公鸡已经飞升到空中,逐渐消失在远处天边。只有雪花还在簌簌飘落。
人们在雪地上找到了浪布,他满面红光地盘膝坐在一片白得耀眼的雪地上闭目养神,仿佛莲花上的观音。有人惊呼一声,发现浪布残废的脚掌变成一株花枝摇曳的腊梅花。上面簇拥着一朵朵鲜艳的红花。浪布缓缓睁开眼睛,村长想去扶他站起来,浪布挥了挥手表示拒绝,接着飘然而起,像一只舞姿优美的仙鹤一般立在雪地上。他的一只脚穿着图案精美绝伦的靴子,另一只脚的下半截杵在雪地上,仿佛从雪地里生长出来的腊梅花。一会儿,他好像从太虚幻境中清醒过来一般,眼神不再飘忽不定。他伸手和阿西边布握手,和其他村民打招呼。大家说要背他回村,他说他能走,接着抬起插在雪地里的梅花脚,飘然而去。等大家赶到村里时,发现浪布已回到他那间残破的土坯房,他用松毛生了火,像过去一样蜷缩在火塘边,像一块随手扔在墙角的破抹布。
没有人再敢像过去一样怠慢浪布了。他如今能占卜吉凶,还能运功作法消除灾殃。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本事。有人说他去了鹰鼻子山,在山脚下拜了一位大苏尼为师。由于天赋异禀,大苏尼倾囊相授,浪布尽得真传。上天遁地,腾云驾雾,识鸟语,懂畜言,辨真假,识善恶,卜吉凶,他几乎无所不能。在鹰鼻山两年,他白天学法,夜间把自己埋于一株腊梅花下,很快就让自己的废脚生根发芽,也长成了一截腊梅花。每年冬天,当万木凋亡时,浪布脚下却一片绚烂。他时常腾空而起,倏然不见,形如鬼魅。那时寡妇阿洛还没有去外面打工,有人经常在冬天的雪地上顺着落下的梅花花瓣一路摸索到阿洛的家门口。但没有人敢揭发浪布的风流韵事。他常常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出现在红白喜丧的场合中,在火塘上角最尊贵的主座上,嘴里抿着泸沽湖白酒,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侃侃而谈,周围满是一双双崇敬的眼睛。
浪布是今年冬天死去的。那天,巫马村照例是飘飞着漫天雪花。下午,浪布去邻村帮人占卜,喝了不少酒,回来时迷迷糊糊的,结果一出村口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农用三轮车撞得支离破碎。浪布的梅花脚折断了,雪地上撒满了大片血红的花瓣。人们都觉得浪布异于常人,他被撞碎的身体会自动拼接,继而复活过来。但没有,整整一个下午,他的身体散落在雪地上,第二天早上还是没有动静,村长阿西边布见状,只好带人将他的残躯装殓,带去后山埋掉。阿西边布说,按传统习俗,应该是火葬的,但姑且埋于地底吧,或许来年春天的时候,浪布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呢。村里议论纷纷,说那天如果不是浪布喝迷糊了,凭他的本事,本可预知吉凶的。但村长阿西边布说,一个人能算出别人的生死,却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所谓命运,是命中注定的劫难,怎能预测呢?
三 樱桃与货郎
巫马村的东边有一个高高的陡坡,坡上尽是青褐的山石,石缝里偶有杂草冒出,此外再无绿意。拉马体火成家那年,带着一班人用炸药炸掉坡顶的山石,接着辟出一片平地并在那儿起了一栋木楞屋,两间土坯房,再围以泥墙,很快搬了进去。他的女人骨架大,体态丰腴,是老辈人眼中生育能力极强的那种女人。拉马体火那时健壮如牛,似乎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他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干三个人的活,很快把日子过得火红起来。
谣言是从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年兴起的。有人说拉马体火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骡子。嘴碎的女人则说拉马体火的女人空有一副好皮囊,却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有人喝醉了酒就指着拉马体火,猥琐地问要不要代劳给他女人下个种。拉马体火愤怒之余操了镰刀要干掉对方,劝了半天才劝住。此后敢当面拿这事儿开玩笑的人倒是没有了,但背后的闲言碎语从来没有停过。其间去医院看过,但女人的肚子依然不见任何动静。
那个时候,巫马村里时常出现操着异地口音的货郎。他们挑着针线,糖果,气球之类的玩意儿吆喝着挨家挨户地换女人梳落的头发。有时,天黑了就借宿在村里的某户人家。有一天夜里,拉马体火抱着一只羊羔出现在村口,说刚刚去林子里找落单的小羊回来。村长阿西边布去屋后撒尿,听见附近拉马体火家的狗叫了大半天。应该是有陌生人进了屋,或许是借宿的货郎吧。第二天,拉马体火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株樱桃树苗种在屋后的空地上,每天用公鸡血浇灌。说是鹰鼻山下的苏尼开的生子良方。没过多久,村民们发现一棵樱桃树从拉马体火家屋后的岩石缝隙处拔地而起。树根盘根错节,将周围的岩石硬生生给挤开裂了。六月,阳光毒辣,樱桃果粒火红。拉马体火爬上樱桃树,眯着眼睛挑出其中最饱满的一粒果子喂给女人,其余的全部打落,踩烂,埋掉。当年冬天,拉马体火的女人产下了一名男婴,取名格尼忍(樱桃子)。每次有货郎出现在村口时,拉马体火就会醉醺醺地出现在村口,挥舞着镰刀驱赶货郎,久而久之,巫马村再也没出现过货郎。
四 香屁王阿西阿都
巫马村村委会炊事员阿西阿都患了肝癌,被村主任阿丁务支辞退了。阿西阿都很失落,自己鞍前马后地侍候这帮孙子十几年,老了老了,不落一句好,倒因陪他们喝酒喝坏了肝脏。想想过去,每次村里来人,在酒桌上,他们喝不了就拉上阿西阿都代饮。阿西阿都本是个老实巴交的羊倌,阿丁务支跟他能扯上点亲戚,还去他家吃过不少阉鸡,觉得有必要拉亲戚一把,于是就将他弄到村委会当了炊事员。阿西阿都说他做不好菜,阿丁务支说不会做菜怕个啥子,洋芋片片会炒吧?腊肉酸菜会煮吧?鸡会杀吧?阿西阿都说这些都不需要啥技术。傻子都会。于是把羊群扔给女人,屁颠屁颠地跑到村委会煮饭去了。十几年来,他的厨艺原地踏步,酒量倒噌噌往上涨。他左手一瓶“泸沽湖”,右手一瓶“五彩丽江”,咕噜咕噜往嘴里倒,倒完还能在众人的喝彩声中灌一箱支格阿鲁啤酒。不到醉得东倒西歪绝不罢休。有一天晚上,他喝了一斤“泸沽湖”,刚在床上躺一会儿就觉得侧腹疼痛难捱,赶紧叫醒女人去村卫生所开了点止痛药。哪知深夜时又痛了起来。他叫村主任阿丁务支派一辆车送自己去县医院看看,主任没好气地骂了他一顿,让他自个儿想办法。折腾了老半天,阿西阿都才联系到一辆农用拖拉机。到医院一查,阿西阿都傻眼了。医院怀疑肝癌,要他去外面查一查。阿西阿都说到这份上了,再查不是花冤枉钱么,还查个屁。于是他叫拖拉机司机拉他回了巫马村。
阿西阿都说他得了癌症,要村委会预支点工资。阿丁务支直接叫他卷铺盖回家。说肝病会传染,哪能干炊事员呢。还让村委会里吃过他的炒洋芋片片,和他共用酒碗喝过酒的人都去医院抽血检查。阿西阿都觉得自己害了人,卷起铺盖灰溜溜地回了家。
他又干起了旧营生。整天早出晚归地跟着几十只绵羊往山上跑。本以为他很快会死掉的——还没有谁听说过癌症能治好呢。但好几年过去了,不见他吃什么药,也没听说他去过医院。他却越发地生龙活虎了起来。他甚至跟人开玩笑说,如果不是没有钱,他一定会再娶个女人重振雄风。有人说这是阿西阿都吃了玛卡的原因。这种作物当年被当作神药炒得沸沸扬扬。玛卡有壮阳之效确实有所耳闻,但从没听说过还能治疗癌症。
有一天晚上,整个巫马村都被一股清香之气所薰醒。人们忙从被窝里钻出来,穿着裤衩背心,趿着拖鞋立在自家院子里贪婪地呼吸着令人神清气爽的浓浓的香气。没有人愿意回屋睡觉。有人甚至将被窝挪到屋外,躺在院落、马路和村口,边打瞌睡边吸气。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这股香气竟然在村庄的上空飘扬,它们像炊烟一般袅袅飞扬,在晨光的映射下显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来,就像棒棒糖一样,绚烂,甜腻,散发着梦幻般迷人的光晕。一会儿,等晨光散尽,人们开始进山劳动时,香气消散了。等到夜晚时分,当星星撒满夜空时,香气又如期而至。人们又习惯性地涌到户外猛吸一阵。起初,没有人去深究香气来自何处。有一天,村长阿丁务支一拍脑袋,似乎突然开窍。他发现每次阿西阿都离开巫马村外出办事时,村里的香气也跟着消失了。当天晚上,月亮很圆,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后半夜的时候,村长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潜入阿西阿都家的屋后,在檐角一个隐蔽的地方躺了下来。
月亮大得出奇,它缓缓升上了正空,圆圆的,发出惨白的寒光。一会儿,它仿佛往巫马村压迫了过来,越来越低,越来越亮,光芒摄人心魄。阿丁务支吃了一惊,差点叫出声来。却听得一阵声音自屋里传来。时而轰轰隆隆,时而哔哔剥剥,时断时续,似惊雷,像炮仗,如拖拉机引擎声。一股浓浓的香味穿过木屋的缝隙,从屋里飘散出来,使人如坠迷雾,如沐春风,如饮美酒,使人醉醺醺,轻飘飘,软绵绵,麻酥酥。阿丁务支觉得自己骨头都被薰酥了。他缓一缓神,晃晃悠悠地挪到村口,发现如往常一样,香气已弥漫到村庄的上空,不久即形成一层浓浓的香雾,连月亮的光华都被它遮住了。月亮显得暗淡起来,朦朦胧胧的。阿丁务支回到屋里,辗转难眠,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床,洗漱完毕,踱到屋外,发现晨光柔柔地倾泻下来,远处天边荡漾着一抹淡淡的红霞。香气早已散尽,整个乌马村笼罩在一片安祥的晨雾中。阿丁务支径直走进阿西阿都家。门口的土狗狂吠开来。阿西阿都的女人见村主任大驾光临,远远地迎过来,边痛骂土狗瞎了狗眼边笑盈盈地将阿丁务支迎进屋里。
阿西阿都坐在火塘东侧一处向阳的地方。边喝浓茶边往嘴里塞一口燕麦粑粑,根本不抬头看村主任一眼。他披着一件羊毛披毡,脸皮红润,显得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一个肝癌患者。阿丁务支表明来意,老炊事员也不怯场,反而态度倨傲,打死也不开口。如今已不在主任手下吃饭了,怕他作甚。阿丁务支一改往日的威严作风,他堆起笑脸,满面春风地请求阿西阿都开口讲一讲这几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阿西阿都看他那副滑稽的模样,也不再沉默不语。他说他这几年跟在羊后面,见羊吃什么就跟着撸一把放嘴里嚼。几年下来,少说也吃了上百种植物和几十种野菌子。这其中有不少花朵艳丽,香气迷人的花草。他并不知晓关于香气的事。他和自己的女人根本感觉不到香气的存在。几年下来,肝脏没再痛过了,估计是要好了。阿丁务支为他准备了一些塑料袋子和密封性极佳的玻璃器皿,让他将体内的香气排放在里面,等凑够一定的数量就当香料卖出去,肯定能发家致富。他说他要立阿西阿都为致富典型在村里进行推广。如果可能,还要在外面打出品牌。至于品牌名称,他水平低,还没想好,得请人好好谋划再敲定。
阿西阿都不放羊了。他终日躺在家里晒太阳,做着发家致富,光耀门楣的春秋大梦。头几天,他倒是将准备好的塑料袋和玻璃器皿成功装满了。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当他如往日一般解开裤腰带,将一个玻璃器皿的豁口对准自己屁股想排放香气时。噗嗤一声,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险些迷晕自己。他一拨通村主任电话,刚哭丧着脸说明情况,对面就传来久违的痛骂之声。“连个屁事都解决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五 阿洛的泥人
整个春天的早晨,阿洛都在屋后挖红土。她早早地爬起来喂了猪食,扛着锄头去屋后的斜坡上,选一块埋着上好红土的地段,先刨掉表层的杂质,接着掘开一个深坑,将里面的红土像掏耳屎一样一点点掏出来,放在畚箕中,装满后抬进屋里。
没有人知道她在干什么。有人说她在用红泥巴刷墙壁,也有人说她在搭灶台。但具体情况谁也摸不准。毕竟谁也没有进过她家院落。
阿洛的男人去缅甸打工,这么多年来杳无音信。巫马村里有人从缅甸回来,说她男人在外面搞女人,孩子都大了。他在那儿安了家,不打算回来了。那是一个傍晚,当时霞光映红了整个巫马村,也映红了阿洛的脸颊。她呆呆地立在村口的那株杜梨树下,听来人讲述她男人的情况。她不发一言,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挑着两担水消失在家门口。一个女人,男人又不着家,寡妇似的,整天下地干活,喂牲口,操持家务,何必操这份心呢?村里的女人这样劝她,她也不恼,说男人嘛,玩累了,就会回来的。况且她还有儿子呢。
阿洛的男人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出现在巫马村里。他浑身上下破破烂烂,衣不蔽体,胡子拉碴,像一个鬼一样从村口的杜梨树下经过。村里有人早早赶着牛羊去户外放牧。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他仿佛中了邪一样,对村民的问候一概不理,迷迷糊糊地往阿洛家走。
所有人都被惊动了,人们涌进阿洛家的大门。只见她给男人换了一套崭新的西服,正给他洗头呢。
在院落里,人们发现了一排排几可乱真的泥人立在晨光中。它们身形、容貌与阿洛的男人全无二致。甚至额间的纹理,脸上的绒毛均纤毫毕现。只有表情各不相同,它们或平静,或大笑,或嗔怒,或悲戚,不一而足。此时,晨光柔柔地泻在院落中。一片朦胧的晨雾中,有人惊叹一声,发现每个泥人的大脚指上均由一条女人长长的发丝隐隐拴住。有小孩好奇之余扯了一下头发,发现每个泥人都整齐划一地往后退一步。在屋檐下的一小片泥潭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小小的泥人和一个胸部和臀部都无比硕大的泥人。凑近一看,可以发现每个泥人的胸口都插了一柄用木片制作的精妙绝伦的宝剑。这时,人群中有的女人羞红了脸,躲在大门囗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大家很快发现了女人们羞耻感的源头。在那一个个用头发丝连缀的男人的胯下,所有的阳根均如钢筋铁骨一般昂然挺立,但上面分明都插着明晃晃的钢针。
那个春天,巫马村桃树红艳,梨花洁白。所有的花草都很快艳得发亮。房前屋后总有野猫因发情而不停地追逐,嬉闹,翻滚。但阿洛的男人一看这个场景就暴躁不已。他找了老鼠药撒在房前屋后,恨不得药死所有发情的野猫。不止野猫,他痛恨配种的猪,野媾的狗以及牛马牲口。
阿洛更勤劳了,她下地劳动,砍柴,挑水,喂牲口。年猪养得比巫马村所有人家的都壮、都肥。她的男人再也不出门了,终日躺在屋前的矮檐下晒太阳。有时,他会大闹一场,村民们躲在他家屋后的小路上偷听。次数多了也就明白了。他说阿洛塑了泥人,害了他在缅甸的家人,还将他强行拉回了巫马村。自己也被她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了。阿洛从来不吵不闹,她和颜悦色地安慰男人,说现在儿子都这么大了。有没有那玩意儿,有什么要紧呢?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