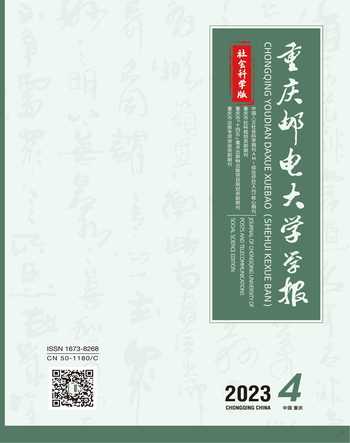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2023-11-08卢代富李晓文
卢代富 李晓文

摘 要: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难题。
关键词:数字平台;初创企业;经营者集中;遏杀式并购;反垄断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3)04-0051-14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勃兴催生了一批用户规模大、业务表现突出、经济体量大、限制能力强的超大型平台。依据《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超大型平台指在中国的上年度年活跃用户不低于5 000万、具有表现突出的主营业务、上年底市值(或估值)不低于1 000亿人民币、具有较强的限制平台内经营者接触消费者(用户)能力的平台。超大型平台能够通过其特有的网络效应以及被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显著放大的协同效应、锁定效应来抬高市场进入壁垒、不断强化自身先发优势,因而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为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并购成为超大型平台的行业信仰。通过并购初创企业,各超大型平台或直接扼杀初创企业,排除、限制竞争;或吸收整合初创企业的人才、技术、数据、用户等资源;或在其主营业务的根茎之上将触角伸向一个个新的关联领域。
不可否认,并购不仅能为超大型平台节约成本、增加收益,还可能通过形成多元化业务以及强化网络效应為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但是并购也将进一步巩固超大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提高市场进入壁垒、削弱市场竞争,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创新活力与消费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监管者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对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新兴领域进行监管,但实践中对该原则的理解存在偏差,这集中体现为重“包容”而轻“监管”。随着平台经济逐步发展成熟,平台经济的特点逐步为人所知,平台经济领域愈发严重的垄断乱象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自2021年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元年”起,针对平台的反垄断执法力度相较之前有了显著提升。据《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0)》和《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1)》公布的数据,2021年反垄断执法机构共审结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案件28件,对98件平台经济领域未依法申报的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作出了行政处罚。而2020年仅审结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案件6件,查结未依法申报的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3件。2022年1月27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明确指出:“加强平台经济……等重点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2年6月24日公布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11条明确规定,国家强化反垄断监管力量,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加强反垄断执法司法。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对实践中“宁纵不枉”、过分包容的态度进行纠正,指引反垄断监管向适度加大监管力度的方向迈进。
然而,与适度加强监管相对的是监管实践中的重重困境。首先,因被并购的初创企业不易达到强制申报的营业额标准,部分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并购难以进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视野。其次,竞争损害分析兼具复杂性和困难性,传统并购类型分析、以价格为核心的竞争损害分析模式以及侧重关注静态市场结构的反垄断分析框架纷纷失灵。再次,执法资源紧缺问题和证据偏在问题使得反垄断监管实践更加艰难。最后,面对模糊不定的竞争效应,错误判定行为违法所产生的“假阳性错误”成本与错误判定行为合法所产生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难以比较【“假阳性错误”指的是对本不应当进行规制的行为错误地进行规制,导致“威慑过度”;由此产生的成本即为“假阳性错误”成本。“假阴性错误”指的是对本应当进行规制的行为错误地未进行规制,导致“威慑不足”;由此产生的成本即为“假阴性错误”成本。】[1-4]。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作出规制与否的决策时难免陷入进退失据、举步维艰的境地。
为应对上述问题,笔者将对规制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贯彻实用主义理念,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经验,在降低错误成本及风险概率目标的指引下提出针对初创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机制构想,以期为相关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一、规制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行为的合理性
长期以来,芝加哥学派的“假阳性错误”成本远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观点在各国执法实践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为避免监管者因为对新业态领域认识不足而过度干预市场,从而产生大量“假阳性错误”,我国提出应当对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新业态进行“包容审慎监管”,然而该监管原则在被贯彻落实时却往往滑向“包容”的极端。随着平台经济的逐步发展成熟以及监管者对平台经济管控能力的逐步提升,实践中过度包容的做法的局限性愈发凸显。因此,有必要对规制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扭转重“包容”轻“监管”的错误认知并修正相关做法。
(一)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危害
1.强化平台市场支配地位
一方面,超大型平台能够识别可能为其带来竞争威胁的初创企业,并实施“胡萝卜加大棒”的收购策略进行扼杀,从而巩固自身市场支配地位[5]85。或利诱,以远高于初创企业市值(或估值)的高价实施并购;或威胁,以模仿开展相似业务并借助先发优势排挤初创企业相胁迫。大部分初创企业在该策略的驱使下,最终同意被收购;即便拒绝,也多因受到超大型平台的排挤而难以为继。哪怕初创企业本身并不属于超大型平台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但如果该初创企业可能被超大型平台的竞争对手收购,超大型平台也可能并购该初创企业,以避免竞争对手通过并购增强自身实力,加大对自己的竞争威胁[6]。通过减少相关市场中的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数量,或阻止竞争对手壮大势力,超大型平台得以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
另一方面,超大型平台通过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并可能形成封锁效应,从而进一步抬高市场进入壁垒。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两个方面。超大型平台通过并购进入新市场、提供多样化产品或服务,能够获得范围经济优势【范围经济发生于大量不同产品同时生产比单独生产更有效率之时,是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之一。超大型平台通过并购进入新市场,一方面可以实现对一定规模的用户资源的整合,使得提供多样化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低于分别提供的成本总和;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多样化产品或服务有助于改善用户的使用体验,可以增强用户对平台的参与意愿与用户黏性,从而使平台收益水平得以提升,平台由此获得范围经济优势。】[7-8];通过并购初创企业和聚合初创企业的人才、技术、数据、用户等资源,能够同时扩大生产服务规模与用户规模,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方面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发生于所有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出水平以更大比例增加之时,是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供给方规模经济表现为:超大型平台通过并购和聚合初创企业的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在扩大生产或服务规模的同时,实现分工细化、专业化、技术化,从而实现规模经济。需求方规模经济表现为:超大型平台通过并购,吸收初创企业用户,扩大用户群体规模,并基于平台经济的生产与消费同一化的特点,使得平台运行的平均成本随用户规模扩大而减少,平台收益随交易规模扩大而增加。】[7-9]。实践中完成了非横向并购的超大型平台还可能会进一步实施平台服务降级、垄断关键生产要素数据等封锁行为[10],或者采取措施将其在原本业务相关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传导至新业务的相关市场,从而阻碍超大型平台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取供应或进入市场,实现封锁效应[11]。
2.遏制行业创新发展
首先,对于资产雄厚的超大型平台而言,相较于自主研发新的产品、服务,通过并购吸取初创企业的创新点所消耗的成本更低,因而超大型平台可能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12]。其次,超大型平台试图从根源上掐灭初创企业的创新火苗,初创企业常常在进入相关市场时就需要预设被收购的结局,因而更倾向于研发能够改进或扩展平台功能的补充产品、服务,很难再形成颠覆式创新[13]。最后,超大型平臺针对初创企业频繁实施的并购活动,会削减投资者对超大型平台潜在竞争对手的投资意愿[14],而资金压力多是初创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这将进一步遏制行业的创新发展。
3.减损消费者利益
一方面,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将直接导致相关市场中经营者的减少,有时也会导致产品、服务的减少,这直接限制了消费者对经营者以及商品、服务的选择自由[15]。另一方面,通过并购初创企业,超大型平台不断巩固和强化市场支配地位。具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平台在与消费者进行直接互动时,极易实施剥削性滥用行为,减损消费者福利。例如,明显不当地收集与处理用户个人信息[16]、制定超高定价[15]、依据用户偏好设定显著不公平的价格歧视,等等。
(二)“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成本比较
鉴于反垄断分析的复杂性与执法队伍素质的参差不齐,在监管过程中,出现“假阳性错误”“假阴性错误”在所难免,因此,面对竞争效应不确定的行为时,“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及成本比较即成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规制或容忍的关键。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认为,“假阴性错误”能够被市场力量所纠正,而“假阳性错误”一旦发生,可能带来显著的成本,且无法被市场力量所弥补;因此,“假阳性错误”成本远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应当假定绝大多数市场行为是好的,拔高反垄断干预的门槛,以减少“假阳性错误”的发生[3]。不过,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分析结论的成立需要具备严格的前提条件,如市场的有效性、对于长期效果而非短期效果的关注等[17]。这种前提假定是否与我国平台市场状况以及反垄断执法现状相匹配,尚存疑问。首先,超大型平台借助其市场支配地位频繁针对初创企业实施并购,纵然颠覆式创新仍然可能发生,但已愈发难以实现。此种情形下,超大型平台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非但不会导致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其次,即便市场力量最终纠正了“假阴性错误”,时间也往往很漫长,此间形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很高昂[18],并不逊于“假阳性错误”成本。因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就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而言,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远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主张存在明显局限性。
当然,据此也不能证明:在超大型平台面前“假阳性错误”成本必然小于“假阴性错误”成本。虽然美国《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反托拉斯案件中若合并行为涉及支配性企业,则“假阴性错误”成本更高;欧盟近年来针对超大型平台采取的严厉监管措施也能够侧面反映其对于“假阳性错误”成本小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判断,但错误成本大小与本土实际情况密切相关,需要大量本土实证分析与研究作为论断基础,照搬结论可能导致水土不服。目前,针对我国平台市场的相关实证研究尚不充分,有待后续进行。
由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行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且可能遏制行业创新发展、减损消费者利益;又因为在对超大型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中,“假阳性错误”成本并不高于“假阴性错误”成本,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行为不应过度容忍,而应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当然,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应当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规制,仍需在综合考虑具体并购损害以及错误成本之后再做决定。对于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不存在抗辩事由、且“假阳性错误”成本小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当然应当对之进行规制。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实现促进創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并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二、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规制困境
(一)营业额标准难以适用
我国对经营者集中申报采取营业额标准,且申报门槛较高。《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要求,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经营者集中应当事先申报:(1)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2)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
由于在超大型平台针对初创企业的并购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往往只有超大型平台与初创企业,因此,初创企业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必须超过4亿元人民币,才可能达到上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然而,被收购的初创企业处于成立初期,营业额一般不高,甚至可能为拓展市场和发展用户群体采取补贴措施而自愿牺牲部分营业额,显然无法达到上述营业额标准。因此,即使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也往往无需进行申报,可以直接进行并购。以传统的营业额标准来筛选需要进行审查的经营者集中,该标准未免过于宽松,会导致大量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被遗漏。
为减少申报标准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3年3月10日公布,于同年4月15日起施行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等有关规范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主动调查权,以应对未达申报标准、但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2022年修改后的《反垄断法》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设置了“要求经营者申报”的环节作为启动主动调查程序的缓冲程序,即对于未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若有证据证明该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经营者未依照规定进行申报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但不论是“要求经营者申报”,还是主动调查,原则上都是申报标准失灵后的补救措施,筛查效果并不稳定,仍无法完全消除申报标准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据此,要想根本性地解决申报标准失灵问题,仍需回归矫正申报标准这一本源,而不能过分依赖于补救措施。
(二)竞争损害分析困难
1.并购类型分析难以应对复杂并购行为
并购可以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类并购均在超大型平台对初创企业的并购中有所体现,但实际区分较为困难。超大型平台为拓展业务范围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既可能属于横向并购,即自主研发开展新业务并扼杀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初创企业;也可能属于混合并购,即并购吸收初创企业的相关业务。但上述两种情形具有极为相似的外观,实践中难以区别。此外,超大型平台还可能为避免竞争对手因收购初创企业扩大市场势力而抢先将初创企业收入囊中[6],此种并购亦难以明确并购类型。既然对并购类型的区分不甚明了,适用何种损害分析理论自然就难以确定。
2.价格分析难以应对非价格损害
与传统企业不同,数字平台具有收费端和免费端两侧,常常在不同边之间采取交叉补贴,实施倾斜式定价策略,初创企业也常常以牺牲营业额为代价来招揽新用户。因此,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行为所造成的竞争损害难以反映到价格上,而更多体现为对创新以及消费者利益的减损。传统以价格变动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特征明显不适配,对此若僵硬套用,则极易产生“假阴性错误”。
3.静态分析难以应对长期、动态竞争
相较于传统工业领域,平台经济领域重视创新竞争,出现创新替代的可能性更大,其动态竞争特征突出。因此,在当下看来不甚显眼的初创企业,若不受超大型平台的打压,则很可能凭借突破性创新来吸取资本、汇聚用户,在未来成长为超大型平台的劲敌。然而,即便新旧产品、服务替换的速度已较工业时代大大加快,初创企业由初创期发展至成熟期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企业成长周期越长,其变数就越多,判定初创企业未来发展情况就越困难。传统静态分析已难以应对竞争的动态性与发展的长期性的双重挑战,因而,在研判市场未来发展态势时,反垄断执法机构面临着严峻考验。
(三)执法资源有限
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向来存在人员紧缺及经验不足的问题[19]。国家反垄断局揭牌成立之后,其下所设的反垄断执法一司、二司和竞争政策协调司为人员编制的扩充预留了空间。虽然执法资源紧缺问题将随着人才的加入而在未来得到一定缓解,但由于人员编制存在上限,且对专业人才的吸取和培养也需要一定时间,执法资源仍难以达到十分宽裕的状态。
(四)证据偏在问题突出
相较于作为“局外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显然掌握更多有关经营者集中的信息而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并且,为确保经营者集中的顺利进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能隐匿或销毁能够体现并购反竞争效果的内部文档,这就加大了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证据的难度。在竞争损害分析本就十分复杂的前提下,证据偏在问题使得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竞争损害的证明难上加难。
三、规制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制度设计理念
(一)谨慎借鉴国外经验,因地制宜探索中国方案
面对市场支配地位日益强化且愈发肆无忌惮地排除、限制竞争的超大型平台,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已成为包括我国、美国、欧盟在内的多个反垄断司法辖区的广泛共识。但监管力度大小与各反垄断司法辖区的特定市场状况、执法及司法机关的工作能力、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发展规划等诸多复杂因素直接相关,存在一定地域差异,不能对其一概而论。欧盟及美国针对平台经济采取的相对激进的反垄断监管措施,固然存在可资借鉴的有益之处,但整体的监管态度未必适合我国当前的情势。
相较我国与美国,欧盟缺少本土超大型平台。近年来,欧盟相继通过《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两部法案,針对美国超大型平台采取诸多严厉监管措施。因此,在严厉监管态度的背后,欧盟很难不被揣测是否隐藏着打压外国数字巨头、保护本土平台企业的私心[20];若盲目跟随欧盟反垄断举措,对超大型平台进行过分严格的监管,就相当于迎合欧盟可能存在的打压国外数字巨头的愿望而无异于自掘坟墓。
盲目跟随美国的反垄断举措亦不可取。首先,平台市场状况是各司法辖区决定监管力度大小的重要依据,我国平台市场虽已趋于固化,但固化程度尚不及美国[19]。其次,美国监管态度从宽容到严厉的转变主要受新布兰代斯学派的影响,但该学派的流行具有偶然性,且饱受争议。最后,美国反垄断采取司法主导模式,且属于判例法国家,其反垄断诉讼持续周期往往较长,原被告双方所聘请专家能够进行充分辩论,且诉讼期间可能经历政府内阁更替,因此司法裁判完全可能为任何不合时宜的法规、政策兜底[21]。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一旦出台,就将在执法、司法中被严格贯彻落实,由于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
因此,我国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时,决不能照搬照抄,而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因地制宜,探索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超大型平台治理方案。
(二)正确认识“包容审慎监管”原则,降低错误风险概率及成本
为避免过于激进莽撞的法律法规、政策、执法、司法为平台经济这一新业态的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我国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始终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面对平台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不急于冒进,对超大型平台保持谦抑包容的态度,在时机成熟时,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慎重采取最恰当的监管措施。“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在反垄断执法、司法层面的贯彻落实为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随着平台经济的深入发展,超大型平台的特性也逐渐为人所知,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超大型平台的监管已由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了现在初步理清治理思路与方式的阶段,监管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并且随平台市场的固化程度不断加深,“假阴性错误”成本已经不逊于“假阳性错误”成本。因此,在面对市场无法自发纠正或至少无法及时、有效纠正的垄断乱象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摒弃过度包容的执法态度,适度加强监管。但总体而言,相较于其他传统行业,平台经济毕竟属于新兴领域,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的监管能力仍存在不足,在超大型平台反垄断监管的“假阴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阳性错误”成本这一判断尚未在我国得到证成的前提下,若盲目效仿欧盟及美国过于激进的监管理念,可能造成大量“假阳性错误”且难以补救。因此,应当循序渐进、稳扎稳打,采取与监管能力相适应的监管态度,并随着监管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包容与规制之间不断寻求新的平衡。而这种相对和缓的监管态度恰与“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不谋而合,这也体现了“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强大生命力,预示着“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作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指导原则发挥重要作用。
受限于初创企业并购反垄断监管的复杂性及执法人员工作能力的有限性,虽然“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的发生无法完全避免,但发生错误的风险概率以及错误成本可以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得到降低。
为降低发生错误的风险概率,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其一,结合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特点,对旧制度力所不逮之处进行补充完善,例如采用符合初创企业并购特点的新申报标准、竞争损害分析方法、证据搜集方法,以补正传统制度安排;其二,在反垄断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立分类分级监管机制,合理配置执法资源,将大部分执法力量集中到反竞争行为高发区,以提高监管准确性。
要降低错误成本,需要两个维度的努力。其一,通过平衡错误风险概率降低整体错误成本。错误风险概率与反垄断监管总错误成本大小密切相关。例如,在“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时,应当采取相对宽容的监管态度,降低“假阳性错误”发生的风险概率,以降低总错误成本;反之则应当采取相对严格的监管态度,降低“假阴性错误”发生的风险概率。但是,当难以明确“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成本大小时,就应当谨慎平衡错误风险概率,而不应盲目倾向于包容或严格,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筹码来冒险赌博。平衡错误风险理念主要体现于证明压力的分配上,应当使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承担基本相当的证明压力。其二,分别降低“假阳性错误”及“假阴性错误”成本。例如,通过灵活选择合适的救济措施来降低“假阳性错误”成本,以及通过引入事后调查制度以降低“假阴性错误”成本。
(三)坚持从实际出发,吸取结构主义的有益理念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在基本原则条款中明确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平台经济领域开展反垄断监管应当坚持“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原则的提出无疑是对行为主义理论的严格贯彻。但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同等的监管力度对待违法实施垄断行为概率明显不同的经营者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监管出现错误的风险概率增加,或监管任务难以及时完成。
为增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平台的用户规模、业务种类、经济体量、限制能力,将平台分为不同等级,并要求超大型平台承担更严格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结构主义理论的回归,即认为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中的垄断企业更容易滋生反竞争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管,以尽可能减少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及对市场竞争的不利影响。
虽然分级监管与“平等对待”原则之间存在差异,但并非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对超大型平台的严格监管必须建立在法律法规等“硬法”和行政指导意见等“软法”的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监管级别划分的依据是特定的标准,而非特定的经营者的名单。在具有动态竞争特性的平台经济领域,任何中小平台都可能通过破坏式创新成为当下市场结构的颠覆者。一旦其成长为超大型平台,就与其他超大型平台一样,需要按照相同的规定承担相同的特别责任。另一方面,对超大型平台的严格监管并不意味着推定其参与的所有经营者集中均具有反竞争效果。认定经营者集中违法、禁止或附条件批准集中,仍将经过严格的分析论证过程,必须满足比例原则的要求,这与“平等对待”原则的行为主义内核并不矛盾。
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到芝加哥学派的行为主义理论的流行,再到新布兰代斯学派的兴起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回归,反垄断理论的变迁与起伏给我们的启示是:既然反垄断理论是为更好地解决垄断乱象、维护市场竞争而诞生,且在与实践的碰撞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在单一理论难以有效应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时,自然无需固守窠臼。坚持从实际出发,求同存异,在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结构主义的有益理念,有助于更好应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难题。
四、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规制机制构建
(一)矫正申报标准
由于初创企业营业额一般不高,对初创企业并购申报适用传统营业额标准可能产生大量“假阴性错误”。为提高监管准确性,降低发生错误的风险概率,可以结合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特点,以初创企业市值(或估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标准补正传统营业额标准。
1.初创企业市值(或估值)标准
在传统行业中,企业市值受营收、净利润等财务指标的影响较大,但在数字经济行业中,企业市值的增速往往远高于营收的增速[22],与仅能体现企业短期市场势力的营业额标准相比,市值(或估值)标准显然更能反映出初创企业的创新价值以及未来发展潜力。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以及奥地利《卡特尔法》所引入的交易额标准与初创企业市值(或估值)标准具有相似性。但是由于交易额存在一定虚构、虚报风险,申报义务可能被回避,因此,企业市值或由第三方作出的企业估值相对更加客观公允,也能更好实现作为申报标准的初步筛选功能。据此,《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条即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行为,拟新增市值(或估值)标准作为对营业额标准的补充【《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条规定:“经营者集中未达到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一)其中一个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超过1 000亿元人民币;(二)本规定第二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其他经营者市值(或估值)不低于8亿元人民币,并且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占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2.用户规模、流量规模标准
用户规模是评估数字市场中初创企业的市场价值的关键因素,数字平台网络效应、锁定效应以及协同效应等的实现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用户作为支撑。但是用户群体依照其活跃度等级又可以划分为忠实用户、活跃用户、回流用户、不活跃用户以及流失用户,用户活跃度是在用户规模的基础之上辅助评估企业市场价值的依据,与用户活跃度、用户规模以及企业处理应用数据能力直接挂钩的另一标准就是流量规模标准。流量规模标准可以同用户规模标准一起,成为数字市场中补正营业额标准的新标准。
(二)改进竞争损害分析方法
1.弱化并购类型分析的地位
超大型平台对初创企业实施的并购行为模式复杂多样,常常难以精准辨别并购类型,若依旧坚持将并购类型分析作为反垄断并购审查的第一步,将无端耗费有限的执法资源,且可能错误判断并购类型,导致分析內容存在遗漏,从而出现“假阴性错误”。因此,可以适度弱化并购类型的分析地位。有学者建议,可以直接将初创企业并购作为一种特殊的并购类别,在目前的非横向并购损害理论中注入横向并购损害理论的内容,构建综合性的损害分析框架[23]。该提议对于提高监管规制的准确性,降低错误发生风险概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还需要框定适用前提,即并购类型分析确有困难时,为某些并购类型较为清晰的并购行为预留空间。
2.关注非价格竞争损害
不同于传统并购,初创企业并购所带来的竞争损害更多体现在非价格维度上,包括创新、质量、选择机会等方面。若依旧盲目套用以价格变动为核心的传统分析框架,将导致大量“假阴性错误”。因此,应当扩充竞争效应分析维度,对创新、质量、选择机会等非价格维度有所侧重,以减少错误发生。
数字经济时代,能够吸引超大型平台注意的初创企业多具有鲜明的创新优势,反垄断监管应当对创新維度予以高度重视,既应关注平台以并购方式直接扼杀创新的风险,也应关注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对超大型平台及初创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的负面影响。质量因素范围最广,包括数字产品和服务本身的质量、数据质量、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等多方面。质量与消费者体验直接相关,是消费者福利的重要内容。选择机会则关乎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消费者福利标准和消费者选择标准共同组成反垄断法分析中消费者利益的判断标准[15]。因此,在评估竞争效应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应当关注并购对质量、选择机会的影响。
3.降低竞争损害分析错误成本
由于对非价格竞争的定量测试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且这一状态短期内仍将持续,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非价格竞争依旧主要采取定性分析方法,而定性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一定主观性及不确定性[24]。与此同时,初创企业并购所带来的竞争损害在短期内多数无法显现,在竞争的动态性及初创企业发展的长期性的重重阻碍之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很难准确研判未来市场的竞争态势,这种预期评估也极具不确定性。因此,面对模糊不定的竞争影响,在“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均可能随机出现、且无法避免之时,采取措施降低错误成本即成为有效应对之策。
(1)运用救济措施,降低“假阳性错误”成本
相较于直接禁止,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所对应的“假阳性错误”成本显然更低。实践中,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规制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中,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比例常常远高于禁止的比例;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救济措施中结构性救济措施的错误成本又高于行为性救济措施。结构性救济措施追求眼前执法效率和力图“一劳永逸”,但忽视执法效果,则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25]156。而行为性救济更具灵活性和可恢复性[25]167,可以避免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错误成本更低,且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更为适配。例如,很多情况下,初创企业之所以被超大型平台并购,是因为其具有某些超大型平台想要获取的技术,或者其技术使超大型平台受到了威胁[26]。因此,可以要求超大型平台必须就该技术向其他经营者授予许可使用权,这样既可以使超大型平台获取相关技术,又不会给市场竞争带来过度影响,即便最终发现无需对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也可以及时止损【如United States v.Baroid Corp.,59 Fred.Reg.2610(1994)中表明:允许大企业收购一项竞争性的技术,但条件是它必须将该技术向他人授予许可。】。
(2)引入事后调查,降低“假阴性错误”成本
由于事后调查可能影响经营者对并购结果的稳定预期,且相关处理措施可能导致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我国《反垄断法》仅规定了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需要申报而未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调查,对余下两种情形:经申报批准进行的经营者集中以及无需申报即可进行的经营者集中,并未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自主调查权。
但是由于初创企业并购所造成的竞争损害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经营者集中审查容易出现错误,所以延长监管时间跨度,在必要情形下进行事后调查以及时发现并纠正“假阴性错误”,对于避免“假阴性错误”成本随时间延续而持续增加具有重要意义,且事后调查对于妄图通过并购初创企业来排除、限制竞争的超大型平台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因此,目前已有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建立了特定情形下的事后调查制度,并且大部分采取事后调查制度的国家为减少事后调查的不利影响,都对事后调查作出多种限制。我国在引入事后调查制度时,也应当对事后调查权力进行约束,比如,规定事后调查的启动条件,框定事后处理措施的手段范围,以在纠错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过度干预问题的发生。
(三)健全分类分级监管机制
为更大限度利用有限的反垄断执法资源,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反垄断法》第37条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应当依法加强对涉及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的经营者集中的审查。上述意见及规定对于分类分级审查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仍有待细化。关于细化分类分级审查制度的举措,学界已有一些讨论。多位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经验,从不同角度进行尝试,先后提出应当对重叠并购、主导型平台(即“平台的平台”)以及连续实施并购企业所实施的并购[27]、特定业务领域的并购[28]、特定并购动机以及特定产品类型的并购[23]进行相较一般审查更为严格的审查。但一方面,上述研究所指出的考虑要素较为零散,不够系统全面;另一方面,不论是《意见》《反垄断法》,还是学界有关研究,其分类分级思路主要汇集于审查阶段,没有拓展至更广阔的监管领域;仅考虑应当严格审查的内容,对可以作为简易案件申报的情形缺乏补充。对此,笔者尝试就超大型平台、初创企业、并购动机、并购行为这四个维度展开论述,讨论应当严格监管的情形以及可以作为简易案件申报的情形,并据此建立多维一体的分类分级监管机制,其流程详见图1所示。这有利于合理配置执法资源,提高监管准确性,降低发生错误的风险概率。
1.应当纳入严格监管的情形
严格监管要求在一般监管的基础上以更加严格审慎的态度进行特别监管,既包括更加严格的审查,也包括更加严密的调查。就现阶段的反垄断监管而言,严格监管的情形可以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1)维度一:超大型平台
首先,应当严格监管长期连续实施并购的超大型平台[27]。相较于偶尔实施并购的超大型平台,长期连续进行并购的超大型平台有更高的概率将并购当作排除、限制竞争的手段,其实施的并购具有反竞争效果的可能性更高。其次,应当严格监管曾多次违法并购的超大型平台。惯于不依法申报即违法集中的经营者多明知并购可能因具有反竞争效应而不被准许,却依旧存在侥幸心理,且数次被罚仍不悔改。相较于其他经营者,此种经营者具有更高的违法实施并购行为的风险。
(2)维度二:初创企业
首先,应当严格监管对处于民生、金融、科技、媒体等行业領域的初创企业实施的并购。民生、金融、科技、媒体等行业领域事关国计民生,在这些领域中发生反垄断监管错误为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最为沉重、深远。因此,在制定细化规则时可以将重点关注的领域限定为“民生、金融、科技、媒体等”,以明确当前时期“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外延。其次,应当严格监管对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实施的并购。初创企业当下的经营状况与创新能力是反垄断执法机构预判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根基所在,而初创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正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评估并购行为竞争效果的重要一环。与一般初创企业相比,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显然更具有成长为超大型平台竞争对手的潜质,超大型平台对这种初创企业的并购具有更大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嫌疑。
(3)维度三:并购动机
应当严格监管以排除、限制竞争为主要动机实施的并购。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动机主要包括三类:排除、限制竞争,拓展多样化业务,集中人才、技术、数据、用户等资源。其中,以排除、限制竞争为主要动机的并购行为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效应,需要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当然,并购动机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等特点,需要经过内部文档调查、举报信息接收分析、并购组成价格分析等途径加以证实,相关程序事项仍有待法律法规的完善[5]99。
(4)维度四:并购类型
首先,应当严格监管横向并购。非横向并购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的相关市场,一般不会造成直接的竞争损失,对竞争的损害具有间接性,而横向并购更容易严重损害市场竞争,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给予更多的关注。虽然超大型平台对初创企业实施的并购具有复杂性,能够辨别并购类型的情况相对较少,但在能够清楚辨别时,上述分析仍有实用价值。其次,应当严格监管存在并购溢价的并购。在进行并购组成价格分析的过程中,若存在不能归于资产固有价值、预期协同效应、谈判技巧等并购交易本身因素的并购溢价,且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无法对其进行合理解释,即可以合理怀疑该溢价是超大型平台为排除、限制竞争或创新损失支付的对价[5]96。鉴于此种类型的并购具有较高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可能性,反垄断执法机构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并进行严格监管,自然具备合理性。
2.可以作为简易案件申报的情形
为更高效地利用反垄断执法力量、减轻执法资源压力,《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与《关于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对可以作为简易案件申报的案件作了规定[29]。2022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将部分适用经营者集中简易程序的案件委托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审查,简易案件对于缓解执法压力的重要意义得到进一步凸显。但目前区分简易案件与一般案件的关键指标——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仍多以销售额计算,在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中的适用具有局限性。结合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特点,可将以下两种情形作为简易案件进行申报。
(1)维度一:初创企业
首先,专门为改进或扩展特定超大型平台功能而开发补充产品的初创企业,对其实施的并购可以作为简易案件申报。以色列竞争管理局即以被收购产品是否只能与特定平台集成为依据划分审查等级。这样设计产品的原因即在于:与特定平台集成的初创企业,既非超大型平台的竞争对手,也无法服务于超大型平台的竞争对手,因此超大型平台并购这类初创企业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一般较小[23],可以仅作为简易案件进行申报。其次,针对经营状况较差且创新性不足的初创企业进行的并购交易,可以作为简易案件进行申报。这种初创企业既难以成长为超大型平台的竞争对手,也极少拥有关键数据、用户等资源,以及具有吸引力的技术、产品、服务,对这种初创企业实施的并购往往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十分有限,可以被归类为简易案件。
(2)维度二:并购动机
以获取人才资源为主要动机进行的并购交易可以作为简易案件申报,这种并购时常发生于初创企业本身经营状况较差和难以为继之时,此种情形下实施的并购几乎不会对市场竞争带来不利影响。即便初创企业本身经营状况尚可,超大型平台以获取人才而不是创新技术、产品、服务为主要并购动机,也侧面反映出该初创企业创新性不足。因此,结合具体情形,对此种类型的并购交易,可以作为简易案件进行申报和简易审查。
(四)调整证据规则
1.调整证据收集规则
提高反垄断执法机构监管准确性、降低错误发生风险概率需要其掌握足够信息,通过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主动搜查权以及类推适用证据开示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证据偏在问题。
(1)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主动搜查权
实践中能够证明并购具有或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的信息往往被发起并购的平台所隐匿或销毁,而不会被主动提供给反垄断执法机构。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可以借鉴欧盟等司法辖区的做法,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相较之前而更为广泛的主动搜查权,包括特定情况下的突击检查权和技术手段调查权[30]。但行使主动搜查权也要严格遵循比例原则,选择以对市场主体经营自由、商业秘密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
(2)类推适用证据开示制度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证据开示制度只适用于民事诉讼中,但其矫正证据偏在的功能也与并购审查的需求相契合,因此可以考虑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类推适用证据开示制度。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应当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出示所有与并购相关的文件资料,拒绝披露或隐匿不报者将承担不利后果,从主动开示和被动开示两个方面降低反垄断执法机构收集证据的难度。
2.调整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就竞争损害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两种主要观点。第一,推定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行为全部具有反竞争效应,将并购审查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交由实施并购行为的超大型平台承担。第二,若通过各类交易动机识别证据,能够合理怀疑超大型平台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目的,即可以推定相应交易具有反竞争损害[5]99-100。上述两种观点中,与第一种观点相匹配的决策前提为“假阴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阳性错误”成本。为降低整体错误成本,该观点认为应当采取严格的监管理念,从而降低“假阴性错误”风险概率。该观点以美国《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为代表,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却未必符合我国国情。第二种观点则与笔者观点存在密切联系,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笔者所提建议,类推适用举证责任缓和制度与优势证据规则,是对“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与平衡错误风险概率理念的贯彻落实。目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固化程度尚不及美国,“假阳性错误”和“假阴性错误”成本大小比较尚无定论,为稳妥起见,应通过制度设计平衡错误风险,将一部分而非全部的证明压力由监管者转移至被监管者,在适度降低“假阴性错误”的风险概率的同时,避免“假阳性错误”的风险概率的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就集中相关信息而言,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相较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地位的不对等性,所以,类推适用举证责任缓和制度与优势证据规则,要求被监管者分担部分证明责任,并不会对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
(1)类推适用举证责任缓和制度
举证责任缓和制度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中,指的是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若原告由于技术或其他方面的障碍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则可以适当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在原告证明达到该标准时,视为其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转换,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31]。类推适用于反垄断执法,即表现为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反垄断执法机构若按照一般证明标准证明存在竞争损害确有困难,则可以将证明标准适当降低,只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竞争损害的证明达到较低的证明标准,即推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再由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对并购交易不具有反竞争效果进行证明。
(2)类推适用优势证据规则
理论上,监管者只有在认定特定并购具有“实质性竞争损害预期”之后,方能够禁止并购或者施加附条件补救措施[5]99。虽然何为实质性竞争损害预期并不清晰,但至少能够明确,作为与潜在竞争损害理论明显相异的标准,实质性竞争损害预期标准更加侧重短期内能够在市场结构、价格等要素上有明显体现的竞争损害。然而,由于并购初创企业所造成的损害难以反映在市场结构及价格上,且短期内并不明显,采用实质竞争损害预期标准将会给反垄断执法机构带来过于沉重的证明压力,监管者很难证明存在竞争损害,从而产生大量“假阴性错误”。对此,借鉴诉讼程序中的优势证据规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思路。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尽最大努力搜集证明材料、进行竞争损害分析之后,只要其能证明有可能存在竞争损害,即可推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不论竞争损害的程度大小,不论竞争损害发生时间的远近,也不论竞争损害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以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竞争损害不存在。结合双方证明内容,只要存在竞争损害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竞争损害的可能性,即初步认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以再就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证明。
五、结 语
由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行为可能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并影响市场的创新活力和消费者权益,且反垄断监管的“假阳性错误”成本并不高于“假阴性错误”成本,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行为不应过度容忍,而应适度加大监管力度。但是,反垄断规制实践中存在传统申报标准难以适用、竞争损害分析困难、执法资源不足、证据偏在问题突出等监管困境。为有效识别应当受到规制的超大型并购初创企业的行为,同时降低反垄断监管的错误风险概率和错误成本,应当完善相应的反垄断规制机制,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在有选择地借鉴有关国外经验、吸取结构主义的部分有益理念之后,矫正申报标准、改进竞争效应分析方法、建立分类分级监管机制、调整有关并购竞争损害的证据规则,如此才能更好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实现促进创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并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EASTERBROOK F H.Limits of Antitrust[J].Texas Law Review,1984(1):1-40.
[2]希尔顿K N.反垄断法:经济学原理和普通法演进[M].赵玲,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5.
[3]李剑.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体系冲突与化解[J].中国法学,2014(6):138-153.
[4]丁茂中.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积极失误”与“消极失误”比较研究[J].法学评论,2017(3):75-81.
[5]王伟.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J].中外法学,2022(1).
[6]BRYAN K A,HOVENKAMP E.Antitrust limits on startup acquisitions[J].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20(4):617.
[7]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译.19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08-109.
[8]鲁彦,曲创.互联网平台跨界竞争与监管对策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9(6):112-117.
[9]阮飞,李明,董纪昌,等.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的动因、效应及策略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7):69-72.
[10]杨东,傅子悦.社交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51-61.
[11]黄勇,蒋涛.非横向企业合并的反垄断规制——以欧盟《非横向合并指南》为基础展开[J].清华法学,2009(2):147-159.
[12]CRAWFORD G,VALLETTI T,CAFFARRA C.How tech rolls:Potential competition and reverse killer acquisitions[EB/OL].(2020-05-11)[2022-11-09].https://cepr.org/voxeu/blogs-and-reviews/how-tech-rolls-potential-competition-and-reverse-killer-acquisitions.
[13]ARGENTESI E,BUCCIROSSI P,CALVANO E,et al.Merger policy in digital markets:An ex post assessment[J].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2021(1):95-140.
[14]OECD.Start-ups,killer acquisitions and merger control[EB/OL].[2022-11-09].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start-ups-killer-acquisitions-and-merger-control-2020.pdf.
[15]焦海涛.反垄断法上的竞争损害与消费者利益标准[J].南大法学,2022(2):15-16.
[16]焦海涛.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从附属保护到独立保护[J].法学,2021(4):108-124.
[17]李剑.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当然违法原则的回归[J].中外法学,2019(4):1004-1024.
[18]卢代富.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解读[J].现代法学,2019(4):116-122.
[19]沈伟伟.迈入“新镀金时代”:美国反垄断的三次浪潮及对中国的启示[J].探索与争鸣,2021(9):74-75.
[20]王先林.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国际观察与国内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5):49-64.
[21]曾雄.论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模式的转型——基于对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思考[J].管理学刊,2022(1):1-12.
[22]仲春.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检视与完善[J].法学评论,2021(4):140-150.
[23]方翔.数字市场初创企业并购的竞争隐忧与应对方略[J].法治研究,2021(2):146-148.
[24]叶明,张洁.大数据竞争行为对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挑战与应对[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6-39.
[25]孙晋.谦抑理念下互联网服务行业经营者集中救济调适[J].中國法学,2018(6).
[26]霍温坎普H.联邦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法律及其实践[M].许光耀,江山,王晨,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557.
[27]王先林,曹汇.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三个关键问题[J].探索与争鸣,2021(9):64.
[28]叶明,冉隆宇.数字平台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疑难问题研究[J].电子政务,2022(8):56-66.
[29]王晓晔.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成就与挑战[J].法学评论,2017(2):11-25.
[30]OECD.Summary of discussion of the breakout sessions exploring investigative powers in practice[EB/OL].[2022-11-09].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AF/COMP/GF(2018)18&docLanguage=En.
[31]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改革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成功与不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9-16.
Research on the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start-ups by mega-platforms
LU Daifu, LI Xiaowen
(Economic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by mega-platforms targeting start-ups may hav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However, due to Chicago Schools false cost theory and the antitrust regulatory dilemma, antitrust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long taken a lenient attitude towards M&A by mega-platforms targeting start-ups,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fair competition,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Because of this, under the premise of “inclusive and prudent regulation”, moderately stronger regulation should be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regulation of M&A by mega-platforms targeting start-ups. Based on this approach, the following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to the future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M&A by mega-platforms targeting start-ups: the existing declaration criteria for M&A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the market capitalization, user size and internet traffic size of start-ups; a competition damage analysis framework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u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regime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ater for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M&A by mega-platforms targeting start-ups; the challenge of obtaining regulatory information for antitrust enforcement agencies is addressed by giving them broader evidence-gathering powers and by increa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n operators participating M&A.
Keywords:digital platform; start-ups; concentration of undertakings; killer-acquisitions; anti-monopoly
(编辑:刁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