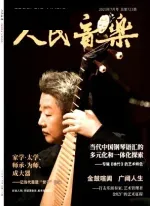托生命于传统 寄情怀于民间
2023-11-08张君仁杨银波
张君仁 杨银波
乔建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躬耕中國传统音乐领域四十余载,著述丰盈。他上承杨荫浏、黄翔鹏等老一辈传统音乐大家的学术传统,下启当代音乐学人的思想与智慧,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承接者与领军者。2023年6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历时四年精心打磨的“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系列·乔建中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出版发行,该文集是乔建中先生扎根田野四十余年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精华之凝结,是中国传统音乐领域又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成果。文集共10册,8个专题,359篇文章,两百余万文字,承载和蕴含了作者睿智的学术理念与厚重的学术思想。文集虽围绕不同对象,选用不同文体,基于不同目的,写于不同时间,但这些“不同”背后都蕴含着深层的“一致”,也即都是乔建中学术理念与思想的具体承载体。所谓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不是一次性思辨的结果,不是偶然性的思想的火花,而是在无数次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倾向与学术态度,它既受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有基于个体学习和判断的主动追求。回望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领域辛勤耕耘的一生经历,再看着眼前这套倾注了其毕生心血的学术文集,先生鲜活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思想跃然眼前,值得我们后辈学人品味学习。
一、眼光向下、躬耕田野的学术理念
乔建中先生一贯主张并践行着“眼光向下”的学术理念,在田野、在民间寻找中国传统音乐的答案。“采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干多年前,《礼记·王制》记载的周代“命太师呈诗以观民风”,《夏书》记载的“遒人以木铎徇干路”,是一种眼光向下:两千多年前,《汉书·艺文志》记载的“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凤”,是一种眼光向下.一千多年前,唐代的《敦煌曲子词》、宋代的《乐府诗集》,同样是眼光向下的成果结晶.八十多年前,毛泽东的“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论说,是一种眼光向下.八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的再次强调,也是一种眼光向下。因此,眼光向下不仅是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也是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乔建中先生的文集全面而完美地体现了这种历史与现实合一的精神内涵,反映了他以“文化托命”的音乐学人之情怀。
传统音乐研究的基础是资料搜集,需要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过程中不断累积与体认。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领域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来自田野,出自民间,因此,先生一生保持着对田野的亲近和对人民的敬畏之心。先生的学术研究始于民歌,就民歌领域而言,从地域、歌种看,他的民歌研究包括西北地区的花儿、黄土高原的信天游、中原地区的鲁豫民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歌、漠北草原民歌、山西民歌、冀中民歌、台南民歌等:从民歌族属看,包括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壮族、瑶族、台湾卑南人、赫哲族等:从研究视角看,歌种分类、音乐本体、历史渊源、族群归属、民俗生活、传承传播、采风纪实、创新发展、非遗保护等话题均有所论。民歌离不开土地与土地上的人,从先生的民歌研究亦可看出其遍及大江南北的田野足迹。2021年10月,先生将其一生所藏的珍贵藏书和资料无偿捐赠给了家乡榆林市榆阳区的陕北民歌博物馆,其中包含着上千小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田野录音磁带,以及数百万字字迹工整的田野笔记和万余张珍贵的田野照片。这些资料书写规范、编码清晰,记录了先生与河北固安屈家营的林中树,蒙古族长调歌手哈扎布、莫德格,花儿唱家朱仲禄,彝族“海菜腔”歌手白秀珍,西安鼓乐“道派”大师安来绪等数十位民间音乐家的故事与情谊。正如他的同行、老友刘再生所言“自1974年至2013年,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研究范围涵盖之民族除藏族民间音乐、新疆十二木卡姆音乐、福建南音等常见乐种之外,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歌种、乐种几乎都在他的田野调查与视野之中,研究重心东至齐鲁,北至燕赵,西至西秦,形成一个三角形的自古以来黄河流域音乐地域文化的重要探索地带。”“作为学者,他知道,离开亲历,就有在叙述上想痛却痛不下去的隔膜感。”因此,眼光向下、耕耘田野就成为先生学术追求的自然理念。
二、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史学思维
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音乐承载着中国音乐传统。何谓“传统”?徐复观认为,传统是“某一集团所代代相传的共同生活样式及思维观念,在时间上因为是一脉相传的,所以有其统绪性:在空间上因为是共同承认的,所以有其统一性”。先生一开始就把握到了“传统”在时间上的“一脉相传”之精髓,将所有的研究对象都置放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进行阐释,因而其文论总是充满着厚重的历史感与叙述的历时性,所论之事,既有久远的“根”,也有当下的“据”。先生的史学思维在其文论中常以三种方式呈现。
(一)专项“学术史”的历史综论
据乔先生在文集自序中的叙述,1987年2月,他作为编委参与了大型丛书《当代中国·音乐卷》的编撰,并承担了“四十年来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来的中国民族乐队作品创作”“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创作”三个专题的撰写任务,这是首次参与学术史性质的写作。这次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研究范围和学术眼光,更重要的是引起了他梳理当代音乐某些领域历史沿革,也就是单个门类“学术史”的浓厚兴趣。文集第四部分《学术史踪》收录了先生与专项“学术史”研究相关的文章35篇,这些专项“学术史”的叙述对象既涉及音乐机构的成长发展史,也有专项学术领域的研究历史综述,前者如《音乐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献辞》《中国音乐学院四十周年院庆献词》《中国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20年运行纪事》《紫禁城室内乐团的不凡之为》《中国香港中乐团建团四十周年感言》等,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十年》《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西安鼓乐研究的六十年》《落潮也有好景观-1900-2000年的民族音乐创作简论》等。“学术史”的时间跨度多为“十年”到“一百年”不等,其中以“百年”为单位的时间跨度出现的最为频繁。“百年”多指向“20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的大转型时期,中-西、雅-俗、古-今等多重关系相互角力,中国传统音乐的方方面面也在这百年之中留下了起落沉浮、波澜壮阔的历史足迹。先生作为百年历史的亲历者与重要的实践参与人,如实书写并评论百年历史中传统音乐的发展变迁,不仅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更将身处其中的“局内人”的见解与看法留与后人品评。如萧梅在《托命于中国传统音乐理想》一文中所说,先生的文集充满了对20世纪的关注,那是一种对一个时代和一个人基于自我认知的自觉反省。
(二)特定对象的历史性叙述
對于一件乐器、一个乐种、一个乐人的综合性研究或评述,先生也会将其置放在某个历史跨度中进行叙述。在先生发表的诸多单篇文章中,《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音乐百年观》是迄今为止学术影响力最大的一篇,该文自2000年在《音乐研究》发表以来,下载2997次,被引212次(数据截至2023年7月14日)。该文从宏观叙事的历史场景、社会生活的主题显示、音乐家个体精神世界的融入、史学研究的路径等角度勾勒并架构出百年二胡发展的“形成期”“传统期”“现代期”,清晰揭示三个时期所展现的“初创”“兴盛““探索”之脉络。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该文的论述亦可看出先生的研究特点,“他从来都立足于民间、传统,在当代的学习、积累、发现中不断反思,他的许多研究不是‘一次性’而是长期观察、细心揣摩的‘多次性’写就,他学习新思维、新方法,既不对抗也不拒绝,而坚守传统成为一种自然和自觉”。此外,先生亦有很多传统音乐人物与传统音乐事件的记录与评述,如《大师的创造——阿炳诞辰百年抒怀》《“鲁艺”民歌采集运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以民间沃土为生命之重的乐坛先驱——简论安波对20世纪中叶民族音乐研究的历史贡献》等,这类文章通过对特定历史阶段的音乐人物与音乐事件的书写,进而管窥特定历史时空下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
(三)传统音乐的源头追溯
当下存在的任何一种传统音乐都有其久远的历史源头,当下的形态特征也是历史沉积和筛选后的结果。对传统音乐的源头追溯成为先生研究中一种自觉的方法论,他的大历史观渗透在其所有研究文论之中,相比前两种方式,这是一种更为间接含蓄的史学思维与方法运用。他在山歌研究中,对“山歌”的称谓从唐代“竹枝“一词开始梳理,对于山歌体裁的形成则追溯至《诗经》,并认为《诗经》中的《苤苜》《箨兮》《采葛》就是早期的山歌⑦,他在音乐地理学的研究中,将民歌色彩区的源头与先秦时期的“十五国风”进行联系,认为“十五国风”这种以地域为统帅的分类原则实际上是中国人民两千五百多年前已经萌发的“音乐地理”观念的反映~.他在曲牌研究中,从汉代以前采诗制曲的“前曲牌”时期开始,梳理了曲牌的萌芽、发生、成长与成熟历程,认为曲牌不仅仅属于音乐形态范围,更是涉及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文学传统和中国人创作特有的音乐思维模式等更广的问题:在谈及时序体民歌时,他将“月令体”民歌的源头追溯至《诗经·豳风·七月》,将“四季体”上溯至汉魏六朝的“乐府”,将“五更体”上溯至晚唐俚曲《叹五更》。.即便对中国两句体旋律结构的本体探源,他也从文化角度上溯至《易》中的“两仪”秩序等等不一而足。韩锺恩将先生的研究实践特点归纳为“弱形态,强渊源.弱实证,强推论”是有道理的。
上述三种史学思维的呈现方式体现出先生“史论互证”的方法论倾向。先生认为,“史”“论”分离,各行其道的学术传统对于音乐学的起步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到了80年代各学科频繁交流融合、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新格局出现之后,再继续延续“史”“论”分离的研究传统就有可能影响学术的整体进步。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而言,只用“论”的方法与视角,就难以触碰到其纵深。
三、宏阔通达的学术视界
乔建中先生涉及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大的方面包括民间歌曲、民族器乐、学术史、音乐地理、乐评乐论、当代音乐生活等诸多领域.小的方面看,每一个大的领域之下又含诸多次级领域,如民歌之下涉及全国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形式的若干歌种与若干体裁,研究角度又涉及音乐本体、民歌体例、社会文化、歌种分类、传承创新、非遗保护等诸多层面。可以说,先生的研究涉及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绝大多数领域。先生在文集自序中说,自己的研究对象较为“杂驳”,一方面是因为长时期担任组织策划与行政服务等繁杂工作,另一方面则与自己的个性和兴趣有关。我们以为,先生自诩的“杂驳”实则是一种学术视界的宏阔与通达,这得益于先生长期浸润的“三个田野”。第一个田野是眼光向下、深入民间的真实田野。天南海北的田野足迹丰富了他的阅历见闻,积聚起丰富多样的思考与领悟之感性素材与真实数据。第二个田野是书斋式田野。先生喜欢阅读,史学、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皆在其阅读范围,多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充盈了先生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视野与格局,成为其“史论结合”研究风格与“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先生重乐谱,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的大量古谱、民间乐谱是他经常吟唱揣摩的对象,长期广泛的视谱吟唱,在先生心中早已悄然形成了一幅隐性的中国音调地图:先生爱助人,在无数次为他人的序跋评论书写中不断听赏研读,用心领会,这也成为他丰富自身人文素养,接受前沿新知的有效方式。第三个田野是各类音乐厅和表演舞台的现场聆听实践。先生爱听音乐会,从他的乐评对象可以看出,他的聆听范围不仅包括传统音乐表演,也包含郭文景、王建民等当代作曲家利用传统音乐元素所创作的新音乐作品。“三个田野”相互衔接、互为比较映照,塑造了先生宏阔通达的学术视界,所以他才能在文论中将舞台与民间、传承与创新、当下与历史、乐谱与音响、学者与艺人等与传统音乐相关的多重二元关系予以合理的理解与把握。也正是这种宏阔通达的学术视界,才使他具有了高屋建瓴、宏观统筹的魄力与能力,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四、“以人为本”的学者情怀
先生始终认为,无论是传统音乐的资料整理、民族器乐新作还是学术研究,“人”的因素都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音乐在一个世纪中的格局变化与利弊得失也是由“人”的因紊决定的,无论是功成名就的音乐大家或是默默无闻的民间乐人,他们都是推进中国音乐“大历史”的有功之臣(参见《乐人行旅》前言)。先生对“人”的关注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不管是传统音乐论域,还是当代音乐范围,他都把视角集中于人——音乐中的人及文化现场(民俗活动、舞台、讲坛)中的人,力图通过人的种种音乐行为解析人的文化精神(参见《国乐今说》后记)。
(一)对前辈乐人的追忆评述
乐人是音乐的实践者,是音乐事项的承载者。“乐事”者,即社会音乐生活的“事”,音乐家们的事。这些“事”,包括音乐的事实、事项、事象、事件等,都是音乐学家叙说、评说、描述、论说的对象(参见《乐事文心》自序)。先生所论及的“乐人”有音乐表演家、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教育家、民间乐人等,所论及的“乐事”指向乐器、表演、作品、创作、论著、学品、教育等。每一个“乐人”都与其特定的“乐事”相关联,如刘文金与二胡、刘德海与琵琶、赵松庭与竹笛、赵季平与传统语汇、郭文景与现代创作、阿炳与传统器乐、杨荫浏与传统音乐学术、刘再生与音乐史学、缪天瑞与学术思想、袁静芳与教学科研、鲁日融与音乐教育、丁喜财与《五哥放羊》、李贵真与民族打击乐等等。先生秉持写人就要“与人交往”,他所写之人都是熟悉之人,最短的交往也有十年,有的则长达数十年。因为交往既久,彼此在意念、情趣、艺术鉴别力乃至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认同就会更多,所以才会有写作的冲动(参见《乐人行旅》前言)。在所有的乐人、乐事叙述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乐人”是杨荫浏与黄翔鹏,最多的“乐事”是二胡与琵琶。杨荫浏、黄翔鹏是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最熟悉、最亲近的同事、领导兼老师,是中国传统音乐领域“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师,也是对他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二胡与琵琶是先生最熟悉、最感兴趣的传统乐器,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涌现大师最多的民族乐器领域。
(二)对青年学人的关爱包容
文集第七部分《序跋辑录》共收录乔建中先生撰写的各类序跋短文113篇,其中书序跋50篇、硕博论文序15篇、曲谱集序23篇、音响作品集序14篇、自著序跋11篇。113篇文论中,除去11篇为自己的著述作序以外,其余102篇皆为“他人嫁衣”。书序需要读书,明了书之大意、作者意图与价值所在:硕博论文需要阅读修改兼规范指导:曲谱集需要视谱吟唱、品味比较:音响作品集序需要聆听玩味、感悟理解,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先生却沉醉其中,乐此不疲。从《序跋辑录》的目录可见,先生的作序对象是作品不论新旧,辈分不论长幼,对求序之人,他总是欣然应允,全力以赴。这是一种宽广胸襟的展露,也是仁者之心的体现。萧梅在《司(思)仁不易守成难、光阴慈悲陇上安——乔建中的学术情怀》一文中援引先生回信中的原话:“我只从‘尊重他人’出发,尽可能取其长、优,而他们的长、优,都在他们的著述里,所以,实质上是精读他们的代表作就可以了。至于短处,能看出来就看,但不必亮出来。因为谁都有‘打盹儿’之时,何必计较!我历来相信朱老忠的话‘出水才看两腿泥’,先做,多做,少议乃至不议,才是‘人间正道’。”近年来,先生还曾为西安音乐学院陕北民歌班的本科毕业生撰写音乐会文案,对每一首民歌的来龙去脉都认认真真,做到一丝不苟。这又是什么精神呢?核心还是“仁”,承上启下,有容乃大。
(三)对学人评述的坦荡真诚
“乔建中”其人、其论、其事本身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界一个较具热点属性的学术话题,仅在中国知网以“乔建中”为主题就可搜索出44篇文章,可见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先生乐于被不同的“学人”评论与批评,乐于提供资料与照片来“成全他人”。他将此看成是与其他学人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也将其作为自我认知与自我反思的依据。此次出版的文集中第八个专题《学人丛谈》共收录了27篇其他“学人”的评论文章。但凡能够谈论、愿意谈论先生之人,多是“熟人”、有交集之人或是有学术共鸣之人。第一个“学人”群体是其学生,如李幼平、张君仁、黄虎、余御鸿、李月红等均为先生所教授的硕士、博士生,第二个“学人”群体是其同事,如萧梅、韩锺恩、张振涛皆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同事,第三个“学人”群体是与其有交集或是有学术共鸣之人,如刘再生、洛秦、蔡際洲、郭树荟等人。“谈”的主要内容是先生其人及其学术,人与学术本身不可分离,只是谈论的视角与侧重点不同而已。主题谈人,但免不了谈其学术,如《学术与生命——对一个民族音乐学者的“个案”调查》《信天游的境界——传统音乐学家乔建中素描》等,主题谈学术,同样离不开谈人,如《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命脉——读乔建中的(土地与歌)》《乔建中与中国音乐地理学》等。围绕《土地与歌》《乐事文心》《咏叹百年》《乐人行旅》等文集,围绕音乐地理学、民族器乐研究、民歌研究等学科理论进行评价、论述的综述性、评论性文章占到各册文集的70%以上。面对学人在评述中过度的赞誉与拔高,先生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与评论者真诚沟通,力求书写客观,评价真实。先生低调自谦、谨慎务实的态度也给书写他的“学人”群体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谨以此文集弁言作为结语“毋庸置疑,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而言,刚刚过去的四十年是一个特殊而又难遇的历史段落,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身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作者以‘文化托命’之情怀,奉音乐前辈治学路径为圭臬,视田野作业为通往该领域堂奥之境的光明大道,不间断投身于传统音乐文化现场,沐浴民间智慧情愫之光,领略音乐遗产之丰腴浩博。不经意间,作者对个人所闻所见的思考、记录、描述、论证,已遍涉当代传统音乐之人、事、乐、调、俗,漫漫求索之际,则着眼于音、地、人之关系,史、论互证,以及传统与当代的比较研究。要之,作者40年前甫入学坛,即矢志以学卒之躯自勉,立水滴石穿之志,求积跬致远之效。此十册文集,或可见证这个洪流巨浪大时代的某些微澜涟漪!”
观先生之学术人生,所呈现给社会的已不仅仅是有关传统音乐的学理论述,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态度、一种学养、一种方法、一种情怀的传承与延续。
张君仁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银波 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