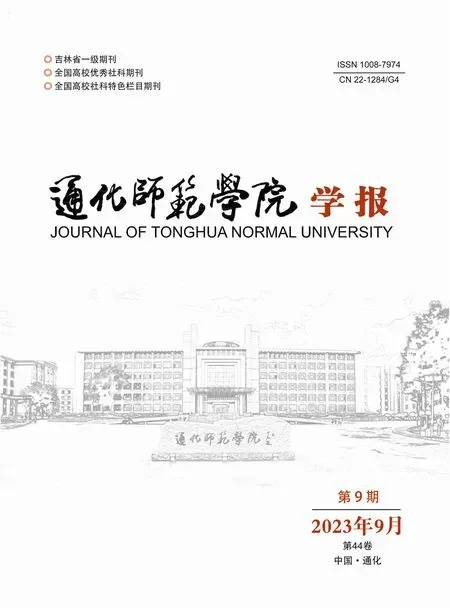论 “史学经典” 通识课内容的选择及价值
2023-11-07宋馥香
宋馥香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她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用汉字连绵不断地记录下来,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史学经典便是其中的精华部分。那么,什么是史学经典、哪些史学经典可以作为通识课讲授的内容便成为首要问题。
一、中国史学经典选择的标准
一般说来, “史学经典” 首先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历史著作,且经过岁月的洗礼,仍然能保持其权威性,并对中华文化、民族精神或学术传统的传承、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依据这一认识,大体上说,史学经典应具有三项标准:
其一是在当时已经产生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在当时就已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可以从中获得思想的力量。在中国史学史上,研究《史记》《汉书》的学术史大约有两千年,因研究《汉书》而形成的 “汉书学” 则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由此可知它们在当时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二是当时虽然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由此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如清前期的章学诚于18 世纪完成的《文史通义》,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产生很大影响,直到20世纪以后,才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其三是诞生时的影响极大,并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尽管它对今天来说未必具有多少现实意义,但它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对史学传统和史学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其历史地位不可小觑。这样的著作在历史上有很多,如孔子编纂《春秋》是中国史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它虽然很难说对今天有多大现实意义,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在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中没有能与之匹敌者。[1]
按照上述三项标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可称之为 “经典” 的史学著作数量之大,并非一门 “史学经典” 通识课所能囊括的,何况这门课只有区区16学时。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中国史学经典只能在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四大系列中选取经典中的经典,并采用精讲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意在透过从《春秋》到《资治通鉴》编年体系列史书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轨迹,认识它们是如何通过变通体例而使之得到发展和完善,从而达到巅峰的过程;阅读 “二十四史” 的 “前四史” ,了解 “二十四史” 的记史脉络及核心内容,目的是向学生展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本面貌;通过《通典》《文献通考》、明朝史家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清乾隆时期官修的《续文献通考》及《清文献通考》,旨在使学生能够大体了解中国制度文明的传承、变革过程,掌握历史,特别是史学发展的规律;学习以记述重大事件为核心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有关朝代史的历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意在展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连贯性细节,使学生通过对微观处的观察,感受史家的精神世界,增长历史智慧。
二、在经典中感悟史家的忧患意识
中国史家历来具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往往同他们的社会思想紧密相联,主要表现为对朝代或国家兴亡盛衰的关切,对民众生活和社会治乱的关注、对社会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忧患,这也是他们致力于历史撰述的重要思想基础。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2]其中反映出孔子撰《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但这样的结论还只是从孟子的言论中得出的。
司马迁父子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但当他进入撰述状态的时候,对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透过《平准书》,可以看到司马迁笔下汉武帝统治极盛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这类认识[3],正是他在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 的过程中见盛观衰的结果[4],是他在深刻分析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作出的正确判断,其中显示出司马迁的忧患意识。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更加突出,这一方面是受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北宋立国之时积贫积弱,因此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深沉而凝重,如司马光在《历年图序》中写道:
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冒死妄陈一二……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 “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周书》曰: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5]
其中反映的正是司马光对世事的忧患。
当近代中国遭受欺凌之际,史家关注中国边疆史地、家国命运,他们大声疾呼 “寸寸河山寸寸金”[6],倡议 “师夷长技以制夷”[7],为此,撰写出《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康輶纪行》这类以捍卫祖国边疆和《日本国志》《法国志略》等研究外国史地以自强御侮的史学经典,成为鼓舞民众誓死捍卫边疆、反抗侵略的 “泣血” 之作。
这些史学经典中所折射的忧患意识,绝不仅仅代表史家个体,它是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不仅仅是一种史学传统,更是一面使人自省的镜子。以这类史学经典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上与史家的精神相遇,在接受史学知识的同时,感受史学经典强大的精神力量,理应是这门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在经典阅读中提升修养和能力
史学经典凝聚着古代先贤的睿思卓识,宝藏着大量优美的历史语言。作为非历史学专业学生的通识课程,除了要让学生感受史学家的精神之外,另一个目的是要提升学生的修养,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经典中的历史语言,淬炼其文字功力。使学生了解史家的治学方法,拓宽其视野,培养其看待现实问题深邃的历史眼光。
毋庸讳言,当代大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述水平出现下滑趋势,怎样丰富他们的语言?从本民族的史学经典中汲取营养,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大学生现代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自然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高校不同专业对汉语水平的训练和要求有关。但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多读一点史学经典,对语言修养的提升都是有益的。现代汉语中的不少成语都出自《左传》,如 “余勇可估” 字面的意思是说这人胆大,勇气用不完,可把多余的勇气卖出去。实际上,它要表达的含义是说这人因不自量力而高估了自己。再如 “祸起萧墙” “灭此朝食” 等这类词语中都包含着哲理和智慧,如果不阅读史学经典,很难真正掌握这类历史语言,也就很难丰富我们的现代语言,提升我们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述水平。再如《左传》,长于写诸侯争霸,齐晋鞌之战、秦晋崤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每场战役都写得非常精彩,对政治与战争间的关系亦揭示得非常深刻。《左传》写战争有个特点,就是非着意于写大事,而是通过小事写出战争胜败的原因,如城濮之战,先写晋、楚两国君臣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两国内部的君臣关系,再写这场战争的原因、导火索,其中穿插了晋文公当年流亡楚国时的承诺等细琐之事,最后只用寥寥数笔描述战役和战术。不仅将这场战争的所有要素都囊括其中,而且反映出史家对待战争的态度。这样的文字,如翻译成白话文,远不如文言文精彩。所以要精练文字,就应该读这样的经典,通过吸收这样的历史语言提升文字功夫。
文史修养不仅是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必备的修养,也是所有专业的大学生应该具有的一种修养,阅读传统史学经典,无疑是提升这种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朝统一以后,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首先将这一历史进程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它不仅写中原的历史,也写包括南方、北方、西南方、东南方、西北和东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通过阅读这类经典,可对本民族、国家的历史有很明确的认知。再如纪传体史书,以记人为主,特别是 “传” 多精彩之笔,在传记文学方面有着极高成就。因此,精读 “二十四史” 的前四史中精华部分,对提高文学修养尤其重要,这些理应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阐发经典的深旨大义,掌握治学的方法论。唐人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他最早提出才、学、识三个范畴,并阐明了三者的关系,即 “学” 是知识,是基础; “识” 是见解,是对事物本质的透彻认识; “才” 是能力,是知识和见解的准确表达。刘知幾对才、学、识三者关系的辩证认识,提出了史家修养和治学的目标和方向。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不仅重申这三个范畴,而且重新排列了它们的顺序,即把 “史学” 放在前面, “史识” 居其次, “史才” 再次,同时采纳清人章学诚提出的 “史德” 范畴,将其置于首位,突出强调了史德的重要性,由此发展出史家素养论的理论体系,并成为史学工作者遵守的职业操守。事实上,这不仅是史学家的修养,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学方法论,提示我们在坚守职业操守的同时,怎样处理好做人、学习知识与锻炼能力的关系问题。
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读这部经典最重要的是领会章学诚 “知人论世” 这一学术批评原则,它是开展学术活动,尤其是进行学术批评的重要原则,他说: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8]即不了解其人所处的时代,便不应轻率地评论其文字。又说: “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8]意思是说,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人,因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开展学术评论时,理应重视被评论对象的人生境遇,不可泛泛而论。将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与 “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合在一起,可以说,这一认识几乎达到了史学批评的最高境界,他告诫我们:只有在了解被评论对象所处的时代,批评才可能公允而中肯;只有了解被评论者的经历,批评才可能客观而深刻。因此,章学诚关于 “知人论世” 的治学方法和方法论,不仅对学术批评至关重要,也是评价历史的根本方法。通过史学经典课向学生传递这样的方法,特别是方法论,必定会对提升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要之,开设 “史学经典” 核心通识课,引导学生阅读史学经典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使学生与优秀的史学家神交,并领悟其精神的过程,是培养学生高尚的职业操守,使其掌握治学方法论,提高学生的文史修养,历练其优美、细腻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述的过程,一句话,就是培养学生的德、学、才、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