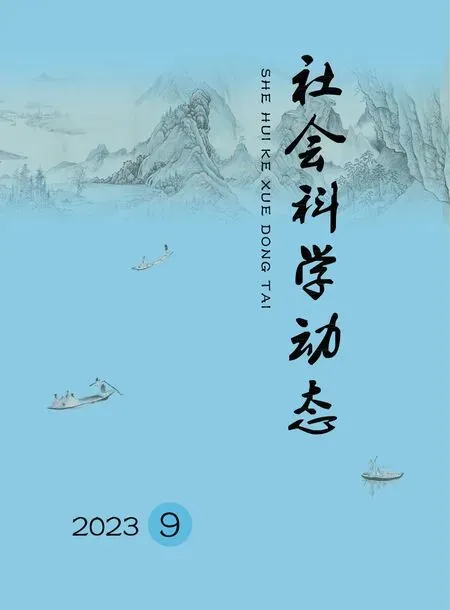论孙光宪词作的怅惘抒写
2023-11-06王春
王 春
晚唐五代是词这一文学体式发展演变的一大关捩。在此之前,作为文人偶一为之的体裁样式,词并未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而于此之后,则迅速发展,在天水一朝成为王国维所言的“一代之文学”①。因此,对这一时段内的词作进行考察分析,无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典范意义——既涵盖文学史层面,又包括美学层面。该时期的许多重要作家作品,均赖《花间集》得以保存,其“裒集温庭筠等十八家‘诗客曲子词’,总五百首,是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唐五代文人词总集”②,在词学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价值,开创了婉丽绮靡的花间词风,对后世词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缪钺先生云:“淮海清真晏小山,发源同是出《花间》。滥觞一曲潺湲水,万里波涛自不还。”(《〈花间〉词平议》)③过去,在讨论和评价花间词时,往往援引欧阳炯《花间集序》:“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④认为花间词一味抒写情爱绮靡生活,而其创作目的亦不过娱宾遣兴,开词为艳科之先河,不无贬低之意。实际上,所谓艳情之作不过为花间词的表象,而花间词人真正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其实是开创了在词作中对怅惘之感的抒写方式。叶嘉莹先生在解释“惆怅”时说:“‘惆怅’者,内心中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一种极迷惘的情意,不像相思离别之拘于某人某事,而是较之相思离别更为寂寞更为无奈的一种情绪。”⑤在花间词人中,孙光宪又有着特殊的地位,其向以“气骨甚遒”(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⑥著称,但从《花间集》所收录的作品来看,不难发现其笔下亦始终萦绕着某种怅惘之情⑦。
一、怅惘意境的营造
杨景龙先生《花间集注校注·前言》中指出:“《花间》情词虽有少数浮薄之作,但多数作品并未停留在追逐欲望满足的浅层次,而是由欲到情,表现出人类爱情心理中专注思念的忧伤寂寞之美。”⑧这种忧伤寂寞之美实际上就是对怅惘之情的抒写,而这种抒写本身也并不局囿于情词这一种题材。孙光宪因其对词境的开拓作出重要贡献而广受赞誉,他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多能刻意营造出怅惘的意境,令人在阅读之时怅若所失。总体来说,这种怅惘意境的营造是以空、远、荒、寒为核心的。
《浣溪沙》(其一)历来被视为孙光宪的名作,词云:“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陈廷焯《云韶集》卷一便认为:“‘片帆’七字,压遍古今词人。‘闪孤光’三字警绝,无一字不秀炼,绝唱也。”⑨此词总体风格偏于俊逸清健,颇能代表孙氏气骨甚遒的艺术特色,但真正能引起读者感动的,依然是对于怅惘意境的营造。开篇言“蓼岸风多橘柚香”,蓼为一种水草名,秋开红白花,其味苦辣,自《诗经·周颂·小毖》有“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⑩以来,其均被作为辛苦困境的象征。“橘柚香”典出王昌龄《送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⑪此词首句似为写景,但若结合“蓼”与“橘柚香”的语码意义,则实际上是在描绘秋风中颇为寂寥的江边景象,同时又内蕴着一种悲苦凄凉的氛围,而这恰与词作所要表现的送别之情相契合。“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运用对比手法,片帆之微小与楚天之辽阔形成内在张力,孤光更着一“闪”字修饰,其似明似灭表现了行舟在江上烟水之际的若隐若现,于空远的背景中愈发衬出个体的落寞。下阕主人公“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依然是一种空而远的意境。江淹《赤亭渚》云:“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⑫到这里,恐怕是连片帆也不得而见了,而天边鸿雁南飞,一去尚有归期,心随流水,则去而难返,何况流水亦寓托着时间的消逝。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亦有“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⑬之句,这里思随流水,既是思念逐故人远去,又因流水不返而折射出相会遥遥无期的悲哀。天地茫茫之中,个人如此无助,没有什么可以挽留,唯一能做的就是“兰红波碧忆潇湘”,回忆往昔种种的美好,结尾“潇湘”为联绵词,皆为阴平,读起来颇为悠远,有无尽缠绵之意。全词“上片景中含情,下片转写情中之景”⑭,情景交融,营造出一种怅惘的意境,颇具感染力。
在孙光宪其他词作中, 往往直接出现“疏”“空”“远” “残” “寒”等词汇来修饰所要描写的对象,直观地呈现落寞的氛围。如《浣溪沙》(其三)云:“花渐凋疏不耐风。画帘垂地晚堂空。坠阶萦藓舞愁红。 腻粉半粘金靥子,残香犹暖绣薰笼。蕙心无处与人同。”花是凋疏的,画堂是空寥的,台阶是苔藓萦绕的(暗示久无人走动),脂粉是半粘着的,暗香是残余的,蕙心是无人相似的,词中所提到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充满了残缺感,由此共同组成的意境也就不免令人悲伤,在这些看似客观的描写之中实则蕴含着深沉的凄凉。这种手法在葆光子词中俯拾皆是,如“一庭疏雨湿春愁”“早是销魂残烛影,更愁闻着品弦声”“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词句大多能情景交融,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⑮,作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⑯,为表达思想情感的需要,词人精心择取各种意象进而构成意境,营造出忧伤的氛围,确乎可以达到“尤有境界也”⑰的美学效果。
花间词向来以绮靡著称,意象精美,辞藻华丽,然而通过阅读分析,则可发现孙光宪所描摹的美好事物都是不完满的,以“空”“远”“荒”“寒”为核心的整体意境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纯美意象的欣赏,并使由此引发的悲哀、叹息显得更为徒劳,进而体现词家所深藏的情感底蕴。
二、怅惘情怀的表达
与孙光宪词作中意境构建互为表里的,是其情感的抒发。怅惘作为一种情怀,包含了惆怅、迷惘、无奈、寂寞、忧伤等许多复杂微妙的感情,可以超越具体的写作内容而成为笼罩全篇的主体基调,这在孙光宪各种题材的作品中均有所表现。
先看描写闺怨相思的《虞美人》(其一):“红窗寂寂无人语。暗淡梨花雨。绣罗纹地粉新描。博山香炷旋抽条。暗魂销。 天涯一去无消息。终日长相忆。教人相忆几时休?不堪枨触别离愁。泪还流。”起首所写之景便颇为寂寞,红窗指有雕饰、颜色的窗子,通常代表着女子的闺房。此美好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出现时,往往与其将要或者已经遭受破坏相联系,如白居易《感苏州旧舫》云:“画梁朽折红窗破,独立池边尽日看。”⑱杜牧《八六子》云:“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⑲徐夤《霜》:“红窗透出鸳衾冷,白草飞时雁塞寒。”⑳均可作如是观。而此处红窗寂寂便已将一位孤单女子托于纸上,更益以“无人语”,愈显其寂寞。“暗淡梨花雨”,既是写景,又是写人,“梨花雨”本指春天梨花开放时节的雨水,但白居易《长恨歌》中用“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泣如雨下时的姿容后,常被借指女子的娇艳。此词进一步描写女子“绣罗纹地粉新描。博山香炷旋抽条”,非常精致地打扮自己,又处在一个异常华美的环境中,本应是幸福浪漫的,然而“女为悦己者容”,因无人欣赏也只能“暗魂销”。江淹《别赋》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由此引出因相思而极其哀愁的心情。下片“终日长相忆”“相忆几时休”,不避重复地使用“忆”字,表现出思念的强烈,这里“忆”的行为不妨借用张爱玲的精彩描述:“回忆永远是惆怅的: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㉑更何况主人公想到的是“不堪枨触别离愁”,她是如此地无能为力,只能徒然“泪还流”,“还”字表示时间的延续和次数的重复,孤单的她屡次、持久地流泪,使这种落寞之感愈见深沉。同样描写别后相思的,又如《菩萨蛮》(其三):“小庭花落无人扫。疏香满地东风老。春晚信沉沉。天涯何处寻。 晓堂屏六扇。眉共湘山远。争奈别离心。近来尤不禁。”“眉共湘山远”,依然描写的是一位精心打扮的妙龄女子,因为恋人不在,这一切都无人欣赏,使美变得那么徒然,于“疏香满地东风老”的怅惘氛围中凸显其心境。孙光宪描写分别时的场景见前引《浣溪沙》(其一),实际上这种痛苦在分别前已然流露,如《临江仙》(其二):“暮雨凄凄深院闭,灯前凝坐初更。玉钗低压鬓云横。半垂罗幕,相映烛光明。终是有心投汉珮,低头但理秦筝。燕双鸾偶不胜情。只愁明发,将逐楚云行。”其怨别之情分明可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孙光宪一些描写艳情的作品,如《浣溪沙》(其二):“绣阁数行题了壁,晓屏一枕酒醒山。却疑身是梦魂间。”《菩萨蛮》(其一):“碧烟青袅袅。红颤灯花笑。即此是高唐。掩屏秋梦长。”古人常以梦来修饰情爱,梦本身的恍惚、迷离与不可捉摸也为词作带来一种朦胧隐约的气质,从而使其所要描述的美好本身透出无法名状、难以确定的特征,在表达欢喜的同时亦流露怅惘。也就是说,孙氏在许多以男欢女爱为主题的作品中,无论是处于感情的何种阶段——厮守、艳遇、分别、相思,词作常是以个体的无能为力作为底蕴的。
其次,孙光宪咏史题材的作品往往掺杂着怀古与悼亡,于历史兴亡中寓托感慨,并引发虚无的浩叹。《河传》(其一):“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偎倚渌波春水。长淮风不起。 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词作大部分描写隋炀帝的游乐淫逸,而“妙在‘烧空’二字一转,使上文花团锦簇,顿形消灭”(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㉒。汤显祖评《花间集》卷三云:“索性咏古,感慨之下,自有无限烟波。”㉓孙词颇有一切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的感觉。再看《思越人》(其一):“古台平,芳草远,馆娃宫外春深。翠黛空留千载恨,教人何处相寻。绮罗无复当时事,露花点滴香泪。惆怅遥天横渌水,鸳鸯对对飞起。”当年西施吴王的艳事便如同西子的泪水、花上的露珠一样,曾不能以一瞬,早已烟消云散,现在所遗留的景色却是这番:“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像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经春初败秋风起,红兰绿蕙愁死。一片风流伤心地。魂销目断西子。”(《思越人》其二)词笔凄艳俊逸,一片苍凉。萧继宗《评点校注花间集》云:“‘想像’二句,不胜华屋丘山,美人黄土之感。”㉔颇能点出此词真谛。再如凭吊张丽华的《后庭花》(其二):“石城依旧空江国。故宫春色。七尺青丝芳草碧。绝世难得。玉英凋落尽。更何人识。野棠如织。只是教人添怨忆,怅望无极。”该词以“怅望”作结,词人胸有所郁,触处伤怀,似有无限哀叹,却均付之于不言中。面对历史消逝的必然性,所有悼念、追忆、叹息,也都愈益显出其虚空的本质。
再次,孙光宪的边塞词亦不以豪迈见长,而代之以悲凉。如《酒泉子》(其一):“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起笔阔大,“空碛无边”,塞外之荒凉惨淡扑面而来,将边关之苦寒艰辛与思妇之忧心体贴熔铸一体,当然也可以解读为上阕直接描写征夫别家,以陇云愁的环境衬托心境,下阕由自己所穿之戎衣转而想象家中的妻子一定也非常思念自己,“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用唐赵征明《思归》“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㉕之句,以三言叠句作结,仿佛一句一叹,而终不能改变分别的现实,一句一徒然。汤显祖称:“三叠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读不禁鼻酸。”㉖并非过誉。再如《定西番》(其二)中的“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亦着重展现边关乡愁,全词以悲伤压抑为主调。
此外,在孙光宪较为纯粹的以南土风情作为题材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窥见怅惘的情怀。《菩萨蛮》(其五)云:“木绵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 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在状写颇具地域特色的风物之时,也往往也以“烟”“波”作结,从而使词作在“艳冶中兼具凄迷之致”(萧继宗《评点校注花间集》)㉗,饶有远韵。
当然,并不是孙光宪所有的作品都涉及怅惘抒写,譬如《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等基调便相对欢快。因此,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将孙词均总结为怅惘抒写,只是在《花间集》所录的词作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孙光宪大部分词作仍是建立在怅惘这一感情基础之上的。
三、怅惘抒写的余韵
王国维言:“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㉘缪钺先生进一步解释:“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是一种以余韵定高下的文学体裁。所谓“故词境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论词》)㉙。与词境相契合,词体具有表达含蓄蕴藉感情的优势,通过句法参差、音节抗坠来抒发那种怅惘的情绪,不仅可以给词作带来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远韵,更因怅惘作为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情感而能引起读者的感动、联想,从而使词作具有不拘于字面的、可以引申的意义,令人咏叹再三。
孙光宪词作中怅惘抒写造成的余韵悠长美学效果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寄托性;一是象征性。寄托性与其生平经历有关,象征性则与其词所具有的丰富联想性、象喻性相联系。就寄托性而言,在传统的分析诗词的理路中,知人论世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讨论模式。花间词虽有娱宾遣兴的性质,但诚如陆游所云:“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㉚正因为其成于绮筵花间,词家毋须假装正经而言不由衷,写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作者的内在真实。华连圃《花间集·发凡》称“其中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取径欲微,陈义至广”㉛,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现象。何况晚唐五代词人均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事动荡之中,不可能不受外界影响,他们并非乱世中一味玩花弄月之辈,如孙光宪一生历经七朝变迁,曾在三朝为官,他尝谓知交曰:“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㉜可见颇有自期。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其劝谏高从诲事:“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㉝欧阳修《新五代史》载其劝继冲献城于宋事,足见其对于当时天下大事颇有判断。孙光宪著述甚多,其自身定位亦非仅为风雅墨客,因此在他的词作中,如能剥离表象,是可以发现某些隐藏着的深远意味。吴梅《词学通论》曾赞赏“孟文之沉郁处,可与李后主并美”㉞,这里不妨借用陈廷焯的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㉟不妨看几个例子,《生查子》(其三):“金井堕高梧,玉殿笼斜月。永巷寂无人,敛态愁堪绝。玉炉寒,香烬灭。还似君恩歇。翠辇不归来,幽恨将谁说?”此作为宫怨之词,描写的主人公自然是不得恩宠的宫女,“翠辇不归来,幽恨将谁说”表现其悲剧的命运,但一定程度上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篇别有寄托的作品,君恩歇之君是否为词人理想之君?“幽恨将谁说”岂不是同样昭示着其壮志难酬的痛楚?再如《河满子》:“冠剑不随君去,江河还共恩深。歌袖半遮眉黛惨,泪珠旋滴衣襟。惆怅云愁雨怨,断魂何处相寻。”“君”所寓托的含义与“妾和君”的关系,均极具象征意义,“断魂何处相寻”的凄楚中,透露着悲凉的底蕴。又如《谒金门》中的“愁肠欲断。正是青春半。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 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凭仗东风吹梦,与郎终日东西”,词中充斥着孤独感。词人以鸾自况,寓示着自己不愿同流合污,“与郎终日东西”,永远无法得到自己所追求的美好事物,这种郁郁不得志正与其感叹“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有着内在的逻辑性。
在这些为绣幌佳人所写作而别有寄托的小词上,也存在可以就其象征性进行解读的空间。谭献《复堂词录叙》云:“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㊱所谓诗无达诂,文本本身是可以演绎发散的,而花间词因其所写题材的特殊,较之一般诗词更具象征性。叶嘉莹先生认为:“《花间集》中的作品……其写作的重点自然集中在美色与爱情,而‘美’与‘爱’恰好是最富于普遍的象喻性的两种质量,所以《花间集》中的女性形象虽然是现实中的女性,但却是具含了使人可以产生非现实联想的一种潜藏的象喻性。”㊲更进一步说,“美色”与“爱情”在词人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也终非永恒,而有着注定殒灭的命运,那么在表面描写艳情的作品中自然地具有了一种徒然、怅惘的深意,给人以苍凉之感。如前引“花渐凋疏不耐风。画帘垂地晚堂空。坠阶萦藓舞愁红”诸句,均可由此维度进行解读,描写得愈细腻幽约,与其潜在的悲惨境遇对比得便愈加强烈。孙氏词作中反复表现的这种“求而不得”的感情和美好事物必将毁灭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因此随之而来的个体失落也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这正是孙光宪以艳情作为描摹对象时又能超越其表面情感而触及灵魂深处的原因所在。从这一层面上看,孙光宪刻意营造的以“空”“远”“荒”“寒”为核心的怅惘意境,恐怕也是其在飘摇之世切身感受的形象外现,词作中所反映的美好意象易遭摧藏的命运,客观地呈现了个体生命的悲剧性,残花、败柳、夕阳、疏雨的象征意义无疑是值得探讨的。
作为花间词人代表的孙光宪在大部分作品中完成了一种怅惘抒写的模式,这种模式也出现在其他晚唐五代词人的笔下,共同构成了早期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写作特色,并成为后世尤其是婉约派词家所取法、承继的传统。孙光宪在营造怅惘意境与表达怅惘情怀的过程中触及了人类所共有的情感经验,其所具有的寄托性与象征性给予了其作品多重的内涵,也赋予读者多层次的阐释空间,使“要眇宜修”的词体特征得以凸显。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讨论孙光宪的词作乃至整个花间词,对于发掘、体认词的发展脉络和美学特质,无疑是有所裨益的。